 J.M.库切
J.M.库切一
“如今还有这样的作家吗?”
一九九五年,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爵士辞世时,布罗茨基追忆他们曾经做过的一个游戏。在伦敦皇家咖啡馆,到访英国的布罗茨基与斯彭德夫妇聚会,餐叙时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与他们同席。他们列出一份“本世纪最伟大作家”的名单: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穆齐尔、福克纳、贝克特。但这份名单只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止,八十高龄满头银发的斯彭德问布罗茨基:“如今还有这样的作家吗?”“约翰·库切或许算一个,”布罗茨基回答说,“一位南非作家,或许只有他有权在贝克特之后继续写小说。”斯彭德问:“他的名字怎么拼写?”“我找到一张纸,写上库切的名字,并加上《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这是布罗茨基发表于《纽约客》的祭文《悼斯蒂芬·斯彭德》中的叙述。
二○二一年盛夏,我在布罗茨基散文集《悲伤与理智》里读到这个细节。此刻作为生活于现在时的读者,我已成一个中介,某种见证。
越过时间的苍茫云烟,同时可以看见存在与逝去者,看见他们的情感凝结和精神联通。
二○○三年十月,J. M.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霍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l)宣布库切获得文学奖的消息时说:“我们都确信他在文学方面所做贡献的持久价值。我不是指书的数量,而是种类,以及非常高的水准。我认为,作为一名作家,他将继续被人讨论和分析,我们认为应该将他纳入我们的文学遗产。”(J. C.坎尼米耶《J. M.库切传》,王敬慧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瑞典文学院在正式报告中说:
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的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毫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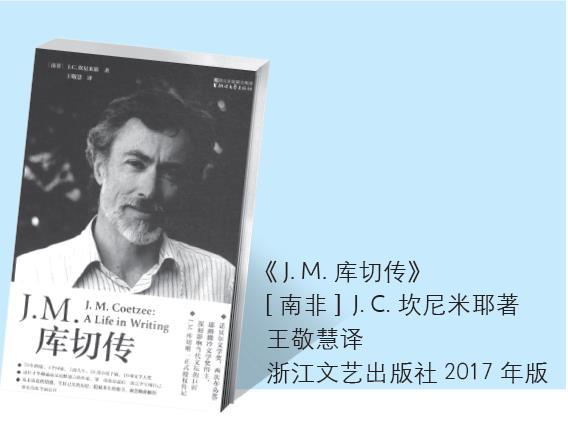
我对瑞典文学院不陌生。曾有三年,我在隆冬之季前往那个昼短夜长的北欧之国,一幢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的城堡般的建筑,昔日是证券交易中心,后来成为瑞典文学院所在的大楼。天光幽暗时刻城市街头映射着璀璨灯光,随处可见门廊前彻夜不息的烛焰。踩着石阶上楼,或乘老旧逼仄的电梯升降,可进入这幢大楼的任何一处。我进入过瑞典文学院的会议厅,那里围着一张长桌摆放着十八张宫廷式座椅,有着十八位院士的瑞典文学院只有十五位院士参与日常工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就由其中部分院士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对南非作家J. M.库切的加冕是一个作家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耀:
库切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财富。这里没有两部作品采用相同创作手法。然而,他以众多作品呈示了一個反复建构的模式:在盘旋下降的命运是其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此刻我想到布罗茨基。他可以是库切杰出的知己。拥有非凡的知己应该是一个人的慰藉。
或许是对精神知己心存感激,库切在二○○二年出版的小说《青春》中写到他对布罗茨基的关切。梦想成为诗人的青年库切迁徙伦敦过着居无所定的漂流者生活,在忙碌的谋生间隙,唯一的盼头就是回到他的房间,打开收音机收听BBC的第三套节目。在“诗人和诗歌”系列节目里,他听到布罗茨基的消息。诗人在冰封的北方阿尔汗格尔斯克半岛服苦役。当库切在自己温暖的寓所里,喝着咖啡,一点点咬着有葡萄干和果仁的甜品的时候,有一个和他同龄的人,整天在锯圆木,小心地保护自己长了冻疮的手指,用破布补靴子,靠鱼头和圆白菜汤活着。

库切的《青春》叙事,尽显他在漂流的困顿中对诗人的挚爱。“仅仅在从广播中听到的诗歌的基础上,他了解了布罗茨基,彻彻底底地了解了他。这就是诗歌的力量。诗歌就是真实。但是布罗茨基对于在伦敦的他只能是一无所知。怎样才能告诉这个冻坏了的人,他和他在一起,在他的身边,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精神联通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宇宙之间,两个相距遥远的人,心灵穿越时空相互贴近。
二○二一年十月五日午夜,我重新阅读库切的《青春》,在第十一章找到这个细节。很多次读到这个细节时我都会被这样的叙事振动心弦—约瑟夫·布罗茨基“从颠簸在欧洲黑暗的海洋中的孤筏上将……诗句释放到了空气之中”,诗句随着电波迅速传到了库切的房间里。“他同时代诗人的诗句,再一次告诉他诗歌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因而他自己可以是什么样子的,使他因为和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而充满了欢乐。”
二
阅读和聆听。同属于精神事务。
《好故事:关于真实、虚构与心理治疗的对谈》,是小说家库切与英国心理学家阿拉贝拉·库尔茨的对话,它的中文版于二○二一年六月问世。这一次库切放弃他所擅长的虚构文体,也舍掉他造诣精深的理论言说,进入陌生的心理和精神学领域,与精神病理专家探寻他所关切的问题。“虚构与真实”“创伤与记忆”“创造的激情与隐秘的生物基因”“书写与治愈”……他们如同临床医生,一次次剖析这些重要命题。这是一次极具专业性的讨论,普通读者需要具备某种心理学知识才可以进入对谈的文本,才可以理解话题所及的要义。
仿佛置身现场聆听这对话。我尤为感触的是库切对阅读的鉴识。
“死的阅读与活的阅读。”这是库切的划分方式。“有一种死读书,也有一种活读书。死读书,那些词语在书页中从来不会产生意义,这是许多孩子的阅读体验,如他们自己所说,那些孩子从未养成爱上阅读的习惯。通过死读书,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学习,也不是不可能,但这本身是一种苦闷的、索然无味的体验。”
对阅读的鉴识当然不是为孩子,它的观念适宜任何的成年人。库切继续分析道:
活的阅读,会像一种神奇魔力一下子把你击中。它包括用你自己的方式走进去,聆听书页里发出的声音,那是对方的声音,沉浸在这声音里,你可以从外部对你自己说话(你的自我)。于是,这个过程就成为一种对话,尽管它只是内心的对话。这是作家的技艺,这种技艺现在已无处可学,虽然还能被捡起来:创造一个形象(一个会说话的幻影),提供一个入口,让读者沉浸于这幻想之中。(《好故事:关于真实、虚构与心理治疗的对谈》)
阅读是精神活动,它是我们内心的生活。阅读也是对人的心灵和智识的开掘。
就像写作对人的心理隐患的治愈,阅读对人的精神暗疾具有疗治功效。
这样的体会是我所有的,我的个人经验是:好作家是慰藉,好故事是灵药。
我们都是受益于阅读的人。受益于阅读,也即被人类文明之光映照。
世间众多智性蒙昧的心灵经由这文明之光的映照而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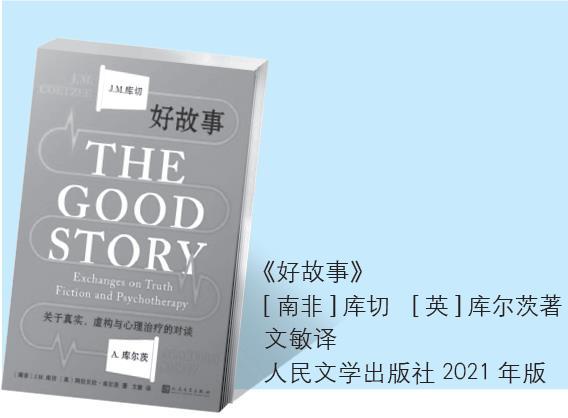
如同心理学家阿拉贝尔·库尔茨在《好故事:关于真实、虚构与心理治疗的对谈》中言及她读《夏日》时的体会:“我们不能完全通过他人来了解我们自身—我们通过感受他人的方式,我们自身亦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这也是他人感受我们的方式。”
三
库切是可以带来心灵慰藉的作家,对他的阅读也是我们对精神暗疾的治愈。
一个身在幽暗中的人。一个书写幽暗的人。我与库切在共同的精神背景遇见,幽暗是我们共同的经验。一个是卑微如尘埃者,一个是灿若星辰的文学巨匠。然而我们在精神疆域中产生交集和互联。库切早年在南非城镇度过,当时他的国家有着最野蛮的社会制度—种族隔离。他见证并亲历了很多暴行。青年时期库切旅居英美,为谋生也为个人的艺术理想,过着飘零的生活。
作为前工业时代的矿工,昔日的漂流者,如今的自由写作人,我与库切有着甚深的契合度。因为出生并成长于矿区,幽暗是浸染我身心的颜色。青年时期迁徙京城,有过多年的漂流者生涯。我所阅历和亲证的黑暗已不再限于外省矿区和漂流生涯,它是更广大世界的某种境况。作为时代的观察者,生活的体验者,这是我从前的自我鉴识。作为一个写作者,过去和现在都有着纷繁的失败经验。我与库切相似的心灵体验还有对失败与挫折的体察,对忧郁与孤独的感知,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疏离,这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基因。
“他的每一次叙述都始于并且执着于人物向下沉降的命运,如同一份追踪地下生活的报告。仿佛只有在这幽暗冷漠的国度,才会见证我们时代的隔离,以及它那些荒芜灵魂的悲喜剧……”这段文字出现在许志强为库切撰写的《夏日》中文版序言里,被我用黑色碳素笔划过虚线反复记忆。这些话语如同密林中的幽径被我发现,沿路而行抵达某处隐秘之境,那是小说家库切的精神疆域。
《夏日》我有三本,其中两本分别置于我在两座城市居室的书架上,这么做是为方便阅读。因为经常乘坐高铁旅行,穿梭于北京和长春,前者是我的工作场,后者是我的庇护所。库切在很多时候是映照我的精神光谱,我需要他在内心的陪护。虚实相间,迷离人生,一个伟大小说家的自我史。一场充满文学快感的小说游戏。最初读到的《夏日》是在二○一二年冬天买的。其时我刚辞职,结束持续十年的新闻职业,我决心侍奉个人的文学写作志业。我认为那个冬天遇到《夏日》对我是个安慰。我是偶尔的机缘看到这本书的介绍,当时我与这位作家并无多少交集。只是看见过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当年的《书城》杂志上看到过他的一些零散的小说文本。还有就是在多丽丝·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我从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赵白生先生那里约过库切写莱辛的文稿,印象中请赵先生与库切确认过刊发的版权。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傍晚,我回到京郊寓所,在书架上找出我在二○一二年买到的《夏日》,令我惊奇的是,书中在不同纸页间夹了三个浅蓝色铁夹,铁夹夹着我写下来的数十页阅读笔记。这是少有的认真阅读,当时我只是喜欢这部小说,喜欢它的叙事格调,缓慢而精致,极具个人化。很有些迷恋小说叙事呈现出来的作家的形象,隐忍而内敛。
我不知道对《夏日》的喜爱,是我对库切充满个人敬意的阅读之旅的开启。
如今我是双城生活的人,有十年的时间往返于北京和长春。在两座城市居所的书案上都有蓝色地球仪,闲暇时我会旋转地球仪,寻找自己想要旅行的国家,查询想要抵达的地方。中国北京—南非约翰内斯堡—澳大利亚堪培拉,从地球仪可见空间相隔的距离。然而我是领受杰出作家慰藉的人,也是被好故事治愈的人。此刻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精神标本。一种异族文化,同时也是普世文明,这是库切所能代表的。他还代表一个杰出小说家应有的精湛技艺,代表一個人文学者的辽阔深邃而多元的精神维度。
《夏日》无疑是一个好故事。充满游戏与讽喻的气息—库切死后,有人想要写作库切的传记,重访他的生前友好,他的情人、表姐、同事,也寻找库切旧日的笔记,传记作者试图从他获取的这些材料拼接出库切的人生实况和精神图景。这是《夏日》的叙事脉络,小说结构采用的口述实录使这部虚构文本显示出真切效果。这本书打开就被吸引,其时我开始往返于两座城市,旅程中我需要在随身的双肩包放几本书,《夏日》是我的选择之一,我想看到当代在世而被称为“一个伟大作家”的状态,他的写作与生活境况。
睿智而诚实,机锋遍布又情感真挚。这是《夏日》显示的令我亲近的文本气质。
小说里的主人公—青年库切—仿佛一个幽灵般的存在,游离于世界边缘。库切是一个与外部世界疏离的人,疏离而艺术精湛,这是令我尊敬的作家的品质。有同类品质的作家都是我喜欢的,比如普鲁斯特、塞缪尔·贝克特、詹姆斯·乔伊斯、罗伯·格里耶。有这样的偏好当然也是因为我当时正处于失业的困顿中,辞职之后全心侍奉自由的文学写作理想,然而写出来的作品无人问津,饱受拒绝和冷遇。这样的个人境况使我对库切书写的困境有切实体会。许志强先生在《夏日》中文版序言中谈到阅读库切的体会,让我感同身受:
……破裂,沉入生命冰凉的残渣。库切带着这种感觉去描写事物,讲述自身的故事,体味他那种孤独的命运,恰恰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命运,去寻找他破裂的生活中值得一写的东西。他用质朴细腻的语言叙述,平稳的笔触带着层积递进的效果,因其尖锐的叙述有时诚实得让人心里打战。
四
隐逸而勇毅,仁慈又坚韧。这是我欣赏的人的精神气质,也是库切的性格特征。
一九七○年一月一日,即将迈入三十岁的库切身穿外套,脚蹬棉靴,把自己深锁在他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帕克大街二十四号地下室的住所里。他在新年许愿中发誓,如果写不到一千字,自己就绝不出来。后来他决心坚持每天写作,直到完成一部小说的草稿。这是库切写作《幽暗之地》的时刻,此后他写作的恒心和毅力从未减退。
这个细节令我记忆深刻,也带给我最初感动。或许很多写作者写作生涯的开始都是如此。
个人的决心与意志和纪律的集合,缔造一个写作者的杰出业绩。
库切重要著作的中文版在图书市场都能找到,这些年他的虚构和非虚构文本多有出版,不同版本也多有上市。《幽暗之地》是我读过《夏日》之后看到的库切著作的第二本。《幽暗之地》是一本有关残忍的书,揭示了各种形式的征服中的残忍。“黑暗”或者“幽暗”,这种光线是我熟识的,它应该是我与库切的共同精神背景。出生于矿区所体察到的黑暗,自然相异于南非社会的黑暗,然而形态不同,精神内核却一致。

《幽暗之地》分为两章,越南计划/雅各·库切之讲述。小说涉及作家对越战的记忆叙事。军人出征前的慷慨悲歌和战争结束后的惨烈与伤痛,这些景象都可以从电视媒介中看到。《幽暗之地》叙述的越战当然是不同的。二○一七年我应邀到美国访问,在洛杉矶有机会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故居参观,在那里看到过越战的全程实况记录。
出现在库切小说里的作家形象令我感到亲近,在他的叙事情境中出现的父亲形象也带给我亲近感。在《夏日》里如是,《幽暗之地》也如是。这个父亲会让我想到自己的父亲—一位前半生有着军旅生涯,穿越血雨腥风幸存下来的老兵,转业到矿区后过着平民生活。
阅读过《夏日》和《幽暗之地》,我开始寻找库切著作的中文版。《男孩》《青春》《铁器时代》《凶年纪事》《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耻》《彼得堡的大师》。
对一位作家的接受和热爱,源自我们心灵的选择,它是内心的契合与印证。
我在阅读过的库切著作的书页里留下个人随想的笔记:
写作作为祈祷的方式。阅读库切时我想起卡夫卡在他日记里的话。库切写出的文本是对卡夫卡的信念的印证。他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灵感来源于对卡夫卡文学世界的洞察。杰出的写作是对人类精神的质询,是对自我的探测。杰出的写作是与神明的对话,它与时间同构,在时间之内呈现超越人的肉身的永恒性。艺术和匠心。在小说的文本里,它不能只是一些事物的轮廓,一些故事或者情节的概述,它在结构上如同精美的建筑,布局对称,构造严密,在叙事上如同自然涌流的江河,它的延展和推进自然又精妙。是的,只有精妙可体现艺术的匠心。好的小说在整体上就是完美的,每个构成整体的部件都是完美的。
杰出作家的存在是一种现实,然而使杰出作家显现和呈示在世人面前也需要他者的努力。比如传记作家和译者。在不同文明与不同文化之间,在不同语言之间,要使杰出者真正与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读者相会更需要传记作家和译者的持久努力。因此每个英雄的诞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取决于其所在的环境,取决于环绕在他周围的鉴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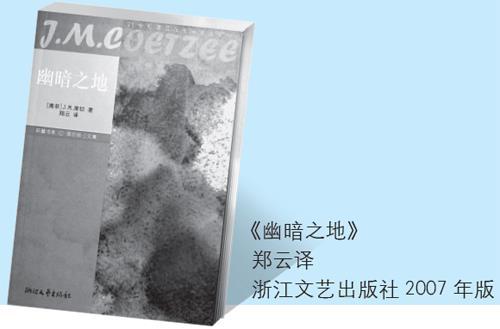
库切的写作并非没有受到过冷遇和拒绝。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完成后被多家出版机构拒绝。“《幽暗之地》最初的被拒反映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南非出版界的糟糕品位,但它也将库切放入了一份著名的长长的名单之中。这个名单包括所有曾经费尽努力想将自己的第一本书出版的知名作家们。”(夏榆《我们比想象中更自由,也更软弱》,《新京报》2017年11月18日)好的作家遇到知己是必然的,只是需要机缘。“读过幾页《幽暗之地》之后,我感到震惊和兴奋,在我看来,这是那一代南非英语写作的巨大突破,”库切在开普敦大学做讲师的同事乔纳森·克鲁评论道,“《幽暗之地》标志着南非后现代小说创作的开始。”
库切是幸运的。依靠精湛的写作技艺,他赢得光荣和赞誉,也赢得世人普遍的尊敬。
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持自然是库切的光环之一。然而很长时间库切却自我命名为“黑暗之子”,他是白种人却长期生活在施行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社会的动荡、人性的混乱和挣扎是他人生经验的一部分,也是他书写的重要的题材和主题。
库切对家族史的关注和书写,只是他对国家记忆书写的一部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对国家现实的思考甚至批评,在库切的小说里随处可见。他经常将个人与一个国家并置。
在《夏日》里随处可见主人公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见他对国家现实的反省式审察。
他的小说更像艺术精湛的政治寓言—
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上哪儿去找一个把自己藏起来不受玷污的地方?难道跑到白雪覆盖的瑞典,远离千山万水从报章上了解他的同胞和他们最新的恶作剧,能让他感觉好些?
怎样逃离污秽: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一个该死的老掉牙的问题—它不放过你,给你留下恶心的化脓伤口,良心的自责。(《夏日》,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五
这一次,我是那个被阅读治愈的标本。
“你自己也应该去做心理治疗。”她嘴里喷着烟对他说。
……事实上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去做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的目的是让人幸福。这样做有什么用?幸福的人太乏味。最好还是接受不幸福的重负,试图将它转变成有价值的东西,诗歌或音乐或绘画:这是他的信念。(《青春》,王家湘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这是有关精神疾患治疗的对话。渴望成为诗人的青年库切周旋于跟女友错乱的情欲之中。库切在《青春》里写到的情感纠缠带来心灵的鏖战与折磨。
“他在证明着一点,每个人是一座孤岛……”我反复阅读过青年库切的独白:“能够治好他的东西,如果来到的话,那将会是爱情。他也许不相信上帝,但是他确实相信爱情和爱情的力量。那个他所爱的人,命中注定的人,将会立刻透过他呈现出的怪的,甚至单调的外表,看到他内心燃烧着的烈火。同时,单调和样子怪是他为了有朝一日出现在光明之中—爱之光,艺术之光—所必须经过的炼狱的一个部分。因为他将会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是早就已经确定了的。如果目前他必须是微贱可笑的,那是因为艺术家的命运就是要忍受微贱和嘲笑,直到他显示出真正的能力,讥笑和嘲弄的人不再作声的那一天。”(同上)
“库切,迄今为止,在我欣赏的作家中,无疑是最好的导师,小说家职业的典范,他是值得终生阅读的作家。”二○二一年九月三日,我在《青春》的扉页留下这样的题记。杰出作家都有他们的精神传承。库切的“外省场景生活”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的诞生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的影响;对库切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更早还有卡夫卡,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春》中库切再次引入对他的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的诗人埃兹拉·庞德与T.S.艾略特,他们也是他人生的榜样,是他在困顿中的慰藉和医治他精神暗疾的灵药—
埃兹拉·庞德一生多数时间都遭受迫害:被迫背井离乡,后来又被禁闭,然后第二次被驱逐出祖国。然而,虽然被打上疯子的标签,庞德却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庞德听从了自己的保护神,将一生献给了艺术。艾略特也是,虽然艾略特的痛苦更多是属于个人性质的。艾略特和庞德过着悲哀的、有时是耻辱的生活……(《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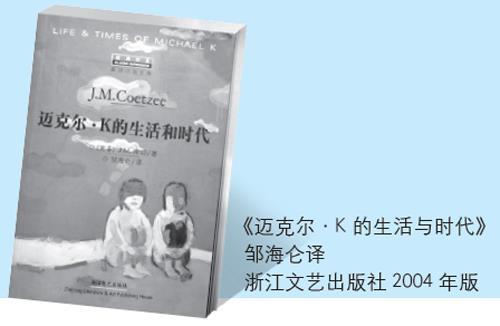
诗人庞德和艾略特对库切的精神影响之深,使他后来写出《何谓经典》的演讲辞。在演讲中库切向艾略特和庞德致敬。演讲稿出现在他的文论集《内心生活》。
“耻辱”,这是我在库切的言说中看到他频繁使用的一个词语。如同幽暗和失败的词语一样,属于他贴身的词语。阅读必须在更为开阔的背景下才更为有效。再读《青春》时我已研读过T. S.艾略特的诗集《四个四重奏》,反复阅读过传记《不完美的一生:T. S.艾略特传》,那是一个伟大诗人同样杰出的传记,在此之后重读《青春》就更懂库切表达的深义:
和庞德和艾略特一样,他必须准备好忍受生活为他储备的一切,即使这意味着背井离乡,微贱的劳作和诽谤。如果他不能够通过艺术的最高测验,如果最后证明他不具备这份神圣的天赋,那么他也必须准备好忍受这个结果:历史的无情裁定。生存的命运,不管他所有的今天和未来的痛苦,都是次要的。许多人受到感召,很少人为神所选中。每一个大诗人的周围都有大群的次要诗人,就像围着狮子嗡嗡飞的蚊虫。(同上)
在无数由失败带来的幽暗时刻,阅读《青春》带给我心灵的慰藉。库切使我看清世態炎凉,看清人性的真相。
洞悉从事艺术创造即为某种献祭,亘古如是。
六
“他一直是我的老师,是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日子里道德的指南针。”
在世间的赞誉中,库切的学生安妮·兰兹曼(Anne Landsman)对库切的评价别有意味。
无疑,库切的存在提供了文学的尺度。他的写作业绩显现出杰出小说家的职业维度。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南非开普敦三百周年基金会将一九九五年度奖颁给库切,以表彰他终生为文学所做的贡献。同年他获得纽约斯基德莫尔学院颁给他的名誉博士学位。这是更早到来的荣耀,库切逐渐被他生活的环境,也被世人所知晓。颁奖仪式上,致辞人罗伯特·博伊斯(Rober Boyers)教授说:“J. M.库切是一位小说家、政治思想家、评论家、理论家、语言学家和权力解剖学家。您的作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生动而内敛,既有风格又有知识分子的勇气。您的创作来自南非的经历,带着特有的压力与执着,您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谈论特定历史所发挥的力量,同时又不局限于单一的时间或国家,您仔细地观察压迫、残酷和不公正,并教会读者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试图表达自由的困难。”
“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这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为加西亚·马尔克斯颁奖时的赞誉。我以为这样的话语也适合库切。寻找能找到的库切著作的所有中文版,这是我这些年做的事情。我愿意成为与库切精神相契的阅读者,然而我反对将这种精神的共振称为“拥趸”,或者如时下的流行词“粉丝”。在我看来失去个人精神立场的拥趸无意义更无价值。
打开一本书的同时也是在打开一个世界,那里如同森林浩瀚,如同海洋深邃。
阅读不是娱乐也非游戏。我们带着自己内心的疑难和精神诘问。
阅读的过程是求证和释疑。比如:什么是真的文学?以创造为业的作家(艺术家)如何自处?作家与他的国家的关系,与他的族群的关系,作家与公共事务的关系,作家的精神立场和道德原则何为?这都是重要的命题。曾经有人说过:“大众的喧哗与狂欢之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文学现场。”

库切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文学是怎样的品质,杰出作家是怎样的样貌。
早年库切写过一部夭折的小说《焚书之火》,他详细考察过南非的某些严苛的法规和制度,他关心的是那些制度会怎样影响自己的写作生涯。库切批评南非政府那些监管中心愚蠢至极。他在小说《等待野蛮人》中写道:“所有的事情都相互关联,当国家的正义秩序坍塌的时候,它在人民心里也就土崩瓦解了。”
作为作家的库切如丰饶之海。使我在更广阔的思想视域得以观看库切的是两本传记,《J. M.库切传》和《用人生写作的J. M.库切:与时间面对面》。前者是由J.C.坎尼米耶撰写的一部六百多页的巨著,后者是由大卫·阿特维尔撰写,聚焦于库切的手稿以及写作秘辛,两部传记侧重点不同可以互为参照。它们都在叙述一个杰出作家是如何炼成的。这是优异的传记对杰出作家的精彩呈现。
库切身材消瘦,但很精神。过早花白的胡子,戴着角质眼镜,低沉的声音,有着沉默寡言的风范和清心寡欲的外观。多年来他用沉默和拒绝对公众谈论自己来保护自己不受外界的入侵。他的私人生活,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南非国内,都处于公共领域之外。当他罕见地出现在社交场合时,他宁愿站在一个角落里,仅同一个人说话。库切是一个有着僧侣般自律和奉献精神的人,他很少接受媒介访问:“我的抵制不仅仅是保护一种幽灵般的全能。写作不是自由的表达。写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要唤醒自我中的和音,然后与之言说。”
我愿意将库切的肖像定格在这幅画境中。
“约翰·库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伟大作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教师中的一员。在典范和见证的传统下,他教导我们怎样阅读一本伟大的书。他教我们更清晰地认出人类灵魂,他课内外的言论都是我毕生难忘的回忆,一直在我耳边不断回响。”库切的学生乔纳森·李尔的评价楔入我心。《J. M.库切传》放置于我卧室的书架之上,在随时能看见的位置。这是更为深入和辽阔的书写,在全球的语境之下对库切的讲述。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杰出作家的品质和风貌,看到他的精神和灵魂的质地,他的文学传承和写作技艺的淬炼,看到他的胸襟和非凡的气宇,也看到他对公共事务的热忱与介入。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壮阔的人性的海洋。
与时间面对面,这是库切得以沉潜文学志业的缘由。库切的手稿上都仔细地标注了写作日期和修改时间。在写作过程中必定有频繁的修改,对手写稿和打印件一字一笔地校正,在电脑上逐词逐句地重新录入,每部作品有十几个版本的草稿都是家常便饭。
荣耀和赞美成为库切生活的一部分。“他一直坚持自我的自由,他也没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南非作家,而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写作者,他所效忠的是小说的话语,而不是南非的政治話语。他的作品已被描述为严肃、复杂和辉煌的,是智慧、道德与审美的结合体。带着决然与宽恕,库切带给读者的是理解的冷静慰藉。您勇敢而不妥协的写作丰富了我们,也给我们带来挑战,迫使我们面对自己和我们所在世界的真相。”然而我记在笔记里的库切在《青春》里对他的内心在困境中鏖战的描写,那是更为痛彻的体验。
读着这样的叙事,你就知道一个杰出作家是如何炼成。
那是炼狱中的淬炼。
“经验”,这是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很想用的一个词。艺术家必须尝试一切经验,从最高尚的到最有失身份的。正如艺术家命中注定要经历最极致的创造的快乐,他也必须准备好承担生活中的一切不幸、悲惨和耻辱。
……他必须坐下来写作,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不到合适的时候他无法开始写作。无论他如何一丝不苟地做好自己的准备,擦干净桌子,把台灯放置好,在一张白纸的一侧画一道线留出页边空白。
……他怎么知道写这些诗的人没有多年面对白纸,和他一样坐立不安地总也不能满意?他们坐立不安,但终于振作起来,尽最大努力写出了想要写的东西,寄了出去,忍受着退稿的屈辱,或忍受看到他们笔下流出物以其全部的贫瘠呈现出令人沮丧的出版物中的屈辱。(《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