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的夏天,一档网络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突然走红,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持续加温,引爆热点。这个让大家“燥起来”的节目一下子点燃了无数人的内心。节目以乐队为单位,音乐形式呈现多样化特征,摇滚、放克、民谣、爵士……既是流行音乐常识的普及与推广,也是大型怀旧的现场。乐队中有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力量盘尼西林乐队,也有成立了三十年的大陆第一批摇滚乐队面孔乐队。一些常年穿梭在各地的live house和音乐节现场的乐队,比如刺猬乐队,也通过这个节目成了一时的顶流。流行多年的新裤子乐队又一次出现在聚光灯下,在摇滚圈有着坚实歌迷基础的痛仰乐队也走进了大众视野。
节目里乐队形式多样,但最让人们激动且战栗的依旧是摇滚。以效果而言,摇滚有一种瞬间点燃现场的魔力,即使是原本安静悠远的民谣系,只要在编曲中加入摇滚元素,现场感染力也大不一样,那种火花四射的金属质感裹挟着你,不仅仅是多巴胺、肾上腺素的分泌,不仅仅是摇头晃脑、跺脚挥手,更是一种内在激情的迸发,一种本我生命的释放,简单点说,就是“燥起来”。
大城市里行色匆匆为生活所困的绝大多数人平日里很难想象,从十几岁的毛头小孩,到“渴望永远年轻”的中年人可以在摇滚乐中制造怎样的狂欢。《乐队的夏天》让人们略略窥到一丝踪影,在节目现场“燥起来”的观众更像是演出的一部分,节目真正的观众其实是在屏幕前,在无数个端口那边,这是一场云端的狂欢。
 面孔乐队(《乐队的夏天》演出现场)
面孔乐队(《乐队的夏天》演出现场)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那很有可能是属于音乐的,属于乐队的,它们自带隔绝现实的功能。《乐队的夏天》一播出,屏幕一亮,音樂一响,多少人瞬间坠入近乎迷醉的异空间。在歌声里,众生平等,群体狂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地唱着歌,摆动着身体。在节目里,青年人看到偶像看到未来,看到灯光看到舞台,看到付出牺牲终有收获;中年人看到信仰看到执着,看到坎坷看到蹉跎,看到遍体鳞伤徒留唏嘘。同一档节目,在不同的人群中引发各自的共鸣,分众时代的观众们在各自的屏幕前哭着笑着,在云端集体狂欢着。
如果没有这个节目,人们大概难以想象乐队、摇滚还能在当前的传播语境中点燃观众。从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而来的摇滚音乐节文化,使大草坪、大操场、万人狂欢成为摇滚的“标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一九八五年“拯救生命”(Live Aid)大型摇滚乐演唱会那种殿堂级的演出,是节目中被不断提起的香港红磡、北京工体。可是《乐队的夏天》偏偏打破了这种固有思维,以一档网络综艺节目实现了云端的草坪音乐节,虽然节目仍致敬般地呈现着摇滚黄金年代的质感,但乐队那些辉煌的过去(“面孔”“新裤子”“反光镜”)、无奈的现实(“刺猬”“九连真人”),时空交错的故事性使乐队大多披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精心打造的舞台上分外耀眼。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窦唯曾经描述自己《黑梦》专辑中的歌曲:“歌曲的内容上,好像自己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不知道方向、好坏、对错……”人们在习以为常的现实世界里有着安全感,也伴随着麻木性,而绝大多数经典的摇滚乐都有解构现实的功能,毫不留情地将人们熟悉的符号所对应的具体意义模糊掉或剥夺走,打破现实世界的安全感,戳破明确的能指、虚幻的意义,带来痛苦、不安与紧张。而真正经典的摇滚乐揭露黑暗不是为了接受沉沦,而是在歌唱中倔强地抬头,骄傲地站立,从而实现漂浮意义的再生,就如张楚说过,“摇滚乐就是叩开天堂之门”。
一九九八年就开始发表专辑的新裤子乐队在节目中备受关注,不仅激活了一直以来喜欢他们的听众,也一下子带来了数量庞大的新粉丝。看看乐队最受欢迎的两首经典曲目《生活因你而火热》与《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锐意创新的美学固然重要,更打动人的却仍然是歌曲打破现实又重建意义的力量。
勇敢的你
站在这里
脸庞清瘦却骄傲
在这远方
没人陪伴
只有幻想和烦恼
……
我不得不去工作
在大楼的一个角落
格子间的女孩
时间久了也很美
我会和她结婚
带我去小城过年
忘了吧那摇滚乐
奔腾不复的时代
(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这是一段演唱者个性化的自我陈述,同时也是代入感极强的对听众们状态的描述,残忍地揭开了无数普通人因追求稳定生活而被迫告别理想的隐痛。大城市的生活、办公室的恋爱、平淡如水的日子,这些貌似笃定的人生意义在歌声中一下子变得脆弱不堪,成为空中漂浮的意义。然而乐队在唱出了平凡人间的无奈、戳破现实生活的荒诞之后并没有完全消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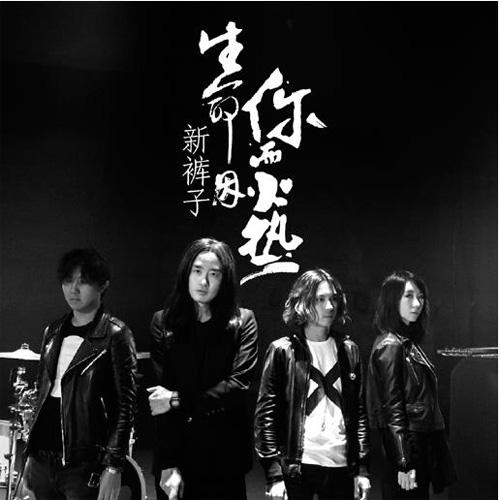 《生活因你而火热》《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收录于新裤子乐队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2016)
《生活因你而火热》《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收录于新裤子乐队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2016)那些昙花一现的灿烂
是爆炸的烟火
那一团耀眼的火焰
在燃烧着你和我
……
那平淡如水的生活
因为你而火热
(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生活重压下放弃梦想而向现实低头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在这首歌里热泪盈眶,在生命中不得不承受的无奈里不服着,倔强着,守着内心最后一点骄傲。在这样的歌曲里,人们不仅仅体验了漂浮的意义、所指的滑落带来的精神上的幻灭感以及生命虚无感,同时又能在意义重建中看到希望,这是一种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快感体验,却是带着真实人生质感的有意义的快感。
摇滚乐队的歌曲能产生这种漂浮意义的再生和乐队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不是影视明星,也不可能是“热搜顶流”,摇滚天生的亚文化性质使得人们对于乐队的想象总是落拓的、潦倒的、愤怒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用来形容他们大概最合适不过,几个年轻人为了音乐梦想聚在一起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画面,可是少有乐队没有经历过分裂、出走、解散,正如歌里唱的“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去了……”最终留下少数幸存者,绝大多数的乐队都会倒在性格不合、音乐理解不同、经济无以为继的困难前。
《乐队的夏天》让本来小众的乐队文化走进了大众视野,许多人通过这个节目才知道还有这么一群“玩乐队”的人。像果味VC乐队与盘尼西林乐队这种不需要为经济发愁的乐队极少,事实上,大多数乐队只能在糟糕的生存环境与音乐理想间不断挣扎,但靠着乐队不稳定的演出实在很难养活自己,更别提负担一家人,许多成员都只能以兼职状态来维持乐队。刺猬乐队的主唱子健在公司上班;九连真人乐队的阿麦和阿龙都是乡村教师,阿龙说他有了家庭特别是当了父亲以后更要精打细算,不敢断了经济来源;走放克路线的Click#15乐队二○一八年的演出收入只有一千块钱;即使是签约摩登天空多年的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在广告公司上过班,当过导演,为了省中介费去房产公司应聘;庞宽说自己妻子为了在家里放下婴儿床,扔了他攒了几十年的磁带。女性乐队成员要面对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刺猬乐队曾因石璐生孩子停摆许久,一个单亲妈妈大晚上转场排练又让多少观众心疼唏嘘。这大概也是“玩乐队”的意思,就像以前说“玩票”。对理想的坚持,除了要有兴趣,还得有钱有时间。虽然九连真人乐队依然咬紧牙关唱着“莫欺少年穷”,但看不清前景的追求总是无力的,何况是“玩乐队”这种心力财力投入都极大的梦想,毕竟鲁迅说过“梦想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学生时代最容易组成乐队杀出血路,并非仅仅因为青春荷尔蒙的推动,恐怕还有相对轻松的生活、未曾直面社会残忍的加持。年轻时总以为生活的试炼是上刀山下火海,殊不知生命中真正的残忍绝非此等咬紧牙关就能挺过去的考验,而是日复一日柴米油盐的消磨,压倒梦想的往往是一根根轻飘飘的稻草。但也正是这些真实生活的轻与重成就了最打动人的歌曲,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正是在不断拆解坚硬的现实,不断击碎固化的世界,以撞南墙也不回的姿态“问个不休”,以永远倔强的眼光凝视着这个世界。
我最爱去的唱片店
昨天是她的最后一天
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
全都散落在街边
我最爱去的书店
她也没撑过这个夏天
……
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
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
沒有文化的人不伤心
他不会伤心
……
他也会伤心
(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痛仰乐队
痛仰乐队歌中诉说唱片店的倒闭、书店的消失、理想的失落之后,大声呼喊的是“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在重复了多次“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之后,结尾部分唱的却是“他也会伤心”,一个意料之外的反转设定一下子将歌词的境界推高。英国的谁人乐队(The Who)曾说:“如果他不是喊救命而是在为真理呐喊;如果他用一种无知无谓的勇气去承诺未来;如果他挺身而出直指时弊,却又不主张流血冲突,那么它就是摇滚。”作为一种文化的客体、文化的实践,摇滚必须产生意义,如果只有控诉,只有黑暗,只停留在满足人们的宣泄,那么力量是有限的。漂浮意义的再生才能带来希望,没有人愿意彻底沉沦,被打倒之后依然看到光明,才是真正意义上人们愿意反复聆听的原因。
“一直往南方开”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证明了二十世纪存在“摇滚诗人”。意象作为诗的核心要素,自然也成为摇滚的重要元素。意象往往是具体的形象,它使诗歌变得丰富多彩,但同时它又是抽象的工具:四季的变化、心里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理想主义的观照,核心意象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搭建桥梁,指明道路,或者欲盖弥彰,画出迷宫。摇滚乐的力量也并不仅仅在于它音乐上的刺激,对麻木身体的唤起或者快感的营造,一首首被不断演绎的摇滚乐往往有着精彩的意象,一个个承载着听众想象与情感的意象则是摇滚乐的经典符号。
被称为大陆摇滚乐教父的崔健一九八六年以一首《一无所有》拉开摇滚乐的序幕,此后的三十年里大陆摇滚产生了许多经典意象:崔健的一块红布、蓝色骨头、“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的假行僧,还有许巍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的蓝莲花,郑钧的“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的拉萨。这些意象是一块块布满裂纹的透镜,我们通过它回望破碎的、片段的过去,也可以通过它观察分裂的、痛苦的自我,还可以通过它看向未来,在断续的线索中寻找指引方向的模糊亮光。
在《乐队的夏天》中,张亚东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一直往南方开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思,可以让大家都这么陶醉?”
梦想 在什么地方
总是那么令人向往
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
就是为了来到你的身旁
梦想 在不在前方
今夜的星光分外地明亮
我想着远方想着心上的姑娘
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
一直往南方开
一直往南方开
一直往南方开
……
滚动的车轮滚动着年华
(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如果单纯看歌词,在简单的旋律中不断重复的“一直往南方开”与“滚动的车轮”是不断叠加的意象,情绪上一浪一浪地调动起观众的共振,形成迷醉的效果。但如果仔细考究“一直往南方开”这个意象,背后其实是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所指对象,是每一个从改革开放的岁月走过来的人所脑补的“理想”与“未来”。正如戴锦华谈到的,“南方”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早已成为一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意象,记忆或想象的南方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踏板,北方似乎是中国历史的隐喻,而南方则是未来的指称。
 刺猬乐队
刺猬乐队在节目的第一期中,编导调皮地把现场的几首朋克作品剪辑在一起,嘲讽了一把其中的“意义匮乏”与“形式雷同”。实际上新世纪前后,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通过音乐进行自我表达,摇滚乐的内涵出现明显的分岔,朋克文化成为年轻一代的主要话语,他们以一种无所谓、无意义、举重若轻的故作潇洒消解着社会带给他们的全新压力。不过,时间会残酷地淘汰不生产意义的产品,只有真正如诗一般有意象有意义的摇滚乐才能经受考验,也只有它们能在舞台上唤起真正的精神亢奋。
黑色的不是夜晚
是漫长的孤单
看脚下一片黑暗
望头顶星光璀璨
叹世万物皆可盼
唯真爱最短暂
失去的永不复返
世守恒而今倍還
摇旗呐喊的热情
携光阴渐远去
人世间悲喜烂剧
昼夜轮播不停
纷飞的滥情男女
情仇爱恨别离
一代人终将老去
但总有人正年轻
(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这一段歌词出现了许多组相对概念:脚下与头顶、黑暗与璀璨、短暂与永恒、老去与年轻;还有热情的消退、悲喜的反复、爱恨的纷飞等,歌名中的意象“驶向云外的火车”是具象的,但并不好理解,而歌词中这些相对概念貌似抽象却句句击中人心,将一代代人必须面对的庸俗生活、爱恨别离、时间流逝展示在眼前,歌词中的意象也就有了多维而丰富的阐释空间,与每一个听众发生共鸣。
黑撒乐队的《校花与流川枫》,其中来自日本动漫《灌篮高手》的流川枫这一形象准确代表了“八○后”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结合整首歌讲述的校园爱情故事和独属于青春的心悸、爱慕、依恋,围绕着这个形象自然而然地产生发酵作用,意义不断溢出形象本身,而且这个表达准确凝练的同时还带着一种排他性,因为它只能在有共同成长背景共同爱好的圈子里产生作用,也就带来了群体内部的认同与归属。
不难发现新世纪以来的意象已经慢慢告别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来自集体、家国的呐喊,走向了个体、私人、温暖的表达,一个小我的世界得到了最大的尊重,虽然也有愤怒,有癫狂,有执着,但毕竟在气质上已经与前辈完全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音乐永存,但每一代人又会有每一代人的音乐,有每一代人的乐队与摇滚。
诗与歌从来不分你我,经典的意象也从来不惧重复,“他不会伤心”(《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重复了多次,“一直往南方开”(《公路之歌》)更是重复了二十几次。这是经典意象的重复,事实上音乐本身就是需要重复的,因为音乐在时间中稍纵即逝,只能依靠重复来持续。在音乐的世界里,“陌生感”并非最有效的生产方式,耳熟能详的歌曲可以不断唤起感动,经典的意象也可以不断唤醒理解,产生新的空间。这些音乐作品也许永远不是成品,它们不仅会被生活、被世界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它们也会在每一次现场演绎中重生,是内容的重复,却不是意义的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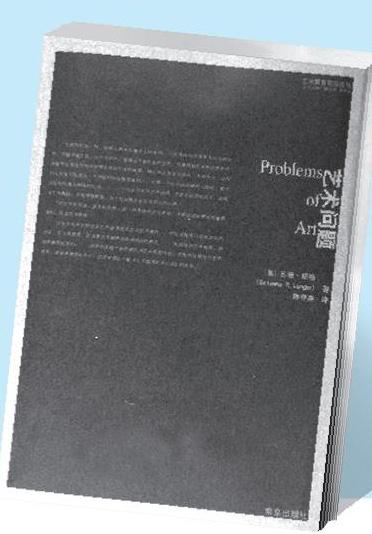 《艺术问题》[ 美 ] 苏珊·朗格著滕守尧译南京出版社 2006 年版
《艺术问题》[ 美 ] 苏珊·朗格著滕守尧译南京出版社 2006 年版摇滚乐的现场更是特别地激动人心,甚至空气中都弥漫着占有与失控乃至毁灭的意味。刺猬乐队演出的时候,子健的吉他卡了弦甚至跑了调,却依然动人,许多歌手在激动时跪在舞台上,或跳向观众,甚至连唱的什么都听不清了,观众反而愈加投入与激动,音乐、灯光、歌声、气味、拥挤的身体、挥舞的手臂都组合成只属于当下这一次的摇滚现场,不可复制。同样地,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生活情景中听同一首熟悉的歌曲,人们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熟悉的音乐带来安全感,同时也更默契地与听众产生共鸣。在歌词、曲调、节奏、作品的撞击中,人们会产生一种被不可名状的东西击中的神圣感,会觉得身体在放空之后又被完全充实,仿佛在一瞬间捕捉到了生命的要义,它可以通过音乐传递,却无法言说。
真实的人生里,现实的生活中,摇滚歌手可能都有各种问题、各种缺点,甚至他们的缺点多如满天星星,但那又如何呢?站在舞台上,只要吉他弦拨动,键盘奏响,架子鼓敲下,熟悉的旋律响起,理想主义的太阳瞬间光芒万丈,满天的星星消失无踪,我们追随着那阳光、那歌声,足以慰藉所有的漫漫长夜。
“一支未来牌香烟”
如今的音乐节目给观众带来越来越新鲜、丰富、专业的音乐体验,观众们的耳朵也越来越挑,不是能飙高音就专业,也不是会Freestyle就厉害。《乐队的夏天》在二○一九年音乐类综艺节目中备受瞩目,在豆瓣上有近十万人给这档节目打出了8.8的高分,其意义早已超出收视率,辐射到了音乐、摇滚、乐队以及观众,不仅科普了流行音乐的各种知识,还结合乐队的情况举重若轻地带出了中国摇滚乐的历程。坐在超级乐迷席上的吴青峰、张亚东、欧阳娜娜、马东、白岩松所组成的混搭阵容,也正彰显了节目的野心,让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背书的他们在点评提问中碰撞出无数火花,覆盖诸多观众群体。
青年人总能找到属于他们的文化形态,中年人总会寻到拯救他们的精神出口。在一个分众时代里,《乐队的夏天》就像从天而降的云端方舟展现了神奇的弥合功能:一方面是年轻的孩子们,当下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们”在迷茫中被摇滚召唤;另一方面则是当年曾经叛逆过、热血过的中年人被摇滚唤醒。在屏幕前热泪盈眶的,绝不仅仅是处于亚文化场域的青少年,还有处于人生焦虑顶端的中年人,这一代中年人正是中国摇滚的最初听众,可以说正是他们与摇滚歌手们共同成就了中国摇滚乐最初的浪潮。
本来怀旧与回忆相关,应该是极其私人与个体化的体验,但是当一些大型事件沉淀为集体记忆以后,就能唤起集体怀旧的功能,人们在其中体验到惋惜、唏嘘、失落、感伤与忧郁,但是也不乏积极、肯定、思慕与美好,这类多种成分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味道充满了魅惑感。
在节目中,张亚东听了盘尼西林乐队翻唱朴树的《New Boy》,泣不成声:“那时候我们说新世纪要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结果呢,就是我们都老了。”这首歌是张亚东与樸树在跨越新世纪的时候共同创作的,二十年之后看着年轻的脸庞再度唱起,不胜唏嘘,当初歌里唱的那“一支未来牌香烟”充满了苦涩的味道,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后来张亚东在自己的微博上复盘这个插曲时说:“我知道这是一种浅层的感动,但我无能为力。”但这并不仅仅是浅层感动,事实上在特殊环境中的怀旧所带来的也会是最真诚最核心的体悟。这没有深浅高低之分,这是真诚而动人的,在戴着假面生活的世界里,歌声成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内心与过去。
如果说以张亚东为代表的中年人群体在“盘尼西林”这样年轻的乐队身上回望了飞扬的青春,青年人则在“面孔”这样的前辈级乐队身上感受到了岁月的分量。这支一九八九年成立的乐队真正显示了那一代摇滚人的金属质感,他们的翻唱给《流年》《张三的歌》这样的流行曲目注入了新的灵魂,前者唱出了剑胆豪情,后者则演绎得潇洒宽广,透着阅历带来的洒脱,在这真正的摇滚老炮身上看到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一首真正有力量有情感的作品就像一个磁场,听众一定会被吸引进去,而越能与作品产生共鸣的听众就越靠近磁场的核心,感受到的力量也越大。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早已指出:“每当情感由一种间接的表现方式传达出来的时候,就标志着艺术表现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传达的感情比起普通的交流方式传达的感情更为生动透彻,它传递的意义也更为深刻感人,更为完整和一针见血。”正是在这种层面上,我们感到经由摇滚乐唤起的情感似乎特别动人,特别意义深刻,也是在这样的维度上,我们相信音乐唤起的怀旧是一种力量,这种怀旧并非单向地指向过去,它帮助我们在无力的现实环境中重新获得源自过去的生命动力,从而更自由地生存,更勇敢地面对未来。人们说“所有的创作者都是怀旧的”,事实上“所有的听众也都是怀旧的”,不管你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都在这份怀旧中获取了一分力量。
多少歌声随风而去了,在外交人员俱乐部,在马克西姆西餐厅,在北京电影学院后面的莱茵河酒吧,在三里屯、什刹海,在广州的木子吧、不插电吧,在成都的小酒吧,在迷笛音乐节,在草莓音乐节……那些呐喊与斗志,那些诗一般的歌词,那些狂欢与迷醉,那些梦一般的呓语。生活的脚步从不停歇,新的困惑从不迟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声摇滚就如盖世英雄,踩着七彩云霞而来;这些年,舞台上的他们为音乐打拼过或挣扎着,舞台下的我们为理想奋斗过或倔强着,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也总会继续有人伴着喑哑的琴、低沉的鼓唱着歌,他们站在那里,是舞台的中心也是社会的边缘,现实浮躁喧嚣,这本身就构成了意义,舞台下也总会有无数的臂膀举起来,人们内心燃烧着信仰:那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