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是个较晚近的词。古文中语义相近的,或许是“严重”,即如说某人“性严重”。但“严重”一词,语义、语用已改变。这里就姑且用“严肃”。“严肃”与“戏谑”并非一定是对极。只是在明清之际的语境中,“戏谑”往往被作为严肃的反面(即“不严肃”)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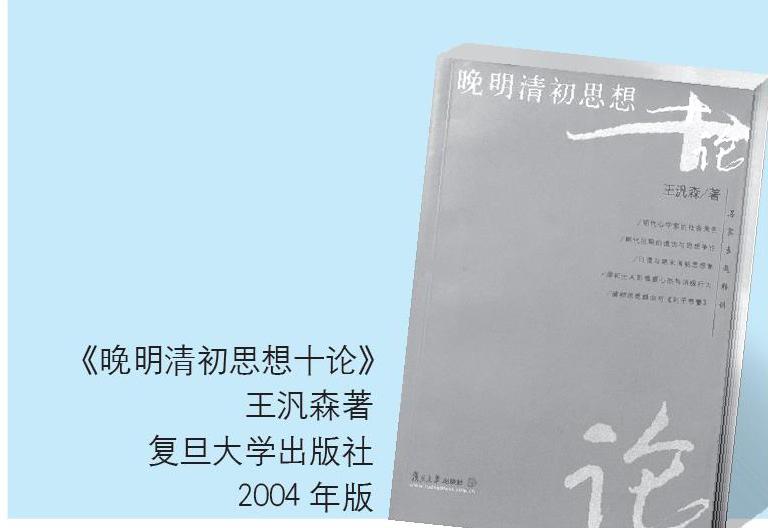
关于晚明士风,王汎森有所谓“道德严格主义”的说法。他的《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一文,希望提示的是,“在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在我看来有趣的是,那些思想家对“气质”“人欲”“功利”等的看法与通常的見解已有不同,认为“情”“欲”是“人的天性中一个天然的组成部分”的儒者,他们的上述“修正”,不是消弭了,反倒加剧了士大夫道德修炼的紧张感、紧迫性。
同一时期,既有为人艳称的“名士风流”,又有“道德严格主义”,可以作为后人关于某历史时期“士风”的想象受制于目标人物及所采用的材料的例子。
古代中国人将“人”做成了一门大学问,不乏精致的思路,其中的有些面向,是今天通行的学科分类不能涵括的。这里也有我谈到过的“文化流失”。古代中国没有以科学实验作为支持的近代心理学,却绝不缺乏对于人的洞察力。即如对于“乡愿”这一种人格,对于种种“似是而非”(“似仁”“似忠”之类),我曾以《读人》为题,对这题目一写再写。近期发表的“读人”,还引了王夫之所说“不才而忮,其忮也忍”(《读通鉴论》),是我虽有类似的切近观察却不能够如此精准表达的。
儒家之徒对道德严肃性的极端追求,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对“人”的探寻。朱子就曾说过:“人之情伪,固有不得不察,然此意偏胜,便觉自家心术,亦染得不好了也。”(转引自《明儒学案》卷五十九钱一本《黾记》)此外也有对人的观察流于浅表却影响深远者,如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即如通常的以不苟言笑为“严肃”,以刻板、拙于表达为忠厚,不就导致了对人的误判?
严肃
古代中国的儒家,以进德修业为终身事业,以“优入圣域”为人生目标,无不有对严肃性的追求:既以严肃的态度求道,也以此保障人生的品质。具体的入手处,仍然互有不同。只是自幼至长,对于人的动作、仪态的规范,是儒家经典中就有的,影响极其深远。

我对于与“身体的技术”有关的一套理论不熟悉。据说该项理论关涉作为交流形式的身体性的行为举止和手势;与此有关的社会规范,或许适用于对我下面所说的现象的研究。“规训”因被用于翻译福柯,有了特定含义;本文中所用,只是其字面上的意思,即规范、训诫。见诸文献,古代中国知识人—主要仍然是儒家之徒—对身体的“规训”,工夫之细密,或许罕有其比。举手投足,一言一动,神情姿态,无所不及。手的动作(手容),目光所注的高低(目容),巨细靡遗。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中庸》有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古人所谓“威仪”,包括了内/外,表/里,是统一了内外表里的完整境界。因此要求内外兼修,身心一致,由外及内,由内而外。《礼记·玉藻》的“九容”,涉及五官四肢,包括了“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所规范的不止于身,更有心(内在意念、精神)。常人的经验,“头容”“足容”等的不正,往往由于生理性的疲劳,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正”即所谓的“提撕”,无非经由规范身体而端正精神。明清之际北方大儒李颙说整顿“九容”,无非“制乎外以养其内”,“内外交养,打成一片,始也勉强,久则自然”(《二曲集》卷三一《四书反身录·论语上》)。由此,规范由外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要求。前于此,吴与弼《与友人书》就说:“人能衣冠整肃,言动端严,以礼自持,则此心自然收敛。”(《康斋先生集》卷二)

对外在动作、姿态,甚至有极其严苛的“技术性标准”。李塨所撰颜元年谱,记颜氏训诫门生“慎威仪”“肃衣冠”(《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43页)。颜氏本人必“坐如泥塐”,“两足分踏地,不逾五寸”(同上,第104-105页)。黄淳耀日记,“忆他书载一人见前辈,方坐,足小交。前辈正色曰:‘小交则小不敬,大交则大不敬。”(《黄忠节公甲申日记》)苛细一至于此!非但坐姿,儒者甚至自检及于睡姿,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礼记·玉藻》不过要求“目容端”,儒家之徒变本加厉,更要求视线“上于面、下于带”,更具体化为“视不离乎袷带之间”(按:袷,交领)。据说“上于面则傲,下于带则忧,倾则奸(按:倾,斜视)”,而袷带之间,“此心之方寸是也”(《明儒学案》卷五二)。还要求:“坐视膝,立视足,应对言语视面,立视前六尺而大之。”(同上)如是之精确,难不成还要拿了尺子去量?知名的儒者陆世仪也说:“人视瞻须平正,上视者傲,下视者弱,偷视者奸,邪视者淫。”(《思辨录辑要》卷八)这一番标准化制作的成绩,自然会是如鲁迅所说“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忽然想到》五)。鲁迅的形容绝不夸张。
规训且及于妇孺。清人所辑《五种遗规》,包括《养正遗规》(《易》:“蒙以养正”)、《训俗遗规》、《从政遗规》、《教女遗规》、《在官法戒录》,几于无所不包,堪称“世故大全”。这也是古代中国的知识人对于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他们以身体力行并推广上述规范,作为自己的伦理责任。

收入《教女遗规》的唐代宋若昭《女论语》,有“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云云。《屠提学童子礼》,较朱子的《童蒙须知》更具体琐细,甚至及于“乂手之法”“下拜之法”,另如“凡走,两手笼于袖内,缓步徐行。举足不可太阔,毋得左右摇摆,致动衣裙。目须常顾其足,恐有差误……”儒教的压抑性,尤见之于此种场合。
上述規训,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最高境界,略近于俗语所谓的“习惯成自然”,以至犹如天性。借用了曾经流行的说法,即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至于规训的有效性,对于严肃性的无厌追求如何塑造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塑造了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心性,则肯定有因人之异,宜于个案分析,不便作一概之论。为此就有必要考察与严肃性有关的道德要求在士大夫中实现的程度,尤其其间丰富的差异。这也应当是关于士大夫日常生活考察的一项内容。
关于外之于内,人的仪态甚至动作的作用于心性,以至更“外”的饰物潜移默化于心性、精神状态,古人思理的精微之处,我们这些粗疏的今人已难以领略。即如说古之君子佩玉,进退揖扬,“玉锵鸣”,“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按:鸾和,铃;辟,便辟)(《礼记·玉藻》)。不但精微,而且诗意。有所谓的“金声玉振”。古人相信玉的温润影响及于内在的祥和。内外交修的必要性,于此也得到了证明。
也应当说,规训正因了“身体”的轻于“反叛”。从来有“异端”,有“叛逆”倾向,有“放浪形骸”的名士,有“箕踞”这一种不雅的姿势,有种种挑战、挑衅的动作。大学问家方以智,据说永历朝就曾裸走,是今人不敢尝试的。
有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有对“严肃性”无厌追求的知识人,“戏谑”就不能不具有敏感性,甚至被作为检验人的品性的重要衡器。明清之际的另一大儒刘宗周,曾引宋儒张载语:“戏谑不惟害事,志亦为气所流。不戏谑,亦是持志之一端。”(《圣学喫紧三关》)
戏谑
《易·家人》卦:“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嗃嗃”,指严厉怒斥;“嘻嘻”,即嘻嘻哈哈。意思是说,即使过于严厉,也仍然较嘻嘻哈哈强。到了现在,嬉皮笑脸、嘻嘻哈哈,语义不也仍然负面,至少被认为“不严肃”?
严肃赖有规训,戏谑的冲动则根于生命,更本能。知识人并不一般地否定戏谑、谐谑,俗间所谓“开玩笑”“逗乐”,甚至能欣赏谐趣,只不过严于雅俗的区分。雅/俗关系文化品质,人的文化品位,至今也仍然是文化分析的重要范畴。自重自爱的士大夫,能接受的是雅谑,至少“谑而不虐”,于此有严格的限度感、分寸感。他们不能容忍恶俗、低俗。那条线往往就在涉“性”处:容忍隐晦的暗示而忌露骨。
应当说明的是,雅/俗并不就对应于士大夫、细民,严肃/戏谑也不就对应于儒家之徒、文人。有种种品位的士和民,也有种种儒者(包括“假道学”),种种文人、名士,于此也不宜作一概之论。
士大夫与俗文化的关系,似乎也有南北的差异。道学的影响力,像是南胜于北。据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城镇化、市场化较发达的南方,士大夫更严别流品,严于雅俗之辨;而乡村的北方,知识人有可能更近俗。染指民间俗文化的明代名臣赵南星,正色立朝,是铮铮硬汉。风节凛然的傅山,其剧作据说有猥亵趣味,语言材料则杂用俚语。有明一代俗文化兴起,既推动了文化分流(两级化),同时也造成了雅俗界限的模糊。
古代中国与谐谑、戏谑有关的经典,就有《史记·滑稽列传》,《世说新语·排调》。《滑稽列传》所记淳于髡、优孟、优旃,都有“谲谏”的事迹,即用了戏谑的方式谏诤。被作为“滑稽之雄”的东方朔,滑稽多智,变诈百出,当班固写《汉书》的时代已然传奇化。
《排调》篇所谓的“排调”,不同于司马迁所说的“滑稽”,欣赏的更是机辩,无伤大雅的调侃、玩笑。玩笑的雅俗,并非总能区分。即如《世说新语·排调》中如下一则就嘲戏调笑而近俗。“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中宗为晋元帝庙号)谑近于虐,这种打趣难免会令对方尴尬的吧。但所用仍然是游戏态度,不同于有严肃性的讽刺。
戏谑即不“庄敬”。儒家之徒难免将戏谑与道德意义上的严肃对立。不威则不重。陆世仪说“笑”:“凡人语言之间多带笑者,其人必不正。”(《思辨录辑要》卷八)江右的魏禧则认为“通脱滑稽之人,使任国家事,辟如童子剪纸为船,而载铁石其上也”(《魏叔子日录·史论》)。明末清初那个特殊时代,空间逼仄,心理紧张,乏“余裕”。内外两面的压抑,在这一点上也有体现。这种环境中,谐谑往往更属狂士行为。袁中道记李贽,曰:“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李温陵传》)
即使儿童,戏谑,包括开玩笑、讲笑话,也在所必戒。上文提到的《五种遗规》中的《养正遗规》,卷上《朱子童蒙须知》曰:“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高提学洞学十戒》,以“小衣入文庙”,“闲坐嬉笑,及将圣贤正论格言作戏语”,统统归之为“侮慢圣贤”。其“十戒”包括“群聚嬉戏”,具体如“群聚遨游、设酒剧会、戏言戏动”。《朱子论定程董学则》要求学子“肃声气,毋轻,毋诞,毋戏谑、喧哗”。《方正学幼仪杂箴》责童子“喜笑勿启齿”,“见其异,勿侮以戏”。五种中的另一种,《训俗遗规》,卷一《陆梭山居家正本制用篇》,曰“居家之病有七”,其一即“笑”(注曰一本作“呼”)。
妇人女子,尤戒嬉笑。班昭《女诫》即有“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后汉书·列女传》班昭传)。上文引过的宋若昭《女论语》,有“喜莫大笑,怒莫高声”。亦收入《教女遗规》的明代吕得胜《女小儿语》,也说:“笑休高声,说要低语。下气小心,才是妇女。”
更为不情的是,认为夫妇间不宜狎昵。班昭《女诫》:“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教女遗规》卷下《唐翼修人生必读书》,说妻对夫“一生须守一‘敬字”,若“尔汝忘形,则夫妇之伦亵矣”,也是一种经验之谈,你不能说毫无道理。处夫妇须用“敬”,无非防微杜渐,避此媟、黩。吕坤《闺范》说某妇人夫妇相处六十年,“自少至老,虽衽席之上,未尝戏笑”(《教女遗规》)。闺门之内如此,由今人看来,不免生趣索然的吧。另有某妇“家法严肃、俭约”,婚后三年,“无少长,未尝见其露齿笑”(同上)。和这种妇人相处,不能不是一件痛苦的事。与戏谑有关的禁忌,还包括了老人。民间有“老不正经”的说法。“老”而“不正经”,被认为较之年轻人,更丑陋、可鄙。
汤普逊(Ewa M. Thompson)《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一书说道:“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莫斯科王国,公众欢笑欣喜是要遭到禁止或厌恶的。”“在莫斯科王国,欢笑和戏谑和犯法联系在一起。不仅观赏民间艺人表演,而且荡秋千、下棋,或者说笑话,都在禁止之列。” (三联书店1998年,第36页)古代中国似乎没有类似法令。儒者对谐谑的态度,是出于道德自律与一种与道德有关的价值感情,即对严肃的人生的肯定。戏谑在他们,有类似“不洁”之感,甚至有某种破坏、瓦解性,或有可能成为“破坏”“瓦解”的“端倪”。
忽而想到近一時常见的“表情”一词。不免想到,明清之际的知识人与细民各是何种表情?其实无论明清还是当今,“表情”肯定人各不同。明清之际固然有严于修身的儒家之徒,也有惯于谐谑的名士,甚至内心严肃者也同样诙谐。今日中国则有“嬉皮”,有所谓的“嘻哈文化”。“青年亚文化”更是在丰富、改换着中国的表情。那种压抑性的文化仍在,却不再有如许的威力,是你我都相信的。
理论上,宋元以降,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想必有妨于戏剧的发展,尤其喜剧。士大夫对严肃性的苛求,对戏谑的抑制,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内影响到戏剧(及其他形式)的演出,是专业研究的题目,要由剧目考察、对诸种演出形式的文献梳理,才能判断。我们都知道的是,戏谑的艺术在民间,从来如野水般泛滥,野火似的狂烧—笑话、谣谚、讽刺剧,以至闹剧。越草根越少禁忌,尤其涉“性”的禁忌。当着士大夫斟酌如何“笑”而不失优雅的时候,普通百姓或许正在剧场中、乡间舞台下狂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民众的娱乐精神、游戏态度,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古代中国的戏谑冲动,戏剧或许竟是最重要的载体,充满了奇思妙想。调侃、嘲谑往往及于尊者(包括圣君贤相)。上文提到“谲谏”;有这种能力与作为的,不乏伶人,即如优孟、优旃。古代中国对戏剧演出似乎有某种宽容度,即如容忍直接的社会批评(往往由“丑”担当),也像是一种“传统”。明代的时事剧就赖有此种条件。另有其他形式的嘲谑、讽刺,包括政治讽刺,即如王夫之所厌恶的歌谣讽刺。
不止于戏谑,更有“闹”,由“闹元宵”“闹花灯”“闹社火”到“闹洞房”。游戏态度只有在民间,也才有如此酣畅淋漓的表现。迎神赛会、佛教的盂兰盆节(道教的中元节),与民间信仰有关的其他活动,城镇节庆的临时性演出,到乡村的草台戏(如鲁迅所写《社戏》),这种狂欢一向有自发性、群众性、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舞台,被作为近代学科划分中“民俗学”的考察对象。至于古代中国民众狂欢的方式、场所、内容,包含其中的文化精神,与巴赫金论拉伯雷时所说欧洲的广场艺术有何异同,需要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超出了我的能力。
知识人也未必都不能与民同乐。明亡之际殉难的祁彪佳,其甲申年正月十三日的日记,记与人“共看村社迎神”(《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乙酉日历》三月二十五日,记“城中举社剧供东岳大帝,观者如狂,予举家亦去,惟予与诸友在山,薄暮,共酌于木香花下”。甲申、乙酉是何种“历史时刻”,祁彪佳和他的家人朋友仍然有如此兴致!
戏曲外,使一城一地“若狂”的,更有流行歌曲,如宋代流行的“挂枝儿”“打枣杆”之属。明代的开封,几于满城尽唱《锁南枝》。风靡的程度,似乎又胜过戏剧,其魔力令士大夫为之惊骇,且不知其所自。
士大夫的家班,士大夫、上流社会的堂会,与民间的演出活动(商业性与非商业性)同属娱乐,“娱乐精神”却有不同。民间演出未必有意与士大夫立异,只不过另有传统。分流而并行,未必即是对抗,更是满足不同人群不同的文化需求,也基于士大夫维持自身文化品质的自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尼采《悲剧的诞生》的译介,引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兴趣,“酒神精神”“日神精神”一时流行。古代中国文化的上述现象适用于何种概括,却仍然是一个问题。“大判断”固然会有遮蔽,总还是需要的。
“严肃”“戏谑”都是大题目,“民间娱乐”更是专业研究的对象,已积累了大量论述。本文涉嫌“大题小作”;且所用材料,偏于我较为熟悉的明清之际,所作判断或不足以概其余。我不过因其他题目考察所及,聊陈一得之见罢了。更进一步的讨论,已非本文所能,请读者诸君参阅有关专家的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