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司令(Radiohead)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为传奇的英国摇滚乐队之一,被认为从手法和风格上重新定义了摇滚乐。事实上,他们给听众带来的精神震动也常超越音乐的审美范畴,歌词往往写向人性和社会的深处。《烧死那个女巫》(Burn The Witch)出自电台司令最近一张专辑《月形池》(A Moon Shaped Pool),曾经荣获二○一六年格莱美最佳摇滚歌曲奖,内容尤为奥妙。
歌词延续创作者,也就是乐队主唱“桶木腰”(Thom Yorke)的一贯风格,像一首隐喻重重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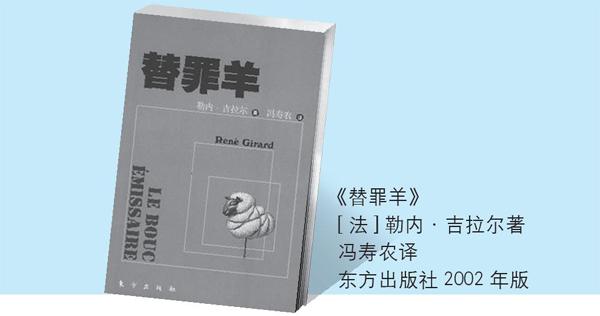
在阴影里
绞架边狂欢
这是一次围捕
这是低空飞行的恐慌症
唱一首点唱机上的歌
烧死那个女巫
烧死那个女巫
我们知道你住哪
门上画好红叉叉
如果你浮起你将被烧死
桌子前随便聊聊
丢掉所有理性就好
不要目光接触不要作任何反应
射杀信使
这是低空飞行的恐慌症
唱首六便士之歌
烧死那个女巫
烧死那个女巫
我们知道你住哪
我们知道你住哪
《烧死那个女巫》发行于二○一六年五月,但却是乐队从二○○○年就着手准备并持续埋梗埋了十多年的曲目。急促冲撞的弦乐营造出一种兴奋而诡秘的氛围,猎杀女巫前的人们“丢掉理性、回避目光、随便聊聊”,而掩盖在这些日常琐碎之下的,正是“平庸之恶”的惊悚与荒诞。“烧死那个女巫”这句唱词口号般循环四次,每一次都强调着女巫围捕行动的正当和壮烈,歌曲尾部弦乐戛然而止的一瞬间,死亡降临,一切凝固仿如寓言。
虽然乐队于二○○五年完成歌词时的具体初衷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歌词内容指向蔓延在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的大规模猎巫运动(Witch Hunting),这场臭名昭著的历史悲剧,使得当时的德国、法国、英国等地至少四万人因巫师的罪名被处死,据统计这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女性。而这些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并不如古老神话中所描述的妖艳并具有超凡力量,相反,她们是整个社会中最为边缘和底层的弱势群体,贫穷、衰老、未婚、独居是她们的主要特征。一个社区的任何灾难都有可能被归咎于这些不受欢迎的女性,妇女不孕、小孩生病、邻人突然死去乃至所在地区的饥荒或瘟疫。
看看当时的“猎巫指南”就会知道这场运动的荒谬和残酷。一四八六年由德国天主教裁判官克拉马(Heinrich Kramer)和司布伦格(Jacob Sprenger)所写的《女巫之槌》(The Malleus Maleficarum),不同于此前的同类著作,它的影响力得益于当时印刷技术的初步成熟,广泛的传播使其成为集神学与法学于一身的“畅销作品”,因此也被认为是欧洲大规模猎巫行动的历史开端。书中列举了女巫因受到魔鬼的蛊惑而在人间犯下的种种罪恶,包括杀死婴儿、取走男性的生殖器以及引发各种灾难等等。同时也详尽介绍了女巫的鉴定方法,主要包括火烧、水淹、称重、眼泪、针刺等。歌词中“如果你浮起你将被烧死”(if you float you burn)指的应该就是第二种,人们认为女巫的体重很轻,如果放入水中则会浮起。书中还介绍了如何审判和惩罚这些符合识别标准的女巫,对于大部分不能通过祓魔、驱逐等方式消除巫术的情况,直接以绞刑、火刑或者其他酷刑将女巫处死。而在民间,更是广泛流传了一些奇特的识别方法,比如一个女人,如果长了一块疣或疤痕,或者养了一只奇怪的宠物,又或者,只是多翻了一個白眼,都有可能招来怀疑。毫无疑问,指认女巫的过程因为这些标准的随意性,充斥着收买、嫁祸和模棱两可的悲剧和闹剧。不信任的气氛笼罩在社会上空,但事实上到了最后,几乎没有实在的证据能够证明死去的女人与鸡毛蒜皮的小事、蔓延的自然灾害之间究竟有什么直接关系。据记载,女巫们被绞死或火刑的现场总是挤满了看客,甚至会有摊贩借此做些生意,在女巫痛苦的尖叫声中,处刑现场则像一场热闹的庙会,刑罚完毕后,正像歌词中所描述的,人们就在“绞架边上狂欢”(cheer at the gallows)。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受害女性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根本原因可能仅仅是囿于中世纪落后的科技、医疗和法律,人们在客观上无法探明不幸的根源,蒙昧与慌乱中将不祥或灾难归咎于巫术似乎也说得通。然而,巫术也并非总是被视为邪恶的渊薮,按照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的说法,巫术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曾一度帮助人类克服对严酷自然的恐惧,客观上对人类的认知发展、对科学的兴起都起到过促进作用。因此,表面上宗教之于巫术的大决裂,并非诱发大规模猎巫行动的深层原因。需要追问的其实是,为什么悲剧发生在特定的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而且主要针对的是孤寡妇人?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大规模猎巫运动的发生既具有历史学意义上的特殊性,也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历史学的解释倾向于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角度,强调欧洲特定的历史困境、文化冲突对灾难的主导作用,而人类学往往要说明的是,猎巫行动基于一种人类社会的深层文化结构,古往今来可能重复发生。
从历史上讲,中世纪的欧洲正在遭遇一次经济危机和观念更迭。气候异常导致粮食减产,大范围的饥荒使得民众丧失理性和同情,而在精神层面,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新旧观念和制度的紧张冲突,则难以为生存焦虑提供宣泄的出口。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所说,两方面的问题最终造成特殊时期人们所处的道德困境。在那个时代以前,邻里间的帮扶救济是一种公共道德,在十六至十七世纪这种善行则被教区垄断。被控为巫女的多是向邻里求助过的孤贫老妇,村民不想伸出援手但又于心难安,当家中突然发生不幸,很容易将不幸视作没有获得帮助的老妇的“复仇”,因此将其指控为罪恶的女巫。普通民众的恐惧最开始还只是限于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的猜忌和怀疑,女巫之原罪的正当化是由神学家们完成的。这个时代的神学理论流行魔鬼附身行恶的想法,负责审判的神职人员不肯放过任何可疑的对象,与撒旦签订契约的女巫罪孽深重,必须被彻底消灭才能攘除灾祸,恢复宗教生活的纯净和神圣。因此可以看到,恐慌的加剧,与整个社会不同阶级、群体间的“共谋”分不开,这是一张从皇室、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从上到下布下的天罗地网。
女巫的罪恶是否能够得以证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巫作为替罪羊得以惩戒,社会恐慌才能纾解,灾祸也在想象中解除。当我们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把目光拉长,就会发现这种“替罪”机制似乎以神话的永恒结构不断循环。法国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替罪羊》(Le Bouc émissaire)在比较神话学范式的基础上,抽象出一种“替罪羊理论”的神话原型。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到美洲阿兹特克人神话,都存在一种迫害替罪羊的故事原型。猎巫行动在吉拉尔笔下是一场典型的“集体间接迫害”,即相对于在黑死病期间直接杀害犹太人的暴行。围剿女巫则是通过间接的群情激昂的舆论鼓动起来,且在形式上合法。任何文化的深层结构当中都存在一类“迫害文本”,这类文本可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的:存在一场出于“模仿欲望”而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一个被归咎为要对危机负责的“替罪羊”被施以集体的暴行,通过消灭或者驱逐“替罪羊”来解除危机,有时还可能存在牺牲被神圣化的情况。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替罪羊”的挑选并非坐实的罪行,而是被指控者“异常”的标记。这使得某些偏离社会“平均数”的边缘性群体成为各种“恶势力”的负面汇集地,老弱病残是典型的“替罪羊”。每个人类社会重复这种神话结构,大多数人将少数异类想象为危险之源,最终通过集体性的激情指控、欠缺因果论证的暴力惩戒,异类作为宣泄危机的替罪羊而牺牲。
人类学的解释使我们超越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来看待问题,也更进一步提醒人们,针对某一边缘性群体所酿成的社会性大恐慌,可能是深藏在人类文化秩序中的隐形炸药,而不只是西方文明的病征,也并不只是发生在物质经济状况不佳的历史时期。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就讲了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乾隆年间的真实故事。一七六八年从江南蔓延开来的妖术恐慌,最开始只是起因于寺庙为了争香火而散布的谣言,不过人们逐渐相信,的确存在一种可怕的“叫魂”妖术,能够通过剪辫、将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放在桩子下击打入地等方式,使得被害者的魂魄与人身相分离并被叫魂者利用,丢了魂的人(常常是男童)将得病或死去。妖党疑犯的控告也是指向社会边缘性群体—流浪者,“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來历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最有可能沦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罚受害者的,是乞丐和没有度牒的和尚。
为什么在乾隆这样的盛世之中,穷弱的“流浪者”也会成为众矢之的?书中也回答了这个问题。盛世的效果是人口兴旺所带来的,而在这层镀金的表象之下,人口压力也造成竞争加剧、粮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这样的生存局面制造的群体,不仅是需要动用一家老小的力量才能勉强不被淘汰的普通人,还有越来越多被排除在竞争之外的流民。“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其实,把僧人与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乾隆的恐慌出于对汉化、谋反和政局不稳的忧患,但这种恐慌的源头毕竟在民间。从普通的民众的角度上说,生活中本来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狭小的生存空间加剧了他们对自身安危的敏感,而最底层的乞丐或乞僧,则是他们唯一能够通过施以一种报复性权力来宣泄生存焦虑的对象。众暴寡、强凌弱,这些被作为异类的乞丐游僧成了替罪羔羊。当然,如同猎巫运动一样,到头来没有一起叫魂案得以坐实。
《烧死那个女巫》之所以震撼人心,正是因为它通过摇滚乐这种直接而剧烈的方式,将我们引向对于历史与当下的深刻反省。这首歌的MV也是关于一个烧死“异类”的故事。MV采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定格动画《特朗普顿小镇》(Trumpton)的风格,人物是圆头圆脑的小泥人造型,色彩丰富而鲜艳,乍一看非常童真,但其演绎的故事则复制和致敬了一九七三年的恐怖片《柳条人》(The Wicker Man)。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去苏格兰某岛调查一起失踪案的外地警察,如何一步步从猎人变成猎物,走进当地人的圈套,最终被作为异教徒装进巨大的柳条人中烧死并献祭的故事。
这些悲剧的酿成,大概只能说是古今中外,人们对于生活中的异类常常难以友善。这些各种各样的异类,无论是外来的异教徒、流浪的乞丐还是孤身的女人,实际上不过是游离在一个社区原生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些人。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薮,实际上是被那些所谓的大多数“正常人”献祭给了自己的想象。
然而,最可怕的除了这种对于伤害无辜者的冷漠和旁观,还在于一个社会关于异类的划分常常是相对和流动的,随着个人生命的展开、历史经济状况的变动,每个人都有可能无法避免一不小心被划为异类,而不得不面对其余大多数人“正义”的围捕。
参考文献:
1. Keith Thomas,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enguin UK,2003;
2. [法]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4. 徐善伟《15-18世纪初欧洲女性被迫害的现实及其理论根源》,《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