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之前, 美国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曾略带夸张地形容当时古典音乐有一群“标准听众”,与普通下层人民的模样格格不入(“有逻辑性的语言是法语,其命运是在世袭君王的统治下,遵照教义生活”), 讽刺之意溢于言表。时至今日,人们也许已经对这样戴着有色眼镜的定论不屑一顾,但如果进一步细究,巴尔赞的“引子”还是很有必要的。请先听两种设问:
可否将如“在奏鸣曲式乐章中将半音和声融入了整体的自然音和声语境”之类的方法归于某位特定作曲家心智内部的某种原型结构?如果是的话,海顿或莫扎特的心智原型又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艺术的可理解性是否等同于它的规范性理想?甚至进一步设问:追求理解性就是艺术的正当目标?
还真挺不容易作答。
无论结构多么强烈地显示出,其自身是有意义的—可能具有自律意义或隐性意义—我们都必须假设该模式与支撑它的某种特定的主题观念(关于对结构的需要)之间存在某种类比。唯有通过我们自身的特定心智结构的中介,我们才能够“知晓”这一观念。
这是学者苏博特尼克给出的解释,不免有些唯心色彩。不过,在这般较深邃的议题上,解答是否唯一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爱思考的你究竟会在如此拗口却有趣的头脑风暴中体验到了几许?《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正是以类似的鞭辟入里的音乐—哲学二重问题,引导我们更加接近“音乐”之本身。
自马克斯·韦伯等人以来,音乐素来吸引着不少社会学者的注意,从古典社会学的现代性课题,到受英国文化背景深刻熏陶的流行与摇滚乐,不断引发着人文、社会学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学界大多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试图在种种努力下使边界逐步消融。在今天的高校里,如若开设一门类似“摇滚音乐和社会学关系”的课程,不说司空见惯,也远不似当年那样新鲜。但也应当承认,从本雅明、阿多诺到列维-斯特劳斯与阿甘本,能周游音乐的哲学家(也未必每篇都好,就算是阿多诺)基本上都有着极强的思维能力,也始终是少数人。其余一些哲学家在闲暇里专门开篇议论音乐时,常会显得力不从心。他们用娴熟的方法论与分类模式来拆解作品的意义,固然如庖丁解牛,但读来总觉别扭;反过来说,换成音乐理论家来讲哲学,张口结舌不也是正常的吗?
于是我们看到,音乐—哲学的经典评论著作门槛甚高,毕竟犹需第一流的大家来完成。《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这册小书的内容,缘自几位大学者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座。导论由编者普莱斯撰写,《影响:剽窃抄袭与灵感启示》著者是罗森,《学术性音乐批评的现状》著者是约瑟夫·科尔曼,这两位都曾是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巨擘;《理解音乐》著者是艺术哲学家比尔兹利;符号学意味浓重的《作为后康德批判的浪漫主义音乐》,著者是将阿多诺学说引入美国学界的女学者苏博特尼克;《音乐批评:践行与渎职》著者是分析哲学家阿申布莱纳。整体观察,全书像是依照着话题类型区分的格式排布,五人可谓各展用武之途。
 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1927-2014)
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1927-2014)《作为后康德批判的浪漫主义音乐》是我阅读的第一篇。文中关于“符号”意义的探讨,从符号交流在人类社会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等等开始“发难”,进一步扩展到古典音乐界,问题就成了:难道古典音乐只是在向受过教育的听众展现出一个符号自律体的规范吗?苏博特尼克的回答很是坚决:“古典音乐结构实际上仅在数量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看来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西方社会也是如此……句法结构联系或附着于这些联系的意义都无法被视为具有自身的内在必然性。无论在最狭窄的技术分析层面,还是在最宽泛的哲学诠释层面。”
假如说苏博特尼克这里的论调有些绝对化,那么就思辨的过程而言,最后一篇才是笔者最钟爱的。《音乐批评:践行与渎职》里,阿申布莱纳的笔法犹如手术刀,丝缕不漏,他不单剖解了“好”这样一个最基本同时也最模糊笼统的概念,还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我们在“指责”或“赞赏”时,到底具备了哪些不易留意的特质,甚至独具慧眼地对批评这件事本身,作出了合理合度的评判:
……批评家必须行使评价的权利,行使表达崇敬或批判的权利,而他们在行使这一权利时所显示出的犹疑和胆怯,恰恰构成了我所说的当下的危机的组成部分。
用一位参会作曲家的话说,“必须从对作曲过程的了解的角度来进行批评”,这似乎毋庸赘言;但实际上必须格外强调这一点,因为具备这种能力的批评家少之又少。音乐批评家的典范是罗伯特·舒曼。读过舒曼对同时代作曲家的评论的外行人不得不被深深触动—若非感到敬畏—因为他们很快便意识到舒曼这位作曲家在他所评论的音乐中听到了什么。
我想这样的表述不应该被理解为刻薄的批评,而更应让人钦佩起阿申布莱纳对客观事实的惊人洞察力才是。
阿申布莱希的身份本就是跨界的,哲学是本行,但是也长期在伯克利从事艺术美学与哲学的研究。他的文章中,准确地捕捉到了“器乐作品最新最奇异的音乐形式未能或忽略了这种艺术的成功必然来自两种终极根源中的任何一种”,那其实也是它的依凭所在:“在最小的结构要素中对听觉产生吸引力、感染力或满足感”主要来自音程;“听觉能够分辨出的这些音程,乐音之间的关联、张力和倾向性,包括大范围的和小尺度的”。于是阿申布莱希顺水推舟:如果作品的最小要素不同于传统的音高和音程,而是源于各种噪音发声器,那创作便具有格外的难度,其要素之间的关联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但这些关系又必须明示给听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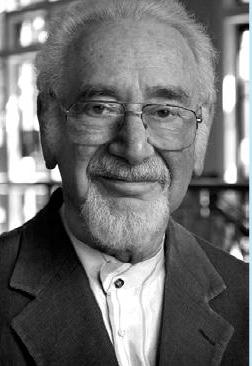 約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1924-2014)
約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1924-2014)精彩而又言简意赅!在他看来,现代音乐的处境难免曲高和寡,因为当听众无法在作品的基本要素中获得满足感,亦难以把握要素之间的联系时,“传统技法所写的音乐中,如果乐音之间的联系模糊不清或不着边际,音乐还是可以依赖其内在的吸引力”。
相比阿申布莱纳与苏博特尼克,由查尔斯·罗森贡献的第三篇,结构相对单薄,虽然看得出他在尽力面面俱到。例如,从“理解音乐”的字面出发,追根溯源地讨论究竟什么样才算是“理解”一样东西?而后,又剖析 “悲伤”这样的对人类情感限定的词汇到底是如何在艺术作品中起作用的。
我想,倘若这样设问:“音乐能不能像其他事物一样被理解?”先不谈苏博特尼克与罗森二人的对错,而是从两种相异的理解途径上进入同一个问题。
苏博特尼克的笔锋犀利,最能体现在他拿浪漫音乐开刀的段落:“它的弱点之一像是在默认它的结构似乎允诺能够自行解释”,他继续解释说,浪漫主义内涵着一种自律性,它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古典主义里那种老的自律性,即被理想化的准逻辑式的符号自律性,是一种更为具体可见但在符号意义上并不完整的自律性。它通过重构另一种符号世界来弥补古典符号世界的丧失。你若要理解其内在机理及其高度复杂的和声要素,针对浪漫主义音乐实践的专门训练必不可少。最终结论是,聆听音乐的领会能力,完全不同于逻辑(或自然语言)中所要求的能力。
而罗森的表述,则更为温润和耐人寻味一些。他说,有人觉得审美标准和价值考量在音乐分析中没有立足之地,但“具有独创精神的分析大师们当然明确无疑地显示出,分析对于他们而言是一套清晰表述、充分阐释的审美价值体系的必要附属”。他随即拿出了申克尔、托维,以及擅长分析的学者福尔特(Allen Forte)的《作曲矩阵》为例。在他看来,末者的理论细致地剔除了一切情感性词汇和评价性语言,正如(康德理论里)逻辑的统一性能够涵盖多样的感官材料(sensory data)。谈到深处,罗森依旧支持这样的论调:“古典音乐结构在其自身结构的独特性内部暗示调性关系的整个等级结构,由此似乎也可以在其自身的理性框架之内涵盖整个世界的多样性。”这一句上,看得出他还是不怎么坚决。苏博特尼克的文章里,就很尖锐地引用了罗森曾经的观点:“……因此一首大调性的古典乐章中主调向属调的运动之所以不可避免,仅是因为该种调性运动对于处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的听众来说‘是可理解性的必要条件。”
 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C. Beardsley,1915-1985)
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C. Beardsley,1915-1985)读到这儿,你应该也能猜出个端倪。终极意义上的疑问与分歧还是发生在音乐到底能在几许深度、多大的广度上与哲学分析对世界的解释相抗衡?抑或只是少数人的螳臂当车?
这些蔓生的“思想枝桠”,大概能算是音乐爱好者们最初没能料到,也不太愿意直面的思想副产品。然而这么一来,便也能很好地去解释,为何不论是国内还是西方的争鸣都长期盘旋于:古典音乐在某种层次上将自身投射为“每个人”的艺术,岂非是太主观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真实感官总有点倾向于聆听者在时间的展开推进时,会假想“自己创造着这种艺术”。既然时间的独占性代表着非此即彼,那么难免会有严格的、自我化的排他标准逐步被锻造出来。所以从根本上说,每一个听者都不太能接受垄断性音乐观点的传播和移植,更不用说是强加了。通俗一些说:不爱听就不听吧,大小不就是个音乐吗?
但哲学不同。若要了解问题的关键,必然先需晓得哲学为何经常被认为“沉重”。它没法不承担更多—将可见、可触、可觉知的日常生活包囊进去,大量涉及无意识和潜意识的部分是它的任务,尽力把现实与意识二者勾连起来,且能自圆其说,也是它的任务。如此艰巨的工程使得哲学理论内部的分化演化得异常细密,可是方便于旁通贯达的音乐理论却没有太大的负担和压力。
哲学家们会说自己任务和负担无疑更重,以及你们音乐家们的理论纵然枯燥,毕竟能在第一时间内滤去了日常真实生活的困难和嘈杂—概念和技法的嘈杂顶多也就那样了,不是吗?音乐的天然属性毕竟轻飘,它有时是与梦和集体意识相连的,有时则是超验的、潜意识的、神秘主义的、朦胧学的,乃至接近出窍的……就算是作者阿申布莱希的话属实:“在舒曼那个时代的情况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当时的音乐语汇不像当下这样持续不断地变化,甚至十二音技法都不能作为现代音乐的标准”,但那又怎么能与哲学家们“思想骆驼”样的重负相比?
诚然不错。可犹需观察到,哲学家们的论断很容易便基于一个远离事实的假设:人们应当按照一定的规则性(起码是大部分时间里的“理性”)行事,如果不这么假设,基于逻辑的议论便无法为续—请看哪怕是福柯关于癫狂的理论,也有较严格的逻辑牵连作为保证。然而音乐理论家们,自知所建立的基石多少倾向于奇妙的情感元素,从最科学化与基本的音程关系和乐音噪音的分辨开始,就已不再是步步为营的数学与哲学,而是一种更易留下回旋、妥协与进一步探索余地的“情感数学”。此中情形,有些类似于很好的经济学家到毫无经济秩序可言的地方,一开始也会手足无措。
话说回来,针对音乐与哲学二者的探讨还是有着一个最大相似点的—它们的核心精神,都是在借助语言工具,尽可能地深挖客观事实里那些不太能够使人一眼看出的“潜流”部分。这种勾连的工作,如果不论完善程度而只谈论灵感高低的话,常喜欢给文章起名“几”个命题的巴迪欧,在他那篇《音乐事件的十三个命题》里完成得最为有趣,也最像结构主义的范本。巴迪欧将音乐历史的既有发展规则“牵引”了过来,多少有去“就”那姿态高高的哲学的意味—倒也不询问一声音乐家们乐意与否。有时还别说,对音乐发展的“崇高性”本身长期持怀疑与批判态度的圈外人,绕开表面而捕捉它的远关系点的做法,反而更易触及本质。
在出版界,人人都心知肚明一个尴尬的事实:如同严肃类中西哲学书籍的阅读量常年徘徊于谷底,音乐理论书籍,也是书架上罕有人问津的劳什子。就算是音乐行业相关者,也很难一下子成为阅读受众。眼下的急切方法,公认的是有赖于那少數几册敢于打破疆界同时不乏预见力的小书,它们在心旷神怡的文笔素养之上建立起了以高就低的亲和力。哲学领域,列维-斯特劳斯和阿甘本的好文笔都曾让我无比钦佩,虽然海德格尔的语言也很美,思维的门槛却很不低。音乐理论范畴,让人心悦诚服的例子更是难得一见,须知很多时候,关于“状态”的描述要比基于“逻辑”的描述更加依赖于特定条件,不稳定的内在分解倾向也愈强烈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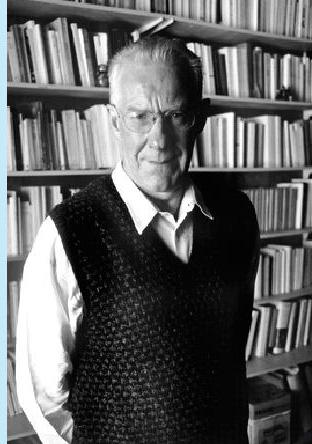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如此想来,“音乐(到底是不是)始于词尽之处”的老生常谈,其实倒暗含着一个事实:对于音乐的讨论浮现时,“词语”往往宁可选择潜藏或回避的姿态,换言之,就算词语成为假借来的工具,也会是“言辞概念”被很大程度遮蔽与压抑的时期。老实说,不单单是听者,历来每一位学者想要挣破此一层都极为困难。而哲学家谈音乐与音乐家谈哲学二者之间的沟壑,仿佛无论到了何时都难以填平,最多只是难兄难弟,遥相招呼。从另一方面,那也正是我喜欢阅读音乐理论书籍的另一缘由,而不只是因为于音乐学者们的论点委婉多姿,千人千面。这册《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问世较早,有着无可替代的先驱价值,至今总算迎来了它姗姗来迟的中译本。
就让我们来观瞻一下这群些各执一词的业界大咖们,如何将人们于百十年间积攒下来的声音智慧在一套自给自足的思维架构内轻松自在地把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