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飓风,带来了一天一夜的强降雨。
院子又涨水了,积水半米高,漂浮着树枝、落叶,漂浮着司空见惯的垃圾。
我走进水中,抢救溺水的小毛鸡,它们的母亲正在哀嚎。
忙碌时,又见漂来一样东西,褐色、圆形、立体,像是一团草,在水面一起一伏。
“草团”到了我跟前,我看清了,不是什么草团,是蚂蚁们的身体。
难以计数的蚂蚁,嘴咬在一起,脚勾在一起,腰缠在一起,凝成了一团,宛如一条“浮船”。“浮船”结构紧密,但并非静止,蚂蚁们在流动,就像流动的水,上面的往下流,替换底下的伙伴;底下的往上流,喘口气后再往下,换出另一批伙伴……
蚂蚁们频频换岗,互相支撑,稳住了“浮船”,乘客们安然无恙。
乘客是谁呢?是蚂蚁蛋,也许还有蚁王。
密密匝匝的蛋宝宝,平躺在“甲板”上,躺得舒舒服服,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
蛋宝宝白花花、胖乎乎、亮晶晶,漂亮得像雪天的雪子。
洪水中,蚂蚁们还在奋斗,分成几路纵队,用力游泳,口衔蚂蚁蛋。登上“浮船”后,它们不再离开,成为“浮船”的一部分,顺水漂移。
成千上万只蚂蚁,用肉身拼成爱的方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孩子。
我抬头看去,洪水中,“蚂蚁船”比比皆是,它们承载着蚂蚁蛋,左满舵,右满舵,越过激流,躲过障碍物,遇到土坡就抛锚泊船,众蚂蚁肩扛手提,转移蚂蚁蛋……
这样的场面,若非亲眼所见,我哪里想象得出来!
那么,小小蚂蚁,怎么懂得利用浮力对抗洪水?
它们又是如何设计、规划、指挥、合作,完成一次气贯长虹的救生行动?
雨还在下,水继续上涨,水面又漂来一些东西,它们褐色、圆形、立体,像一团团草叶。
是的,我已知道那是什么。
我家居于乡下,大黄蜂无处不在。
大黄蜂的巢穴出现在树梢、房顶、屋檐下。
蜂巢们高高挂起,像高高挂起的小灯笼,仰望它们,就像仰望星辰。
蜂巢的材料,大多是碎木屑,建筑并不豪华,轻轻薄薄,像一朵朴素的小纸花。
蜂巢由重兵把守,卫兵们贴着蜂巢站岗,或绕着蜂巢飞行,飞行时翅膀平放、细脚垂下、臀部翘起,嗡嗡地吹着警笛。
对于黄蜂、黄蜂巢,我哪敢打扰,只能低眉顺眼,敬而远之。
所以,我从没看清过大黄蜂,也没看清过蜂巢的内装修。
有一天,机会来了,屋檐下的蜂巢冷冷清清,没见一个卫兵。我搭好了梯子,悄悄上去,想看一眼巢穴,看一眼就撤。哪里想到,人还没挨近,有黄蜂杀将过来,我滚下了梯子。
老骨头没摔断,脑门上留了几个大包包。
我以为无人监视,其实我在监视之中,大黄蜂看着我。想到《1984》的名言:“老大哥看着你!”从此不敢胡乱窥探,连窥视心也不敢有,老大哥看着你啊!
直到有一天,这样的格局打破了。
那天,飞来一只大黄蜂,贴着玻璃窗溜达。玻璃窗对着餐桌,我正在用早餐。
大黄蜂走着转着,抖着小脚丫,仿佛进行着某种测量,然后若有所思地飞走了。
大黄蜂第二次飞来,衔来了一嘴木屑,拌着口水,涂在了玻璃上,开始筑巢了。
大黄蜂的筑巢过程,就像我们女人织毛线,起针、编织、织出长度、织出花形、收针……
几天后,玻璃上出现一朵小纸花,花脸朝下,花瓣卷起,有四五个花洞,这就是巢穴。
几天后,大黄蜂往巢穴放蛋,放完蛋继续搞基建,扩大婴儿房的数量。
又过了些日子,第一批蜂宝宝问世,是些肥胖的小虫子,倒挂在蜂巢上,我着实担心,怕虫子们掉下地,摔个鼻青脸肿,岂不惨也。
当然,这样的事没有发生。
原来,蜂虫的尾部有挂钩,挂住了巢穴,就像衣服挂住了衣架,万无一失。
这一枚钩子,是黄蜂妈妈送给孩子的第一件礼物。
又过些日子,巢穴封口了,虫子被封在了里边,像被封住的秘密档。
这时的蜂巢,不再像一朵小白花,倒像是结了果子的小莲蓬。
这时的黄蜂妈妈,不再被婴儿事务牵绊,又开始织巢,她想有更多的孩子。
有一天,小黄蜂破茧而出,穿着醒目的黄背心。这件黄背心,是妈妈送孩子的第二件礼物。
看见这件黄背心,人们小心走路,或绕道而行,谁也不想出个“交通事故”。
据说交警的黄背心,路工的黄衣服,公路的黄线条,以及种种黄色警示,创意来自黄蜂。
另外,小黄蜂的屁股携带毒针,这是妈妈送的第三件礼物。
几个月过去了,玻璃上的蜂巢越变越大,沉沉甸甸,像身子笨重的向日葵。
我盯着蜂巢看,天天看,仿佛在看美剧,一集也不肯落下。
我终于看清了蜂巢,看清了黄蜂的日常。黄蜂的日常,与人类一模一样,做工、养儿女、吃三餐、享受天伦。
不同的是,人的尾部无针,不会飞,不会织巢,这些事上,人得拜黄蜂为师。
当然,这不是故事的结尾。
有一天,暴风雨来了,蜂巢在玻璃上摇曳、颤抖,像一片可怜的树叶。大黄蜂全部归营了,它们扑在蜂巢上,护住了蜂宝宝,再没离开,像被胶水黏住一样。
忽然,又一阵狂风吹来,吹得窗子“哐哐”响,“忽”一下吹走了蜂巢。
我的蜂巢消失了,消失在风雨中。玻璃空了,只有眼泪一般的雨水。
当然,这也不是故事的结尾。
暴风雨过后,我出去找,找了许久,找到了那枚蜂巢,它掉在了水沟里。
我凑近去看,看到惊心一幕:蜂巢底部黏满了黄蜂,它们泡在水里、托着蜂巢,全死了。
大黄蜂托起蜂巢的样子,让我想到洪水中托起蚂蚁蛋的蚂蚁们。
我知道,蚂蚁、黄蜂不会死在水中,除非它们愿意去死,为了某个理由。
这些从容赴死的大黄蜂,理由一定是强大的、不容阻挡的。
但我想不明白,风雨那么大,吹倒了树木,吹破了房顶,怎么没把大黄蜂吹散呢?
或许是吹散了,大黄蜂又找到了自己的蜂巢?它们记得蜂巢的模样?它们闻到了蜂宝宝的气味?
平生第一次,我抚摸了大黄蜂,轻轻地,手尖划过那件黄背心。
我捧起那枚蜂巢,挂到了橡树上,用铁丝好好固定,加了一层网,谁也伤害不了。
几周过去了,有一天,蜂巢空了,破茧而出的小黄蜂,飞走了。
它们会像妈妈那样,找一个好地方,衔一嘴木屑,打一个地基,织一个巢穴,形状像朵小纸花。
这才是故事的结尾。
麻雀在花盆做窝,保密工作极好,我去浇水时,鸟妈妈从叶间飞出,我才看到了鸟窝。
鸟窝里有四枚蛋,椭圆形、银白色、有好看的雀斑。
过了些日子,我过去偷看,看见了一堆没毛的孩子,它们向我讨吃,一起张开嘴巴。
它们是世界上嘴巴最大的婴儿。
有一天,我又去浇水,撞见了我家的老猫,它蹲在花盆前,盯着鸟窝,目不转睛。我大叫一声,想阻止一场杀戮,但为时已晚,老猫跳起来了。
小鸟的命运似乎已成定局。
但是,就在这个瞬间,鸟妈妈扭转了乾坤。
鸟妈妈冲出了鸟巢,重重跌倒在地,翅膀扑腾着,站不起来,似乎伤得很重。
猫立刻转身,扑上去逮鸟,却没逮到,鸟挣扎着跳开了。猫紧追不舍,那鸟斜着翅膀,一瘸一拐,向着密林逃跑,不见了踪影。
猫没捉到鸟妈妈,也忘了鸟宝宝,管自己找地方睡觉去了。
没过多久,鸟妈妈飞回,叼着绿色的虫子,潜入草窝,哄孩子去了。
我看呆了。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女邻居家。
女邻居家有火鸡,我家有土鸡,她来我家看鸡,我去她家看火鸡,结下了友谊。
有一天,女邻居告诉我,九岁的老火鸡抱窝了,肚皮下有八只蛋,二十六天后就会有小火鸡了。
我向她提出要求,送我一只小火鸡,我想养火鸡。女邻居一口答应。
二十六天后,我跑去抱小火鸡,女邻居却说,还没呢,再等几天。
几天后,我又去抱小火鸡,女邻居说,还没呢,再等几天。
结果,我足足等了两个多月,老火鸡还没弄出小崽子,肚皮下面无声无息。我们明白了,老火鸡老了,不中用了,它的蛋并没有受精,是废蛋。
但老火鸡不同意我们的判断,它继续留在产房,守着废蛋,像守着珍珠宝贝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八只火鸡蛋发臭了,气体膨胀,一只只炸开,臭气几米外都能闻着。
某一天,女邻居取走剩下的火鸡蛋,为了让老火鸡幡然醒悟,结束做妈妈的梦想。
老火鸡却不为所动,继续蹲在产房,仿佛肚皮下面还有蛋似的。
老火鸡为了得到宝宝,废寝忘食,瘦成了皮包骨,这样下去可怎么好。
我灵机一动,从家里抱来一只小毛鸡,放到老火鸡肚皮下,希望它带着孩子离开产房。
这一计不灵,老火鸡没离开,也没赶走小毛鸡。小鸡钻到它的翅膀下,认了干妈。
小毛鸡对老干妈很亲,但老火鸡心里清楚,娃是别家的,它想要自己的娃。
有一天,我与女邻居合力,把老火鸡拖出产房,拖到草地上,强迫它吃草、运动。老火鸡哪里肯依,发起疯来,见狗追狗,见树撞树,弄出一身血,又跑回了产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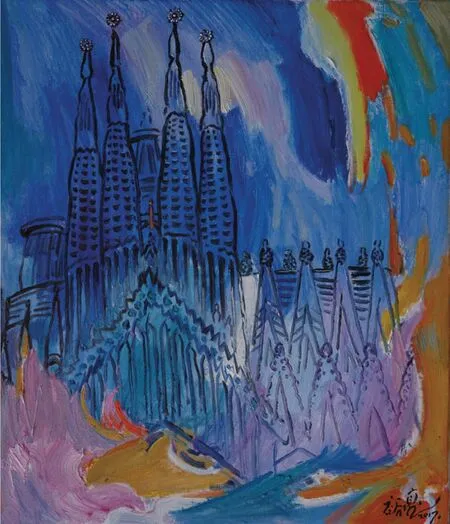
王裕亮 印象圣家堂
我们觉得对不起老火鸡,老火鸡没有错,它只是想要孩子、想做妈妈,如此而已。
结果,女邻居上网,买了三只受孕的火鸡蛋,郑重其事地交给了老火鸡。
老火鸡喜出望外,用嘴给蛋宝宝翻身,“咕咕咕”与蛋宝宝说话,脸色好了,脾气也好了。
二十六天后,三只火鸡蛋破壳,小孩子滚了出来,像三枚黄色的毛线球。
老火鸡努力了三个月零二十六天,终于当上了妈妈!
老火鸡如愿以偿,带着孩子离开了产房,就像童话里写的,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看着老火鸡,我不禁想,如果没给它三个蛋,它是不是还蹲在产房?再蹲三个月、六个月,蹲到死为止呢?
爱的故事是美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世上有千千万万不可思议的故事,爱的故事是最不可思议的。
(摘自《香港文学》202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