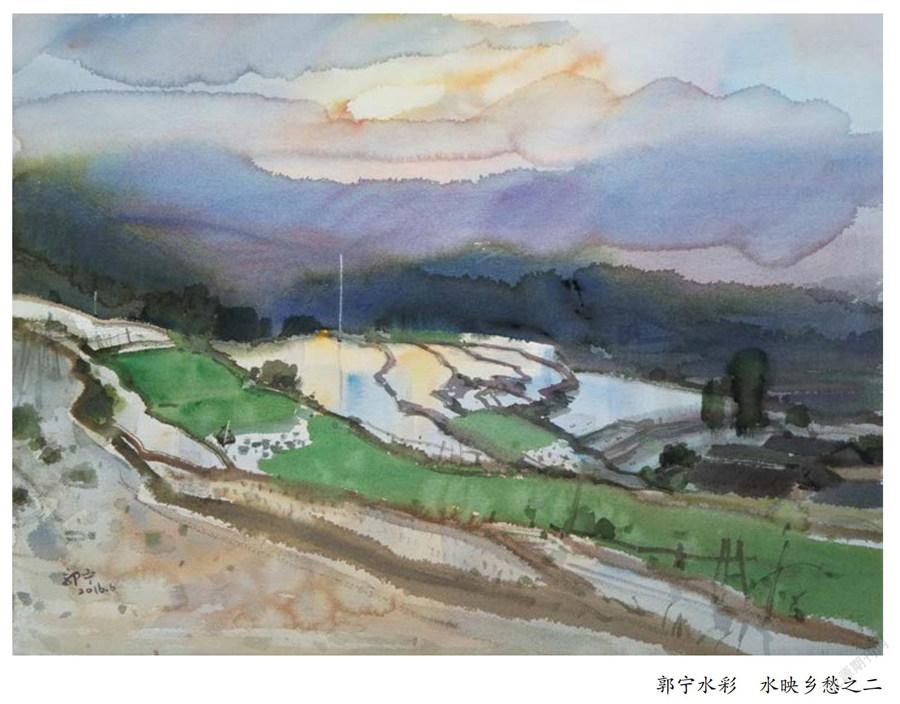
朱西甯(1926-1998),中国台湾小说家,祖籍山东临朐,1949年赴台,曾任《新文艺》月刊主编。
天大约只有二更,村子早就沉进静静的黑梦。留下树梢上冷丝丝的风啸,和一两声闲散的狺狺犬吠。
村儿里,牛车路两旁夹着高大的树木,还不曾放芽,苍黑的密枝,遮去了天上微弱的星光。
牛车路的尽头,亮起摇摇曳曳的一盏红灯笼,左摆着,右荡着,看起来像是一只独眼的甚么妖精,打树行里向这边耸耸蠕动。从那里飘来妇人凄凄凉凉夜号似的叫魂:
“小龙嗳——快点回来罢!”那样的困倦、颤索,也像那盏红灯笼一样地在黑里栗栗发抖。
“回——来——喽!”另一个小姑娘家幽幽惚惚地应着。
“小龙嗳——快跟娘回家罢!”
“回——来——喽!”
……
这么样一唤一应地重复着,没有比这样更惶惶的夜。
红灯笼缓缓地游动,灯光里现出一双腿脚,扭呀,扭呀,扎腿的棉裤筒儿扭出些暗红的折绉。糊在灯笼上的红油纸有几处小小的破洞,裤筒上落印出一些斑点,自顾自地闪烁着,老跟棉裤上扭出的折绉合不拢,隔着一层甚么。这一双腿的后面,一把竹扫帚拖在地上,上面平放一件红色的小衣裳。
“小龙——快点回来罢!”
“回——来——啦!”
跟在竹扫帚后头挑着灯笼的小闺女,带着很浓的睡意应和着。灯笼顶端的圆口里,漏出一团黄黄的烛光,时不时照出这个女孩平平板板的一张脸,老被鼻子投射上去的阴影遮住的那双眼睛,直定定瞅着竹扫帚上的小衣裳,好像不敢放过,要看清楚那个走失的小魂灵怎样被唤回来,怎样一下子跳到竹扫帚上,就像平时把他放在扫帚上拖着玩一样地拖回家去。
小闺女似乎看到了甚么,眼睛突地发亮:对面路中央的老树底下,黑糊糊站着一个人,又肥又大的影子。灯笼晃着眼睛,看不十分清楚,她把灯笼挑高一些,想从灯笼底下看暗处是个甚么人。
那个人老远搭上话来:“又怎么啦,小龙这孩子?”
低着头走在前面的妇人好似吃了一惊,“谁呀?”
“又作怪了不是,小龙这孩子?”
“我道谁呢,谷雨哥吗?”
“午间到你家逗谷子去,还玩得挺好呢。”
妇人撩一撩包头,叹口气:“谁说不是呢?又发大热了,晚上饭也没吃。还不又是老死鬼回来疼孙子,也不知带往哪儿耍去了!”
“别信道婆那一套,规规矩矩还是请谁……请伏二先生家来瞧瞧,开服方子吃是正经。”
灯笼照出一个穿着臃肿的大汉,手里拄着一杆红缨枪。这位谷雨哥是村上的更夫,大约是“谷雨”那天生的,起了这个名字。谷雨打更不带大锣,也不带梆子,拖着一杆红缨枪,不声不响地躲在黑地里到处串,村儿上有他打更,敞着门睡觉都成。
“骆大嫂,正经的,你还是送给伏二先生看看。”谷雨规劝说。拄着九尺来高,缀着红麻缨子长枪,枪头磨得亮闪闪。妇人叹着气,仿佛一点也拿不出主意。
“不该我说,骆大嫂,小龙生得不怎么泼实,跟他爹那个体质一样,你就别太娇养;当条小狗喂着就行了。”
“唉!能像你跟前那几个哥哥姐姐,倒省多少神!”
“我就是当作小叭儿狗一样养。”这个更夫掮起红缨枪,缓缓走向那边的横路去,走上两步又转回头。
“叫一会儿,还是早点回去罢!”谷雨又站住说,“小龙他爹不在家,门户留神点总好。这两天,你知不道吗?南村儿一连几家都挨偷了谷子。”
“说的是呀,这两天风声不大好。”这妇人有个高挑身材,说话却像小姑娘一样嫩。
“有甚么事儿用得着我,尽管说。赶明儿清早,小龙要还不见利落,你就找大丫头来跟我说,我给你备个牲口,去請伏二先生。”
“怎好劳累你,打更守夜,通宵不合眼!”
“真是,你说这话!老大不是不在家吗?”
妇人叹口气,拖着竹扫帚要走不走的,“你说,谷雨哥,他爹回得来吗?”
更夫拄着红缨枪走回来,责怪地瞪着这妇人,“大正月里,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大军粮仔拉夫子不是常事儿?送出县境总要回头的。”
这位骆大嫂让谷雨瞪得手脚没地方安放,耷拉着眼皮,回头看了看闺女。
“怕就怕呀,他那个身子荏弱,天寒地冻的,身上就只顶着件小袄头儿。”
“也没甚么,好在车子上推的也不是甚么重东西。至迟三两天,差不多也就到家了。”
黑里看不见人,谷雨走了几步,在那边横路上叹着气:“早点回家罢!家里没人。”
这母女俩望着暗处,愣了半晌,又照旧恢复那阴惨惨的叫魂:
“小龙嗳——快点回来罢!”
“回——来——喽!”
凉飕飕的黑风,正月里这天气不算最冷。红灯笼摇曳着,沉睡的村子里似乎只有这声声叫魂无告地颤抖着,寻找那样容易走掉的魂灵,似已飘去更远的远方,慢慢在幽黑里沉落,隐没。
在幽黑冷清的牛车路上,这位忠心的更夫袖着手,把红缨枪夹在胁窝里,缩紧了身子,脚底下拖一双羊毛窝。
夜愈深,寒气愈重。在那些温暖熟睡的家屋里,或有一两声老年人的咳嗽,婴孩的啼哭,听来不知有多气闷,有多遥远。除掉这些,就只有他轻轻的脚步声,沙啦,沙啦……只有这个陪伴他,从长夜走到天明。
这个村子只有四十多户人家,两条交叉的牛车路把村子分作四大块。村子中央的交叉口有棵古槐,树底下有块不知来历的大红石。更夫走乏了,便蹲到大红石上歇歇脚。蹲在这上头,守着一天迟一天升起的月亮,守着北斗星的尾巴从西旋到东,天河从东旋到西。在众人沉睡的时辰,清醒的更夫该是人间最寂寞、最孤独的人。
谷雨是个老更夫,尽管年岁只才三十出头。
过去有两年,谷雨出外吃粮当兵,一直都由黎三打更。那两年里,村上没有安静过。去年收高粱的时节,谷雨胳膊上挂了彩回来,村子上不由分说,又硬派了他出来打更。谷雨原不肯夺掉黎三这个饭碗。打更这个差事虽苦,一个冬天过来,逗得上两三石谷子,合上三五亩薄田的收成。他跟黎三都是一亩薄田也没有的贫户,靠着种村子上首户姜大麻子的田地过活。可拗不过村上大伙儿的意思,算是把黎三给得罪了。
打更是重阳到二年清明这五个月的事。一年中最冷的天气都在这五个月里。当了两年兵的谷雨,似乎更耐得风霜雨雪、寂寞和孤独了。
“有钱难买五月旱哪!六月连阴吃饱饭!”他跟自己重着这句老话。旧年恰正是五月里闹涝。一交六月,又打月初旱到底,注定了歉收。挨门挨户去逗更粮,就没法子逗得齐全。该出五升的,只收了两升,多半一粒谷子也出不起,允到收了麦子再出更粮。
这才只是正月底,春荒就开头了,到处闹着偷谷子,哪一天才偷到一个尽头?
从南村传来打更的梆子声:“,……”三更天了。这跟串村子卖香油的梆子声不怎么两样,深夜里听来却像给棺材敲钉子。谁家屋顶上猫叫窝子,猫那个嗓管儿里发出人声,能叫得人汗毛竖起来。
谷雨又一回坐到红石上歇脚,刚坐下来,一个黑影一晃,横穿过正前面的牛车路。赶紧持起怀里的红缨枪跟踪追上去。
连连赶过几家人家,差不多就是刚才那个黑影穿过的去处,谷雨蹲下来张望。人都喊他作夜猫子,怎么样乌云斗暗的黑夜里,风吹草动总瞒不过谷雨。或许他也并不全靠一双眼睛,或许像驴子一双前腿弯子里长一对夜眼那样,另外还生了一对眼睛。
那个黑影站在他家菜园墙外,手弯在脑袋上不知做甚么。过一阵儿,重又鬼祟地往东走去。
“你要挖窟子偷谷子,不能尽往东去呀!”这个更夫心里在说,“这尽往东去,就活该你没辙儿了。”
东半个村儿全是穷户,都是篱笆泥墙,掏挖不出窟窿。挖窟子小偷总得拣土墙或砖墙下手。
黑影停了下又匆匆地往东去。村子最东头,只有骆大孤门独户那一家。
骆大家里人口少,只有两间茅屋,外带一小间灶房。骆大的女人跪在供桌前蒲垫上。小龙刚刚安静下来,跟他姐姐睡在里间炕上。
供桌上,两只墨青土窑小香炉里烧着香。油灯只燃一根灯芯草,短短的小火焰,照出墙壁中间供奉的一张水印观世音菩萨。左首是张钟馗捉鬼年画,大红大绿两种犯冲的颜色,直直爽爽拼堆在一起。这两张画上下都用劈开的高粱秸压得很平,牢牢钉在高凹不平的篱笆泥墙上。菩萨右边供奉着祖宗牌位——长方一张喜红纸,上端两个角剪掉,上书“骆氏门中先远三代之神位”,贴在墙上。那两副木旋的蜡烛台,淋淋漓漓的蜡油上蒙一层厚厚灰尘。供桌两端一只又一只黑泥罐,里面装着菜种和腌小蒜儿。
骆大家的跪在蒲垫上,垂着头发怔,拿不定求谁才宜当——菩萨还是祖宗爷?再不就干脆求求鬼王老爷来吃鬼。婆婆在世时,疼的就是这个宝贝孙子,如今三天两头总是回来把小龙带走。
“老死鬼呀!谁用你来疼?该去哪儿托生,你就快去投胎罢!”
骆大女人咒怨着,好像听见篱笆门响。
“他爹回来了不成?有这么快呀!”女人从蒲垫上爬起,直着耳朵听。
“小龙可好点儿没有,骆大嫂?”
外边这么唤着,她可一时听不清是哪一个,望着墙上的红灯笼。
“是我,给你送点儿药丸子来。”
“谁呀?”骆大女人把房门拉开,隔着院子问。
“我呀,听不出罢?”
真的听不出是谁,心想也许是谷雨哥送药来。篱笆门打开,靠着屋里飘出的那点儿灯光,这才认出是谁,心里却疑猜,姜大麻子也是这种人?
“姜大爷,你这是……?”女人怯怯臊臊那个嫩腔儿,真是惹人怜。
姜大麻子走进屋子。“刚听你给小龙叫魂,我家里她说,还不是发烧!咱们现成的丸药,送几粒过去罢!”
说着放下个小纸包,去头上卷起驼毡帽子。个子太高了,碰上了矮梁上挂的棒子种。
“咱們家那个小的,也正发烧闹人,我家里抽不开身,要不她自个儿给你送过来了。”
口口声声的我家里、我家里,骆大女人口里千谢万谢,心里可就更疑猜。分明这天清早,他女人包裹着小的,带两个大的,手里拿着根避邪的桃枝儿,坐在泥拖上走娘家去了。
“来罢!”姜大麻子重又拿起药包,要教她怎么给孩子吃下去。骆大女人望着这位老板,心里很怵。高高胖胖的大个子,一脸黑麻子。她自己也不算矮,站到面前也好像一座山。“要没有,就现烧一点罢!半碗水就行,见效得很。”
这女人没办法,总归种的是他姜家的田,住的是他姜家的地,老板吩咐怎么样,不能不听从,又为的是自个儿孩子。
“姜大爷,你这边坐坐罢,我去泥罀子撩点个水。”
“来,这儿有火!”
火柴硬塞到女人手里,两只手碰了一下。
骆大家的来到灶房里,人有点发傻,抓起泥茶罀,找不到水瓢。点着了油灯,还在找油灯在哪儿。搓弄着手,刚才被碰着的那一块,好像挨烫到了,老觉着有些火辣辣的。
姜大麻子跟进灶房里来,嘴上吊着一支没点火的烟卷,蹲在她当面。
“这天气一时怕还暖不起来呢!快惊蛰了不是?”没话找话说,东一句,西一句地扯淡。
女人垂下眼皮,瞧着自己照在火亮里的一双褪色绣花鞋。泥炉子口里伸缩跳跃的火舌,把她那张白胖富泰的脸子染得一红一红的。
姜大麻子说:“小孩子生病,那是常事儿,别发愁。没钱打药,你找你家大妞去跟我说,小意思。”一本正经地瞅着面前这个俏娘儿们。油灯照着半面脸,麻脸上的小坑窝儿,一颗一颗数得清,地上尽是干树枝儿,偏去骆大女人手里抽一枝来点烟,又着意地碰了一下。
“嗳,我说了,你家老大乍乍离开家,想是不想呀?”浓浓的一口烟,喷到骆大女人脸上。
泥罀里装的水不多,不知怎么还这个慢法儿,好像烧有半年也不止,罀还没有半点动静。气得骆大家的扯上大把豆秆儿,结结实实塞进泥灶里。那座泥灶肚子小,口也小,反而闷熄了,急得低下头去吹火。
姜大麻子一下子贴过脸来,帮忙吹火,吓得她赶紧躲开。火又重新旺起来,小小灶房里全是熏眼的浓烟,辣辣的,爨爨的。
“说的也是啊!乍乍的炕上少了那个人,抱一下空空的,蹬一蹬松松的,真不是滋味。”
说呀说的,姜大麻子就不老实了。女人只等着水快点开。又一口浓烟喷到脸上。“你家老大身子可不怎么壮实,你也是够苦命的。”
女人着急得不知怎么处。
泥罀子总算有了响声,那只手却又伸过来捏捏女人的脚,“真可惜了你这对儿俊脚,裹得多秀气!”
“姜大爷,你稳重点儿!”骆大女人赶紧蜷起腿,往后挪挪。手触到埋在碎草里冰凉冰凉的剔火叉。
总算挨到水开了,用火叉去把火按熄,一股子黄烟辣住眼睛,揉着搓着张不开。姜大麻子乘这个当口把骆大女人抱住,按在灶门前的柴火上,就动手轻薄。
女人想喊没有喊,被压在底下咬着牙猛挣,左右躲闪着那张喷着酒糟气味的嘴巴亲过来。“姜大爷!”女人央求着,“别让我喊出去,都不好见人!”
“听话,大爷不会亏待你,完了给你好处……”男的喘着,凉凉的一只手探进骆大家的棉袄底下。
灶房的风门喀喳喳一声从外面拉开,红缨枪那锃亮儿枪头伸进来,抵在姜大麻子正在扭动的脊梁上。
门外墨黑墨黑的,看不见人,只有这杆长枪伸进来,姜大麻子翻一个身,一把掯住枪头,眼睛直直地望着门外。“谷雨,你可好大的胆子!”一时他还不便站起,衣着很凌乱。
外面的人不声响,也不收回长枪。灶台上飘飘摇摇的油灯,只照出那一双羊毛窝、一溜老蓝大布打着补丁的袍襟。姜大麻子这才松开手,勾着脑袋约略整整衣裳。
“走开,这儿用不着你管!”
“话不能这么说,姜大爷!”外边那个仍只露出下半个身子,“姜大爷,谁都是有家有道,有妻有女的。谁能守住妻女一辈子不出门?骆大是你姜大爷派的夫子……”
“你他妈的滚不滚开!”
这位老板恼恨地卷着皮袄袖子跳起来,回头看一眼缩在墙角儿里蒙着脸的骆大女人,冲着外边说道:“大爷花的是大洋钱,有买就有卖的,要你外四路的吃哪一门子飞醋!”
“姜大爷,咱们可不能玷了人家媳妇儿清白。”
“你说你想怎么样?”姜大麻子撩起皮袍子,伸手到腰兜里摸钱,就便也把裤腰紧了紧,“要别的没有,哪,大洋两块,拿去花!”
两枚银元摔到那一双羊毛蒲鞋跟前:一枚平落地上,一枚贪玩地滚上一个转转儿才倒下。
“你别发火,姜大爷!”谷雨收回枪,踏过地上的两枚银元走进来,“咱们是哪儿见到哪儿完,担保一个字儿不说出去就截了。可是姜大爷,往后也该……也该疼惜点儿身子。”姜大麻子鼻子里冲出一声冷笑,“好,你倒教训起大爷来了。嫌少,哪,再加你一块,你给我走开!”
“姜大爷,人吃的是米,讲的是理,钱不能把理儿买了去。”谷雨闭上眼睛,叹口气,“咱们穷苦人家,一辈子没落得一身,也没落得一肚子,当真连两口子炕头上,也不让咱们干净点儿?”一双眼睛恳求地盯着这位大老板,擤了一把鼻子。灯里油不多,就快要涸干,灯焰越来越小,谷雨阴沉沉一张脸围在棉套头里,人往后退着,拿着他的红缨枪。
“人家男人也是替地方上出夫子,早晚咱们总得多招呼点儿个……”
“谷雨儿哥,你就少说一句罢!”骆大家的顶着一头扯散的乱发,受不住寒似的抱着两肩求着他。
“你让他说嘛,他不怕,就让他说!”姜大麻子整完了衣裳,走过去拾起地上银元,临走跺一跺脚,“谷雨,我对你不错,今儿你跟大爷来这么一手,你留神着点儿!”
胖大的身躯从灶屋小门底下塞出去,隔着墙,听得见咚咚咚的一阵脚步声。
灶屋里这两个不声响地对着,静静听着远处犬吠,屋顶上的风声。
骆大家的默默擦着眼泪,“谷雨儿哥,你说,前生前世咱们是作的甚么孽?要受这么个折腾法儿!”
“别怨命!只怨人心!”
女人蹉着脚,抱着脸埋在膝头上哭泣起来:“叫我怎么见人!叫我怎么有脸见人!我没受过这个!”
“这是干吗啦!难道咱们被欺负了,还是咱们过错?”
骆大女人甩把濞子,眼巴巴望着面前这个更夫,“我死到姜家去!我到姜家去死给他看!反正我活着也没脸见人了!”谷雨似乎发了脾气,“干吗?咱们该甚么罪?咱们该死吗?再说,我谷雨也是生着一张嘴乱说乱道的那种人?我说过了,哪儿见到哪儿完,刀口压着脖子,也不能说给别人家知道呗!”
灯光一直地往下暗,两个人都要对看不清了。
女人抽噎着:“还有你,该怎么办?你这不要吃他大麻子苦头么?”
“大不了跟以前的孙疤眼儿一样——地不准我种,更不让我打,房子不让我住!”
谷雨顿顿手里的红缨枪,转身朝着门外。
“活不下去,我领着一家大小去逃荒。飞禽走兽,老天爷还养活着,好歹我有的是力气,能挑能担的,难道老天爷不给一份儿粮!”
这个更夫当门站着,女人泪眼望着他微微有些佝偻的背影,越看越模糊。灯焰陡然一阵儿亮,就熄灭了。
那双羊毛蒲鞋轻轻擦着地,轻轻走开,在黑漆漆的夜色里。
天大亮的时节,村儿上出了事儿,姜大麻子家的谷仓叫人挖出一个大洞,谷子不知道给偷走了多少。
姜家支使伙计黎三,领着一帮人往谷雨家去,一路上气势汹汹地叫呼着,早晨的雾气还不曾退净。
农户捧着热粥,等在场边拦着黎三探问。
“是啊,这得问谷雨儿去。昨儿白天才逗的更粮,夜里他就不管事儿啦!吃更粮,不守夜,这像话吗?找他娘的算账去!”
黎三真有点儿八面威风的气势,手里拖着一根小扁担,外一只手插在袍襟底下,不断地撒落一些棒子米落在路心儿。后面跟着一帮伙计。赶着看热闹的孩子愈来愈多,几十只腿脚,从路心儿谷粒上踏过去。
谷雨住在村子東首第三家,这帮人直冲进他家里去,然后就有其中的伙计,打后头喊着跑出来,从姜家谷仓,经过院落,一直到打麦场上,一路上撒着黄澄澄的谷粒儿。再往前数,不就通到村中央的牛车路上吗?
黎三把不曾清醒的谷雨拖到门前打麦场上,要他立时到姜大爷那儿去回话。
门前的伙计却喊嚷着:“地上一路撒着谷粒儿,这不是有鬼啦!”
“跟着地上撒的谷粒儿走,看看通到哪儿去!总不是昨天逗更粮撒掉的罢?”
霜还不曾化尽,霜地上撒着谷粒,断续地从谷雨家通出来,从麦场上,到村儿中央的牛车路,一路上深深的沙土,净是刚才这一伙儿人留下的脚印,沙土和脚印掩埋不住一颗颗亮亮的棒子米和小米。
大家都看在眼里,沿路上好事儿的数着路心的谷粒,人多嘴杂地叫唤着。
“这两天风声不大好,他谷雨怎么又疏忽了?”家家门前,人一头喝热粥,一头议论着。
“这是从哪儿说起呀!不该有的事儿。”
“说的是啊,谷雨打更,向来万无一失!”
结果分外出人意料,路上这些撒落的谷粒,零零落落地直通到姜家谷仓墙外,通到那个窟洞口。一时之间,村儿上到处哄闹着,把偷谷贼和谷雨连上了一起。大家总觉着这就好像太阳跟月亮一道儿打东天升起一样出奇。
这可是怎样也抵赖不掉的,谷雨被架持到姜家大门前,身上早已挨上了几扁担。
姜家门口高石台上,姜大麻子叉腰站在那里,太阳穴上一边贴着一张红膏药,面带病容。
“不用噜苏,先给我绑到马桩上,揍他个半死再说!”
姜家三四个伙计撕撕扯扯之下,谷雨冲那个方向挣着身子,脸孔气得煞白,“姜大爷,你不能跟我来这一手!”
“甚么大爷大奶奶的!”姜大麻子把卷起的皮袍袖子一抹,“给我狠狠揍个半死,打出人命有我顶了!”说着说着眼睛笑笑,就转身进去了。
“姓姜的!你不能昧良心硬栽赃!”
谷雨吼叫着,被拖开,拉到那一排马桩的头一根前面,早有个伙计张起井绳等着,不由分说,把谷雨反剪着手,那么大的个头儿,从上到下结结实实绑到马桩上。
那一旁,黎三理着一根长长的车缆,一圈一圈折叠起来,挽到手里。
村子上,人从四处聚拢来,一层层围上。冬季里橘红色初露的阳光,照着那些攒动的困惑的脸子。人丛里传出抽打的响声,谷雨他女人孩子号啕着,大伙儿争吵成一片。
树上,草垛上,也都爬满了人,大新年里看会那样挤,一张张橘红色的面孔上却没有看热闹的喜气,一律透着气不忿儿,气他谷雨做了偷谷贼,也有气他谷雨给冤枉地诬害了。门口那边的高石台上,姜大麻子又出来了,驼毡帽压住眉毛上,叼一支烟卷,皱着眼睛,老去按按太阳穴上的红膏药。骆大女人抱着小龙,也匆匆赶了来,密密的人丛挤不进去,四处张望着,一眼瞧见那一张满是疤麻的大脸子,女人止不住一阵子惊慌,躲到人背后。昨夜里和这时节,同是这张脸,曾经挨得那样近,口涎滴到她领口。呼呼的热气夹杂着酒糟和蒜臭,还有烟酸,冲着她脸上喘,死尸一样重的身子,留长的指甲掐得她痛到心窝儿里。这张脸在灯亮儿底下是一个样子,在老阳里又是另一副神气了,怎么这会是一个人?骆大女人心里恨着,不由得指甲深深掐进怀里小龙的小腿上,小龙叫起来,她掐得更深,仿佛不曾听见甚么。
又一阵重重的拷打声,骆大家的脸色跟着煞白起来,咬紧了嘴唇,披散的发髻颤抖着。女人偷偷抹把眼角儿上眼泪,闭着眼靠到背后枣树上,好似要昏过去。
“你说出来呀!你怎么不说,谷雨!”这女人心里哀哭着,“你说罢!你说出姜大麻子怎么丑,怎么欺侮我!我拼着这张脸不要,也要跟他对质!”
可人丛里面只有谷雨嫂在那儿哭骂,孩子喊着爹,谷雨不曾哼一声。人丛里钻出个小伙子,高声叫着:
“昏过去了,打昏过去了,要闹人命了!”遂又引起了一阵子哄乱。
小龙从怀里滑落到地上,骆大女人天旋地转地昏眩了一阵,觉着背后靠着的枣树大大地晃荡,要把她摔到地上。“怎不肯说呀!你冤枉了!”女人跺着脚。
身旁一个老妇人衣襟把眼睛擦红了,不住念着:“造孽呀!造孽呀!”拍手打掌望着四处叫唤,老头子过来赶她回家去。
这边两个老人议论,怎么没有人去南村儿请伏二先生来调停。
“难道想把谷雨活生生打死!”骆大女人冒冒失失冲着这两老人叫嚷,像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姜大麻子。
“造孽呀!这个世道人心!”老妇人摔着鼻涕,衣襟不住地擦那一对昏花老眼,非要擦得更红才甘心。惹得她老伴像赶鸡子似的喝着:“嚷嚷,嚷嚷,谁不知道造孽?净听你穷嚷嚷!赶紧给我回家去!”
“真是造孽!一点不假。”另一个干巴巴的老头喝光了粥,端一只空碗舔着。
“谁知道怎么把大麻子给惹啦?”这老人舔着黄胡子说,“门前我扫得干干净净,哪儿见到他娘的一粒谷粒儿?黎三儿他那伙儿走过去一趟,就出了毛病!”
“听听,造孽呀!谷雨甚么样的人呀?赖他!”
骆大家的止不住嚷着:“大爷,你就该当去给谷雨申冤哪!光在这儿说有啥用?”女人带着哭腔。
“申冤!”这老人脸一扭,“瞧瞧,那边,还空着一排马桩。咱们不想种姜家地啦?”
“瞧着罢!话先说在这儿,又是一个孙疤眼儿!”
大伙儿纷纷攘攘的当儿,谁把那位伏二先生请来了。一个飘着灰白胡子的小老人,拉着一支高过头顶的长手杖,黄杨木做的,上面雕着老龙头。
这位看病的伏二先生,又老又矮小,却是健步如飞,声音出奇地洪亮,众人迎上去,争着告诉他这个那个。
“不行!这不行!”
老人察看了一下绑在马桩上昏迷过去的谷雨,急忙从人丛里走出来,大步大步往姜大麻子那边冲去。
“不行!你这样!”老人咳一口痰用劲地呸掉,“那么些眼睛看着你,凡事要服人!搜出谷子沒有?”
姜大麻子冷冷脸,终又把笑堆到脸上,“这也用得着劳动你老人家,快家里坐!”
“我不要进去。到底怎么个长短?你快跟我说说。”
人比方才更骚乱,吵嚷着,好像忽然有了甚么希望。这样一片嘈杂声里,只见姜大麻子滔滔地说着,指这指那地挥着冒火的手势,不知说些个甚么。
灰白胡子的伏二先生听着摇着头,打手势制止说下去,却插不上嘴。
高石台真像座戏台,人像看庙会那样,远远地看着听不清的小戏。总常有这样的戏文,土地公公替包老爷办案子,台下听不清不要紧,总有老懂戏的给你解说。
这两个戏子唱完了一出,走下台去。听说要去看看谷仓墙上的窟窿。看戏的人众也都跟着涌过去。
前几天给拉差去的夫子回来了。
骆大的女人立刻清醒过来,四处张望着,一眼就看见她男人夹在围上去的人众中间,脖子上挂条土车辫子。
这几个夫子挤进人丛里,看见谷雨血惨惨的脑袋歪在肩膀上,昏昏迷迷哼唧着,老婆孩子哭作一窝儿。
“怎打成这个样?黎三儿,你也是人哪?”
“你伙儿知道个屁!”黎三瞪着眼,两下里争吵起来。那个骆老大伸长脖子,直起眼睛打量这个绑在马桩上被打成这样的老邻居。
“我不在家,我家的谷子也不知道少了没有?”骆大自言自语地,转过去望望四周,指望谁能告诉他。
“要脸不要?”背后有人讥诮,“有几把谷子呀也有人偷?偷去喂小鸡?”
骆大给挤着转不动身子,掉过脑袋来瞪着背后,连带地嘴巴也歪到一边了。“操你的!处上贼邻居,谁能保得稳?他连姜大爷家谷子都偷,哼!”
好像有一肚子怨气要出出才行,便从脖颈上拿下土车辫子,横折一个双。很用不上劲儿,从人们腦袋顶上够着抽了谷雨一下。“操你个贼种!”随后红着脸挤出来。这个老实人只有被人欺侮的份儿,差不多这算是生平第一次揍了人,得意地臊红了脸。找到他女人,开口就炫他这一手。
“真是啊,想不到的!”老实人着意地比画着,扬起手里土车辫子,“气得我狠狠抽了他两下子!”
“大面瓜!真有你两下儿啊!”
蹲在地上的瘦老头,对他点头笑笑。他可发现到他女人沉着脸。“多能干!就该给人欺压一辈子!”抱着孩子一转身走开。弄得骆大脸黄黄的,看看周围,没有一张好脸色对待他。
这一场风波让伏二先生调停平息了。谷雨由老人领回来家里包伤。姜大麻子立刻差派了伙计过来,逼着谷雨搬出姜家的地。
“你这帮子狗仗人势!也要等人家拆蹬拆蹬!别他娘的墙歪众人推,破鼓齐伙儿擂!”
伏二先生挥起龙头手杖,把这一伙儿家伙骂回去。“先到我南村儿落户罢!慢慢给你找几亩田种种。”谷雨脑袋上裹着布,收拾种田的家伙往土车上堆放。“谢了,你老人家。天生天养,哪儿不是过活?”
“别由着性子,又不是真的偷了抢了,没脸见人!”老人虎下脸来,“到哪儿去?到哪儿去不得从头来?住近点儿,等着还有笑话看!”
“就是那么个直性子!”后来老人硬把谷雨的小毛驴先骑着走了,“我先回去,给你腾出间车屋,随手你就给我搬过来!”
前村后村隔不五六里远,破家值万贯,一搬就搬上大半一个整天还没完儿。
夜里,村儿上黎三敲着梆子打更,老在谷雨家前屋后转,存心苦恼这一家人似的。天刚蒙蒙亮,谷雨家里的怀里揣着顶小的,领着一窝儿没睡醒的大大小小。谷雨用他那杆红缨枪挑一副担子,一头柳条筐子里塞着棉絮被窝,上面坐着才学走路的孩子。另一头,净是些盆盆罐罐,上面盖着一只黑锅。
这个小小家族,就这么样一声不吭地走了。村头上站着些送行的,也都不言语地愣愣望着。
天空堆着乌云,慢慢地烧起早霞,云块一片片烧红了。夜来落过头场春雨,湿淋淋的光树枝给唱唱儿的山喳子蹬下几滴水珠,打落在湿地上,嗒嗒有声。
含雨的初春之晨,总是这样清凉里含着温和,打更守夜的人久没有这样一段儿时辰。今天有了,却又走了。谷雨没有回头,脸对着云层里的朝阳。
站在村头上的骆大没有留意许多人都红了眼圈,只看到他女人含着眼泪倚在门旁篱笆上,痴痴地目送渐渐远去的那一家人,嘴里咬着小龙风帽上红飘带。
骆大心里不能不难受,多年的老邻居。可骆大疑心了一整夜。出外只这三五天工夫,他女人陡然对他变了,思来想去,总不见得是为了他抽了谷雨那一下土车辫子。
“人走远了,还舍不得?”老实人,心里冒着火星。昨夜里,女人不让他挨近一点,试着伸过手去,让她甩开了。难道这个偷谷贼也偷了他家这朵花?骆大疑心地跟自己发誓:“今夜你要再不……你瞧我的罢!”
可他自知并没章程降住他女人,心里越发又恼又气恨。望望远去的那一家,望望他女人,心中隐隐作痛。
那一家人愈远了,大路弯向左首去,密密的白杨树行里,偶尔现出那一绺红缨子,闪了一下,又隐没了。
早霞愈烧愈烈,人脸给烧得通红,好似这都是那一绺飘打的红缨子照的。
湿淋淋的光树枝上,还不时滴落一两点清泪,山喳子唱着凄清的唱儿。
(选自《朱西甯自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