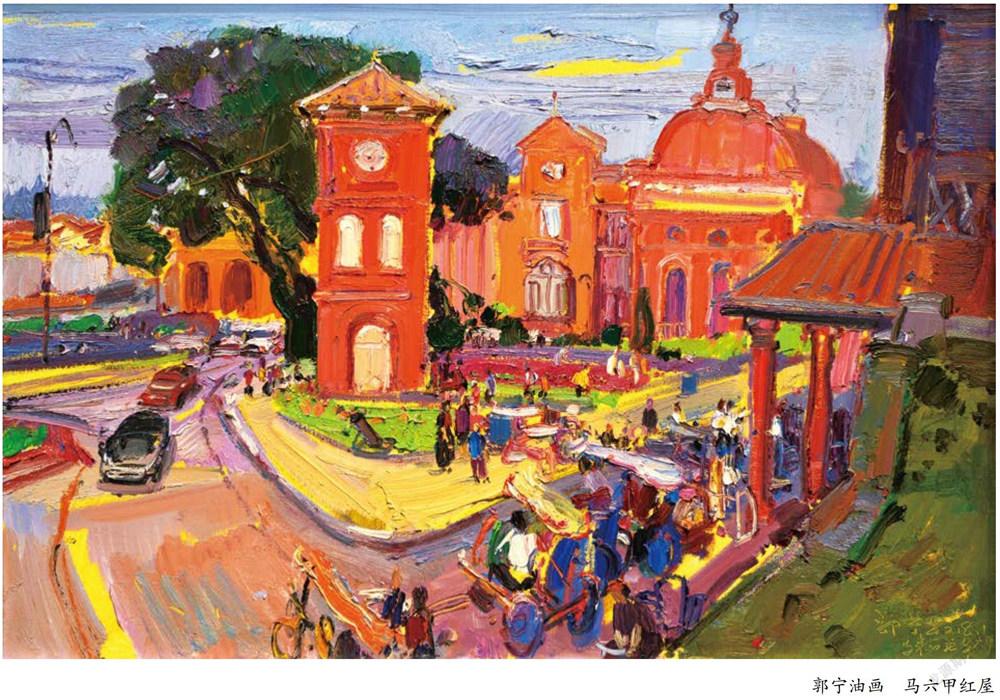
春梅最爱看父亲画的梅。
春梅的童年,几乎都待在父亲的画室里,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父亲画梅,出枝、圈花、点蕊、点花蒂、点苔、题款,最后将画悬挂起来,审视一番,不足处再以点垛调整。
上学之后,一回家,春梅必先去看父亲新写的画。父亲笔下的梅花,或正、或仰、或俯,或骨朵、或半开、或盛开,疏密流畅,总让春梅着迷。
春梅的母亲,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个儿不高,喜欢穿蓝色斜襟上衣,短头发上,经常盖一条红格子方围巾,一见人眼睛就笑得眯成一条缝,除了忙农活、操持家务,她唯一的兴趣就是去梅子庵烧香拜佛。梅子庵庵院不大,透着清净秀雅,庵后一大片梅林。春梅的母亲和庵里的静安师父很投缘,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春梅也喜欢跟随母亲去梅子庵,却是惦念上庵里的味酵粄,用清冽的山泉水,石磨,铁锅蒸出的梅子庵味酵粄,口感柔韧,再蘸上黄糖或少许蒜蓉、辣椒、酱油熬成的汁,那味道更佳。要是有缘,碰上细细密密的白梅花开,还能吃上掺有梅花蒸的味酵粄,轻轻咬上一口,满嘴留香。
若是碰上初一、十五,香客多,庵里的味酵粄就显得不够分,往往后面去的香客就尝不到了。但春梅不管什么时候去,静安师父都会变戏法似的端出一两碗味酵粄来,每次看着春梅狼吞虎咽,静安师父就会慈爱地摸着春梅翘起的羊角辫:“慢点,慢点,莫噎着了。”然后又微笑地转向春梅的母亲:“真好,这丫头,又长高了呢。”
春梅父亲非常疼爱女儿,小的时候,出门都不舍得让春梅走路,总是让春梅坐在他的脖子上。去邻居家串门,得个瓜儿枣儿,总是偷偷带回给春梅。并不宽裕的日子里,父亲常给春梅开“小灶”,煎荷包蛋、蒸瘦肉汤,那浓香的味道,常引来围屋里邻近小丫头们艳羡的目光。
春梅觉得,父亲一半是母亲的,另一半就是她的。
可是上了初中之后,春梅隐隐约约觉得,父亲的心里,除了母亲,除了自己,还住着另外一个女人。
春梅是从父亲的画里看出问题的,父亲的梅花图里,不知何时开始多出了个似曾相识的女子,秀发如云,衣袂飘飘。画中的女子,有时撑了一把油纸伞,踏花而来。有时携一把古琴,静坐花丛,等清风入弦。有时临水梳妆,楚楚动人,令人心醉。
这件事得悄悄提醒下母亲,春梅想。
“妈,你可得多关心关心咱爸。”
“你这鬼丫头,我怎么就不关心你爸了?”母亲戳了戳春梅的额头。
“妈,我觉得你该多看看爸爸的画,接受下艺术的熏陶。”
“艺术?两个人都搞艺术去,谁给你饭吃?”
“你不懂艺术,哪一天,父亲要是给哪个女人拐了去,你可别厌我没提醒你。”
“就你父亲那呆样,谁折腾。”春梅母亲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春梅讨厌母亲的没心没肺。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依旧醉心于写画,母亲依旧醉心于上梅子庵。
突然有一天,春梅发现父亲新作的一幅画落款为:赠与春梅惠存。这是一幅春梅图,初春的溪边,三两枝春梅古老蒼劲,虬枝上绽放着串串冰姿清影,两三只小鸟雀跃枝头,溪上一座独木桥,桥上,走着春梅父亲平日画的那位女子,溪的对面,村庄远景隐约,这真是一幅好画,但此时春梅已无心观画,她的眼光狠狠盯在落款处,不用说,父亲一直画的女子,便叫春梅。莫不是父亲早就背着母亲和这女子好上了,才把自己的女儿也取名为“春梅”,想到此,春梅便觉一肚子怒火和失落。
春梅截住挑水的母亲:“妈,你可得把爸管严点,别让他跟别的女人瞎掺和。”
“你这鬼丫头,脑子尽想些啥,乱七八糟。”母亲把瓠瓜水瓢往春梅头上一扣。
“妈,我跟你说真的。”
“你这鬼丫头,再乱嚼,把你舌头剪了。”
“妈,那个女人也叫春梅!”面对母亲的榆木脑袋,春梅急了。
春梅母亲愣了下,“鬼丫头,读好你的书,莫要管大人事。”
“妈,你再不管,爸肯定给那个不要脸的妖精抢去。”
“没大没小,不许你这么说春梅。”啪的一声脆响,从没打过春梅的母亲,竟然给了春梅一巴掌,春梅委屈地跑回房间。
南方三月的天空,经常沉着一张黑黑的脸,大雨小雨每天一场接一场地下,溪里的水一下涨了许多,梅子庵前的那座独木桥,水已快漫到桥面了。对岸有七八个小孩要经过此桥去上学,去的时候,大都有大人领着过桥。回的时候,大人还在田里忙农事,便由孩子们自己走回家去。每当大水涨起来,小孩放学的这个时间,静安师父总是守住桥头,一个一个把孩子们送过桥去。
那日大雨整整倒了一天一夜,雨停后,春梅听到静安师父救起一个落水孩童后入寂的消息。静安师父,法号静安,俗名春梅……人们还说了什么,春梅已无心思再听,她的耳际,轰隆隆只响着两个字:春梅。
许多年后,春梅用自己卖画的钱和从乡里乡亲们那募捐而来的钱,把梅子庵旁那座独木桥,改成了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那座桥,叫静安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