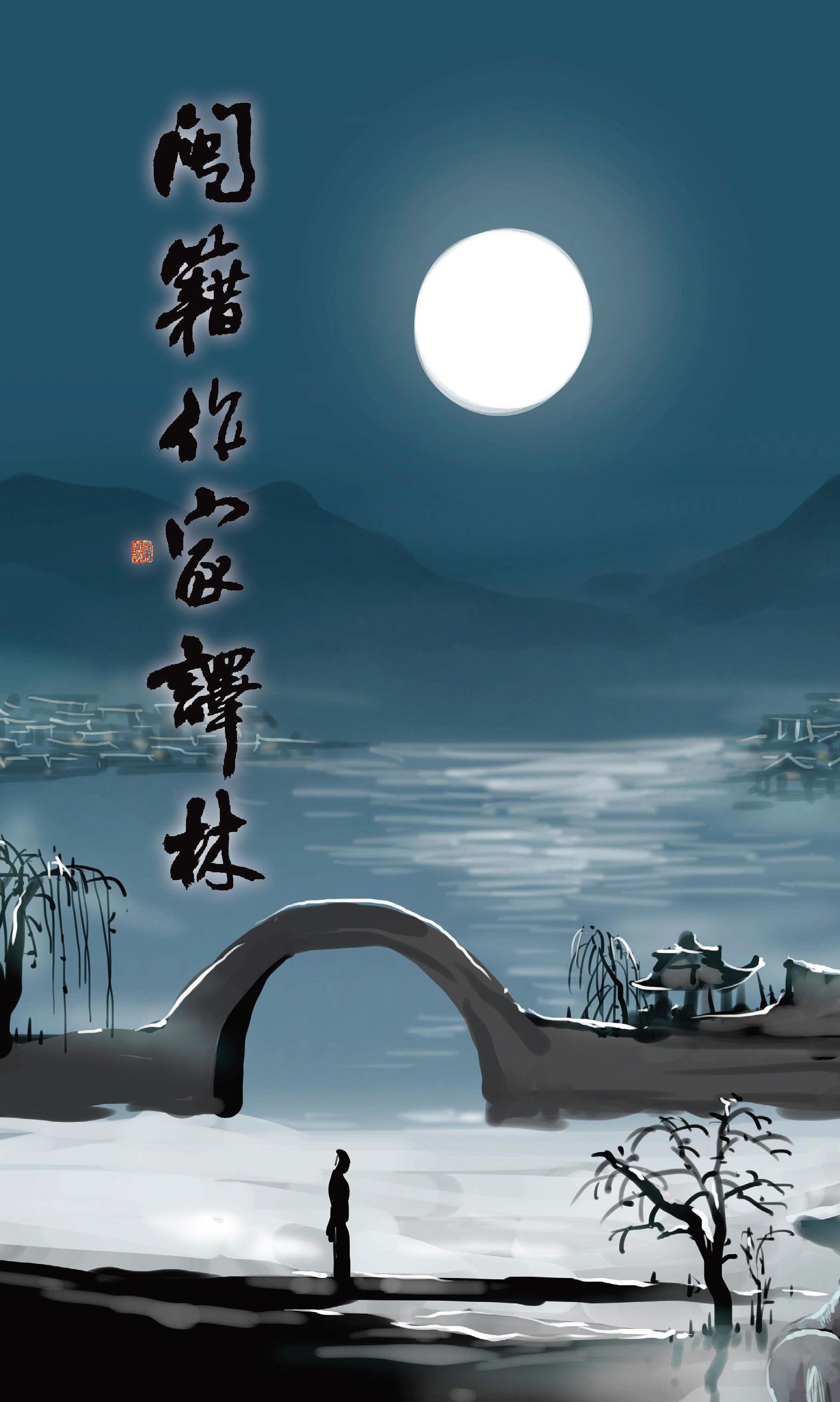

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过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是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撇开,暂时不必顾及这些小节,专在心灵上用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这个方法应该对他很有益处。基础已经打好,真实的文学个性已经培养成功时,笔法自然而然会产生,一切技巧也自然而然地跟着纯熟。只要他的立意精辟,文法上略有不妥之处也是不妨的,这种小小的错误,自有那出版者的编校员会替他改正的。反之,一个初学者如若忽略了文学个性的培植,则无论怎样去研究文法和文章,也是不能成为作家的。布封(Buffon)说得好:“笔法即作者。”笔法并不是一个方式,也不是一个写作方法中的制度或饰件,其实不过是读者对于作者的心胸特性,深刻或浅泛的,有见识或无见识和其他各种特质,如:机智、幽默、讥嘲、体会、柔婉、敏锐、了解力、仁慈的乖戾或乖戾的仁慈、冷酷、实际的常识和对于一切物事的一般态度所得的一种印象罢了。可知世上绝不能有教人学会“幽默技巧”的袖珍指南,或“乖戾的仁慈三小时速通法”,或“常识速成十五法”,或“感觉敏锐速成十一法”。
我们须超过写作艺术的表面而更进一步。我们在做到这一步时,便会觉得写作艺术这个问题其实包括整个文学思想、见地、情感和读写的问题。当我在中国做恢复性灵和提倡更活泼简易的散文体的文学运动时,不得不写下许多篇文章,发表我对一般的文学的见地,尤其是对于写作的见地。我可以试写出一组关于文学的警语,而以“雪茄烟灰”为题。
甲 技巧和个性
做文法教师的论文学,实等于木匠谈论美术。评论家专从写作技巧上分析文章,这其实等于一个工程师用测量仪丈量泰山的高度和结构。
世上无所谓写作的技巧。我心目中所认为有价值的中国作家,也都是这般说法。
写作技巧之于文学,正如教条之于教派——都是属于性情琐屑者的顾及小节。
初学者往往被技巧之论所眩惑——小说的技巧、剧本的技巧、音乐的技巧、演剧的技巧。他不知道写作的技巧和作家的家世并没有关系,演剧的技巧和名艺人的家世并没有关系。他不知道世上有所谓个性,这个性其实就是一切艺术和文学成就的基础。
乙 文学的欣赏
当一个人读了许多本名著,而觉得其中某作家叙事灵活生动,某作家细腻有致,某作家文意畅达,某作家笔致楚楚动人,某作家味如醇酒佳酿时,他应坦白地承认爱好他们、欣赏他们,只要他的欣赏是出乎本心的。读过这许多的作品后,他便有了一个相当的经验基础,即能辨识何者是温文,何者是醇熟,何者是力量,何者是雄壮,何者是光彩,何者是辛辣,何者是细腻,何者是风韵。在他尝过这许多种滋味之后,他不必借指南的帮助,也能知道何者是优美的文学了。
一个念文学的学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辨别各种不同的滋味。其中最优美的是温文和醇熟,但也是最难于学到的。温文和平淡,其间相差极微。
一个写作者,如若思想浅薄,缺乏创造性,则大概将从简单的文体入手,终至于奄无生气。只有新鲜的鱼可以清炖,如若已宿,便须加酱油、胡椒和芥末——越多越好。
优美的作家正如杨贵妃的姐姐一般,可以不假脂粉,素面朝天。宫中别的美人便少不了这两件东西,这就是英文作家中极少敢于用简单文体的理由。
丙 文体和思想
作品的优劣,全看它的风韵和滋味如何,是否有风韵和滋味。所谓风韵并无规则可言,发自一篇作品,正如烟气发自烟斗,云气发自山头,并不自知它的去向。最优美的文体就是如苏东坡的文体一般近于“行云流水”。
文体是文字、思想和个性的混合物,但有许多文体是完全单靠着文字而成的。
清澈的思想用不明朗的文字表现者,事实上很少。不清澈的思想而表现极明白者倒很多。如此的文体,实可称为明白的不明朗。
用不明朗的文字表现清澈的思想,乃是终身不娶者的文体。因为他永远无须向他的妻子做任何解释,如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之类。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英国作家,译有《荷马史诗》)有时也是这样的古怪。
一个人的文体常被他的“文学爱人”藻饰。他在思想上和表现方式上,每每会渐渐地近似这位爱人。初学者只有借这个方法,才能培植出他的文体。等到阅世较深之后,他自会从中发现自己,而创成自己的文体。
一个人如若对某作家向来是憎恶的,则阅读这作家的作品必不能得到丝毫的助益。我颇希望学校中的教师能記住这句话。
一个人的品性,一部分是天生的,他的文体也是如此。还有一部分则完全是由感染而来的。
一个人如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
世上有合于各色各种脾胃的作家,但一个人必须花些工夫,方能寻到。
一本书犹如一个人的生活,或一个城市的画像。有许多读者只看到纽约或巴黎的画像,而并没有看见纽约或巴黎的本身。聪明的读者则既读书,也亲阅生活的本身。宇宙即是一本大书,生活即是一所大的学校。一个善读者必拿那作家从里面翻到外面,如叫花子将他的衣服翻转来捉虱子一般。
有些作家能如叫花子积满了虱子的衣服一般,很有趣地不断地挑拨他们的读者,痒也是世间一件趣事。
初学者最好应从读表示反对意见的作品入手。如此,他绝不致误为骗子所欺蒙。读过表示反对意见的作品后,他即已有了准备,而可以去读表示正面意见的作品,富于评断力的心胸即是如此发展出来的。
作家都有他所爱用的字眼,每一个字都有它的生命史和个性。这生命史和个性是普通的字典所不载的,除非是如《袖珍牛津字典》(Concise of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一类的字典。好的字典和《袖珍牛津字典》,都是颇堪一读的。
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是老矿,一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去掘取材料,唯有高等的艺术家会从新矿中去掘取材料。老矿的产物都已经过溶解,但新矿的产物不然。
王中(公元27年至100年)将“专家”和“学者”加以区别,也将“作家”和“思想家”加以区别。我以为当一个专家的学识宽博后,他即成为学者,一个作家的智慧深切后,他即成为思想家。
学者在写作中,大都借材于别的学者。他所引用的旧典成语越多,越像一位学者。一个思想家于写作时,则都借材于自己肚中的概念,越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越会依赖于自己的肚腹。
一个学者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家则像一条蚕,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
一个人的观念在写作之前,都有一个“怀孕”时期,也像胚胎在母腹中必有一个怀孕时期一般。当一个人所喜爱的作家已在他的心灵中将火星燃着,开始发动了一个活的观念流泉时,这就是所谓“怀孕”。当一个人在他的观念还没有经过怀孕的时期,即急于将它写出付印时,这就是错认肚腹泻泄时的疼痛为怀孕足月时的阵痛。当一个人出卖他的良心而做违心之论时,这就是堕胎,那胚胎落地即死。当一个作者觉得他的头脑中有如电阵一般的搅扰,觉得非将他的观念发泄出来不能安逸,乃将它们写在纸上而觉如释重负时,这就是文学的产生。因此,一个作家对于他的文学作品,自会有一种如母亲对于子女一般的慈爱感情,也因此,自己的作品必是较好的,犹如一个女子在为人之妻后必是更可爱的。
作家的笑正好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观念的范围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
一个作家因为憎恶一个人,而拟握笔写一篇极力攻击他的文章,但一方面并没有看到那个人的好处,这个作家便没有写作这篇攻击文章的资格。
丁 自我发挥派
十六世纪末叶,袁氏三弟兄所创的“性灵派”或称“公安派”(袁氏三弟兄为公安县人),即是自我发挥的学派。“性”即个人的“性情”,“灵”即个人的“心灵”。
写作不过是发挥一己的性情,或表演一己的心灵。所谓“神通”,就是这心灵的流动,实际上确是由于血液内“荷尔蒙”的泛滥所致。
我们在读一本古书或阅一幅古画时,其实不过是在观看那作家的心灵流动。有时这心力之流如若干涸,或精神如若颓唐时,即是最高手的书画家也会缺乏精神和活泼的。
这“神通”是在早晨,当一个人于好梦沉酣中自然醒觉时来到。此后,他喝过一杯早茶,阅读一张报纸,而没有看到什么烦心的消息,慢慢走到书室里边,坐在一张明窗前的写字台边,窗外风日晴和,在这种时候,他必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优美的诗、优美的书札,必能作出优美的画,并题优美的款字在上面。
这所谓“自我”或“个性”,乃是一束肢体肌肉、神经、理智、情感、学养、悟力、经验偏见所组成。它一部分是天成的,而一部分是养成的;一部分是生而就有的,而一部分是培植出来的。一个人的性情是在出世之时,甚至在出世之前即已成为固定的。有些是天生硬心肠和卑鄙的;有些是天生坦白磊落、尚侠慷慨的;也有些是天生柔弱胆怯、多愁多虑的。这些都深隐于骨髓之中,因此,即使是最良好的教师和最聪明的父母,也没有法子变更一个人的个性。另有许多品质,则是出世之后由教育和经验而得到的。但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印象乃是在不同的生活时代,从种种不一的源泉和各种不同的影响潮流中所得到的,因此他的观念、偏见和见地有时会极端自相矛盾。一个人爱狗而恶猫,但也有人爱猫而恶狗。所以人类个性型式的研究,乃是一切科学中最为复杂的科学。
“自我发挥派”叫我们在写作中只可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出乎本意的爱好,出乎本意的憎恶,出乎本意的恐惧和出乎本意的癖嗜,在表现这些时,不可隐恶而扬善,不可畏惧外界的嘲笑,也不可畏惧有背于古圣或时贤的。
“自我发挥派”的作家对一篇文章专喜爱其中个性最流露的一节,专喜爱一节中个性最流露的一句,专喜爱一句中个性最流露的一个表现语词。他在描写或叙述一幅景物、一个情感或一件事实时,只就自己所目击的景物,自己所感觉的情感,自己所了解的事实而加以描写或叙述。凡符合这条定例者,都是真文学,不符合者,即不是真文学。
《红楼梦》中的女子林黛玉,即是一个“自我发挥派”。她曾说:“若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却使得的。”
“自我发挥派”因为专喜爱发乎本心的感觉,所以自然蔑视文体上的藻饰,因此這派人士在写作中专重天真和温文,他们尊奉孟子“言以达志”的说法。
文学的美处,不过是达意罢了。
这一派的弊病,在于学者不慎即会流于平淡(袁中郎),或流于怪僻(金圣叹),或过于离经叛道(李卓吾)。因此后来的儒家都非常憎恶这个学派。但以事实而论,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全靠他们这班自出心裁的作家出力,方不至于完全灭绝。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他们必会得到其应有的地位。
中国正统派文学的目标明明在于表现古圣的心胸,而不是表现作者自己的心胸,所以完全是死的。“性灵派”文学的目标是在于表现作者自己的心胸,而不是古圣的心胸,所以是活的。
这派学者都有一种自尊心和独立心,这使他们不至于逾越本分而以危言耸人的听闻,如若孔孟的说话偶然和他们的见地相合,良心上可以赞同,他们不会矫情而持异说。但是,如若良心上不能赞同时,他们便不肯将孔孟随便放过去。他们是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威武所屈的。
发乎本心的文学,不过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好奇心。凡是目力明确,不为外物所惑的人,都能时常保持这个好奇心。所以他不必歪曲事实以求景物能视若新奇。别人觉得这派学者的观念和见地十分新奇,即因他们都是看惯了矫揉造作的景物。
凡是有弱点的作家,必会亲近性灵派。这派中的作家都反对模仿古人或今人的,反对一切文学技巧的定例,袁氏弟兄相信让手和口自然做去,自能得合式的结果。李笠翁相信文章之要在于韵趣。袁子才相信做文章无所谓技巧。北宋作家黄山谷相信文章的章句都是偶然而得的,正如木中被虫所蚀的洞一般。
戊 家常的文体
用家常文体的作家是以真诚的态度说话。他把他的弱点完全显露出来,所以他是从无防人之心的。
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应像师生的关系,而应像厮熟朋友的关系,只有如此,方能渐渐生出热情。
凡在写作中不敢用“我”字的人绝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我喜爱说谎者更胜于喜爱说实话者。我喜爱不谨慎的说谎者更胜于喜爱谨慎的说谎者。他的不谨慎,表示他的深爱读者。
我深信一个不谨慎的蠢人,而不敢相信一个律师。这不谨慎的蠢人是一个国家中最好的外交家,能得到人民的信仰。
我心目中所认为最好的杂志是一个半月刊,但不必真正出书,只需每两星期一次召集许多人,群聚在一间小室之中,让他们去随意谈天,每次以两小时为度,读者即是旁听的人。这就等于一次绝好的夜談。完毕之后,读者即可去睡觉,在明天早晨起身去办公时,不论他是一个银行职员,或一个会计,或一个学校教师到校去张贴布告,他必会觉得隔夜的滋味还留在齿颊之间。
各地方的菜馆大小不一,有些是高厅大厦,金碧辉煌,可设盛宴;有些是专供小饮。我所最喜欢的是同着两三个知己朋友到这种小馆子里去小饮,而极不愿意赴要人或富翁的盛宴。我们在这小馆子里边又吃又喝,随便谈天,互相嘲谑,甚至杯翻酒泼,这种快乐是盛宴上的座客所享不到的,也是梦想不到的。
世界上有富翁的花园和大厦,但山中也有不少的小筑。这种小筑有些虽也布置得很精雅,但氛围终和朱红色大门、绿色窗户、仆婢排立的富家大厦截然不同。当一个人走进这种小筑时,他没听见忠狗的吠声,他没看见足恭谄笑的侍者和阍人讨厌的面孔。在离开那里,走出大门的时候,他没看见门外矗立两旁的一对“不洁的石狮子”。十七世纪某中国作家有一段绝好这种境地的描写,这好似周、程、张、朱正在伏羲殿内互相揖让,就座之时,苏东坡和东方朔忽然赤足半裸地也走了进来,拍着手互相嘲笑作乐。旁观的人或许愕然惊怪,但这些高士不过互相目视,做会心的微笑罢了。
己 什么是美
所谓文学的美和一切物事的美,大都有赖于变换和动作,并且以生活为基础。凡是活的东西都有变换和活动,而凡是有变换和活动的东西自然也有美。当我们看到山岩深谷和溪流具着远胜于运河的奇峭之美,而并不是经由建筑家用计算方法造成时,试问我们对于文学和写作怎样可以定出规例来?星辰是天之文,名山大河是地之文;风吹云变,我们就得到一个锦缎的花纹图案;霜降叶落,我们就得到了秋天之色。那些星辰在穹苍中循着它们的轨道而运行时,何曾想到地球上会有人在那里欣赏它们?然而我们终在无意之间发现了天狗星和牛郎星。地球的外壳在收缩引张之际推起了高高的山,陷下了深深的海,其实地球又何曾出于有意地创造出那五座名岳,为我们崇拜的目的?然而太华和昆仑终已矗立于地面,高下起伏,绵延千里,玉女和仙童立在危岩之上,显然是供我们欣赏的。这些就是大艺术造化家自由随意的挥洒。当天上的云行过山头而遇到强劲的山风时,它何曾想到有意露出裙边巾角以供我们赏玩?然而它们自然会整理,有时如鱼鳞,有时如锦缎,有时如赛跑的狗,如怒吼的狮子,如纵跳的凤凰,如踞跃的麒麟,都像是文学的杰作。当秋天的树木受到风霜雨露的摧残,正致力于减少它们的呼吸以保全它们的本力时,它们还会有这空闲去涂粉涂脂,以供古道行人的欣赏吗?然而他们终是那么冷洁幽寂,远胜于王维、米芾的书画。
所以凡是宇宙中活的东西都有着文学的美。枯藤的美胜于王羲之的字,悬崖的壮严胜于张猛龙的碑铭。所以我们知道“文”或文学的美是天成的。凡是尽其天性的,都有“文”或美的轮廓为其外饰,所以“文”或轮廓形式的美是内生的,而不是外来的。马的蹄是为适于奔跑而造,老虎的爪是为适于扑攫而造,鹤的腿是为适于涉水塘而造,熊的掌则是为适于在冰上爬行而造,这马、虎、鹤、熊,自己又何曾想到它们的形式的美呢?它们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为生活而运用其效能,并取着最宜于他行动的姿势。但是从我们的观点说起来,则看到马蹄、虎爪、鹤腿、熊掌,都有一种惊人的美,或是雄壮有力的美,或是细巧有劲的美,或是骨骼清奇的美,或是关节粗拙的美。此外则象爪如“隶书”,狮鬃如“飞白”,争斗时的蛇屈曲扭绕如“草书”,飞龙如“篆书”,牛腿如“八分”,鹿如“小楷”。它们的美都生自姿势和活动,它们的体形都是身体效能的结果。这也就是写作之美的秘诀。“式”之所需,不能强加阻抑;“式”所不需,便当立刻停止。因此,一篇文学名作正如大自然本身的一个伸展,在无式之中成就佳式。美格和美点能自然而生,因为所谓的“式”,乃是动作的美,而不是定形的美。凡是活动的东西都有一个“式”,所以也就有美、力和文,或形式和轮廓的美。
责任编辑:马洪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