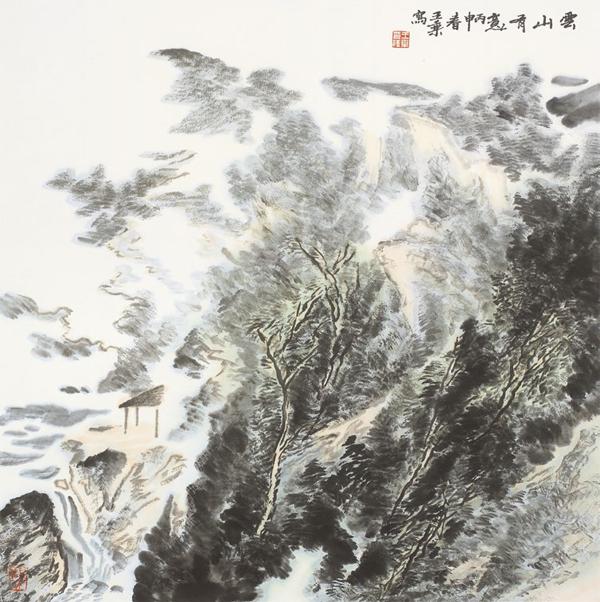
相思古镇有多少年历史没人说得清,古镇人喜欢木版年画,说不清从哪朝哪代开始。镇子上的老人们说,木版年画有多少年,咱古镇就存在了多少年。
据沈家的家谱记载,明朝末年,沈全的老祖宗们就已经在古镇上讨生活了。那时的沈家单门独户,苦苦守着木版年画这份手艺。许多年过去了,沈家老祖宗开枝散叶,自然人丁兴旺,能人辈出。木版年画到了沈全这辈儿,手艺越发精湛,且有了自己的名号“全成”。
沈全内向得近乎于木讷,有人说他一天说不了三句话,沈全的媳妇儿连连摆手说不对不对,他是三天说不了一句话。沈全不是不会说,是不说废话。他把该说的话该做的事该有的心眼儿都聚集在木版画里了。“全成”老店刻印出的秦琼敬德双门神、刘海戏金蟾、五子登科、三娘教子,抱花瓶,线条流畅,色彩绚丽,栩栩如生。沈全最拿手的绝活儿是自个儿设计、绘画、雕刻、套印的新版年画“大钟馗”。
传说开元年间,唐玄宗病中梦到终南山的钟馗为报高祖赐绿袍厚葬之恩,誓替大唐除尽妖魅,画家吴道子按玄宗梦中所见画了一幅《钟馗打鬼图》。自从有了这幅图,世人才知道了打鬼人的模样:蓬发虬髯,面目凶猛。绿袍在身,单臂坦露。除妖降怪,神武盖世。所以,所有年画中的钟馗都是怒目圆瞪,面目可怖。
沈全是个爱动心思的精巧人,他根据坊间传说,仔细研究了钟馗的性格特点后,就把自己反锁在屋内,几天几夜过去了,沈全红着眼睛拿出了一幅与众不同的钟馗。
用朱红茄紫藤黄油绿套色印出的新版钟馗头戴长方鱼鳞盔,一左一右的帽翅像两个沾满墨汁的羊毫。绿眉毛绿鼻子紫脸膛,四色虬髯,阔口大耳,两颗长长的獠牙,左手一卷书,上写大吉大利。右手执笔,落墨之处,有“大钟馗”的字样。
真是奇怪,钟馗打鬼没斩妖剑;眼睛不小却无凶猛之光。沈全的新版大钟馗面目威严不失清雅,不似凶猛捉鬼判官倒像点化劝诫之神。镇子上有人就说了,瞎胡闹,这叫什么大钟馗?抱着书拿杆笔,跟妖魔鬼怪说理去?
沈全自有沈全的道理,他说世人皆知钟馗的神武,可他毕竟也是个读书人,“因赴长安应武举不第,羞归故里,触殿前阶石而死”,可见他性子刚烈,把功名看得很重。话说回来,他若是武举得中,荣归故里,人间的妖魔鬼怪也就无人捉了。
古镇上最有权威的沈家老爷子发话了,他说:沈全不拘泥于传统人物的外部形态,属于创新之作,他的大钟馗,有颠覆传统之意趣。若是静心观看,倒也气韵生动,清正神武,用意颇深哪。
说来也怪,虽然“全成”字号的大钟馗面目温和,却受到不少人的认可和推崇。沈全也有头脑,想打造名牌,所以新版大钟馗一上架就价格不菲,销路出奇的好。渐渐地,取代了凶狠可怖的钟馗老版年画。标有“全成”字号的大钟馗不光在国内热销,还远及法兰西英格兰美利坚。有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小伙儿来沈全店里进货,不叫沈老板,直接就把沈全叫成“大钟馗”了。沈全也不推辞,叫着叫着就叫响了。
古镇上商铺林立,经营木刻年画的也占多数。沈全有个叔伯兄弟叫沈金,也经营着一家年画店,眼热沈全的新版大钟馗,就动了歪主意,比葫芦画瓢也制成个大钟馗的新版,字号标上“金成”,抢先注册后倒回来状告“全成”侵权。
沈全接到传票后又惊又气,被人叫了许多年“大钟馗”,没想到这次却实实在在地被鬼打了。更让他伤心欲绝的是,這个鬼不是别人,是供奉同一个老祖宗的本家弟弟。
沈全像当初创作新版“大钟馗”时一样,把自己关屋内苦思冥想了几天几夜,决定应下这场官司。不为别的,“大钟馗”不是徒有其名,他要替自己捉一次鬼。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件件确凿的证据,使得真假“大钟馗”一案水落石出,沈金抢注无效,沈全胜诉。新版大钟馗属于沈全的专利,除了他,谁也不能据为己有。
尘埃落定,沈全却平静如水,做出了个出乎大家意料的决定,他要把“大钟馗”底版上的“全成”字号去掉,古镇上的木版年画店谁愿意卖新版“大钟馗”,他都会亲手刻制底版,分文不取送给谁家。沈全还说:从今以后“大钟馗”不分字号,那是咱相思古镇的“大钟馗”。年画这门手艺也不属于咱自己的私人财产,到了法兰西英格兰美利坚了,人家老外能说这是“全成”“金成”的?人家说这“大钟馗”是China—中国的!
沈全一气儿说出这些话后,古镇上的人都惊呆了,老少爷们儿全拍起了巴掌。沈金一言不发,转身走了。
两天后,沈金捧着一卷画轴来到沈全家,进了门,亲亲热热叫了声哥,接着打开了画轴。也是幅木刻年画,两个童子造型,笑态可掬,悠然自得。一人手持荷花,一人手捧圆盒,盒中有几只蝙蝠飞出。
沈全当然认得,这幅画有名儿,叫“和合二仙”。
有了和合二仙,“大钟馗”从此无鬼可打!
坯王
大柱是远近闻名的坯王。
相思古镇上的人家盖房都会争相请大柱,大柱脱的坯坚硬结实与众不同。别处盖房用青石砌根基,半人高时才摞坯垒墙。可用了大柱脱的坯,那些石料就能省一半儿,大柱的坯坚固得可与石料媲美。
镇东头花戏楼隔壁卖膏药的瘸子老三不屑地说,土坯是土坯,青石是青石,没听说过土坯能和青石一样结实。老三走起来总嫌路不平,一脚深一脚浅地来到大柱干活的地方,呲牙咧嘴憋了半晌劲也没搬起一块坯来。大柱见状一笑,取过一块坯,高高地举过头顶,使劲一摔,硬土地面上便被砸出个大坑。再看那坯,完完整整,还不带掉皮儿裂缝。瘸子老三的眼睛瞪成了牛铃铛,只顾竖起大拇指比划,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瘸子老三回过神儿后就把大柱叫成坯王了。坯王不是白叫的,坯王自有过人之处。大柱身高八尺,相貌堂堂,稳稳当当往那儿一站,就是托塔李天王,两个拳头赛油锤,脱坯不用杵子。大柱的坯模整整比普通坯模大一倍,一下能装八块坯,充满湿土坯后足有七八十斤。别人脱坯图省事就地取土,可大柱总是不厌其烦地起五更到离镇子八里远的李家坡起土,说那儿的土质黏度大且细腻。最为当紧的一道工序是和泥,放水浸泡,反复踩踏,直把那土捣鼓得像麦子粉一样的暄腾筋道才肯动手脱坯。
大柱将醒好的泥奋力摔打堆在一起,脱坯时,双手上前,卡满一捧泥,至模具前再忽地分开,左右开弓,把泥摔进坯模中,两只胳臂忽高忽低,上下翻飞,大拳头腾腾腾砸上九下,扎个马步,端起湿坯,往地下轻轻一磕,八块坯分两行就晾那儿了。
清晨的太阳温柔到极致,即便是不眨眼地看它也不会刺伤眼睛。大柱扛着脱坯用的家伙什出现在杏儿家时,杏儿正站在窗户边那棵桃树下梳头,浓密的乌发瀑布般泻下,头顶上桃花夭夭,蜂飞蝶舞。阳光毫不吝啬地透过满树繁花,把杏儿的长发染成了七彩锦缎。大柱一阵眩晕,揉揉眼,定定神,才看清是个花一般的闺女。
杏儿这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也不晓得让多少人惊羡。辫子长及腿弯处,乌黑发亮。一整天,大柱只闷头脱坯,衣裳甩在柴草堆上,贴身的那件白夏布褂被汗塌得精湿。他不敢再看杏儿,大柱的眼睛让这个长发妹结结实实的给弄伤了。
杏儿来续过几次茶水,每次,大柱听见杏儿细碎的脚步声,心里就像揣了一百只兔子狂跳个不停。杏儿把辫子从胸前甩向身后时,辫梢扫着了大柱的胳臂,大柱一激灵,像过了电。
杏儿说,大柱哥,看你脱坯就像听张天辈说书,你手里也拿着月牙板呢。大柱手没停,脸红得像刚飞到矮墙头上那只小公鸡的冠。
坯王大柱在杏儿家脱坯,起早贪黑,一连干了半个月。杏儿她爹捋着山羊胡子,高兴地围着坯垛子转来转去,连声叫好。杏儿说,爹,是坯好,还是坯王大柱哥好?
都好,都好。杏儿她爹一手拍着坯,一手端个红泥小壶朝嘴里倒水。杏儿说,那爹就把他招过来让他给咱家脱一辈子坯。杏儿她爹一口水含嘴里还没咽就被茶水呛住了,咳了好大一阵子。
杏儿她爹总想把杏儿嫁个殷实人家。坯王虽说有门好手艺,可一个汗珠掉地下摔八瓣儿,终归是个泥腿子,不中不中,不能嫁他。
瘸子老三家有个儿子在城里开店专卖膏药,据说生意好的不得了。前些日子回来进药,在河边儿碰见杏儿了。不见还好,一见顿时傻了,回来就央请他爹上门提亲,说:我进城那年杏儿还是个黄毛丫头,咋一转脸就出落成个天仙了?那长辫子,我的天哪,迷死人了。
杏儿她爹看着瘸子老三家送来的聘礼,高兴得在屋子里待不住,一会儿工夫,端着个茶壶在镇子上走了八个来回。杏儿恼了,说要嫁你嫁,我就看上大柱哥了!
杏儿她娘走得早,杏儿还有个哥哥,脑子不太灵光,就指望着杏儿的彩礼给傻哥哥娶媳妇呢。杏儿她爹比葫芦说瓢,声泪俱下,好话说了一河滩,总算稳住了杏儿。
坯王自从认识杏儿,心里再也搁不下旁人了。坯王想,有了杏儿,这辈子算没白活。等忙过这阵子,就央人到杏儿家提亲,把娘留下的那支凤头银钗送给杏儿做聘礼。
这天夜里,坯王大柱静静地躺在炕上,两手交叉枕在脑后,想着杏儿要是把辫子盘成发髻,再插上银钗和红绒花该是什么模样啊?忽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大柱忙起身开门,杏儿跌跌撞撞地进来,抱住大柱就哭,坯王慌乱不堪。
上弦月,像美人盈盈含笑的嘴角。今夜,因了这弯月,星空没心没肺地乐成了一朵花,它对杏儿大柱的愁苦浑然不觉……杏儿离去时,把两条乌黑的发辫齐根铰下留给了坯王。
一所崭新的土坯房远离镇子,孤零零地立在南岸的柳树下,大柱从此不再帮人脱坯,整日待在坯屋里。有人在夜间见过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问他,也不答话,只痴痴地望着远处。那里,有璀璨撩人的光,是城的灯,杏儿住那儿。
来年八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塌了不少房屋,可相思古镇南岸那座土坯房却完好无损。据说,大柱在脱坯时,把杏儿的青丝秀发剪碎搅合在土中,每一块土坯都散发着杏儿的气息。
如今,坯屋尚在,坯王不知去向……
祭秋
缨子紧紧地拽着娘的衣襟走在十月的旷野里。
相思镇田里的秋庄稼都拾掇完了,褐色的土地像赤裸着胸膛的汉子,惟有一棵枯黄的高粱傲然挺立在地中央。一阵秋风吹过,黄叶簌簌,似在诉说着什么。
地头开有一簇黄莹莹的野菊花,缨子松开娘的衣襟,快步上前连根儿掐断,又飞快地跑到那株枯黄的高粱前,刚要动手折,却被娘厉声喝住了。
为什么呀娘?缨子委屈地问。
娘说,独独留一棵庄稼在田里是有说头的,那叫祭秋,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人丁兴旺。
哦,祭秋……缨子好像明白了。
那个妖精呢?娘突然问。
娘只要说起金雀儿,历来就是这个称呼。
缨子跟爹在城里读书,心里有一百个不乐意,又不敢跟爹娘说。娘死活不去城里住,说是不想看那个妖精。
金雀儿没给缨子爹做小前是个唱眉户的戏子,好歹也算是个角儿,演过《张古董借妻》里的沈赛花。戏里的赛花女本是有夫之妇,被秀才李成龙借去哄骗老丈人家的财宝,不想弄假成真确确实实做了秀才娘子。戏外的金雀儿却被在县衙做事的缨子爹一眼相中做了二房。
缨子爹本无心娶小,只是缨子娘有了缨子以后多年不再生养,缨子爹说,丫头片子终归要嫁人,百年后连个打幡摔老盆的人都没,还不叫族里人笑掉大牙?
金雀儿被收房后便不再唱戏,跟缨子爹住在城东一处宅子里。缨子被爹接进城读书的那天清晨,金雀儿早早起床做饭。别看她自小跟班唱戏,却也做得一手好茶饭。时候不大,桂圆红枣粥,红豆冰糖馅儿馍馍,细细的咸菜丝儿就端上了桌。缨子坐在炕沿上,一句话也不说,大眼睛追着金雀儿的身影转。
金雀儿比娘年輕多了,穿碎花布旗袍,琵琶扣,小圆口绣花鞋,走路轻轻的像在云彩里飘。缨子心说,她就是比娘的腰细些,会打扮些,可不如娘好看,她脸上有浅浅的雀斑呢,别以为旁人看不出来!
缨子吃饭了……正出神想心事的缨子吓一跳。看着金雀儿递过来的青花瓷碗,欲伸手接时,却瞟见她白嫩嫩的胳膊上有一道一道的血痕,结着褐色的痂,缨子吃惊地瞪大眼睛,突然觉得恶心,起身抓起书包一溜烟儿跑了。金雀儿一手端碗一手拿筷子追到大门口,没追上。摇摇头,叹口气,怏怏而回,不知这孩子怎么了。
缨子爹寡言少语,忙完公务回到家中,一进门先把头上的礼帽摘下递给金雀儿,接了她递过来的手巾擦脸擦手后就坐下咕嘟咕嘟抽水烟儿,眼皮也不抬。再不就是撩起大褂快步走到当院里的那株石榴树旁,对着鸟笼里蹿上蹿下的画眉子发呆。每逢这个时候,缨子会轻手轻脚沿着墙根儿溜进西厢房内,摊开书本温习功课,耳朵却听着外面的动静。姨娘金雀儿扎上个蓝花围裙,挽起衣袖忙着升火做饭。如果不是风箱啪嗒啪嗒响的话,这所青砖黛瓦的小院死一般的沉寂。
学堂放假了,缨子被爹送回相思镇。缨子娘围着女儿问长问短问东问西,最后的话题总会落在姨娘身上。
那个妖精待你好不好?待你爹好不好?缨子娘一连串地发问。
缨子说,别的都好,就是金雀儿姨做的饭我不想吃。缨子从不叫金雀儿姨娘。
娘仔细端详着缨子说,我家缨子果然瘦了,脸尖得像我纺出来的棉线穗。
缨子接了娘递过来的糖水蛋,嘴角一撇,说:她胳膊上总有血,一道一道的,真脏。
缨子娘闻言,一怔,不再言语了。
姨娘金雀儿是关中人,自小被卖进戏班子,几乎和家里断了来往。有时金雀儿也会倚院门站着,偶尔听见有关中口音的人就会招呼人家来屋坐坐,东绕西拐,变着法打听娘家的消息。
小院儿里的石榴花红灿灿得晃人眼,金雀儿在这个院子里不知不觉也住满两年了。两年里,金雀儿一点没变,走路还是轻飘飘的似在云彩里飘,腰还是细得一扎就能握住。缨子爹越发沉默寡言,脸上能拧下水来。动不动就回乡下住,把金雀儿和缨子留在小院里。
金雀儿开始频繁地找郎中把脉,吃完汤药吃丸药,吃完丸药吃膏方,把个小院折腾得像个中药铺,就连画眉子的叫声也弥漫着浓重的药味。
傍晚,隔壁李二婶送过来几个红柿,缨子贪吃坏了肚子,晚上起夜时,听见姨娘房中有动静,缨子敛声屏息听了一会儿,像是哭声,低低抽泣,很压抑的样子。缨子就在窗外叫,姨,你哪不舒服?金雀儿没回答,房里却没了声息,缨子讪讪回到西厢房。
次日清晨吃饭时,缨子又问。金雀儿说缨子你发癔症吧?缨子越发奇怪,大人们的事真让人不明白,哭就哭了呗,还不愿承认,真是的。
缨子爹回来了,娘也来了。娘是第一次踏进这个小院,金雀儿乱了方寸,赶紧拢了拢头发跑出来,低眉顺眼站在一旁。缨子娘也没看她,只是拉着缨子进了上房。
夜里,缨子娘熄了灯,坐在炕上搂着缨子,也不说话,偶尔往对面屋看一眼,又看一眼。缨子爹和金雀儿不知在说些什么,身影映在窗棂上,像皮影戏里的人儿,很晚很晚,灯才熄掉。
太阳露了头,画眉子叫得正欢,缨子娘把六个银元硬塞到金雀儿的蓝布包袱里,拉起缨子随着金雀儿向外走。
深秋时分,通往关中的那条官道上几乎没有行人,雾气氤氲中,金雀儿挎着那个蓝布包袱急急地走着,羸弱的身影像田里那株枯黄的高粱……
缨子小声问,娘,那妖精还回来不?
娘劈头给了缨子一巴掌,厉声说:少调失教的丫头,那是你姨娘!
绒花红桃花鲜
花奶奶不姓花。婆家不姓花,娘家不姓花,可妞子非叫她花奶奶。妞子说,谁让她头上老戴朵红灿灿的花呢。
花奶奶住的村子在山那边,妞子说,离城有八百里吧?
小孩子家的话不能信,妞子说的八百里就是很远很远的意思。
妞子就住在离这儿有八百里远的城里。一放假,就被妈妈送回山里来了。
山里真好!有满坡的野花,黄色珠珠花,粉色打碗花,紫色铃铛花,还有花奶奶头上的红绒花。
花奶奶爱说爱笑会唱曲儿。
山里人说的唱曲儿不是咿咿呀呀的真唱,是念;曲儿也不是抑扬顿挫跌宕有致的调儿,是乡谣,一句一句合辙押韵。花奶奶唱曲儿唱得最好,妞子爱听。妞子说,花奶奶的声音脆脆的像炒豆子。
门前有棵木槿花树,花奶奶搂着妞子坐在树下,一阵清风掠过,那些花儿轻舒腰肢,摆动个不停。花奶奶眯眼望着满树的花朵,不知想些什么。妞子说,花奶奶,唱曲儿吧?花奶奶扯着妞子的羊角辫,脆脆地唱:木槿花下有一家,姐妹三人会扎花。大姐扎的红牡丹,二姐会扎白菊花。剩下三姐没啥扎,搬起纺车纺棉花。线儿细细织成布,布上开满木槿花。妞子说,我也要穿开满木槿花的大花袄!花奶奶就笑,笑得头上那朵红绒花颤颤巍巍就像树上被风抚摸过的木槿花一样。
很多时候,妞子缠磨着花奶奶,就坐在花奶奶家的那张雕花大木床上,看花奶奶飞针走线,扎花绣朵。累了,就倒在花奶奶怀里。花奶奶放下手里的活儿,揽过妞子,轻轻拍着唱着:妞子睡,妞子睡,奶奶去地掐麦穗。掐一篮,煮一锅,妞子吃了不撒泼……妞子就在花奶奶唱的曲儿中酣然入睡,做了多少多少甜蜜的梦?妞子扳着嫩嫩的手指,数了又数,数不过来。
妞子眼中的花奶奶和隔墙的那些奶奶们不同,那些奶奶的头上没有红灿灿的花,那些奶奶家都有爷爷有叔叔姑姑。花奶奶家没有,什么都没,就她一个。
独个儿过日子的花奶奶一点都不愿闲着,针线筐里有永远也补不完的烂衣裳和破袜子。每逢这时,妞子就会安静地坐在旁边,两手托腮目不转睛地盯着花奶奶看。花奶奶不时地将针插入浓密乌黑的头发里篦一下、又篦一下,然后停下来,抿嘴一笑,从针线筐筐里摸出仨核桃俩杏递给妞子:小小青杏尝个鲜,二月果子涩巴酸,三月樱桃搁暑天,四月李子甜又酸,五月石榴疙瘩瘩,六月葡萄一串串。妞子说,七月呢?花奶奶就说,想听就要等到下半年唱了。妞子乐得对准手中的杏猛咬一口,酸得眼睛鼻子皱成一团。于是,花奶奶就扑在膝盖上笑,笑得直不起腰,惊得木槿树上的花蝴蝶,急急忙忙扇动着翅膀溜走了。
有花奶奶为啥没花爷爷?这事儿一直困扰着妞子。
妞子在花奶奶那张雕花大木床上翻跟头,翻累了,就睡。隐隐约约听见有抽泣声,妞子翻个身,嘴里含糊不清地叫了声花奶奶,那抽泣声倏地没了。
太阳透过窗棂柔柔地洒进来,妞子把两个绣花枕头并排摆在床上玩过家家,嫩嫩的手輕轻地拍打着枕头娃娃,拍着拍着,惊讶地说,花奶奶,我的枕头娃娃哭了!那枕头足有半截都是湿的。
清澈的小溪从花奶奶家门前欢快地流过,打村东头洼地那儿敛声屏息汇集成一片宽阔的水面,偶尔会有一两只白色的大鸟单腿立在水中,尖尖的嘴巴不时地从水中寻食小鱼小虾,村里人把这个地方叫作东场。
花奶奶经常带着妞子来到东场,靠着棵老榆树,不笑也不唱曲儿,目光追逐着那些大鸟。妞子拉着花奶奶的胳膊激动不已地问那是啥?花奶奶一手拽着妞子的小辫儿一手刮着妞子的鼻尖儿说它叫长脖子老等。等啥?花奶奶的目光就黯淡了,伸手把头上的绒花取下,翻过来倒过去地看,幽幽轻叹一声,半晌才说:绒花红桃花鲜,绒花四季戴发间。桃花杏花年年有,人老不能转少年……花奶奶没说长脖子老等耐心地在水中站立是等鱼吃,爱唱曲儿的花奶奶一脸心事的模样。
一只小母鸡咯咯嗒咯咯嗒从后园溜达着出来了,花奶奶说小母鸡也会唱曲儿,咯咯嗒,找婆家。妞子饶舌地问花奶奶的婆家在哪?花奶奶说傻女子,这儿就是我婆家。妞子又想起那个困扰她很久的话题,有花奶奶就一定会有花爷爷,花爷爷在哪?花奶奶不言语了。妞子越发糊涂,坐在大门口那棵核桃树下,双手支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不远处那条小溪里一群鸭子在嬉戏,听着崖头上放牛郎嗒嗒咧咧地吆喝声,想啊想啊想得头疼……
六月葡萄一串串的季节,痴迷于文学创作的妞子带着她的《新编童诗》和十二朵红灿灿的绒花回到了离城有八百里的山沟沟里。妞子最大的心愿是把这本新书送给花奶奶。花奶奶的曲儿是妞子人生中最早接触到的启蒙教育和文学样式。
柴门轻掩,院子里荒草有半人深。
妞子赶到东场,水面还是那个水面,却不见了老人的踪影。
花奶奶—妞子对着宽阔的水面大喊。
妞子打开那本书,书里收集了四百多首乡谣。妞子说花奶奶,我给你老人家唱曲儿,你听好了:
绒花红桃花鲜,绒花四季戴发间。桃花杏花年年有,人老不能转少年……
妞子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