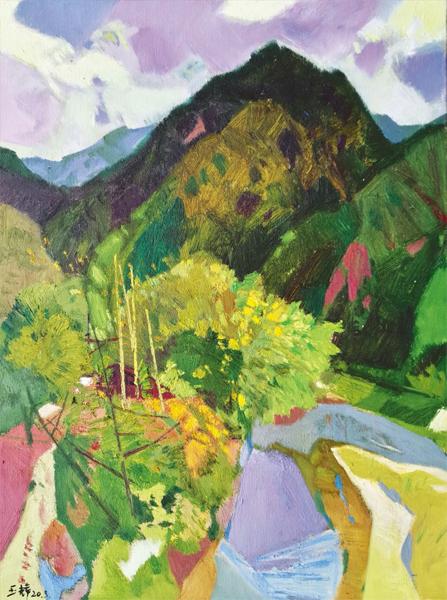
晨雾飘过斜坡,当轻风拂过坡上那一片齐腰高的草丛,几棵草轻轻地抖了抖。那里,艾伦小心翼翼地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酸的颈部与双手。他一动不动地握着一把长程联发弩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坡下小河对岸,是异教徒的地盘。从艾伦记事起,就知道部落里已经和对面异教徒部落打了几十年的仗。战争中,双方你攻我防、你进我退,互有胜负,占的地盘也是犬牙交错。
年少时,他曾经好奇地问过部落里的大祭司,对面的异教徒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打我们?大祭司说,我们的神灵给我们的启示说,他们是一群灵魂肮脏的异教徒,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杀光我们。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杀光他们。
大祭司在部落里是代表神灵意志的。大祭司将部落里所有能狩猎的人编成不同的小组,赋予不同的任务,或小组执勤,或单人执勤。大祭司要求每位狩猎者无论在狩猎途中看到什么都不得在部落里传播,而是要在第一时间向他汇报,违者严惩。只有大祭司有权向部落民众发布消息。对艾伦来说,大祭司是很重要的一个长辈。大祭司看着他长大,还教会了他一身的本事,使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部落狩猎队的一员。
九天之上,两位仙人在观察下界的这片战场。那是他们以山川为棋盘,以人为棋子,布下的棋局。棋局进行中,棋者纵横捭阖,棋子往来攻防,或占山掠川、繁衍生息,或毁山断水、绝敌生机。这局棋约期百年,以己方占地多寡论输赢。因以人为棋子,故名人棋。
人棋,风靡一时,棋者却不在人间,而是在仙界。在人间,在棋盘里充当棋子的人们,一种是得到神灵的启示后,自愿来到棋局中,并遵从启示里得到的法则去做一些事情。另一种则是棋子们的后代。一代又一代,棋局中每一方棋子们,成为同一个部落,信奉同样的神灵,按照同样的法则去为神灵做事。他们以神灵的名义,为了神灵的荣耀去浴血拼杀、攻城掠地、聚敛财富。无论哪一方哪一代,他们都是身在局中而不自知。
身在仙界的对弈者们,可能因为一个不经意的笑话或由头,便在他们俯视的人间里,随意选一处山川设下棋局,又各自按喜好通过祭司向棋子们传达启示去启动棋局。然后,对弈者便在仙界灵山中寻一好玩之处把手为话、对酒当歌。酒半微醺时,偶尔想起棋局,便看一眼人间,下达些启示,动几步闲子。若得酩酊大醉,自会去卧松听鹤,置人间之局于脑后。仙界一天,人间一年。一局下完,也不过就是百天。台面上,或赢或输,只博一笑,当初的由头却多已淡然。虽是如此,私底下,棋手还是会在下达启示时动些心思,以增大自己的赢面。
草丛中,艾伦眨了眨疲惫不堪的眼睛。他已经在这个警戒战位上,专心地观察对岸一草一木快八个小时了。再过一会,就可以下岗了。一阵睡意袭来,他强迫自己睁着眼睛,可脑海里还是出现了几年前的那一幕。那是他第一次独自执行狩猎任务。夜色暗暗的,密林之中升起白雾。他在林中寻找自己的狩猎潜伏点。忽然,咔的一声响,他倒在地上,腿上传来一阵剧痛。他向腿上看去,一排捕兽器的钢牙深深地咬进了裤子里,本该直着的腿已经折弯了,血沿著钢牙汩汩地流了出来。就在神志离开躯壳的前一刹,一个淡黄色的光晕出现在他面前。光晕里是一个仙女。她伸出玉手,隔空拂过艾伦的腿。捕兽器的钢牙裂成几瓣,落到地上。弯折的腿又直了,血不再流了,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艾伦拜倒在地,感谢仙女的再造之恩。仙女叹了口气:“你是被奴役之人,今天刚巧路过,施援手与你,也算有缘。记住不要把遇见我的事告诉任何人。我指你一条路,说不定你将来能脱离这片苦海。”说罢,她伸出手指朝艾伦的额头点了一下。淡黄色的光晕不见了,艾伦脑海里似乎多出一些信息,像一个地图。
以后的几年里,那一幕一直深藏在艾伦的心底,沉沉的,有时会让他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他不敢和任何人说,因为他知道一旦说出去,他面临的将是叛族罪,是死罪。他看过印在脑海里的那幅地图,知道有条路可以让他走出这片山区。可他不能走。因为这里有他的部落,有他的亲人,还有从小到大将他培养成一个出色猎人的大祭司。虽然他曾经好几次在心底自己问自己:“什么是被奴役?”却是一直都找不到答案,也不知道去哪里找。
看看天时,到了下岗时间。艾伦收拾好自己的装备,小心翼翼地清除痕迹后,悄然无息地向着回家的方向前行。就在他翻过坡顶的那一瞬,一支弩箭射入了他的后背,他扑倒在地……
(选自《中国日报》加州版)
李光,笔名木子,现居加拿大渥太华,从事互联网设备研发。加拿大渥太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四季诗社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