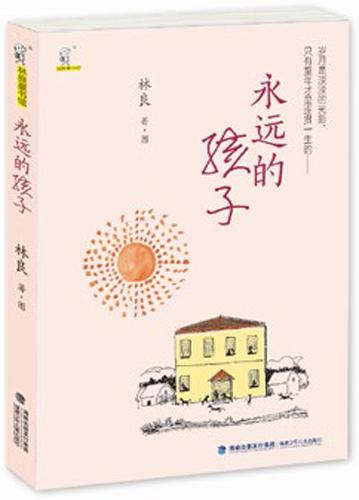
图书简介:
80篇散文,按照時间线索分成四辑,集合了林良先生自幼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他经历辗转迁徙,从富有到贫穷。林良先生用平静的童真之笔叙述,看不到泣诉,只看到因为磨难而更加温暖的亲人、邻里、陌生人之间的珍贵情谊;看不到生活窘迫的萎靡之心,只看到默默承担中也偶尔闪现的生活之光,以及坚毅地为实现理想的努力。《永远的孩子》带读者一起倾听林良爷爷细说——他是这样长大的!一窥“小太阳”温暖魅力的起源。随文搭配林良爷爷亲笔私房涂鸦,韵味十足。
这样的幸福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对不吵架的父母。但是能不能有这样的幸福,全靠运气,因为这是只有父母亲两人才能给的,不是小孩子想要有就能有的。
我很幸运,从我懂事的时候算起,一直到二十一岁父亲过世为止,从没见过父母亲吵架,所以我常常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尽管因为几次逃难,遍历家道中落、人情冷暖的严峻考验,但是并不真正觉得这世界有多寒冷,心中永远葆有一股不灭的暖意。这股暖意,就是相处和睦的父母亲给的。
出现在我脑子里的“记忆画面”,如果主角是我父亲,那画面就是他“和颜悦色”地正在跟母亲说话;如果画面的主角是母亲,那么画面就是她“和颜悦色”地正在跟父亲说话。他们交谈的时候,总是和和气气,好像一个是主人,另一个是来访的客人。
虽然是在家里,他们也很喜欢互相打招呼。母亲要出门,喜欢说一句:“我去百货公司了!”父亲就会说:“路上小心。”父亲从外面回来,喜欢对母亲说一句:“我回来了!”母亲就会说:“辛苦了,坐下来歇歇。”有些家庭是不打这种招呼的,但是我的父母亲好像很提倡。
从小到大,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跺脚、拍桌子、摔碗盘,或者用力关上房门出气的暴力场面。我们小孩子都不知道家庭里会有这种事。直到上了小学,有电影看了,才在电影里看到一些。
英语里有一句话说:“雄辩是银,沉默是金。”我年纪渐渐大了以后,才慢慢知道父亲和母亲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那种情况一出现,他们彼此好像都有了戒心,立刻收起话头,不再争论,尽量让自己保持沉默。
事实上,他们双方保持沉默,不只是不想争论,反而是开始有心相让。在你让我、我让你的情况下,大家反而更能平心静气地检讨自己意见的得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从来不吵架,而且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也较少做出错误的决定。
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但是彼此都能互相尊重。父亲每天清晨五点钟就会爬起来读书,点亮桌灯,研读他的化学课程,所以一到晚上八九点,就会呵欠连连,不停地打盹。因此,母亲和亲戚们晚饭后的夜谈,父亲都可以豁免参加。
母亲喜欢夜读,看章回小说。她习惯扭亮床头灯,读到夜深才抛书入睡。父亲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帮她灭灯,收起掉在地板上的小说,从来不说一句怨言。
在我们家道中落之前,父亲每次要量身定做西服,一定会邀母亲同行。他不相信裁缝,不相信镜子,只相信母亲的眼睛。在我们因为多次逃难、家道中落、在漳州落难的时候,母亲每次变卖首饰,也会邀父亲同行,一来可以避免金店老板计算错误,二来还可以一路保护她。
母亲也曾经为一件事伤心落泪,要找人倾诉。那时候,父亲一定会坐在旁边安慰她。父亲也曾经为某件事难过,要吐露他的心事,母亲就会一边聆听,一边为他倒一杯茶。在那个时候,我会有一个错觉,以为父亲是母亲的父亲,母亲是父亲的母亲。
在我们最后一次逃难之前,父亲投资一家“九龙餐厅”失败,家庭的经济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父亲心情非常抑郁。母亲就建议父亲,每天下午到港仔后海滩去走走,散散心。她不但自己陪着父亲去,也叫我和二弟一起去。
那时候我们住在鼓浪屿。“港仔后”是鼓浪屿西侧一条长长的美丽沙滩。沙滩很美,最适宜散步。母亲陪父亲在前面走着,我跟二弟远远地在后面跟着。我们特意走得很慢,好让父亲和母亲可以自由自在地谈话。
看着他们越走越远的背影,我这个读过许多小说的高中生觉得有一股暖流通过全身:“爸,妈,你们已经给了我们幸福!至于未来的日子怎么过,那算不了什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拼哪!”
剪报
我们在香港等待父亲一位表叔的消息。他早一步到了越南,正在安排我们全家到那里落脚。越南那个时候叫“安南”,还没有独立,是法国的殖民地。
等待的日子里,父亲忙着写信,办理移民手续。母亲在租来的房子里,照顾小弟、小妹,为大家洗衣做饭。我和二弟,一个上过初中一年级,一个小学刚毕业,闲着没事做,父亲就叫我们替代不会说广东话的母亲,每天结伴到菜市场去买菜。
菜市场很大,我的广东话又只会几句,母亲要买的东西广东话怎么说,我不知道;在菜市场的哪个角落才能买到,我也不知道。我干脆把那些东西画成图画,拿去问菜市场入口处的菜摊子。我画过猪,画过鱼,也画过豆腐。其中有一个菜摊子的主人,喜欢我的画,还跟我要走了一张。
跟那些菜摊子混熟以后,买菜变得很顺利,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买完了菜,我们常到没走过的街道去逛逛。有一天,二弟在人行道上发现一个报摊,报摊上摆满了好几种不同的报纸。香港人大都不订报,习惯早早出门,在报摊买一份报纸带到茶楼去“饮茶”。二弟是掌管菜金的,口袋里总有一些找回来的零钱。他看了我一眼,算是商量,就弯腰向报贩买了一份报,好像就是《星岛日报》。
逃难到香港的那一阵子,我们家里连一本书也没带,又没有钱逛书店,所以过的是“不阅读的日子”,心中有一种空空洞洞的感觉。现在有了报纸,就像两个饿汉得了一个热馒头,巴不得能立刻咬下一口似的,真想在街上打开来看。我们又有东西读了!
母亲对我们的自作主张并没说什么。从此以后,买完菜顺手带回一份报纸,也成了一种习惯。一份报纸有好多张,我跟二弟可以轮流看。不久,我就发现二弟读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动了剪刀。他把报纸上的各种刊头、插图、政治漫画、广告图画都剪了下来,汇集在一个大纸盒里。他剪,我也剪。我剪的是副刊上我读了觉得喜欢的文章,我也有我自己的纸盒。我们兄弟两个,总是把每天的报纸,就像母亲说的,“剪得稀烂”。
我也常把二弟的宝盒捧过来看,欣赏他收集的图画。看的刊头多了,有了一些心得。长大成人以后,我无师自通,竟能为我的朋友所编的副刊画起刊头来。
因为天天看报,我和二弟才有机会知道美国迪斯尼拍摄的第一部长篇动画要在香港放映的消息。那部片子就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二弟的宝盒里有他剪下的白雪公主、狠心皇后和七个小矮人的造型。我的宝盒里,有叙述影片拍摄过程的报道,有介绍迪斯尼兄弟怎样从画“米老鼠”开始而成就一番事业的过程。
我捧着我们的宝盒去见父亲,请求父亲允许我们兄弟去看这部电影。我们的剪报感动了父亲,他竟亲自带我们兄弟到香港皇后大道的皇后大戏院去看这部片子的首映,而且给我们买了戏院代售的精致纸偶和周边商品。那部片子,港译的片名是“雪姑七友”。
也因为要看《雪姑七友》,我才有机会进入当年香港最有水平的一家电影院:地上铺着红毯,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吃零食。那气氛跟老家厦门的电影院有很大的不同。为了看这一场电影,父亲花了不少钱,我也觉得在逃难期间这一笔花费等于是一次挥霍,但是父亲却很愉快地说:“你们爱看就好,在别的地方节省一点就是了。”
我和二弟继续每天结伴去买菜,并且买一份报纸回家。我们的剪报越积越多,两个宝盒捧起来都有些分量了。有一天,父亲突然宣布,到越南去的船期已经定了,船票也买好了,三天以后我们就要动身。逃难的人必须学习的功课是:忍痛抛弃身外之物。那两个宝盒就这样安放在香港那间租来的房子的角落,无法带走。我们只能把它带在心中,成为永远不会失去的行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