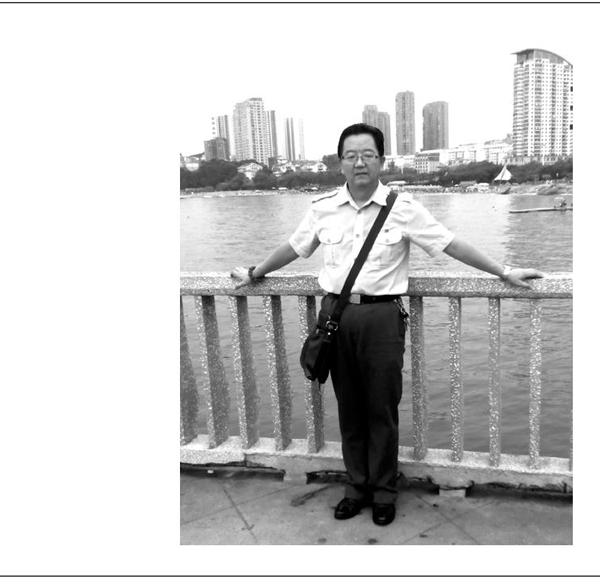
许侠客,本名许金燕。1976年生于甘肃省高台县,1980年进疆。1999年毕业于河南郑州大学新闻系,先后从事过新闻记者、史志编纂、文学刊物编辑等工作。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随笔、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380余萬字,先后荣获石河子、兵团及国家级文学奖项多次。
我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小镇已经工作、生活了9年的时间。小镇中心有一个花园式的广场。每当盛夏黄昏,都能看到许多上了岁数的军垦老人围坐在一起说笑和聊天。在他们的讲述中, 最触动我的是荒原狼的故事。
小镇名叫西古城镇,番号名称是第八师一五0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85个团场中的一个,距离师部所在地——石河子市100公里,是一个水电路三到头、较为偏远的团场之一。
史料记载,这个小镇在明、清时是一个古驿站,左宗棠手下名将刘锦棠曾在这里率部浴血抗击沙俄,在当地留下了许多传奇佳话。小镇地处新疆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1958年建团时,这里风沙肆虐、野兽出没。
那时,内地许多热血知青踊跃报名,来到了西部杳无人烟的大漠、戈壁和荒原,开启了开荒造田、植树造林、改造自然的屯垦热潮。当时各项工作正处于草创时期,工作和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夏天生活用水取自涝坝水,水面上时常漂浮着黄羊、野兔等动物的粪便;冬天则到室外搬回冰块和冻成方块的积雪,放在火炉上坐着的大铁锅里化成水。那时候冬天常常零下40摄氏度,可以说是呵气成冰,大雪厚得埋到了大腿根。男人们身着棉大衣戴好棉帽子,脚上穿着笨重的毡筒才敢出门。回到地窝子,整个口鼻处和帽沿上都凝结着一层厚厚的冰霜,就像一个大雪球顶在脖子上。
这些苦大家都不怕,内地来的年轻人最怕的是荒原狼。寒风怒吼的冰雪世界是荒原狼主宰的世袭领地。女人和孩子只能躲在温暖如春的地窝子里猫冬,只要一听到门框和窗扇发出轻微的响动,就会杯弓蛇影胆战心惊,好像有无数双绿莹莹的狼眼在觊觎着他们。孩子哇哇大哭,女人们感到后脊梁一阵阵冰凉。
冬天寒冷而漫长的日子里,荒原狼成群结队,它们鬼魅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肆意晃动。女人和孩子白天也不敢贸然出门,连队上甚至还发生了白天狼吃人的惨剧。尤其是在冬夜里,荒原狼仰天长啸,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女人和孩子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狼张着獠牙的凶残相还常追到他们的噩梦里来。
几乎每一个夜晚,连队上饲养的驴、骡、马、牛、羊和鸡、鸭、鹅等畜禽都会无缘无故地消失一些。靠近沙漠边缘的几个连队狼害尤甚。
男人们面孔扭曲,紧握拳头,血脉贲张,牙齿被咬得咯咯作响。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起而拯之。连队立即做出决定,抽调连队上的青壮年男人和知青成立了打狼队。猎枪人手一支,由团部武器库配发。打狼队被分成几个小组,对连队及周围进行全天候巡护,畜禽圈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半个月下来,打狼队别说打狼,就连狼的踪影都没看到,狼毛没打着一根,畜禽的数量却仍在减少。
打狼队在荒原狼经常走动的狼道上,加大了狼夹子的布防密度,还把温热、散发着浓重血腥味的野兔肉下在夹子上作为诱饵。第二天跑去查看,野兔肉已经被冻得硬邦邦的,狼群根本就没有触碰一下。打狼队彻底领教了荒原狼狡黠的本性。荒原狼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嗅觉也异常灵敏,只要闻到人类的一丝丝气息,即使诱饵再肥美可口也不会去碰一下,更不会明知机关险恶而去自投罗网。
进入寒冬十二月,天气阴沉沉的,铅云低垂,一场大雪即将到来。打狼队员们又去查看了一下布防的狼夹子,才放心地回到地窝子吃饭、休息。这天夜里的上半夜,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覆盖了连队的地窝子和远处连绵起伏的沙梁子,也盖住了狼道上的狼夹子。
半夜里,一声撕心裂肺的狼嚎声划破雪夜,像一股潮水由远及近传来。有狼被夹住了。被惊醒的队员们个个睡意全无、热血沸腾。打狼队所有队员带着两条猎狗立即出发,朝着狼发出惨叫的方向赶去。
赶到地方,手电筒的光亮照在了两头狼的身上。其中一头狼的一条后腿被夹子牢牢地夹住了。两只狼此时都低着头,奋力地用嘴啃咬着被夹子夹住的那条后腿。被夹住的后腿已被两头狼啃咬得血肉模糊,快要被啃断了。看到有人来,两头狼都抬起了头,满嘴血污,目露凶光,龇着牙,露出了尖利的獠牙,喉咙里发出滚雷般的低吼声。两头狼嘴角上的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掉着,在雪地上砸开一朵朵血花,分外醒目。
队员们明白了,这是对夫妻狼。正巧赶上夜里下大雪,两头狼赶夜路,没有发现被雪埋住的狼夹子。被夹住的是母狼,公狼眼见母狼身陷险境不忍离去,两头狼合力啃咬被夹子夹住的后腿,准备以舍弃一条后腿的代价换母狼脱险。
就在打狼队员们愣神的工夫,一条猎狗邀功心切,往前猛地一蹿就扑了上去,一口咬住了公狼的一只耳朵。公狼负痛昂起头颅反咬猎狗。另一只猎狗见势,不失时机一口咬住了公狼的喉咙。公狼和两条猎狗在雪地上扭打、撕咬起来。一个虎背熊腰的队员慢慢翻转枪,把枪管部分紧紧攥在手里,拼尽全力一枪托砸在了公狼的背上。公狼的脊背遭此重击应声而断,惨叫一声,一下子趴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两条猎狗见状拼命撕咬,公狼不一会儿就呜呼毙命。
看到公狼死去,母狼两眼通红,更加疯狂,整个身子跳起来向两只猎狗反扑,钉在雪地里的地桩链子被扯得哗哗作响。一声枪响,空气仿佛凝固了,母狼的身子晃了晃,重重地摔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再也不动了。两只充血的眼睛圆睁着,望着不远处死去的公狼。
两头狼当晚就被打狼队运回了连队。第二天中午,炊事班在连队场地上架起了一口硕大的铁锅,两头狼被人去皮毛、剔骨,足足煮了一大锅。连队上所有的人都来了,包括老人、女人和孩子,还请了团里的干部。大家热气腾腾、畅快淋漓地大快朵颐,享受了一顿香气四溢的狼肉宴。
一位老人在讲到打死这两只狼的情景和细节时,眼睛里弥漫着一层愧疚和自责的波光,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老人们讲,自从各个连队相继成了打狼队,旷日持久的打狼活动最后演化成了全民的自觉行为,导致荒原狼的种群数量锐减,加之人类的活动范围和空间不断扩张,把荒原狼逼进了生存环境更加残酷的大沙漠。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荒原狼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只能偶尔复活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和一个个传说里。
放飞一只隼
找不出更合适和准确的词汇来界定这只隼和人的关系,权且称之为宠物吧。
我的朋友郑辉,她的宠物是一只隼。每次吃过晚饭后带着这只隼去空阔地带,让隼在高空中散步的时候,郑辉的手里都会拿着一个偌大的线轴。把隼往空中抛去,然后一点一点地放线,隼就会越飞越高。等隼飞累了,再一点一点地收线,把隼从高空拉回到大地坚实的怀抱。一副很奇怪而有趣的场景,像放风筝一样放飞隼。问郑辉这样做的目的和初衷,说是不用线系着,担心隼在高空中会迷路,找不到回家的路。
郑辉在沙漠边缘一个名叫“驼铃梦坡”的景区工作。两年前的“五一”,她陪内地来的一帮朋友去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游玩,在一棵胡杨树的枝桠间发现了一个桌子般大小的隼巢,隼巢里四只张开喙嗷嗷待铺的小雏隼。许是成隼在外觅食遇到了什么凶险和不测,这四只小雏隼早已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不忍心看小雛隼被活活饿死,郑辉和她的朋友生了恻隐之心,便把这四只小雏隼带了回来。
郑辉母性的光辉很足,对弱小和濒临困境的动物充满了怜悯之情。她喜爱隼,收养了其中一只小雏隼。郑辉告诉我,也许是朋友饲养隼缺乏经验、饲养方法不科学,或是小雏隼对人类不信任、怀有强烈戒备心理,另外三只认领回家的小雏隼没有能够存活下来。说起这些,郑辉俏丽的脸庞上梨花带雨,弥漫着浓浓的忧伤之情。
郑辉把认领回家的这只小雏隼视如己出,当做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照料这只小雏隼的“饮食起居”上。
刚开始,郑辉对喂食这只小雏隼缺乏经验和信心,她在网上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隼只能吃精肉、瘦肉和动物的肝、肺等内脏,一丁点不能喂食肥肉,因为隼一吃肥肉,就容易拉肚子,而且很难治好。每天中午、下午下班后,郑辉就到镇里的农贸市场买一些精肉和瘦肉,回家洗净、切碎,喂小雏隼。后来随着小雏隼的食量逐渐增大,郑辉在经济上开始“吃紧”。小雏隼处于发育生长期,一天下来吃的精肉花销在百元左右。后来郑辉就开始买牛、羊等牲畜的肝、肺等内脏。两三天买一次,放在冰箱里冻着。郑辉把有异味的动物内脏和饭菜放在了同一个冰箱里,遭到了丈夫和女儿的强烈反对。
郑辉依然故我,每次在小雏隼“吃饭”之前,郑辉把动物内脏从冰箱里拿出来,先解冻,用清水洗净,再放到锅里用滚沸的热水过一下消毒,把内脏切成均匀小块,端给小雏隼吃,为的是防止有稍大的肉块会噎着小雏隼。小雏隼“吃完饭”,郑辉就开始忙着给小雏隼清洁卫生、梳理羽毛……有了郑辉细心的照料,这只小雏隼的生命得以延续,并健康、快乐地成长。
郑辉与小雏隼建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每次喂食前,只要一见到郑辉,小雏隼就像一个学步的孩子,歪歪斜斜地扭动着双脚,拍打着肉嘟嘟的小翅膀,一头扎进郑辉的怀里。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令人看了心生羡慕之情。
郑辉住的是楼房,在楼里饲养隼不方便,她就把这只小雏隼寄养在了她婆婆家的平房院子里,我同郑辉经常去她婆婆家看望小雏隼。在院子的场地上,小雏隼来回走动,就像一个滚动的肉团。身上肉嘟嘟的,已长出了一些细小的羽毛,羽毛上面是一层黄色的绒毛,一有小风吹过,身上的黄色小绒毛就会飘动,一双黑豆似的眼睛东瞅瞅、西瞧瞧,煞是可爱。拉开小雏隼的小翅膀,末端一排肉质、粉红色的羽管历历可数。喙已呈弯曲状,两个鼻孔分列左右。
那段时间,我正巧借调到郑辉所在的单位,从事景区的文字申报工作,得以同郑辉一起研究和探讨隼的生活习性等诸多话题。我们从网上查阅了和隼相关的资料、信息,根据图像确认,这只小雏隼是新疆隼特有的一个品种,性情桀骜难驯,一般很难在人工饲养环境下成活。郑辉以“保姆”的细心和爱心,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小雏隼越长越健壮。身上的黄色小绒毛已经褪去,羽翼变得丰满,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趾爪孔武有力,显示出猛禽王者的威仪和气度。每次郑辉给小雏隼喂食,小雏隼都像饿极了的样子,叨起盘里的碎肉就是狼吞虎咽,吃相十分凶猛。长到五个月大的时候,小雏隼开始踮起趾爪在院子里拍打着翅膀练习飞行。有时候还能半空飞一会儿,但过不了多久,还会落到地上。郑辉担心小雏隼一不小心会飞出院子,遭到意外伤害,就用一根挺结实的细绳子拴在小雏隼的腿上。慢慢地,这只小雏隼已能在院子的上方低空飞行,但它的腿上多了一根奇怪的绳子。
小雏隼长大了,长成了成隼的模样,两只翅膀完全展开有1米多长。郑辉通过淘宝网购买了隼架、护套、眼罩等全套隼具,对这只隼进行了“全副装备”。在野外放飞时,郑辉就让隼站在自己的手臂上,和隼一起目视前方,俨然成为了驯隼猎人。
但是隼的生活成本太高了,郑辉突发奇想,想让隼在景区大门口陪游客拍照合影,收取费用。她把想法跟景区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负责人当即表态,点头同意。在旅游旺季,这只隼主要的“工作”就是“陪”着游客拍照合影,一人一次10元。隼终于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郑辉非常高兴,脸笑成了灿烂的花朵。
去年八月一天的黄昏,我和郑辉一起去僻静的旷野放飞隼。在我的极力劝说下,郑辉解开了系在隼腿上的绳子。隼越飞越高,渐渐地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郑辉惊慌失措,开始责怪我。就在我暗暗高兴、郑辉彻底失望的时候,隼又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里。郑辉高兴得又蹦又跳。
隼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已经有了强烈的依赖关系,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它在落下来的时候,不小心一头扎进了一块棉花田里,整个身体卡在棉花枝叶中间,动弹不得,两只翅膀无助地拍打着。看到我俩来解救它,隼的眼睛里流露出求助和依恋的神情。
带着隼回家时,郑辉和我都很少说话,一种甜蜜而忧伤的气氛笼罩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