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公巷是我必经路程的一个关卡。
曲折蜿蜒通到尽头,看似死巷,走到拐角处却又柳暗花明,往左又是仄仄的幽深。
这拐角的地方,就安放着蜡烛和祭祀的白的包子、红的粿品,金色白色的纸钱,这些通往阴间的物品像一个黑洞,旋着恐惧。当香火升腾,纸钱随风飞舞,我只有努力地让视线和嗅觉关闭,以为这样能稳住自己的灵魂。
乡间庙宇于我是一种潜在的接近窒息的畏惧,一切皆因这必经路上低矮的神龛。若有路人,那怕是跪在神龛前不断拱手祭拜的老太婆,都是一种阳间的气息壮着我的胆。
这么一条九弯十八曲的巷子,大白天连半个人影都没有,我提着及膝的铁食格(一种桶状饭盒),边走边张望,希望前后能冒出个人影来。
阳光下的我是个张皇失措的影子。
有时屋漏偏遇连夜雨,冒出来的偏是个神经兮兮的人,让我恐惧的泥沙冲溃成哀号的逃亡。一个芦柴棒的女孩,羸弱的身体于我的童年是悲悯的眼眸,眼眸里接收着来自大人小孩的鄙夷,这种鄙夷扩张到“猴子”这个无辜的字眼:猴子如我皮包骨头,这可怜的动物是街坊给我的写真,殃及我对它的忌讳。
大人,在这深巷子里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威胁。每冒出一个,我便用一双深深的眼眸盯着他(她),我的眼睛会直逼他的灵魂,把“好人”和“坏人”给划分出来。这种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像一根线垂到我成人的世界,我依然用它来判断这个缤纷的人世。
走过阴森莫测的神龛,我绷紧的神经松了下来,让我的眼睛能顾及周遭寂寞的世界。陽光照进灰黑的墙壁,上面垂下些一样无聊的植物,水沟边一群觅食的鸡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来自一只跟它们同样觅食的猪。鸡对世界的认识跟我一样,猪正拱着臭水沟里黑乎乎的泥水独自品食。
我提着食格的身子不自觉地加入到它们的行列,我站立身子比鸡群高一丁点,我进入它们里面无忧无虑的热闹,看着它们啄食着沟边布满青苔斜冒出来的绿色植物,只有这些没人管的植物显示着造化的蓬勃生机。
猪的脚步随着拱食的嘴靠近鸡群。
突然鸡群惊飞,惨叫之际一只健硕的母鸡已进入猪的嘴里,长长的猪嘴不停咀嚼,母鸡的形体很快肢解,活生生的脖子和鸡头就在嘴外挣扎,我看着它的眼睛和鲜红的鸡冠,它给我最后的一瞥,就消失在猪的嘴里。
在我惊呆的一刻,吞下一只鸡的猪也向我朝来一瞥。
这一瞥,有着盗贼般的深意:我是一个知情者。
这一瞥的凶光,直射我的心脏。我意识到它眼睛和嘴巴的距离是我危险的所在。我是鸡群中的一只。我像那只鸡一样毫无反抗之力。我第一次发觉体积庞大者的力量。一只鸡被吃掉了,毫不留痕迹。一滴血、一片鸡毛也没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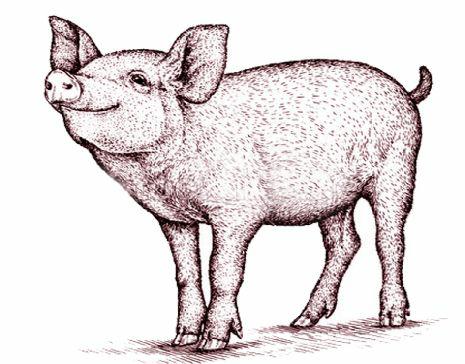
脑中的空白,只有面前这个庞然大物,还有它那犀利的眼神,我提前食格,转身踉跄而逃,继续伯公巷接下里的路程。那路程已经缩短在这只猪的阴影之中。
这只猪依然在我身后若无其事地拱食。
晚上,哪家会发现丢了一只鸡,这只鸡无缘无故地从地球上消失了。说不定会惹来邻里的猜忌。谁也不知道这水沟边发生的一幕,除了一个路过的小女孩。
那只猪或许在鸡之后不久也成了人们的盘中餐,世界上并不会因此多了些什么或少了些什么。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我一直在我的光阴里不时咀嚼着那几秒钟的一幕,渐长的身量和见识,一直无法除去脚下这鞋底般的一页。食草的猪在那一刻的血腥,笨重的猪在那一刻的身手敏捷,世界上有多少真相让我用一双童眼窥见。
那一只猪的阴谋和罪恶。
选自《草根纸上的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