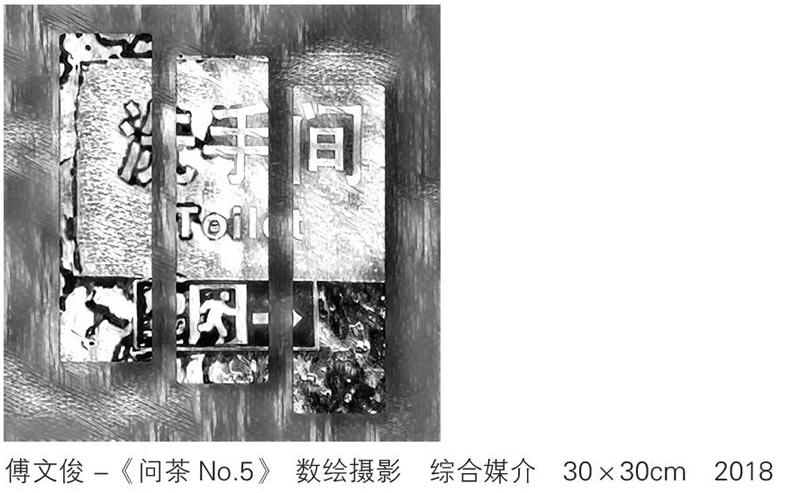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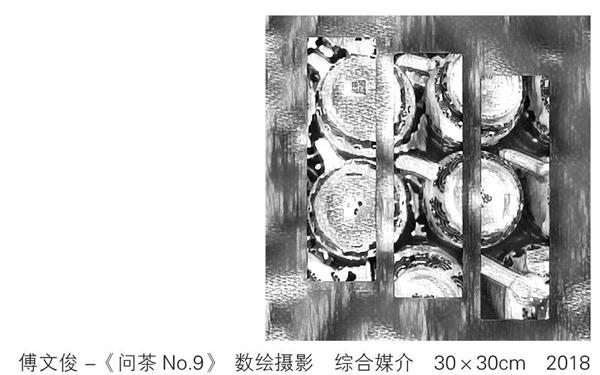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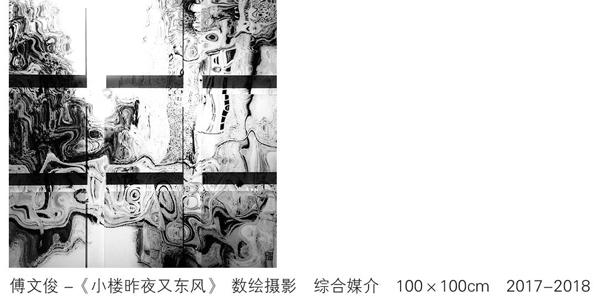
你是个幸运之人。在时间的每个节点上,在命运的每个转角处,你都无需做什么。无需你操心什么。命运之绳自有人帮你提着。在别人奋力拼搏的时候,你只管袖着手。你所有的事情都被人提前安排好了。被安排是种常态。一向如此。那是最好的安排。费尽心思,曲线救国。不可稍作修改,也不可稍作增删,否则会露出破绽,会不完美。你有现成的秩序,现成的待遇。你的位置一直在那里,你只要按部就班去接受就行。在你的生活里,你似乎是另外一个人。你看着自己像木偶一样被人牵过来牵过去。你能够看到另一个自己。这种状况你没有反抗。曾经有过的反抗苗头老早就被掐灭了。然后慢慢习惯,习惯于这种被安排。你不动脑子,因为不需要你思考什么。你经常要做的事情是报到,登记。填写各种表格,比如姓名包含曾用名、民族、籍贯、出生年月以及直系亲属,当然还有身份证号、住址、邮箱和电话号码。个人申报事项。诸如此类。通常,人们经常会被要求填写这些东西。你不知道已经填写过多少次了。接着你被安置在某个地方。在那个位置上,你要学会说那些规定好要说的话,做那些规定好要做的事。这些都很容易。无非是你的身份衍生物。就像什么样的身份应该穿什么样的制服,什么样的身份也就应该说什么样的话。这是同样的道理。所谓规定有些是明文写在纸上的,是公告。有些则是约定俗成。你与常人无异。你愿意接受被安排,是因为你从小就知道,那些安排是你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可以不走弯路。是可以得到实惠的,也是别人想得到却又得不到的。你被告知,别人奋斗也好拼搏也好,想要的也不过是你已经得到的。这个毫无疑问,你是幸运的。关键是你将以此度过一生。你的人生道路不可复制。你是可辨识之人。事实上你性格温和,甚至有些懦弱。你是个很听话的人,老实,明事理。所以你不危险,任何时候你都不会制造出任何危机。你单纯平庸而且轻信。你信奉规则,相信道理。很多时候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按照道理你必须做什么便自会去做什么。你让人放心,绝不会出乱子。某些人以道理之名支使你。你过着被安排同时也被支使的生活。你没有个性,个性对你是多余的。这样挺好。能給你安逸,也会让你觉得安全。你不与人争执。但你是个好人。很多年份里你都在单位被评为先进分子。你强调被人羡慕的那一面。在县城你有体面,受人尊敬。你拥有很体面的家庭也拥有很体面的生活。
当我见到你的时候,你的头发还很浓密。我惊异于你头发黑漆漆的,没有变得灰白,也不曾脱落的状态。你的面孔无忧无虑。戒毒者颓废的症状和高亢的志向在你身上都不曾出现。你气定神闲。你说出去后你还会继续上班。我问你在哪里上班,你说是药品监督管理局。你还补充说,你戒毒还能拿工资。拿基础工资,没有奖金和补贴。他们做了工作,没有开除你。
“他们”是谁?这个称呼将反复出现。
“单位领导很关心我!”你告诉我,你是领导送进来的。我们在阅览室闲聊。我对这次采访不抱期待。所长说你是公务员。我不相信你能跟我说什么。你已经四十一岁了,一眼就能望到职业生涯的尽头。从前你是药品稽查队的队长。你说回去后不会再担任这个职位了,领导和你交代过。我问你对此有想法吗?你愉快地回答我说,没想法,领导的考虑很周全。你说,你是个有前科的人了,肯定不适合再当队长。可能会为你另行安排一个闲职,但是级别不会变。你不需要关心这些,领导对你自有安排。
你小时候成绩不好,注定考不上大学。读到高二,父亲忽然让你报名参军。老师和同学都很意外,这意味着你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但是你不问为什么,糊里糊涂就当兵去了。你父亲年轻时在部队做军医,转业到县医院,是外科一把刀,由外科主任做到医院院长。县医院院长官职不大影响却大活力也大。你母亲是县妇联主任。他们都忙碌,在你儿童时期没时间管你。家里没人做饭,你被安排在县医院食堂吃饭。吃食堂长大的孩子和在家里长大的孩子性格上有差异。吃食堂更有纪律。你那个年龄理应滋生出的野性被食堂纪律磨灭了。你的父母只是不管你吃饭,他们在其他方面把你管得死死的。比如在你读高二时就把你送到部队去了。你参军先是在北京,后来被调到河南信阳,再被调到湖北孝感,最后又被调到黄陂。黄陂是武汉郊区。你当兵四年,被调动了四次。这是很奇怪的调动曲线。而且,在部队期间,你还进入武汉理工大学培训了一年半。我问你这一年半培训发文凭吗?你说不发文凭,只发结业证。退伍后,你被安排在幸福县药品监督管理局。刚报到不久,就被送到党校学习三年,拿到本科文凭。回到单位顺理成章当上药品稽查队队长。你那些高中同学,辛辛苦苦考上大学也就是拿个本科文凭。你没遭那个罪没受那个苦也拿到了一样的本本。他们对你侧目而视。在他们眼里,你无疑是大赢家。就算拿到本科文凭,也很难找到好工作。他们若想当公务员,还得经过又一轮考试。万人争过独木桥。不像你,你从文凭到公务员再到升职,一气呵成。故事的转承启合衔接得严丝合缝。你背后有只手,所谓无形之手。提着你的命运之绳,把你提到这里,再把你提到那里。你是只灯笼,提着你能在暗夜里发光。听说你姐姐是军官,驻地武汉,军衔上校。姐夫也是军官,驻地南京,军衔大校。你说他们马上就要调到一起。有关他们,你没有提供更多线索。
你由此尝到甜头,不证自明。就像某种植物,适合怎样生长,就会怎样生长下去。
那是一个过程,一个被催眠的过程。你从来没想过被唤醒。催眠者和被催眠者始终是双赢的,或者多赢。我看着你的头颅,你硕大的头颅。我突然对你的头颅产生兴趣,不可遏止的兴趣。我开始思考你的被动人格是怎样形成的。“被动人格”是我给出的命名。倒不一定确切,可是我又不知道怎样指认你。总之你不需要主动。主动对你来说是多余的。凡事你只要被动承受就行了。就像我们眼中的某件物品,你不必把它拿到手上,它自己会以某种方式到达你手中。比如杯子,你想喝水时,它自会靠近你嘴边。这么说有点过分,近似于巫术。这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虽然很接近,但不是事实。事实是你无需去敲命运之门,你也不知道命运之门在哪里,但是它们都已在暗处依次为你打开。
因此,我猜想你脑子里有些地方被关闭了。这大概是必然的结果。你在,一直都在,长期被灌输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恰恰又是最好的东西。你不由自主地接受就可以了。无需思考也无需判断。不就是被提着吗?不就是被安排吗?脑子里当然会关闭一些地方,因为不需要是吧,因为用不着。那么,你脑子里被关闭的那些地方——会不会慢慢失掉功能呢?
由你的头颅,我想到了老家里的邻居。我不该想到他,想到他对你有些失敬。但是没办法,你的头颅引导我想起了他。那时候我住在幸福县河西小区,那可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啊。每到夏天,我们整栋楼上的人都会走出家门,到楼下的河滩去乘凉。我的邻居是位脑萎缩病人。他的头颅和你的头颅一样硕大。他是乡下一个村里的民办教师,教体育。曾经是个很强壮的男人。他体罚学生,也打老婆。他老婆是当年的武汉下放知青。知青嫁给他之后再没能回到武汉。她也当了民办教师,后来转正,双双调到幸福县城。他刚成为我的邻居时,就是个脑萎缩病人了。他总是呵呵笑,笑声像是婴儿或傻子。所谓脑萎缩,我以为是他的头颅会渐渐萎缩,就像摘下来晒蔫了的瓜果——渐渐变小。但不是这样,他的头颅从来没有变小过。真正的萎缩可能发生在他的头颅内部。
乘凉的时候,知青总是当众指责他,指责他年轻时怎样殴打她。
她说,“你那时候那样坏,没想到现在也会落到这步田地吧。”
在我的印象里,他从不顶嘴,总是呵呵笑。知青后来得了乳腺癌,切除了一只乳房。她又说,这一次是对围观的人说,“他每次要那个,总是猴急猴急,像畜生扑腾几下就完了。又不摸摸我,如果他知道摸摸我,至少能早一点发现我里面的肿块吧。”
听到她这么说,他也还是笑,呵呵呵。围观的人笑得更起劲。我的邻居是我们乘凉时的活宝,总能带给我们欢乐。他们身边环绕着欢声笑语。但是他们是真正的悲剧人物。悲剧人物的要素在他们身上一样也不缺少。知青非常要强,她一定是不甘心做悲剧人物。她故意幽默,故意调笑。她在这样抗争,以此消解他们身上的悲剧。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的笑容并不是他当时的真实表情。他脑子里给出的是另外的指令,而他脸上呈现的却是笑容,是呵呵呵的笑。即他脑子里想要做的——和他正在做的往往不是一回事。他的意志和他的行为是脱节的,不一致。这是知青亲口告诉我的。比如他脑子里想着要上床,结果却坐在地上了。意念与动作相悖。知青不只是在外面指责他,她同时还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患难夫妻。没有她精心照顾,他不可能又活过三年。
三年之后他才去世,而知青到现在还活着。她住在廣西,和她的小女儿生活在一起。听说她还是那样口不择言,拿那些在别人眼里属于禁忌的事情取笑调侃。她嘲笑癌症,嘲笑自己不翼而飞的乳房。她还嘲笑死亡。很可能,她也正是以这种蔑视的姿态和老不正经击败了乳腺癌。
我不是想说女知青的故事,我是从她老公的头颅想到了你的头颅。他死去了,他的头颅我还记得。你们的头颅都很硕大。我再一次想到硕大。你会步他的后尘,也成为脑萎缩病人吗?慢慢变小。我不是说你的头颅外部,而是它的内部。被压缩,关闭的地方被挤压。他的经历当然不能和你比,没有可比性。可是这种病的诱因是什么?难道你被安排被控制的大脑就不会萎缩吗?我疑虑重重。刚好我有个朋友是脑科医学专家,我把你讲给他听。问他你是否有脑萎缩风险?他的回答明显是在敷衍我,就像是从百度上搜索到的肤浅知识。他是个苍白的人。他如此敷衍我是源于他对作家这个行当持久的不信任。他认为,如果把医学比作眼睛的话,那么文学就是白内障。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白内障!他说,有没有脑萎缩要做CT及MR检查。要靠仪器和科学说话,肉眼看不出来。不过,他又说,脑萎缩也有些外在的病理症状。仿佛是恩赐,他又跟我讲了一些。比如性格变异智能下降、痴呆、发白齿落甚或偏瘫癫痫。我查了一下,他说的这些,百度上也能找到。我特别注意到癫痫。在我看来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我就是固执,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但是在戒毒所里,你身上没有这些症状,至少暂时还看不到。
那么,我所想到的脑萎缩,或许不是疾病想象,而是精神想象。你是个标本。
所长说,你被选为戒毒所的学员组长。你在外面很听话,在这里面也很听话。听话是你的本色。你总是那么无怨无悔地听话。多么好。你带头唱歌,歌声嘹亮。你劳动积极。行为举止既端正又规范。你说,他们讲道理讲得清楚,讲得通透,讲到本质上去了。你说的他们,指的是戒毒所里的干警们。他们讲戒毒的道理,句句都是为你们好。他们设置的各种科目,所作的各种规定,也都是为了你们戒毒成功。所以,你都要无保留遵守。
从这里看,你的戒毒前景一片光明。
有人说,你父亲做军医时,曾经救过一位高级将领。机缘巧合,他以高明医术救了那神秘领导性命。这个被掩盖并被秘密流传的故事,至今无法得到证实。我不太清楚这个故事是不是杜撰。若是杜撰,又是谁杜撰出来的?它太像民间流传的旧时候的故事 。贵人落难,之后知恩图报。怎么就有那么巧合,好运为什么会从天而降?问题是你父亲确实得到了不明来由的庇护,同时,庇护还延伸到了你身上。你所有的被安排,源头就在那个故事里面。除了这个故事,再找不到别的源头。
从求学开始,比如高中二年级,你的人生道路被简化,被修改。有一支笔在勾勒你的人生。你不过是那支笔里的墨水。看似是墨水画出的轨迹,实则是笔在写你。随意地把你写到这里,或者写到那里。参军文凭就业都给你安排好了。那些位置,椅子都摆放好了,你坐过去就行。既然如此,同样的道理,你的恋爱婚姻也应该被安排。这是必然。你父亲果真看中了县医院财务科的一位出纳。那是他的手下,他对她观察了很长时间。她温厚贤良,是做儿媳妇的合适人选。没有比她更合适的女孩,你父亲把他的意见转告你母亲。你母亲也私自去作了一番考察。她考察的内容倾向于持家和生育能力。两人的结论都没有问题。他们的意见有惊人的一致性。于是,请人去做媒,提亲。出纳像中了彩票一样高兴。真是天上掉馅饼,她做梦也没想到能到院长家做儿媳妇。许多女医生和护士都这样想过,到头来却是财务室的出纳梦想成真。
房子安排好了,日子也安排好了,马上可以举行婚礼。
你还没有过自己的恋爱,这没有什么。对你,恋爱不是不被允许,只不过是你还没有机会开始。你父亲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粗暴、专制。他的隐秘想法倒是希望你在婚姻之前就能获得性经历乃至性经验。他不愿意亏待自己的儿子,谁愿意亏待自己的儿子呢?这方面是有途径的。可是他没有告诉你,也没有和你交流。他可能囿于某种道德感,有些羞于启齿。这是他唯一没有为你安排的事情。你父亲没有安排你如何在婚前得到性,事实上你因此也就没有得到。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反正你对此一无所知。你母亲希望你结婚的时候,女朋友仍然是也必须是个处女,但并不勉强你也是处男。这一点他们夫妇有相同的想法。你父亲没有安排的事情你母亲更无从安排。在你结婚前,他们没有为你安排一桩或数桩风流韵事。你的生活里于是也就没有了风流韵事。这件事只能证明:你不仅已经习惯于被安排,而且还在等待被安排。
婚姻可以安排,那是组织家庭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万万马虎不得。既然恋爱没有被安排,那么恋爱也就不会出现。没有被安排的生活是无效的生活,也是不道德的生活,或者根本就不是生活。这么一想,你也就释然了。
你读党校时认识了郭蓓蓓。她有过短促的婚史。不是婚变,是丈夫早早去世了。有一天她和你聊天时告诉你,她结婚之前就知道丈夫是绝症病人,将不久于人世。他们俩有约定,丈夫希望她生下或至少在他死前能怀上他的孩子。他的意思是,即使他已死,也有骨肉之躯以他的名义活在这世上。之后郭蓓蓓可以另嫁他人,她带走孩子也行,把孩子留给他的父母也行。与其说这是约定,倒不如说是请求。奇怪的是郭蓓蓓居然接受了他的请求。没有谁绑架她的意愿,她是心甘情愿接受的。她认为丈夫是个纯粹的人,是个天真的人。她愿意以生殖为目的,与一个将死之人维持短暂的婚姻。
可是他们虽然结婚了,她却并没有怀孕。郭蓓葆悄悄去做了检查,原来是她的身体有毛病,此生她都不能怀上孩子。她独自吞下苦果,没有把如此不幸的消息告诉丈夫。在她预见到丈夫即将去世的前一两个月,她欢天喜地地谎称自己怀孕了。她模仿并逼真表演出孕妇的各种表现。尽力把谎言说得可信。她丈夫为此数度哽咽,感激涕零。她贪吃,无端呕吐。信誓旦旦地要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赛跑。她要跑过它们。她最怕的事情是大姨妈如期而至,并被丈夫意外发现。好在没有发生。因此,丈夫是怀着幸福去世的。
你不知道,郭蓓蓓为什么要把这件事的隐情告诉你。别人眼里的她是个忧伤的寡妇。在你这里她是另一个样子。只能说她对你有好感。她对你的评价和她死去的丈夫一样。碰巧你也是个纯粹的人,天真的人。她对纯粹和天真有很高的评价。拥有这种品质的男人,她只碰到了两个。一个是她没能为其生下孩子的丈夫,另一个便是你。丈夫撒手去了阴间,而你还在人世。
在我采访你的时候,你跟我讲到了郭蓓蓓。你反复强调那不是恋爱,即使她的确向你表白过,也称不上是恋爱。我相信你,也和你意见一致。你可能只是觉得和她聊天很愉快,她是那种让你很舒服的异性。她的傲慢和矜持收敛起来了,她在你面前敞开着。有一天她说爱上了你,这是她的命。你很惊讶。甚至你有些被吓着了。事情不是那么突然,可是从她嘴里说出来,你还是有些茫然失措。你说这种事情要和你父亲说说,或者和你母亲说说。郭蓓蓓说,我知道你的家庭状况,所以你不一定要和我结婚,我只想和你谈一场恋爱。有没有结果我不在乎。话说到这个份上,你算是明白了。可你还是迟疑,主动的一方是郭蓓蓓。你们约过几次,仅限于聊天,还没发展到上床那一步。不是女人的问题。是你!你躇踌不前。郭蓓蓓说,你就像是在等候某个迟迟没有发出的指令。真让人难过。郭蓓蓓说,她都想要强暴你了。事实是,如果她真能强暴你的话,你也就坦然接受了。但是,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你是这种性格。
恰在这时,院长和妇联主任安排好了你和医院出纳的婚礼。你毫无怨言地同意了。你顺从他们。当时,你们家还开了个简短的家庭会议。院长介绍了出纳的品德和个性,妇联主任重点说到了出纳的持家和她潜在的生育能力。她拿到了出纳的体检报告,还出具了几份她同学或同事的证言。然后,他们一致认为,出纳比较适合做你妻子。她是他们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是她能和你组成体面而又稳定的家庭。不会有流言蜚语。她能做家务,还会在最好的时候生下你们的孩子。
你说好,谢谢父亲,谢谢母亲。
郭蓓蓓听到这个消息后哭了一场,她眼里这个纯粹天真的男人很快就要有家室了。她和别人合伙送了份子钱,前来贺喜,参加你的婚礼。这是幸福县的礼节,熟人朋友都会来。她在宴席上把自己喝得大醉,随后和桌上的异性挨着个儿亲吻。一边亲吻一边恣意大笑。有的男人事后说吸进了她的口水,里面有股苦涩的滋味。另外的男人回忆说,她的口水里还混进了泪水。当然是她的泪水,不可能是别人的。邻桌上的人用手机拍下她的丑态,在微信朋友圈广为传播。拍摄者肯定是女性。你也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她鲜艳的嘴唇在照片里咧得很开,像是巨大的伤口。
第二年,你和出纳的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儿。你被人羡慕,该有的你都有了。正如你的学历和职业被安排得无比完美一样,你的婚姻家庭也被安排得欣欣向荣。该有的什么你全都有了,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孩子恰到好处地在她该出生的时候出生了。一切都很体面。你有房。你还买了车,车的档次中等偏上。能有那樣一部车很不错了。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在县城,能把日子过成你那个样子——可以称得上美好了。
结束了对你的采访之后,我私下里跟戒毒所所长探讨过你的未来。我对此次采访颇有些意犹未尽。我有态度。我觉得你太顺利了。你从前的生活太顺利了,你在戒毒所里的戒毒生涯也太顺利了。所长耐心地听我说,他真是有教养,等我说完了,他才开始说话。他其实也很担心你。他对我说出了他的忧虑。他说你在戒毒所里表现得太好了,恰恰是这种好让他担心你出去后还会出岔子。你太听话了,因此太容易被支配。你是个不设防的人。对所长说的不设防这种说法我持不同意见。我认为,可以说你是不设防的,也可以说你对有些事情的防备很严密。所长想了想,认为我说得也不无道理。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你总是自动接受那些强加给你的东西。你永远活在道理里面。这个其实很可怕。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没有自己的道理,你的道理全是别人给你的东西。人家这样说你觉得有道理。一旦那样说,你又会觉得有道理。凡是有道理的东西你都能接受。所长打了个比喻,你之所以在戒毒所表现积极,是因为你认为干警们让你戒毒是有道理的。到了外面,假如另外有人,比如也有能力把继续吸毒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设想一下,他也有能力把他的道理灌输给你——相信你还会重新吸起来。我们无法排除这种人,这正是所长的忧虑所在。
我和所长的观点不谋而合。你是个什么都被人安排的人,防范你不再吸毒不一定只是防范你自己,更要防范那些为你作安排的人。我们有理由信任你,却不能信任所有为你作安排的人。所长犀利的眼神从眼镜片后面盯着我。我又问所长是否知道脑萎缩这种疾病,他说不是很了解。我说像你这种情况,脑子会萎缩吗?所长说不知道,但是萎缩这个词语令他印象深刻。它好像是一个持续的可见的动作。比如脑子里的沟回如何蠕动。比如像软体虫子那样爬行。他还想到了实物,比如放久了的茄子。放久了的茄子太有冲击力了。看来所长也有很好的联想能力。他被我勾起了好奇心,建议我就此事专门去咨询一下医学方面的专家。
正是在所长的提议下,我前去拜访了那位脑科医学专家。他的回答我在前面说到过,也转述过。他的观点貌似很中立。我的意思是,那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中立,更是顾左右而言他的某种策略。原因无非是他对文学怀有戒心,作家对疾病的描述和想象,在医生看来很有可能只是旁门左道。他担心,我从他那里获得的咨询结果,会对我的咨询对象有失公允。所以,他才会那样谨小慎微。
可笑的地方在于,我对医学专家的请教就像是在电脑上百度了一下。整个过程即使不是味同嚼蜡,那也是如同在默默地吞食苍蝇。
你是药品稽查队长,这是你进来之前的职务,也是你被安排的职务。这个职位的职责就是管理全县的药品市场。所有药店和流动人口中的黑市交易,都由你管。它所包含的内容至少有:查出来的问题你都有权力放人家一马,或者不放。在当时就是这个样子。谁能保证药店没有问题?换句话说,每个药店的经营都有问题。这个说法当然有些夸张,但所有的药店都可能会被整顿,被罚款。这也是你的职责所在。有的罚款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很久没有被整顿,有的频繁被整顿。这些事情都由你决定。你说过,出去之后你可能不会再担任这个职务,你会被安排另一个闲职。级别不变,待遇不变,但是不再管具体事情。
可是在当时,药店老板都要想方设法巴结你,请你吃饭。他们排着队请你。每次吃饭你都坐在首席。刚开始,你还谦让过,后来发现那是你必须坐的位置。你不坐,老板便一直站着。于是你不再谦让。吃饭要坐在首席位置上,这个事在你生活中其实具有隐喻意义。那是安排好了的事情。位置从来都是安排好了的。他们在你面前卑躬屈膝。你渐渐会明白,他们敬畏的是你的身份,你的稽查队长这个职位。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多事情都好理解了。吃过饭,还要请你泡脚,或者去唱KTV。他们还给你红包。红包里包着购物卡优惠券或现金。你也曾经拒收红包,我记得你说你推辞过。那些药店老板便苦口婆心劝告你,跟你讲道理。你不收下就是不给他们面子,瞧不起他们,你这是在当面打他们的脸。实话说吧,收下红包也是请你吃饭的应有之义。你不能不给他们面子,也不能打他们的脸。你接过红包,也算是收下了这应有之义。应有之义,说得多好啊。换了别人,也会这样。道理是明摆着的嘛。想通了,彻底想通了。
然后,就到了那一次。在KTV包房,两个药店老板在请你。就你们仨,没有别人。随从们都打发走了。都是自己人。吃过饭,泡过脚,也收了红包。你准备唱两支歌就回去。歌都替你点好了,你打算唱《弯弯的月亮》和《涛声依旧》。如果实在不让走,再加唱一首《北国之春》。都是你从前唱过的。唱得虽难听,也算是有个交代。你是主宾,是主角,不给个交代说不过去。把歌唱完,你这一天也就结束了,你也可以回去了。这时,两个老板中的一个拿出麻果。实际上他们两个是一伙的,他们经常在一起搞这个。所以,东西是由这个或那个老板拿出来无所谓。你也不记得到底是谁。你只记得他说,玩玩这个吧,醒酒。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玩。那还是你第一次见到,你本能地想拒绝。你说不玩吧。另一个老板赶紧说,玩吧,醒酒,还提神。现在都在玩这个。都玩吗?你还问了这么一句。是啊是啊,有钱人有身份的人现在都在玩。那两个老板笑着说。他们还随口列举出了好几个人的名字。那些人的名字你都熟悉。都是些很有面子的人,他们玩的话,你也可以玩。两个老板先做示范,每人带头搞了一颗。
你也搞了,你在那天搞了第一次。
出纳洗衣服时,发现你口袋里有颗麻果。她不认识,问你是什么,你说是药。但没说是什么药。她有疑问,带到医院去问药房同事。同事也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出纳有个亲戚在派出所工作,她又拿去问他。亲戚一看就说,这是麻果,是毒品。
你父亲退休了,母亲也退休了。这是大事。虽然这不是他们安排的事情,但是事情发生了就要想办法解决。他们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又出面了。需要为你做出新安排。你父亲认为,首先必须戒毒,这是第一步。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做到。你母亲坚决拥护。他们给你讲道理,你很快就醒悟了,愿意配合他们安排。戒毒方法共有两种。一种是在医院自愿自费治疗,另一种是在戒毒所强制戒毒。他们选了第一种,治疗为期五个月。你去了,先治疗了两个月。后来他们发现这种治疗不合理,容易反复。因为医院环境松懈、开放,从前吸毒的同伴总能找到你,联系到你。他们这才决定,把你转送到强制戒毒所。你父亲和你单位领导商量过,这是他们共同作出的安排。问你愿不愿意,你愿意。你当然愿意,你怎么会不愿意?对你的所有安排,你都会愿意。你父亲深信这一点,即使你不小心走了弯路,他也能把你拉回来。并且,你父亲还深信,即使他们作出了前后不一样的安排,你也會遵从。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安排对你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从戒毒所里传出的关于你的消息都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你父亲并没有在开头几个月的会见日里前来探望你。他在十五个月之后才来的。以他的测算,十五个月足以令你的戒毒成效达到最好的峰值。他满头白发,身躯高大,躇踌满志地向你走来。我在探视人流中老远就看到了他,他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
但是你的第一次癫痫发作,正是出现在你父亲探望你的那个会见日。这是多么令人痛苦和难以理喻的事情啊。你理应让他看到你戒毒成功无比光鲜的那一面,不巧却让他看到你癫痫发作。你父亲透过玻璃,亲眼看到你扔下话筒栽倒在地。你全身抽搐,口吐白沫。你被抬了出去。你父亲没有大喊大叫,他捂着眼睛,没有让自己看到从你裤管滴下的尿液。你母亲也在场,她在等待你和父亲对话结束后,再和你说话。她没有等到。她说,以前可没有癫痫病。你父亲恼怒地说,确实没有。可是以前没有,并不意味着现在没有,以后也没有。他分析道,你的癫痫病很可能是由脑部疾病引发的。脑部疾病是个什么病?你母亲不依不饶地问道。你父亲却在反思,把你送进强制戒毒所是对还是错。
他们当天就把你接出去了。据说你出来后再没有发作过癫痫。就只那么一次,却把戒毒所的干警们吓着了。所长介绍说,把你从会见厅抬出去时,还伴有其他症状。你流涎水,口鼻歪斜。牙关紧咬,死命闭合。尿液淌了一路。身体抽搐。脑袋像挂在脖子上一样摇晃。我询问过所长好几次,你那种症状是不是跟脑萎缩有关系。所长坚持说不知道。没有人能够回答我,谁也回答不了。或许只有你的家人,在你出去后带你诊断过。但是,他们对诊断结果守口如瓶。我没有去问那位医学专家,我相信他会对我的问题嗤之以鼻。
后来,我听说你在大街上遇到过郭蓓蓓。你已经不认识她了。她试着和你打招呼,你没理她。你和她擦肩而过。郭蓓蓓还不死心,她在后面尾随你。尾随你走过两条街道,目送你走进医院。她抬头看了看医院大门,十分困惑。她居然忘记了你的家是不是就在医院里面的家属院里。如果是,意味着你正在回家。如果不是,那你去医院干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