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编《董桥七十》,即刻买来,尽管其中的文章读过了一部分,但不妨碍重读。董桥文章有重读的价值。
《董桥七十》中有《七十长笺》,是董桥的自序,是新文,一如旧文,记人言事,情理相应,字响调圆。该文有一段文字言及书法,不佞细细瞧来,发现诗意融融的文字,没有切中字学肯綮,慵慵懒懒的絮叨,把市井轶事,当成真相,看着,总觉是看一段废话。
提及刘墉的书法,董桥拿一个小故事说事:刘石庵和翁方纲都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翁方纲极认真地模仿古人。刘石庵则正好相反,不仅苦练,还要求每一笔每一画都不同于古人,讲究自然。一天,翁方纲问刘石庵:“请问仁兄,你的字有哪一笔是古人的?”刘石庵却反问:“也请问仁兄,您的字,究竟哪一笔是您自己的?”翁方纲听了,顿时张口结舌。
这则故事典出何处,姑且不论,细究对翁方纲和刘墉书法的指陈,顿见扞格。一、中国书法是文化接续性极强的艺术,离不开古人的遗韵,甚至书法艺术评判的标准,也要看临习的火候和融会的分寸;二、刘墉的书法明显胎息颜真卿、苏东坡,如果翁方纲问其刘墉的字那一笔是古人的,我也要问,翁方纲对书法史的了解究竟有多深,有多广。显然,董桥相信了翁、刘的这段对话,并确认刘墉的书法是“艺术书法”,笔笔属于自己。另外,董桥对刘墉学书经历的描述也有问题,他说:“刘石庵远窥魏晋,笔意古厚,初从赵孟頫入,人到中年自成一家,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一点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董桥说对了一半,刘墉书法的确笔意古厚,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但不是初从赵孟頫,更不是“一点不受古人牢笼”。
康熙皇帝喜爱董其昌,我们便想到他对后人会产生影响。刘墉乃乾隆体仁阁大学士,当然知道前朝皇帝的喜好。但,这不是说他初学赵孟頫、董其昌的理由。刘墉说自己初学锺繇,观其书作,此话靠谱。刘墉生活于乾隆之世,博通经史文学,书名显著,时人将其与邓石如、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伊秉绶视为有清第一等书家。董桥说刘墉“初从赵孟頫入”,不是自己的发现,乃人云亦云耳。至于“一点不受古人牢笼”,更是差强人意。分析书法家,重要的依据是作品,一位书法家临习了什么碑帖,腕下自有表现。刘墉的书法有锺繇流韵,同时,也有二王、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的影子。刘墉后期作品,得力于颜真卿,沉实、厚重,不然,人们不会以“墨猪”相讥。
在书法学习和创作过程中,刘墉的字来路清晰,流转有序,是古典书学的正脉,深得世人喜爱。不过,刘墉的确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有时写字,不拘法度,努力写出个人气概。“然他试图力避宋人米芾尽力尽势之缺点,却又过于蕴蓄,缺少纵逸之气”(王宏理语)。董桥说“我倒偏爱石庵的‘自己’了”,权且视为一种姿态而已。
我一向注意董桥谈字的文章,比如《字缘》、《倪元璐的字真帅》、《梁启超遗墨》等,头头是道,加上绵绵细雨般的文笔和湿漉漉的笔调,煞是好看。董桥讲到自己看字的习惯——“我看字也常常带着很主观的感情去看,尽量不让一些书法知识干预自家的判断;这样比较容易看到字里的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看台静农的字有文人的深情——“台静农的字是台静农,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许多地方固执得可爱,却永远去不掉那几分寂寞的神态。这样的人和字,确是很深情的,不随随便便出去开书展是对的。他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把心事满满挂在展览厅里毕竟有点唐突”。我敢说,这段谈字的文字,是当代书论的华彩乐章,没有专家的生硬的强调,多的是才子的灼见和感慨。
董桥谈字,最好不具体,一旦具体,就有破绽。他说沈尹默的字“有亭台楼阁的气息”,鲁迅的字“完全适合摊在文人纪念馆里”,郭沫若的字“是宫廷长廊上南书房行走的得意步伐”,显然是一孔之见。至于袭张大千旧说,认可台静农是“三百五十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并强调“许多年过去,台先生的字我看得多了,真实漂亮,真是倪元璐”,恰恰是他“带着很主观的感受去看,尽量不让一些书法知识干预自家的判断”,结果是“容易看到字里的人”,没有看清字的本身。
台静农在《静农书艺集》的序中写道:“余之嗜书艺,盖得自庭训,先君工书,喜收藏,耳濡目染,浸假而爱好成性。初学隶书《华山碑》与邓石如,楷行则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皆承先君之教。尔时临摹,虽差胜童子描红,然兴趣已培育于此矣。”
台静农先生对北碑、二爨也下了功夫,我看过台静农的碑体书法,雅重行实,超凡脱俗,苍劲沉稳。他以楷书、汉隶的基础染指行草书,格调不同凡响。
说他是“三百五十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所指当然是他的行草书。台静农的行草书,提按险峻,八面出锋,风驰电掣,线条、节奏,易见荒疏、激荡。人们愿意拿台静农的行草书说事,甚至把书法家的台静农,解读为仅写行草书的台静农。这一点,启功先生也看出来了。启功先生与台静农先生在辅仁大学时就有情谊,《台静农散文选》中《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一文,其中提到启功带他往恭王府拜访溥心畬的旧事,称“吾友启元白兄陪我们几个朋友去的”。相隔数十年,启功先生见到台静农先生托人带来的书法,瞩字思人,言称台静农先生是“一位完美的艺术家”、台先生“隶书的开扩、草书的顿挫、如果没有充沛的气力是无法写出的”。又说台先生“与其是写倪黄的字体,不如说是写倪黄的感情,一点一画,实际都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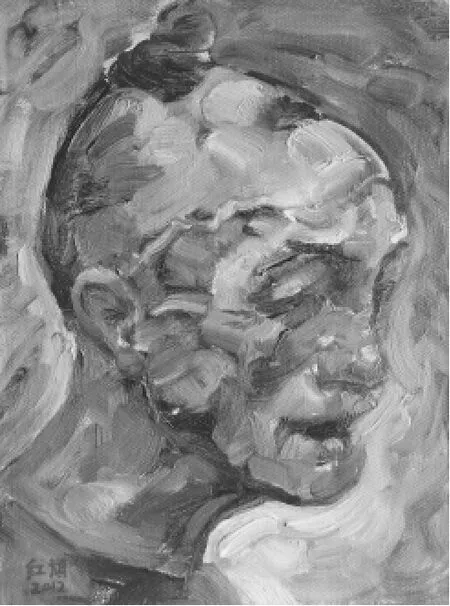
陈红旗作品-《巫师》 30×40cm 2012
至此,我明白了董桥对倪元璐的推崇,对台静农得益倪元璐书泽的强调。“明代的从容文化浸淫出了素美的沧桑颠倒了多少苍生,政治的挽歌一旦化为山河的呜咽,传统唯美意识终于款款隐进末世的风雨长亭:道统盛宴钗横鬓乱,人文关怀余温缕缕,几代星月繁华的艺情匠心难免空遗宣德名炉沉潜的紫光;政统摇落的一瞬间,桃花扇底斑斑的泣红宣示的岂止媚香楼上佳人的伤逝!”。于是,这位“我看字常常带着很主观的感情去看”的人,低吟着对倪元璐书法的谶语:哪一个字不是一念执著的看破?甚至家仇国恨的不甘也许也夹杂着那份浑金璞玉的难舍。
董桥谈字,偶有政治化,也不难见信口开河。在《张秀本色》一文中,他说“胡先生那手字是娟秀的东坡体,少了雄浑多了清畅,我最爱看,早年南洋有个会馆集他的字做招牌也很气派”。胡先生即胡适,大学者,字真就一般。从上海的中国公学,胡适考取第二次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名额,在异国他乡,他接触了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文明,包括政治的、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等等,使胡适眼界大开,并开始深刻反思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优劣。去国数载,胡适不仅没有兴趣探求书法,就连给他带来无尚荣耀的中国字,也以怀疑的目光去审视了。在美国,还没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拿到手,他就匆匆归国,赴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位,开始以学贯中西的头脑,来推动新文化运动了。果然出手不凡,几篇文章,几首新诗,就塑造出一个别出心裁的大师来。这位有历史癖的大师说“但我相信,汉字实在是很难学的教育工具,所以我始终赞成各种音标文字的运动,我始终希望音标文字在那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对中国文字的改革,胡适一直关心。在谈到中国固有文化的优劣时,他说:“依我的愚见,我们的固有文化有三点是可以在世界上占数一数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我们的语言的‘文法’是全世界最容易最合理的。……文法是最合理的简易的,可是文字的形体太繁难,太不合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美国纽约做寓公的胡适,对新政权的文字改革工作密切关注,据他的学生、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大陆的文字改革方案一出台,他会马上找来细看,一边看,一边称赞。对中国文字的忧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关切,它说明,一个具有国际意识的学者开始有的放矢地拆除横躺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障碍。他对文字的复杂心态,就能理解他对书法的复杂心态。
胡适不能以书法家称之。他的墨宝有人文价值,却没有艺术属性。他用毛笔写的字是名人字,而不是有历史传统的文人字。董桥言其“是娟秀的东坡体,少了雄浑多了清畅”,耸人听闻了。
胡适与苏轼书法,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不能等量齐观。董桥定位苏东坡书法为“娟秀”,乃根本之误解。苏东坡五言古诗《和子由论书》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可学。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刚健含婀娜,几成后人解读苏东坡书法的美学基础。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中杰出的代表,诗文书画俱佳。苏东坡对颜真卿情有独钟,又上溯二王,于书法学习、创作,甚至是理论探知,有着系统的规划,明确的追求,因此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用笔方式和“刚健含婀娜”的艺术风格。以“娟秀”言之,乃有盲人摸象之虞。
董桥与胡适有相同之处,在国外呆的时间有点久。人的大脑是有限度的,拉丁文字挤占多了,中国的方块字就要模糊。胡适、董桥如此,季羡林、钱钟书、吴宓、曹禺亦然。董桥的文章有意境,有识见,有情感,是学人之文,是智者之文。正如他说:“我要求自己的散文,可以进入西方,走出来;再进入中国,再走出来;在入……总之我要叫自己完全掌握得到才停止,这样我才有自己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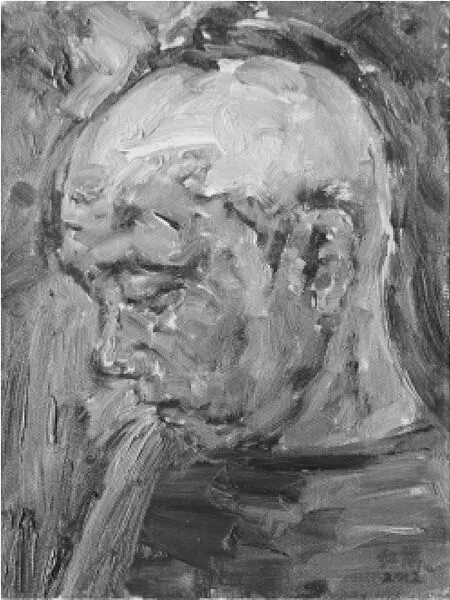
陈红旗作品-《下葬的人》 30×40cm 2012
董桥谈字,也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依循写散文的感受“可以进入西方,走出来;再进入中国,再走出来”,显然要出问题。董桥喜欢楷书,张充和般隽永的字,是董桥致命的诱惑。在《张秀本色》一文里,董桥表达了自己书法审美的取向——“书法我一生偏爱楷书行书,尤其小楷书小行书,真本领,真性情……小时候家中大人天天叮嘱写字一笔一画有头有尾才富泰,才长寿:字无福相,人无福气。我从来信,老了还信,不写难认的蓬头草字,一见俞平伯沈尹默张充和眉清目秀的小楷忍不住都想要。”
因此,他极其排斥草书——“草书笔走龙蛇,都造作、都矫情,摆出假名士潇洒的样子其实满肚子是机关是密圈”。为什么这样呢,董桥道出心声:“草书难读,世人不懂,不合时宜。乔旸前几天从上海给我寄来新印祝允明《草书杜甫秋兴八首卷》,认识的几个字确实好看,不认识的那些字也懒得费神核对原诗了。”
不认识草书,是他不喜欢草书的理由。正如同读不了英文的人,面前摆一本英文版的善本书,也不会动情。应该说,草书是中国书法的代表书体,笔法、字法、墨法,气韵、神彩、格调,要求极高,绝对是书法家的真本领,真性情。同时,对欣赏者也提出了专业的要求,既,要懂书法史,要懂草书代表性书法家和作品,最好还要有临帖的实践。草书的学习、领悟、判断,是需要时间积淀的。这一点很像是对交响音乐、京剧和昆曲的欣赏,如果我们不明白演奏的曲目,不明白唱腔,不明白角色的特点,对演员也一问三不知,自然不会找到一条平坦的审美途径。看来,董桥对草书的拒绝,真如他所讲“也懒得费神”。这是董桥自己的事情,我们需要尊重。然而,他说“草书笔走龙蛇,都造作、都矫情,摆出假名士潇洒的样子其实满肚子是机关是密圈”、“草书难读,世人不懂,不合时宜”,大大露怯了,让我们看到当代才子不“才”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