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离开故乡贵阳已有十三个年头了。十三年来,我为了生存和生活而奔波劳碌,始终疲于奔命,因而曾经与我的生命密切相关的许多故乡的人和事,也都在时间的无情冲刷下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但总还是有些人和事是难以忘却的,是注定要铭记终生的。何士光先生就是我时常惦念和怀想的人物之一。当然平日里也还是淡忘,如果不是有人刻意提起,我大约也不会记忆起我和他交往的那些点点滴滴。但是,那天,事有凑巧,我偏偏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无意间看到了一则关于他的消息,说是在他当年被下放的凤冈县琊川中学,如今建起了一座“梨花屯图书苑”,同时还建起了一座“何士光旧居”。博文配有图片,文图并茂,使我能在遥远的他乡异地再次清晰地观瞻和打量我久违的何士光先生的容颜,也再次见识了他的那一笔优雅的字体——不用博客主人介绍,我也能一眼看出,“梨花屯图书苑”和“何士光旧居”那几个字,都一定出自何士光先生的手笔。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见到士光先生了?从照片上看,他的身体还是一如既往的健康、硬朗,身材也还是像先前那么清瘦。先生退休后一心向佛,遍读释家经典,又亲自练习和实践一种养生的气功,我因此很难相信他也会有年老体衰的那一天。但仔细看,也还是看出了时间的痕迹,到底是肉体凡胎啊,任谁都经不住岁月的消磨和剥蚀。先生的背明显有些弯曲了,额头上的皱纹也增加了不少。但他的笑容,就依旧是那么的灿烂而慈祥,安静又平和,俨然一个现世的活菩萨。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几位亲人,一位是我所熟悉的师母周乐碧;另一位是他的女儿,这面容于我有些陌生,但从长相上可以看到明显的遗传特征——我以前去过先生家不知多少次,却似乎一次也没有见过他的女儿,我只在他的散文里读到他对于这个生长在乡村跟他一起经受了若干时代厄运的女儿的一些描述,后来零零星星听过一些关于她人生命运的传闻,印象里,仿佛也是相识相熟已久的故人了,但实际上却始终未曾照过面,想不到这一回却是在网上见识了;还有一位大约是先生的女婿和外甥吧?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博客里也没有详细介绍……总之就是这样的一家子人吧,都齐刷刷地聚集在新落成的“梨花屯图书苑”前,参加着由当地政府为其主持的庆典仪式……
我仰慕先生久矣!1980年,当先生以一篇《乡场上》横空出世轰动全国一夜闻名的时候,我就刚刚从黔东南一个极为偏僻闭塞的侗族山寨来到了他的家乡贵阳,进入大学念一年级。那时候,我虽然也爱好读书,但还不知道文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记得教授我们《文学概论》课程的,是一位姓郭的老师,当他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讲解着先生的这篇成名作时,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从此我知道了人间还有一种美好的事业叫写作。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一直疯狂地阅读先生的作品。我那时虽是一介贫寒学生,但却极尽所能地购买了先生业已出版的所有书籍。我对先生所写文字的迷恋,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中国当代的文学中,先生的作品是格外与众不同的,可谓独树一帜。先生的文学语言承接五四传统,追求古雅修辞,却仍以现代白话文为主,文白交融,又不失流畅自然。其叙事节奏舒缓,描写和刻画又细腻又饱满,字字珠玑,韵味无穷——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何士光先生的文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在相对独立的单元和段落里,最末一字基本上都是押韵的。我早年特别陶醉于他对古典诗词与现代汉语的那种极尽自然的巧妙糅合,看似不经意,却又独具匠心,最终浑然天成。如“在那有鸣苍庚的日子里”,“不思量,也自难忘”……还有,往往在句末了,先生会突然反问一句,“是不是呢?”像是在跟读者商量似的。“那么”也是先生最常用的字眼,这也还是商量的口气,使你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都能感受得到一种亲切。
说起来,我正是受到了先生文学的启蒙,才羞怯地拿起笔来涂鸦一点东西的。最初几乎全是毫无节制的模仿——事后想来,那时其实也不是想要刻意去模仿,而是还不懂得怎样去摆脱——当然无一成功。后来终于面见了先生的时候,我谈到对他作品的模仿一事,先生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还是要努力建立起自己的风格为好。”又说:“哎,其实,任何人的写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我刚写作的时候,也模仿过别的作家。”话语里似乎既给人指明了道路,同时又表露出了对年轻人的极大关怀和宽容。那么在这之中,从我最初拜读到先生的文字,到后来我真正面见先生,其间大约相隔了将近十来年的时间。而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于先生方面来说,其一面继续经营和开拓着他的文学事业,把他的文学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甚至创造了连续三届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辉煌成就,叙写了贵州文坛一段令人仰止的神话,一面也经历着他人生事业的巨大转折——他先是从遥远的凤冈琊川调回了故乡贵阳,先在贵州省文联得一个职位,继而入主贵州省作协,当起了作协掌门人并兼任《山花》杂志的主编。而于我而言,命运也一样的有所改变,我先是在他的家乡贵阳读完了四年大学,开始尝试着写了一点不成样子的东西,并凭着这些东西很幸运地被留在了省城贵阳工作,而我单位的宿舍就紧紧地挨着省文联的办公大楼,那么理所当然地,我就有了更多的接近作家的机会。我那时虽然已经开始发表了一点文字,但对文学还是十分陌生,自然就会对所有作家都十分的恭敬。于是经常地,我会跑到文联去闲逛。去得最多的是苗族作家伍略老师的家和《南风》编辑部。一来二去之间,我就难免耳闻目睹贵州作家的种种逸闻趣事。这自然也包括了先生的事迹。我那时对先生的文学成就是愈来愈敬佩而景仰了,欲面见先生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但始终缺乏机缘。尤其使我深感妒忌的一点,是当时贵州许多的业余作者,居然都莫名其妙地拥有一本甚至多本由先生亲自签名赠送的新书,而我却无缘见先生一面,就更不用说还能有机会跟先生讨教和索要赠书了。
时间一晃就是十多年过去。那么大约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吧,我记不清是1992年还是1993年了,或者是更晚的1994年,总之是有那么一回吧,我破天荒地获得了一次参加由省作协主办的文学活动——当然那时我已经正式在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了,《山花》还给我出过个人小辑,《花溪》也连续发表了我好几篇大家认可的文学作品,我想士光先生此时对我的名字也不应太陌生;尤其幸运的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册一套的首辑“贵州文学丛书”中,我与先生各有一本,而且都是那十册中最薄的——我们先是被安排去一个烟厂参观,乘车途中,我居然就跟先生坐在一起了。我记得当时自己的心情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紧张,但我尽量克制着自己,故意表现出一种很平常和很自然的样子。然后,我们聊了起来。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士光先生对我有印象,应该就是从那一次的交流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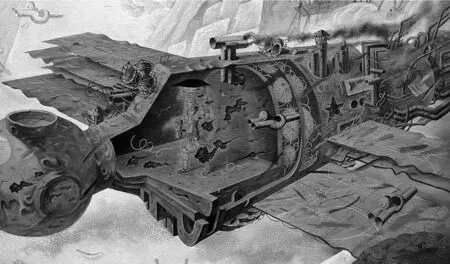
徐松波作品·大象鸿蒙局部3
这之后,我和他的交往就日渐频繁了。他似乎也比较关注我的写作状况,尽管我并没有拿出作品去向他讨教什么的,但从我们的交谈中,可以得知他看过我的一些作品。他对我一面是鼓励和鞭策,同时寄托着相当大的希望。1994年,在他的主持下,我被推荐到全国参与庄重文文学奖的评选,结果我如愿评上了。这是我平生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项,也是我从事文学创作至今获得的唯一奖项。虽然后来阴差阳错,我最终也没能出席那个在成都举行的颁奖仪式,但荣获此奖,于我提升自己的写作信心确有很大帮助。而我后来的写作证明,我的确没有辜负先生的希望。“你是可以写出好作品来的,”有一回,先生十分诚恳地对我说:“你有那个能力,也有那个生活的积淀。”受到这样的勉励,我当然不敢再像之前那样懒散和懈怠,那几年在创作上的确暗暗下了点功夫,成绩也有较大进步,先后在《上海文学》、《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1995年,贵州省作协召开我个人作品讨论会,士光先生亲临会场,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的创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先生主持《山花》工作期间,曾亲自为我编辑过一篇稿子,题目叫《月亮山见闻录》,是一篇纪实的散文。我把稿子恭敬地呈献给先生。这是我第一次拿着稿子向他请教。“好,先放我这里,我看看再说。”他的表情依旧像先前那么谦和。大约一个礼拜之后,他约见了我,说:“稿子我看过了,写得很不错,可以发,但你还得再拿回去改改。”他把稿子交还给我。我展开一看,顿时目惊口呆,原来他用红笔把我的稿子改得一片通红,完全面目全非了,我的脸颊似乎也立即潮红起来。我哪里料想得到,这篇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的稿子,竟然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毛病,我内心当然惭愧无比。我按他的要求把稿子拿回家重抄了一遍,也认真地琢磨被先生修改过的地方,我当然只能是由衷的敬佩。后来那篇稿子就在《山花》上刊发出来了。不过,后来收入文集出版时,我还是采用了我原先的底稿,而没有采用发在《山花》上的定稿——我觉得那个经过先生过分润饰的文稿,其实已经不是我的东西了,除非署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我才有胆量收入我的个人文集。

徐松波作品·大象鸿蒙局部4-1
那么除了关心我的创作,先生也还关心我的生活。有一回,他问我:“你目前生活上是不是有些困难?”我说是的。那时候,我每月工资不到100元,而我的爱人当时又还在遥远的家乡县城工作,两地分居,往来奔波,生活的成本增大,难免时时捉襟见肘,陷入困顿。“这对写作是有影响。”他沉吟道。之后不久,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份第二职业,就是到省林业厅去编辑一份关于林业方面的文学杂志。时隔多年,如今我已然记不得当年接洽我的那位编辑的尊姓了,但却十分清晰地记得她的大名叫“凤翥”,因我是拿了先生所写的介绍信过去的,我当时并不认得这“凤翥”的“翥”字,就问先生这字怎么念?先生说:“凤翥嘛,就是凤凰高飞的意思,《诗经·大雅》上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晋人陆机《浮云赋》,‘鸾翔凤翥,鸿惊鹤飞,鲸鲵溯波,鲛鳄冲道’;韩愈《石鼓歌》也有‘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的句子……”传说先生博学而记忆力惊人,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我认识先生的时候,他已经疏远文学了,而开始沉迷于佛学。我和朋友每每去他家求教,话题一打开,他所说的基本上都是他个人学习佛家经典的心得体会,我们于此鲜有常识,因而多半只能洗耳恭听,难有插话的机会。那时,文坛的江湖里常常传言先生性格孤傲,并不平易近人,而我接触到的先生似乎与此恰恰相反。因为我们每次到先生家去打扰,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夜,先生从来都是既温和热情又言语滔滔的,从未对客人有过半点冷遇和怠慢。我记得有一回,我和诗人陈绍陟前往拜访先生,正聊着,突然间先生家里的电话就响起来了,有人说要过来拜望他,他说,来嘛,来嘛,潘年英和陈绍陟也正好在这里。来人很快就过来了。一番客套和谦让之后,他又继续聊起我们先前一直聊着的佛学话题。那些人听着听着,就兴奋起来了,嚷嚷着要喝酒。先生说,好哇,可惜没下酒的菜。那些人说,没关系,有酒就行。于是,先生给他们打开了一瓶上好的习酒。那几位老兄毫不客气地豪饮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瓶酒倒干净了。然后吆喝着辞别而去。先生把客人送走,回头又来招呼我和陈绍陟。我问:“这些人都是哪里的啊?怎么那么狂放啊?”先生说,他跟这些人其实也并不熟悉,只知道他们是来自黔北地方的。
先生素食。不吃肉。不饮酒。但吸烟。好几回,他都说他最后会把这烟也戒掉。但我离开贵阳时,他似乎还没有把烟戒掉。现在不知道戒掉了没有?
有一年,我家乡天柱举办文学笔会,我和先生都被邀请过去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生活了18年之久的贵阳,去到遥远的福建泉州,谋求新的人生。那么此次与先生重逢于我的家乡故土,我内心当然有无限的欣喜。在天柱三门塘清水江畔的一处草坡上,我和先生沐浴着暖暖的故乡夕阳,交谈了很久。“为什么要走呢?”他问道,似乎对我的出走很是不解。“换个环境。”我说。他点了点头,说:“嗯,其实,你最后会发现,到哪里都差不多。”我们就这样漫无边际地闲聊着。远处隐约传来侗族姑娘忧伤的分别歌。《山花》杂志的编辑黄祖康先生过来给我和先生照了不少照片。我想那画面一定很美。可惜后来祖康兄一张照片也没有给我。我多次向他索要,他都说有,但又说照片太多,太难翻了。“什么时候有空我翻出来给你吧。”他每次都这样说。他哪里知道,我平时是从未向人索要照片的,这回之所以那么执着,实在是因为那照片于我太有纪念意义了——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我和先生唯一的一次合影。
记忆里我与何士光先生最近的一次见面大约是在三四年前吧?那次是他在一家企业里做关于老子和庄子的讲座,我又被曾经的诗人好友现在的牙科医生陈绍陟先生邀约着一同前往聆听。说实话,士光先生的课讲得那真是太好了,比我们大学里的那些牛皮哄哄的教授博士真不知要强多少倍,也比我们电视里那些貌似口若悬河的明星人物不知要好多少倍!他没带一页讲稿,但他对《道德经》和《庄子》的任何一章都能信手拈来,倒背如流,而且,他还能完全凭借记忆讲评各种版本的利弊优劣,如果没有经年累月的积累,是断难有这等功夫的。遗憾他并不在大学里教书,也很少在公众场合里显露自己的口才和学问。我记得那天先生的讲演结束后,很多人还要继续围着他发问。我没机会跟他交谈,只远远地跟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之后再没联系。我与先生似乎向来都是这样,相逢相遇时,自然可以做推心置腹的交谈,但转过身,似乎一切都立即淡忘。不通往来,江湖相忘,既没有书信联络,也从不电话问候。我想,这恐怕就是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所谓君子之交吧!
几年前,据说先生退休了。其实退与不退,于先生的生活而言都应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我听朋友说,退休之后的他,一如既往地每天坚持在家参禅打坐,研习佛经。小说似乎就不再创作了。但最近却突然拿出了一个叫《今生》的长卷来,部分章节发表在由年轻一代作家们主持的《山花》杂志里。我立即很认真地拜读了。先生的文字还是那么的凝练和老辣,我不能不说依旧迷恋和喜欢,但我在这样的文字里,看到的已然不再是文学的感动,而是生活与生命本身的伤怀了。
从照片上看,“梨花屯图书苑”与“何士光旧居”的建筑都承袭黔北民居的风格,并且有刻意仿古的韵味。楼是新楼,砖也是新砖,但都被涂成了老旧的黑灰色。我料想先生是比较喜欢这种颜色的。先生早年有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就叫《青砖的楼房》。大概楼房的设计者们不会不知道这部作品吧?那么可以想见,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当我才刚刚出世,当先生恰好正值青春华年,从大学校园毕业,满怀憧憬走向未来的时候,他哪里能料想得到人生会突然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转折呢?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将他发落到了这里,这个被他命名为“梨花屯”的一处偏僻乡村,他在这儿挣扎沉浮,而后又在这儿奋起腾飞……你说他还有什么荒诞人生没有遭遇和经历过呢?因此要说还有谁能比先生更理解这片土地,我是不会相信的。那么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两处楼房作为历史的见证,纪念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文学历程,这是怎样的可喜可贺啊!可惜山高水长,信息闭塞,我事先没有得到任何的音讯,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前往祝贺的,至少,我可以发去一份贺电或贺信。而眼下我就只能写下这样一篇简陋的文字了,权且作为我对先生的一种特别的问候和致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