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卡厚先生作品集《逐梦》一书,由线装书局出版社于今年的2月份正式出版发行。作为他的下级与文友,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这本书反响强烈,《榆林日报》对其后记《沿着昨天的足迹继续逐梦前行》一文摘要刊登,很便于广大读者了解作者的人生履历、文学创作以及本书大概。
郝卡厚先生只在学校念了七年书,上学没能使他走出生身之地的那个小村庄。这种欠缺并没有阻挡他逐梦的铿锵步伐,进入军营以后,他发奋图强,终至后来居上。他在向书本苦学的同时,还广泛而谦逊地向身边的师友请益,笃学力行,不断从社会这本大书中汲取营养,踏踏实实一如既往地践行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古训。
他的原始学历虽低,可他自学的能力极强。尤为可贵的是,他一直保持着一种不肯落后的学习上的前进动力。你看他的文章,不论是语言,还是逻辑,都处理得十分到位,力争立于不刊之论的境地,那种老辣果敢,绝不似出自一个初中肄业生之手。这也有力地向我们证明,学力比学历更重要。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为了更好理解郝卡厚先生的大作,我曾利用两个上午,对他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访谈。他娓娓道来,关于他的出身、他的奋斗、他的文学创作,一切看似平凡,却处处闪耀着真知之光——“上天不负苦心人”。
稍感遗憾的是,那些他在部队经历的趣事逸闻,听起来颇富吸引力,在这本作品集里却全无涉笔。我以为,那样宝贵的素材资料,一旦时机成熟,或有什么触发了他喷薄的写作欲,他也开启了足够的文胆,就一定会词源倒峡,笔扫千军。
其实,此书三分之二的文章我在此书出版之前即有拜读,特别是散文这一部分,数十篇在《解放军报》文艺副刊刊登,颇令同行刮目。解甲归田之后,他又多篇作品陆陆续续发表在了本土关注度较高的《榆林日报》文艺副刊。所以,圈内的文学创作者、爱好者,想必像我一样都有一定的了解。
其中,我执行主编的机关内刊《神木政协》杂志,也有幸获准刊登他的一些大作。行文之朴素,用语之精确,叙事言物,条分缕析,少有辞费,一如他多年来职业军人所养成的行事风格,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令人读后尤为难忘。
这部作品集,分为新闻之实、研究之深、散文之美三个部分。我是很喜欢看作者初出茅庐时撰写的“豆腐块”一般的新闻消息,以及《寻梦》《雪的记忆》这些散文篇什中的抒情小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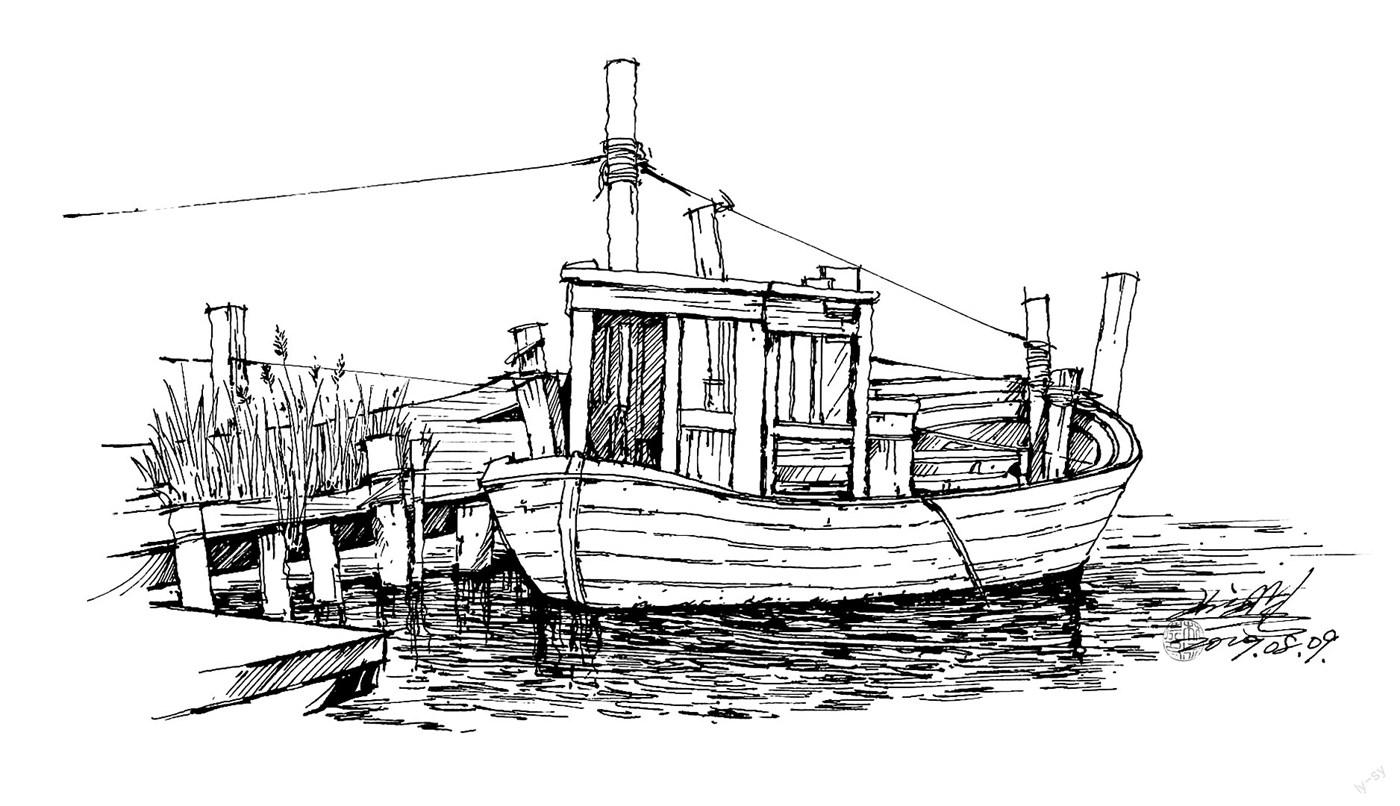
特别是那些新闻,虽去今三四十年,现在读来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陈旧,反倒很是新鲜,尤其现场感强烈,读来如见其人、如历其事,甚至还有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气息,让那个火热时代的品质真实可感。彼时的报端,虽仅一色,却分明有一种五彩缤纷的内涵。
《逐梦》一书的作者郝卡厚先生,本是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农家子弟中极不起眼的一份子,他因吃不了农活的苦,发奋要别开生路,便毅然走进军营。然而实在地说,不吃苦,何以谈人生。他弃农从戎,只是换了一个赛道,以另外一种方式的刻苦钻研,兼之一些重要的机缘际会,终于成长为了一位正处级别的领导干部。此种奋斗成果,又来之何易?
通过几年来的共事结交,我对郝卡厚先生的几件事情印象较深。
记得他提过几次,他的爷爷郝惟明,是清末民国时候他老家栏杆堡一带非常知名的秀才先生,能文工书,在神木城西的名胜二郎山留有题碑之作。于是,我在之后特别留意过,果然有一通《三教殿圣像重光碑记》,是由“邑士郝惟明敬书”。能与邓宝山、何柱国等知名将领以及本土文化名流王雪樵、张祉繁等人物济济一堂,名镌名山,这当然是一种尊荣。郝老先生当时在神木的影响力于此亦可见一斑。
或许,正是有这样的文脉余荫,冥冥之中注定了郝卡厚先生能在军营中另辟蹊径,在握住枪杆子的同时,他也坚定地握住了笔杆子,从而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勤勤勉勉地写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他的双手手指关节严重变形,似乎总处于执笔状态,是那样的屈曲挛缩,基本没有完整舒展开来的可能。我想,这与他常常通宵达旦伏案握管一定不无关系。由此不难看出,他在码字过程中用功之深、付出之多。
有一天,我到他办公室,见他正在翻看很大的剪报本子。他指给我看,那些他最初见报的消息新闻作品,其中一篇,赫然入目,竟是与王久辛的联名之作。我颇为惊诧,原来他们早有交接,共在一个部队,而且从事的都是文字工作。因我写诗,知王是久负盛名的军旅诗人。这一发现,让我顿多亲切。
现在,合上这本沉甸甸的著作,我想及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句名言,他说“一世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郝卡厚先生明确有这样的精神文化追求,他将过去散落在报刊的各類文章辑集出版,欲意作为精神财富流传子孙后代,能有如此意识,这在当下的神木堪称难得。
但愿所有别具怀抱的人们,于此能够得到些许启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梦为马,以笔为枪,继续征战文场,斩获更大的荣光!
——选自西部散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