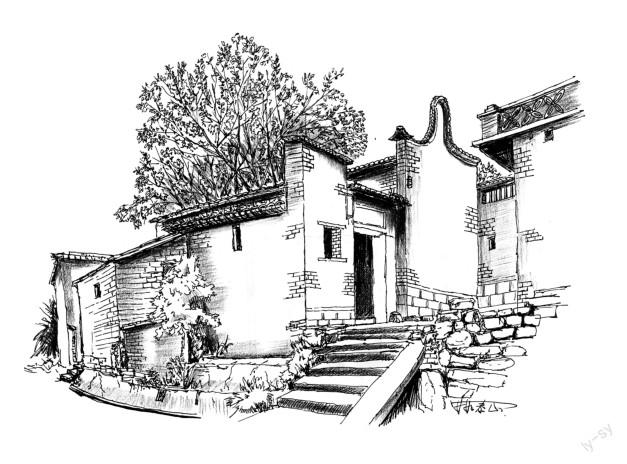
正值腊月,刚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雪。桃园里半隐着一大片白。两只喜鹊忽而跳上,忽而跳下。这片桃园,是夏庄街道西石沟村村民几十年来引以为傲的“寒露蜜”桃子源产地。
李家桃园的主人穿着棉衣,踩着咯吱咯吱的声音走近了。几根树枝戳在雪地里露出大半截,他弯腰拾起来,堆成一小堆。这是前些日子请村里的能人修剪的,枝条如何疏剪直接关系到来年桃树的开花和坐果,也与家里的年收入息息相关。他望向不远处青白相间、绵延起伏的山峰,好像在深远地想着什么。
再过一个多月就立春了。到那时,春风又会回来叫醒这一大片桃树。积蓄了一冬天的能量输送到桃树的全身,每根灰色的枝条都泛起了红,枝条上的每个芽点都鼓着劲儿,托举着新生的花苞。一层毛茸茸的包衣,过不了几天,就会被快速生长的花苞撑开了,露出了娇嫩的粉。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待到春分,几朵性子急的花苞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要将春天探个究竟。仿佛一夜之间,桃花开得漫山遍野,西石沟村已经掩映在十里桃花之中。此时,这座小山村似乎有了辽阔山海万里天的气势。
不知是谁传递的消息,数不清的蜜蜂都赶来参加这场一年一度的桃花盛会。一同赶来的,还有四面八方的人们。
倘若有幸,会遇到晨雨初霁。两面青山青似洗,白云朵朵山中起。阳光撒到桃树上是彩色的,苍遒有力的主干,蜿蜒的分枝都透着黑亮。对比之下,桃花微微展开的花瓣,散发着淡淡的香,微微的甜,这份娇羞粉嫩,便呼之欲出了。偶尔会有几片油绿油绿的小叶子,顶着水珠,探出半个身子,来凑热闹。在桃花的海洋里,人们也变得温和、柔美起来。但是,却不敢多说一个“美”字,生怕声音一出口,就会打碎这如梦般的仙境。
桃花的花期大约有半个月左右,在这短暂的春光里,西石沟成了拍照打卡胜地。爱花的女人怎肯错过,她们梳妆打扮,穿梭在十里桃花园中。绽放着笑容,闪耀着光芒,真是应了那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红”。脚下的土地松松软软,刚钻出土的青草嫩绿柔软。一阵春风缓缓吹来,粉白色的花瓣如雨似雪,落英繽纷。1800多年前,三位铮铮铁骨的英雄人物,或许正是被桃花的柔美唤起真情,才有了“桃园三结义”佳话。
西石沟的十里桃花,吸引着成千上万城市、乡村的人们偕老带幼前来观赏。随着季节赏花,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习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有了闲情逸致,说明国运昌盛,百花齐放。
有心的人,赏花的同时,不忘向村民要一个电话号码存好。等到桃子成熟时,找个周末,或带着家人,或约上朋友再来相聚。既能亲身享受采摘的乐趣,又能吃到沾着露水的新鲜桃子,还可以免费挖桃园里的荠菜,带回家包饺子。想来这就是陶潜心中的“桃花源”吧。
每一朵桃花都是一个希望。这十里桃花开得热烈,承载着村民的无数个愿望。李家今年盘算着秋后换辆新车;杜家今年要装修新房;刘家春节前要娶新媳妇进门……这一桩一件都是村民家的大事,也是村里的喜事。
李家桃园的主人,后背着手,踱着步,围着自己家的每一株桃树细细打量。情不自禁地跟着手机里哼唱起来,“阳光的油彩涂红了今天的日子,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
——选自西部散文网
打石头
天刚蒙蒙亮,唱了一夜“洗洗浆浆”的秋虫终于歇息了。大花狗伸着懒腰。王师傅洗了把脸,就着芥菜疙瘩,三五口吃了两个热乎地瓜,又端起茶缸儿喝了两口水,咕嘟咕嘟嘴咽下去。他轻声跟家里说:“我走了。你熥熥饼子和嫚儿一块儿吃吧。”他慢慢抽开横在大门中间的门关,又轻轻摇开上面的门关。一手握着铁锤,一手攥着錾子,走出胡同,奔采石场去了。
“哦吆!还有比我更早的。”王师傅拍打着被露水打湿的裤腿说道。“你心思你能挣个第一名!”接话的是胡老黑。他被炮声震得一个耳朵不好使,自己听不清以为别人也听不清,说话声音很大。他实际上也就四十岁出头,是经过公安机关培训领到炮证的社员。“王麻子,这几个錾子好煎了。”大建咧着嘴跑过来。“王麻子是你叫的?学本事不行!吃,一个顶俩。”胡老黑瞪着儿子大建嚷嚷。“王师傅”。大建笑嘻嘻地凑过去,把几支錾子放到王师傅脚边上。王师傅小时候脸上生花(长水痘)落下几处深深浅浅的小坑。在别的大老粗脸上也就罢了,谁让王师傅天生高大俊朗,有点瑕疵格外显眼。男人们打趣给起了“王麻子”的外号。王麻子夏天再热也要穿着长裤,还不光膀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石头用的工具都是石匠们自己锻造的。王麻子做的钎子、錾子、铳子个顶个地好使。“煎钻子”的技术更是让石匠们竖大拇指。“煎钻子”是石匠对经过使用磨得不锋利的工具进行淬火修理的一种叫法。需要先用砖头和泥理起简易火炉,烧火时有风箱,也会备着一个鼓风机。放着不花钱的石头不用,是因为用砖头理得方正好看,而且保温效果好。烧钻子要用热量卡数高的煤。烧的时候须精准地把握好火候,烧过火就会化掉。烧好后用铁钳钳住在铁砧上用手锤敲打,钻尖打好后还要经过煎火。“煎火”就是把钻尖放在冷水中一沾捞起来。这样一来,“煎钻子”就完成了。成功与否则要看“煎钻子”师傅的手艺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先拿几块开铁煤生起火来。哈哈哈,慢慢学吧老孩子。”王师傅按了按左手上缠的几处胶布,蹲在石料堆旁边熟练地卷着旱烟。山下各家各户的釜台陆续开始冒烟儿了。
石匠们打石头,是不分春夏秋冬、农闲农忙的。山涧里一年四季回响着叮叮当当的打石声。除非下大雨歇个雨工、大雪没过脚脖子歇个雪工。一般的雨雪天是舍不得歇的。天长的时候,一大早上山叮叮当当抡上两个小时大锤再回家吃早饭。傍晚借着太阳下山的霞光也要多打会儿,直到看不清人了才下山回家。
知了一声声地喊着“热啊!热啊!”。石匠们一双双粗大的手上,血水泡变成了茧子,汗水和着石粉淌进没来得及愈合的裂口里与血肉一起生长。指甲盖上有紫寨(音)子是司空见惯,就是缺个指甲也不足为奇。打石头的时候被飞石崩了脸,手上腿上破点皮,那就跟挠痒痒似的。大多数石匠光着膀子,身上的大裤衩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冰溜柱子挂满屋檐的隆冬。手脚冻木硬了,搬着石头砸了自己脚的事,时有发生。不幸砸掉半个脚指头也只是去卫生所包扎一下了事。狠下心歇上两天。之后自己在家碾碎消炎药,把药沫子撒上,忍着钻心的疼,继续去山上采石。
“嫩爹要放炮啦,别乱跑!”在山下果园锄地的云姨放下锄头一把揽过大健的妹妹小瑞。
轰轰隆隆的响声刚随着石块落地,石匠们就跑上前去,蹲在一堆落石旁边以示圈占。
这一天,大发有些反常,没等炮声落地就朝着一块大石头冲过去。谁料刚站稳,就被落石不偏不倚打在后头上。生产队长、民兵连长带人分头抢救,人们惊呼着急忙上前小心又快速地把他抬到拖拉机斗子里,可惜没赶到医院人就不行了。他老婆抱着腿上的大嫚,拍着炕上的二嫚,哭得撕心裂肺,埋怨自己头一天晚上不该嫌他没本事挣钱。村里的人都来帮衬着,给挑水的,给送地瓜干和饼子的。大队专门安排人帮着他家春耕秋收。
活着的人总要活下去。胡老黑挂在脖子上的哨又吹响了。
石匠们都是极为普通的人,他们中很多人听到放炮都会吓尿裤子。因为极少有女人在山上打石头,每到放炮前都要先找个地方小便。
石匠们又是充满智慧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胆大心细、善于钻研。胡老黑围着山体端详了两袋烟功夫。王师傅上前慢悠悠地说:“这遭得打个抬炮吧”。胡老黑笑着点了点头:“我就是这么想的。”抬炮得横着打眼,这可比打立眼难度大多了。打立眼人是顺着劲儿,由上往下打,用力的大小、方向都好掌握。打横眼就是使偏劲儿,扭歪着身子,斜着使劲,发力的大小、方向和落锤到钎子上的力量、方向都很难把握。想要把钎子横着一锤一锤打进花岗岩山体里五米深,不但需要强壮的体力更需要毅力和技巧。胡老黑用锤头敲了敲定了点。看着旁边打炮眼的人说:“嫩上一边吧。王麻子,你敢不敢和我干这个活?”“试试就试试”王麻子说着脱下黄胶鞋倒出一些石渣又穿上,起身走过来端详着这块硕大的挡住云彩的山石。“来,建国也过来,咱就开始吧!”三人打抬炮小组成立了。王麻子捧起手,往手掌中吐了口唾沫对着搓了几下便抡起打钎锤(8磅锤),“一二!一二!使劲啊!”建国扶着钎子。(等炮眼打深了需要两人扶钎子。)打炮眼过程中会产生石面子,需要经常用挖窝勺抠出来再继续打,否则会影响进度。随着炮眼越打越深,钎子也从1米、1.5米、2米……不断增加长度。打1米以内的钎子时不需要拔,每打一锤转动一次,钎子不快(锋利)了随时更换。有提前煎好了放着备用的。三人会轮流着打锤或扶、拔钎子及抠石面子。如此反反复复耗用了三个人的七八天功夫(具体石质软硬度会影响进度快慢)。王师傅抹去左手指头上裂口渗出来的血,另外两人合力拔出钎子,这个5米深的抬炮眼终于打好了。
“装药!放炮!”王麻子抽完两袋烟起身说。他和建国先装了少量的炸药轰窝儿,然后根据这次的石量,评估出火药的用量。建国将一管一管的硝铵炸药装到炮眼里。把雷管和导火索做好后包在一管炸药里,用炮杆推送进炮眼。为了预防在送雷管的时候出现雷管和炸药脱离,需要再压上两管炸药。导火索的长短需要根据装完药剩余的炮眼长度来确定,以导火索露出炮眼为标准。
准备放炮前,建军大声喊:“要放炮了昂!快闪开!快闪开!”紧接着,胡老黑吹几声短而急促的哨响。等他确定危险区内没有人了,吹一声响亮悠长的哨响后点燃导火索,自己也迅速退到安全区。他心想:“可别出现哑炮。”
“轰——”震天响的轰隆声冲破了山涧上空的那块儿黑云。
胡老黑在一旁认真观察,等他认为安全了便会吹一声欢快的哨响。表示石匠们可以从安全区出来上前打石头了。
轰炸下来的大石块要先用打石头锤和錾子打窝。铁锤头大约10公分重量四斤左右,木头把手长度大约20公分。先在石块上定好点,石匠挥动锤子不停地敲击錾子,根据石块大小评估出打多大多深的窝,完成这一步就需要换响锤和铳子把大石块劈开了。大锤的铁锤头就有18-20公分,重十斤(最重的二十多斤),木把手有1米多长,木头要选腊木,因为借用腊木“颤”的特性,挥动锤头的时候能有助于石匠发力,敲击到铳子上,传到石头上的力量也更大。这样一来能多少省点力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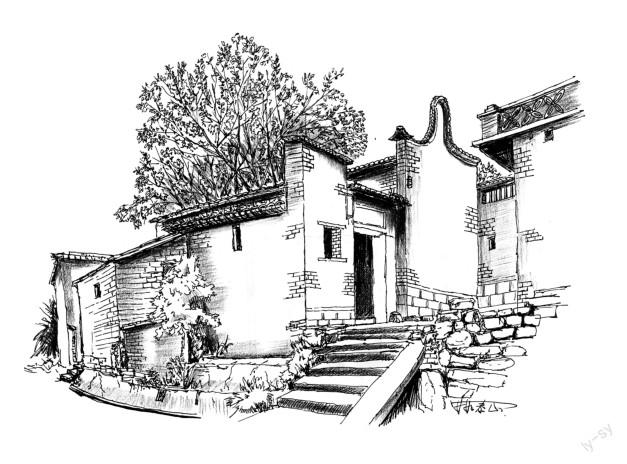
一个艰难的过程后,齐刷刷的石块排布在石匠们眼前。方正漂亮的个(块)石,一块能卖八毛钱。周正的是甲级石,最高四元一方。差点的是乙级石,3元一方。再次些的不规整的叫地瓜石,一元一方。还有小石子,甚至是石面子都能派上大用场。袁家小子大诚假期也去采石场打石子。打200斤1-2公分或是2-3公分的石子装满一编篓(棉槐条子编的筐)能换6毛钱。6毛钱差不多能买一两斤好地瓜干。这小子去领钱的时候别提多高兴了。
198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生产队里的喇叭响了。
广播员在广播室里先放了一小段即墨柳腔《赵美蓉观灯》。社员们知道这是队里有事要说。“这个,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听到广播后都到村东头集合啦。”社员们伸长脖子听着。黑涧生产队实施分田到户,村里一口人四分地。村民们更有干劲儿了!石匠们除了管理自己山地的果树,就到采石场上工。
花岗岩作为架桥修路、水库砌坝、建设工厂、打预制板和古力盖的好材料处处用得上。村民自家和亲戚盖屋也是离它不行。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中处处浸着石匠们的汗水。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打石头的手艺已经失传。石匠们的子孙不用再打石头了,已纷纷融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大健、大诚当了兵。大健的妹妹小瑞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成了公职人员。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继续为家乡,为人民做着贡献。
今天,我行走在这座当年石匠们开山劈石,打磨石块修建的水库旁。不远处,细密柔软的绿草地上孩子们正在嬉笑奔跑。水库四周是高楼、洋房和别墅。丝丝黄绿的垂柳和几枝桃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一阵春风拂面而来,水面上恍惚出现了石匠们的身影,他们吞咽饼子如食珍馐;他们身穿粗布,心有锦缎;他们身处黑涧,守望红日;他们身有钢骨,心腹柔肠。石匠们在石头堆里摸爬滚打,在岁月里跌宕。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追逐着时代的脚步。有眼泪也有欢笑,有沉沦也有崛起,有叹惜也有梦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封闭式管理的社区静谧,安然。居民从容,祥和。花开了赏花,果熟了采摘。当年的黑涧已经被称作瑞云社区了,当年的打石头的山体也基本被修复。这里成为人们假期亲近大自然的理想去处。特别是东山顶那块象形石,引起很多人的爭议。究竟像什么呢?像不像是一位守望者。
——选自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