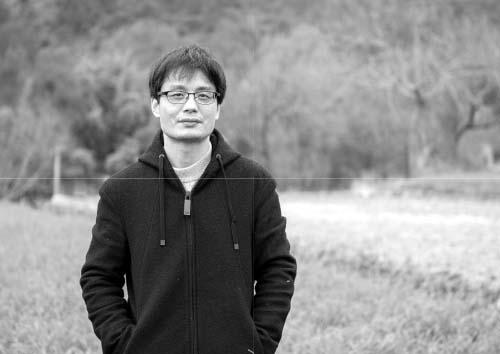
一
“文章”二字在中国古代原指花纹:青红二色成文,红白二色成章。后来转义,变成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文章,它可以涵盖小说、散文、戏剧、公文等多种文体。日本有“文章读本”一说,据翻译家李长声先生考证:“文章读本”这个说法是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创造,或源自中国的“文章轨范”。既然有文章读本之类的入门书,自然就有工于文章的人。在中国古代,这一类人称作“文章家”。我们通常认为,“文章家”这个词最早见于柳宗元的《与杨京兆书》:“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但我以为,这种称法或许还可以往前推。西方亦有“文章家”一说。布鲁姆在《文章家与先知》一书中把蒙田、德莱顿、鲍斯威尔、哈兹里特、佩特、赫胥黎、萨特、加缪称为风格独特的文章家;把帕斯卡尔、卢梭、塞缪尔·约翰逊、卡莱尔、克尔凯郭尔、爱默生、梭罗、罗斯金、尼采、弗洛伊德、肖勒姆、杜波伊斯这些人称为酷似先知的智慧作家。如果我们效仿布鲁姆把中国古代的文章家罗列一下,柳宗元是完全可以进入那个“风格独特的文章家”的行列。木心先生曾经评价柳宗元是古代“最具现代感”的一位作家。他在某处所说的一句话恰好替这个说法作了注脚。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古典的好诗都是具有现代性的。在文学手法、美学取向上,柳宗元的散文与现代散文是接近的,就像他的某一部分诗与现代诗同样也很接近。具备这种现代感的要素,恐怕与他那种“辅时及物”的文学主张有关。辅时而不趋时,及物而不溺于物。这是文章的正道,在今日依然管用。好的文章会把一个诗人与作家推到时代前面,让人铭记。我们都知道,莫里哀是福楼拜所称的第一位资产阶级诗人,而波德莱尔是本雅明所称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他不仅是“神的代言人”,还是一个“时代的代言人”。我对柳宗元的诗与文章有过交叉阅读,作为诗人的柳宗元我们不妨称他是“神的代言人”,作为文章家的柳宗元则不妨称之为“时代的代言人”。
柳宗元写得最好的诗是山水诗,写得最好的文章是山水记。可是如果我们觉得,柳宗元写的不过是一些模山范水之作那就错了。柳宗元的才华是与器识是相配的。唯其如此,他的文章显示出不同一般的格调。读他一些论述性质的文章,我们就能感受到他的文字里浸润着一种思想。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说出来会吓我们一跳。那就是民主自由的思想。他曾经在《送薛存义序》中说:民众纳税,是让官吏做仆役的,如果官吏无道,民众可以黜罚他。这句话就意味着,民众对执政者具有合理的监督权。这些话不是即兴说的,而是与他在《贞符》一文中的民本主张一以贯之的。柳在永贞革新事败后被贬到永州,壮心瓦解后的憋屈与疲惫,因了山水带来的抚慰,略得平复,文气也渐渐归于平静。可是,平静的文字底下又藏着一股不平之气。就在他谪官南裔这段时期,他见到烟火围困的小桂树、风霜欺凌的木芙蓉,都会拿来自比。他把衡阳移栽桂树、湘岸移栽木芙蓉的事写进诗中,实则就是写自己移居永州的寂寞心境和那一点尚未泯灭的心志。
柳宗元的身份、履历、命运、读过的书、交往过的人(包括政敌)等,构成了他的文化视野与整体诗学,如果他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则有可能成为一名踔厉风发的改革派官员;天命让他退一步,他也就顺应人事,索性让自己回归平淡隐忍的生活,做一个纯粹的诗人和文章家。他一生很多重要的诗文,大都是在被贬之后写就的。他的诗歌成就已经是很高的了,没想到,文章的成就还会更高一层。
柳宗元的文章有重的一面,也有轻的一面。如《永州八记》,看似率性而为,其实有一种自由精神在里面,这就使他的写作与那种追求小情趣的不及物写作区别开来。从柳宗元那里,我看到了一种朝向现代性的写作方式。“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二十字,横跨古今,也足以抵抗一切古今之变与时间带来的销蚀。与之匹敌的一首诗则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者只有客观描述,而后者孱入了主观情感。因此,我更倾心于柳诗所营造的那种意境。绝、灭、孤、独。这四个字重若千钧,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然而,一个“钓”字,却是举重若轻,把那种加诸己身的沉重感突然化解掉了。应该说,柳宗元是一个内心深处无比孤独的诗人。只有孤独到极点,才有这孤绝的诗篇。某个寒夜,我独自一人驾车穿过一座荒无人烟的浙南山谷,其时乌云合拢,仿佛一道门慢慢地合上。车灯的冷光与寒气交织着在地上冉冉爬行,仿佛会一点点伸展到石头或枯枝里面去。前面是一圈又一圈盘陀山路,我开到略显平旷的地方,停下车,摇下车窗,静静地望着与黑夜融为一体的山谷,忽然被一种弥天漫地的孤独感所笼罩。那一刻,我想,我跟一千年前坐在孤舟之上独钓寒江雪的渔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很多年前,我读到斯奈德的诗《松树的树冠》:
蓝色的夜
有霜雾,天空中
明月朗照。
松树的树冠
变成霜一般蓝,淡淡地
没入天空,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声。
兔的足迹,鹿的足迹
我们知道什么。
(赵毅衡译)
之后,我在偶然间读到柳宗元的一首诗《秋晓行南谷经荒村》,就发现了二者之间似乎有一种同构关系: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谷幽。
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
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这两首诗都写到了树、霜、鹿这些意象。“我们知道什么”这一自省式的句子与“机心久已忘”有着内在的相似性;而“兔的足迹、鹿的足迹”,也让人想到“何事惊麋鹿”这句诗。斯奈德的意思是说,我一旦察见兔与鹿的行踪,它们就会识破我的机心,逃遁而去。而柳宗元的意思则是:自己已经忘掉机心,却不明白麋鹿见他还会受惊而远遁。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麋鹿总是与高人逸士并论。鲁迅的小说《采薇》就用了《列士传》中伯夷叔齐的典故,借小说中一个叫阿金姐的虚拟人物讲了这么一段话:“……那老三,他叫什么呀,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了。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不坏的。一面就慢慢地伸开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灵的东西,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走了。老天也讨厌他们的贪嘴,叫母鹿从此不要去……”如此看来,柳宗元说“何事惊麋鹿”,只是说说而已,其潜台词大概已教阿金姐之流道出:“鹿是通灵的东西,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不过,这一句诗是用反问的语调写出来,自有一种冷洌的幽默感。斯奈德在诗中提到鹿,也只是借用一下中国古典诗歌中颇为常见的意象,并没有打算袭用那个与鹿相关的典故。但“兔的足迹,鹿的足迹”这句诗显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隐喻意义。斯奈德在這一点上与柳宗元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清明的省思,点到即止,不作留驻。
就我阅读所及,年纪稍长于斯奈德的法国诗人博纳富瓦也曾写过一首类似的诗。诗的题目就叫《糜鹿的归宿》:
最后一只糜鹿消失在
树林,
沮丧的追随者的脚步
回响在沙地。
小屋里传来
杂沓的话语,
山岩上流淌着
薄暮的新醒。
恰如人们所料
糜鹿蓦地又逃走了,
我预感到追随你一整天
也是徒劳。
(葛雷译)
将博纳富瓦这首诗与柳宗元的诗并读,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它有唐诗的意味,也能感受到柳宗元的诗有一种强烈的现代感。
柳诗的超逸之气,在山水记中也时有发露。要知道,柳宗元被贬到南方瘴疠之地后,不仅内心苦闷,身体状况也在不断恶化,以至行走的时候膝盖颤栗,坐在家中的时候大腿麻痛。他既会忧于所思,也当欣于所遇。人与山水,偶成宾主,或有所得,就把那一瞬间的心境,溶解到那些描述山水的文字里。他写《小石潭记》这篇文章的心境与他写《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这首诗的心境应当是一样的。按理说,柳宗元身为僇人(受辱之人),明明是心中忧愤,却时不时地在文章里提到“喜”“乐”二字:如“孰使余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钴鉧潭记》);“李深源、元克己同游,皆大喜”(《钴鉧潭记小丘记》);“心乐之”(《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这喜乐的背后,有着一种不言自明的苦涩,也有一种阅尽世情后的淡然。在山中,他不仅与山相融,还与山中的时间相融。而时间也以山的形状将他融入了自己的怀抱。
二
正是《永州八记》,确立了柳宗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柳体”。柳体既出,后人争相追摹。元代的李孝光就是其中一位。
元代的诗文成就,远远不如书画。但李孝光却是一个异数。即便把他的诗文放在宋朝,也丝毫不见逊色。他是乐清人,家住雁荡山下,家学与山水的浸润,使他的诗文别有奇气。他的《雁山十记》显然是受《永州八记》的影响,但他的确是一个很懂文章之道的人。陈增杰先生做《李孝光集》校注时,举了几个句式,我这里就不作赘述了。《永州八记》第一记题为《始得西山宴游记》,而《雁山十记》第一记则为《始入雁山观石梁记》。光看题目,就有相似之处。文中写山水,写饮酒,也是抱同一情怀。
柳的第一记,类如古琴中的《流水》,有一股沛然而下的气势:
“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
“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
这两段文字里,不停地穿插顶针句。古诗如《西洲曲》中就有这样的句式,古文如《礼记》也在多处运用过这种句式。流动不居的文字与流水的忽然契合,让人不难感受那颗自由而激荡的诗心。柳宗元的文字像是从地底自然涌出的,他写景,无一字不是往内心深处写。即便是写斗折蛇行的山路,也能写出一种周回曲折的意致来。李孝光写流水,虽说不如柳宗元那样恣肆,却也是舒畅自如,有些片段甚至能让人想到书法中的一笔书,绘画中的一笔画。
流水与酒,是野逸文人的标配。没错,二人都写到了“酒”:
柳文: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李文: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主俱醉。
有人问我,寺庙里为何藏着酒?现在看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在元以前,有些高僧是不拘门规的,像东晋时期,在庐山结莲社的慧远和尚曾沽酒招待过陶渊明;北宋时期云门宗僧人佛印也曾烧猪肉款待苏东坡。元之后,类似的事其实也多有记载。翻看叶绍袁的《甲行日注》,也读到了这么一条:“舟即在寺门后河耳,买寺僧酒浇寒,夜宿寺中。”這些虽然都是闲话,但也颇可一说。看柳文与李文,一提到“酒”或“醉”,文字里就飘出仙气了,继而凌虚蹈空,渐至缥渺之境。但他们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才华,一段文字在空中作短暂的自由滑翔之后,他们有本事“接佛落地”。也就是说,文字在他们手里,可以撒得开,也可以收得拢;可以上接仙气,也可以下接地气。
柳宗元的八记中,时常可见漂亮的比喻。而李孝光的十记中也能看到一些随手拈来的比喻:
“岁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万里外。”
“客行望见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游方僧自襆被者。”
“时落日正射东南山,山气尽紫。鸟相呼如归人。”
“石梁拔地起,上如大梯倚屋檐端,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
“设应真像悬崖上五百,然皆为人缘取持去,空遗士坐,如燕巢栖崖上。岩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鸣屋檐间。”
“月已没,白云西来如流水。”
需要注意的是,李孝光是雁荡山人,与家门口的山之间,要么朝夕相处,要么朝别暮见。除了《始入雁山观石梁记》一文中他把雁山喻为朋友,其他文章里面,也时有类似比喻:出得林中,忽见明月,说是“宛宛如故人”;外出回来,见了门前的山,也说是“如与故人久别重逢”。雁荡山之于他,是一种及于人心的浸润。因此,他写的雁荡山,与外人不同。他的比喻,用现在话来说,是有一种在地性,读来也很亲切自然。
柳擅长写水,李擅长写山。柳写的八记,篇篇有水,篇篇有情;李写的山是眼中的山,也是心中的山。他们把目之所遇与心之所感写出来几乎是不着力气的,写到极致时,便透着一股清冷之风。
柳文: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李文:风吹橡栗堕瓦上,转射岩下小屋,从瓴中出,击地上积叶,铿镗宛转,殆非世间金石音。灯下相顾,苍然无语。
同样写静。柳宗元这一段,是写视觉中的静;李孝光则是写听觉中的静。李孝光的静,是以动衬静。风吹橡栗,先是堕落瓦背,继之是岩下小屋,从瓦沟中滚落,最后落在积叶上。橡栗落在三处,把寂静分出三个层次,可说得上是造微入妙。这样的写法,是把自然物象与潜意识心象结合在一起,是很有现代感的。
古人写文章,大至章法,小至用字,均极讲究。在章法上,如前所述,李孝光有意套用柳文;在用字上,他也是有意或无意地受柳宗元的影响。如“布”字,柳的《小石潭记》中就有这样一句:“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而李的《始入雁山观石梁记》中也有“冬日妍燠,黄叶布地”一语。一个“布”字,使静态的事物忽然有了动态的效果。他们对文字的讲究,很大程度上缘于对细小事物的敏感。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确像汉学家们所说的,是一门“选字”的艺术。如果一个人把文章当作诗来写,则不免也要费一番苦吟。只有像庞德、斯奈德、布罗茨基这样翻译过中国古典诗歌的诗人才能体味到,每一个字里面都包孕着异常丰富的内在含义与想象空间。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古代那些经典诗文,不光是极难翻译成外文,连翻译成白话文都会丢失原味。它是经过高度压缩的,是要精确到每一个字的,稍有疏失,则谬以千里。在古代汉语写作中,一个汉字,如果经由一个诗人或文章家的精心拣择,恰到好处地用在某一个句子里面,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此人的独特气息。后人即便重复使用,他也不怕被人夺去。贾岛写出“僧敲月下门”这一句之后,“敲”字就归他所独有了;王安石写出“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一句之后,“绿”字就归他所独有了。
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位“选字”的高手:选一个简单的字,即能让人洞见纷繁。而李孝光在写作《雁山十记》时也在“选字”,他选中了一个柳宗元用过的字,用得巧妙,让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幽细而邈远的回响。在中国古典诗文里就有这样一种做法:一篇诗文里出现前人用过的字句,既不是表明作者才力不及,也不是意在炫耀学问,而是为了在某一个句子里,以古人之心为心,以古人之意为意,让自己的心意与古人暗合。
三
李孝光之后,又有何白作《雁山十景记》。
何白又是何许人?他是一位与李孝光同乡的晚明诗人、散文家、文论家,书画也很了得。有人说他“文宗韩柳”,但从《雁山十景记》来看,他更偏于柳。古人作文,就像学书法一样,以追摹古人笔致为务。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是“致敬”。才气相近,敬意弥笃;才气不够,这敬意也仿佛显得浮薄了。
李孝光写过灵峰、灵岩、石梁洞、大龙湫、能仁寺等,何白亦复写之,他有大才,因此敢与古人较劲。这个古人,当然包括乡党李孝光与更早的柳宗元。
我曾有意把李孝光的“十记”与何白的“十景记”放在一起读,并作了比较。在我看来,何白的文采很足,但才气毕竟是略逊一筹。李孝光的《始入雁山观石梁记》《大龙湫》有点像写老朋友或自家人。有时会写一些局部细节,有时则会一笔宕开去,如写意画。而何白连工带写,用力有点猛,文字间不免见到斫琢痕迹。但何白毕竟也是大才,他能透过自己的目光看山水,看山水之间包含的万物。
李孝光写鱼,何白也写鱼。鱼的出现,使静止的空间突然有了时间的流动,使重的那一部分突然变轻。他们都是诗人,在文章中都很注重意象的经营。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可以感受到:鱼的动感愈强,则其境愈清。
李孝光是这样描述大龙湫中的鱼:
潭中有斑鱼廿余头,闻转石声,洋洋远去,闲暇回缓,如避世然。
何白笔下的鱼则是这样的:
斑鳞文雉,上下若乘空。信如白地明光,五色纂组耳。
斑鳞,就是李孝光所说的斑鱼。“上下若乘空”这一句就有点像柳宗元的句子“皆若空游无所依”。可以看得出,他写鱼时,心里是存着柳宗元与李孝光的影子的。在他的文章中,流水、鱼所呈现的时间性与山、树所构成的空间感是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柳宗元八记中有多处写到了鱼。《石渠记》写的是:“潭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儵鱼”。儵鱼是什么鱼?讀过庄子《秋水篇》的人大概不会忘记,庄子与惠施在桥上看到的鱼就是这种鱼。他们所谈论的,就是“鱼之乐”的问题。
柳在《小石潭记》中写到的鱼最是传神: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我在学生时代初读《小石潭记》,不免疑惑:这篇文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篇幅写一些无关紧要的鱼?现在我弄明白了,他写的是鱼,心底里渴望的是一种自由的生命状态。“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同时也投射在他内心深处那个幽暗的部分,鱼与整个水潭乃至整座山由此而构成了一个斑驳的内心景观。在何白的笔下,鱼已着我之色彩;在李孝光的笔下,鱼已着我之姿态;在柳宗元的笔下,鱼已着我之灵魂。不错,这是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似与游者相乐”,就是两个灵魂进入了静默的对望,忽然有了相通之意。那一刻,“我”仿佛就是鱼,鱼仿佛就是“我”。“我”曾经是网中之鱼,而现在复归于自然。这也意味着“我”已复归于“我”。就这一点来看,李孝光与何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意趣上,而柳宗元进入了更深的层面。
我在胡兰成的一篇文章里无意间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我想着谢灵运,他的被杀亦非不宜。此刻我伫立溪桥看浅濑游鱼,鱼儿戏水,水亦在戏鱼儿,只觉不可计较。
一千多前的谢灵运与“我”有什么关系?鱼与水有什么关系?鱼与“我”有什么关系?鱼与谢灵运有什么关系?水与谢灵运与“我”又有什么?读至此,我就更明白柳宗元看潭中游鱼的心境了。
一个人在写作中是否沉潜下去,在文字里亦可隐约察见。何白写石梁洞时,把上下左右里外都写了个遍,泛泛而言,未见沉潜,但他写灵峰洞就有感觉了,因为他二十年前有过一次游历,旧地重游,就有话好说了。后来写到了李孝光的家门口——石门潭。笔调则近于李孝光:
中有巨鲤长丈馀,每遇风日和煦,辄从容扬鬣水面,小鱼景附者以千计。土人常夜见赤光上烛,潭水尽紫,盖神物窟宅也。地方干识夫云:曾于月夜刺两艇,以繂联束之,与客携酒具轰饮。令小童吹紫箫一再弄,箫声夹秋气为益雄,殊有穿云裂石声。夜半古泓闻殷殷若雷鸣。客惧而散,嗣后无有继其游者。
李孝光写家门口的诗文殊为少见,仿佛是故意留出给别人来写。好了,后生何白来了,他写石门潭,文笔不让前人,总算是跟李孝光握了一回手。
四
到了清代,又出了一个试与同乡李孝光、何白较劲的人。他就是施元孚。施的主要作品有二志一集,即《雁荡山志》《白石山志》《释耒集》。他在编山志之余,写了《雁山二十八记》,在数量上压人一头。二十八记的第一篇即是《始入雁荡山宿能仁寺》,看题目,也能大致知道他的路数。
古人作文,讲究脉承。竟陵派有竟陵派的作法,桐城派有桐城派的作法。他们以为,只有把自己的文章放进某一脉中,才能获得认可、流传。李孝光的《雁山十记》可以归入柳宗元这一脉,何白的《雁山十景记》与施元孚的《雁山二十八记》则可以归入李孝光这一小脉,自然地,也与柳宗元这一脉远接。
在施元孚的文章里,已经有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习气”的东西出来了。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末尾部分这样写道:“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在施元孚的《雁山二十八记》中,凡是写到水处,时常可见类似的句式。如:“心异之,然脚跟若浮,不敢留,急渡而西下”(《入北閤登仙桥记》);“恍若潭底神物,乍为惊扰。余心动,遂至下流,舍桴而去。”(《泛石门潭记》)。
不过,施元孚总算也能得几分柳氏笔意。柳宗元写鈷鉧潭时,开头部分有这样一个句子:“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这里施用了一“抵”一“屈”,水的动感就出来了。施元孚则是这样描述大龙湫:“风入障中,郁不得畅,与湫斗,湫力不能胜,则役于风。”文中一“斗”一“役”,也颇能显示出一种冲夷之中的激荡。当然,施元孚也会对前人的文章轨范稍作偏离,让自己笔下的文字随着心性跑开去。他写大龙湫就有一种日常化的诗意,能把人融入景里面,把景融入某种情境里面。比如这一段:
湫随风作态,雨雪烟雾。初无定质。目之所击,其态即变。有顷,风益劲,变态更奇。攸斩中断,而上段断处,横舞空中数十丈,缭绕如游丝,久而不下。
作者写到这里笔法忽然一转,又写到了人:
余与客皆笑呼起舞。客蹈空,跌阶下。
行文至此,作者以人跌落的姿态为瀑布作张本,笔锋一转,接着写景:
湫倏自潭面倒卷而上,蜿蜒翔舞,飞入天际,不知所之。
再转而写人:
余拍手大呼,客亦蹒跚而起,忍痛而视,相顾诧异久之。
在视点的切换之间,人与景构成了某种富于戏剧化的情境。不过,这种活灵活现的文字在施的文章中并不多见。
《雁山二十八记》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李孝光与何白的影子来:
余之东游雁山也,从丹芳岭入西谷,即所谓四十九盘岭者也。既度岭,沿涧行。涧水淙淙,作金石声,若鼓乐以迎客者(案:“作金石声”四字,容易让人想起李孝光那句“殆非世间金石音”)。
会日薄暮,朔风萧萧,黄叶满径(案:此句类如李文的“黄叶布地”)。
近阅四山合翠,岩门飘瀑,寒猿升冈,文雉出谷。天然之趣周环凑合,入山未深,已翛然非复尘世。余不觉欣然而喜。未几,日没,风吹山谷,飒飒如暴雨至,觱发侵人,遂入寺,宿西舍(案:这一段很容易让人想起李孝光那种清冷的散文意境来,其诗意的发散与绾合也多有暗合之处)。
鼠大如狸,多兔多野豕,无豺虎熊罴(案:这是施写雁湖冈的文字,李文则为:“山鼠来与人相向坐,如狐狸大”)。
余之游湖也,升于荡阴,晨则就道,薄午而至湖。仰瞻红日,晃然悬于人上;俯瞩白云,悠悠然远浮于下。斯时也,寒威未杀,而湖高风厉,瑟瑟如也;日中湖游,冷冷如也;惊宿雁之遐逝,眺海天之苍茫,骇目动心,懔懔如也(李文如下:“日初出时上山,正中仅可到山颠。望见永嘉城下大江,如牵一线白东面海气苍苍,如夜色”)。于是群集湖曲,漱湖流,啖干糒(案:糒即馅肉的米饼,在李孝光文章中也有这个词),寻沉钟之迹(案:李孝光《雁名山记》云:“湖旁有比丘尼塔寺,一夕沉湖中,至今五百余岁,然犹余遗地败址”)。
在用字上,也能见出施元孚所受的影响。施写到自己乍见大龙湫时用“白光射人”四字狀其奇险,之后又写到自己“走至潭右,水又射至,遂退而止”。这个“射”字用在这里按理说是很有动感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它平淡无奇。之后忽然想起,我曾在李孝光、何白等人的文章里就看到过这个铿锵有力的动词,如“山风横射”(李孝光《大龙湫记》)、“忽劲如万镞注射”(何白《大龙湫记》)。与何白同时代的一位旅行家徐霞客的《游雁荡山后记》中说“风蓬蓬出射数步外”,也是以“射”字凸现风水相搏的动感画面。在《永州八记》中我不曾发现柳宗元使用过这个动词。但柳宗元那一代诗人中,倒是有人喜欢用这个动词,如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就有“东关酸风射眸子”的诗句。这种动词使用频率过多,很容易让读者发现“人巧”之处,作者如能自觉规避,选用一些陌生化的字,或许能得“天工”。
山水记本无规范,但柳宗元写了《永州八记》之后,它就有了轨范。后人写山水,往往是参照《永州八记》的结构、声调、修辞形式。这种用文言写成的山水散文,在行文上多持简洁,并且始终恪守一种古典的克制。文章合乎轨范了,八记与二十八记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永州八记》的好,就在于它是没有刻意去写。从写作时间来看,前四记与后四记相隔三年。这三年间他流连于山水之间,有感而发,才把后四记补上。身处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柳宗元知道,眼前没有更好的去处,只能在转圜之间尽量免受身心的摧折,从而在山水中保存一个完整的自我。山水的抚慰人心,有甚于经书的指引。这八篇堪称治愈系的山水记至少让柳宗元的内心平静了些许。而在扰扰尘世间奔逐的人突然读到这样的文章,也能略得一丝抚慰吧。
对李孝光、何白、施元孚来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源头性文本。他们无法绕开,更是无法超越。但我相信,他们在状态最好的那一刻里,是与柳宗元走到了一起。通过山水记,元代的李孝光、明代的何白、清代的何白与唐代的柳宗元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与后人构成了另一种对话关系。每至雁荡,我就会感觉自己与他们更近一层了——这些古人,与我在空间上相近,时间上相远——及至我读到他们的作品时,时间的阻隔也就随之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宛宛如见故人”的感觉。
在今日,我们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接触往往通过一张门票变成了一种消费行为,而消费的对象便是自然风景区。我们已经无法像柳宗元们那样直接面对山水,进入物我两忘之境。我们的山水记里面,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停车场、检票口、电线杆、水泥广场、地方特产、塑料制品,以及无比粗粝的噪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