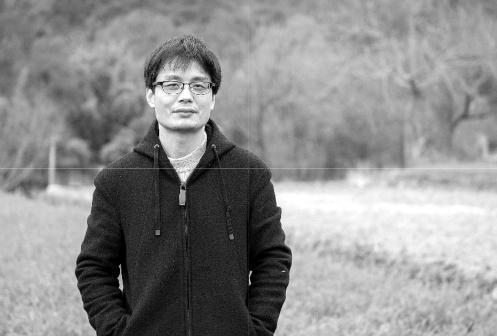
刚念初中时,父亲有一回见我用毛笔在写字本上涂抹,就问,这是什么?我说,是一块石头,两棵树。父亲沉着脸说,你在写字本上乱画什么?!过了半晌,父亲又问我,你想学画?我点了点头,父亲说,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位画画的先生。父亲习惯于把那些受人敬重的老师称为“先生”。大一点的,称先生伯;再大一点的,称先生公。次日,父亲带我去拜访那位“画画的先生”时,我才知道“先生”原来就是我的美术老师胡铁铮。父亲把我的涂鸦之作递给胡老师,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胡老师瞥了一眼说,山水画。然后就在构图上指点二三。后来,我想,父亲那天带我去拜访胡老师好歹也该带点伴手礼的。父亲舍不得花这个钱,我自然也不好意思登门学画。学画的念头,就此搁下了。现在想來真是有些惭愧,当年有这么好的老师在眼前,居然没有把握机会追随他学画。
胡老师有大雅的一面,也有大俗的一面。他的酒量是惊人的,好啖猪蹄也是出了名的。有一回,有位书法家朋友做东请客,其中一个盘子里满当当盛着从乐清西门一家老字号店带回的猪蹄。座中有人动箸,书法家突然伸手说,先别动这一盘。那人问,为什么?书法家说,这一盘猪蹄是特意为胡老师准备的。胡老师未动筷子之前,大家照例不动。胡老师来了,也不客气,豪饮之间,把一盘猪蹄吃了个精光,连连称善。
一个热衷于喝酒吃肉的人应该是热爱生活的。苏东坡虽说不善饮酒,却爱吃肉。他的《禅戏颂》有这样一段话:“已熟之肉,无复活理,投在东坡无碍羹釜中,有何不可!问天下禅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吃得,是吃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碗羹,勘破天下禅和子。”吃肉吃出禅意来,东坡一人而已。换成胡老师,他大概会说,吃肉便是吃肉,有甚么大道理好讲的?人家都说“肉食者鄙”,胡老师却是一个例外。胡老师自有他的一套说法:为什么古人常说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酒喝进去,伤胃,此时若有肉垫底,定然可以把酒力吸走一些。吃了这么多年的肉,不会腻么?有人不禁这样问。“很多人吃不住,我却吃得住。”胡老师曾这样说道。吃肉,喝酒,画画,是胡老师这辈子最热衷的三件事。凡事“吃得住”便好。
有关胡老师啖肉吃酒的事,就此打住,这里要谈的,是作为画家的胡铁铮。
胡铁铮是南方人,但他的画格局阔大,是近于北方人的。这样的格局,是大碗喝酒喝出来的,是从十万真山真水里养出来的。有些人,住到山里面,天天与山水相亲,画出来的画照旧很俗;有些人身在闹市,卧游一番,画出来的画却没半点尘土气。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有些人本质上就是“俗”人一个,有些人本质上是一个乐山爱水的人。胡铁铮即属后者。
胡早年师承戴学正、林曦明两位同乡前辈。六十年代,他在温师读书时期,追随戴学正先生习画,除了临摹戴先生的画稿,还临摹了宋画、元画以及明清时期董其昌、石涛、石溪、龚贤、蒲华等人的作品,三日一石,五日一水,做的是“取法”。之后,他又带着自己的临摹作品向林曦明先生移樽就教,林先生对他说:“如临摹,临摹一家已不容易,再跳出来更不容易,这叫死学,好多老画家就死在这点上。要学会一边临摹,一边在写生中消化,适我者生存,不合吾意者去之……”循着林先生所指明的路径,他渐渐悟到了“取法”与“舍法”是一件同等重要的事。他佩服林曦明先生的地方是:学黄宾虹不像黄宾虹,学林风眠不像林风眠,学关良不像关良,学李可染不像李可染,最后让人看到的,就是林曦明自己的面目。
胡成名成家之后,又做了贾又福先生的“编外学生”。贾先生对他影响最大的,恐怕不是画风,而是那种不守成法、不留恋古人一笔一墨的创造精神。贾先生是从宋人范宽、李唐那里悟得皴法,从龚贤那里悟得积墨法,变而又变,就有了自己的画风。胡初学贾先生,笔下雁荡山的石头跟太行山的石头确有几分像,但贾先生看了就给了他当头棒喝。胡铁铮在《学画问岳楼》一文中谈到了自己追随贾先生学画的一段经历。师徒间的一问一答,颇见机锋。
一天下午雷雨过后,西北角的天空忽现瞬息万变的云彩。师徒二人一边观云,一边散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问:这不是老师的巨幅画?
答:我画云彩,许多人不理解,说这是油彩、粉画。殊不知这正是我长期观察云彩的感受……我尊重自己的感受,尊重自己的技法,别人不理解,因为别人没有这样的感受。
问:画云是否先铺色?
答:方法很多,可以先铺色,亦可先泼墨,还可以多次擦染,这要自己去试验的。当然,还要注意运动的方向和空黑的处理。
问:空黑是老师创造出来的吧。
答:古人没画过空黑,我是第一个这么画的。空白不能理解为一张白纸,同样空黑亦不可理解为一张黑纸,而应该理解为通向无穷无尽的空间,这个空间包含着万千变化,微妙无穷啊。
有一回,有学生带画给贾先生看,贾先生连声称赞“画得好”。好在哪里?好在“这里能用手摸进去”。“用手摸进去”是什么意思?胡在旁细细琢磨,便悟到了“山石之间能转进去”的法门。如何转进去?他看到贾先生在用笔略显杂乱的地方加了数笔淡墨,两个面之间忽然就有了微妙的变化。原来,心腕之间,前人的笔墨、自己的主张,该来或去,都是不必刻意深求的。心念一转,手就转进去了。那一刻,眼中的山水不是心中的山水,心中的山水又不是手中的山水,山姿水态,随手万变。
真山真水在举步间可以到,但山水入画后的境界却不是说到就能到的。胡铁铮观看了贾先生现场作画之后,反观自己之前所作之画,总觉得画来画去,还是被古人的笔墨技法所拘牵。山水画画得太像山水画,终究还是执着于相。如何“破执”?问道归来,他有一阵子闭门苦苦思索“取法”“舍法”“变法”之间的一条路子,还零零星星地写了些画论。我们都知道,无论中国画还是西洋画都有它的常道,也有它的非常道。取法,就是常道;变法就是非常道。没有“取法”,就谈不上“变法”。对画家来说,“变法”是一个漫长而又纠结的探索过程。陈子庄当年师法黄宾虹,但师法归师法,主张还是自己的。为黄宾虹所不取的路子,他也要走一走,于是就有了新去处。黄“浑厚华滋”,陈“平淡天真”。至于他在山水画中所用的“破墨卧笔皴”,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是“为古人所无”的“自创之法”。陈子庄如此,贾又福亦是如此。
在山水之外画山水,在笔墨之外思考笔墨。有一天,胡铁铮突然像悟道一般,对自己早前所作之画,只用五个字打发过去:统统去你的。“去你的”,换一种文雅的说法,就是“舍法”。慢慢地,他从笔墨中“舍”掉了一些“共适”的东西,找到了一些“特有”的东西。这就有了胡氏独创的绿墨山水。这种绿,是放旷山水之后的一种冷凝,与山石攒聚内敛的造型是融为一体的。胡氏绿墨山水与青绿山水的不同之处在于,青绿山水用石青、石绿,而他用的是纯绿;青绿山水重着色,少皴笔,而胡氏绿墨山水则是在皴笔之间的空白处施以纯绿。这一用色技法,据说是他在雁荡山中写生时琢磨出来的,其时正值春夏之交的清晨,阳光洒在露水滋润过的草木上,浑厚而不乏滋润。那时他就认定,这就是他要寻找的那种色彩语言。为此,他在纸上做了多次调试,先用石绿中的二绿、三绿着色,然后在边上掺以花青加藤黄调成的汁绿,确保纯绿不为墨色所掩。绿墨山水虽已初见成色,但他还是觉得画中的绿墨有点艳,压不住,因此就采用龚贤的积墨法,以淡墨皴擦,层层晕开,在秀润之外,渐见厚重,这样一来,色的表现力与山石的体积感便相得益彰。纯绿的妙用,对他来说,等于是给山水“发明”了一种色彩。苏东坡把竹子画成朱红色,他就成了“朱竹的创造者”;莫奈把伦敦的雾画成紫红色,他就成了“伦敦雾的创造者”。在某种意义上说,胡铁铮也可以说是“绿墨山水的创造者”。这种画法与古人拉开了距离,与今人也不相近,因此难免受到同道的质疑。但他的回答是:我要的是真山真水,这山是我心中的山,这水是我心中的水。绿墨山水既出,胡铁铮的个人面目由兹而彰显,而清晰——它不同于蓝瑛的没骨重彩山水、张大千的青绿泼彩山水,也不同于贾又福那种以黄、红为主色调的大山大水。它已经在那里,不容忽视。
如果说,问学于贾又福那个时期,胡所画的石头还分不清哪块是自己的哪块是贾先生的,那么,这些石头后来就从他笔下慢慢分离出来了。一块有思想的石头,是贾先生所独有的。胡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要画出自己的石头。有很长一段时日,他“满眼满心都投在没有古人山石处”。像一个石匠那样,他精心打磨着自己的石头——把一块石头当作一座大山来画,把它的气势一点点画出来,把自己的气息一点点融进去。于是,他把别人的石头画成自己的,把死的石头画得活起来了。一块好石头,便好似得之自天,而非手中。那时候,他脑子里已经没有了太行山的石头或雁荡山的石头。他要画的,是自己心中的石头:这是一块沉默的石头,也是一块呐喊的石头;是一块静止的石头,也是一块运动的石头;它是万物,也是“一”。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石头。当不同的石头组合在一起,它们就以诡异的造型、苍辣厚重的色彩,直扑人面而来。这些年来,我不知道他已经画过多少块石头。这些石头构成了一座山,也构成了一种精神的向度。我以为,胡所画的石头正好阐释了他的老师贾又福的艺术观:“画中一块贴近真实的石头表现的是物质景观,经过适当的艺术处理,融入思想与感悟,物质景观就变成了精神景观。当把一块石头变成精神景观时,就不再侧重它是什么特质、什么地区的石头了……”是的,你看不出它是什么特质、什么地区的石头。可它的的确确是一块中国的石头。它跟所有的石头放在一起,你都可以辨识出来。它不是巴黎的石头,也不是东京的石头。但你把它放在塞纳河畔或富士山上,仍然可以发现它的属性,掂量出它的分量。
外行人吃茶,便说茶还是热的好喝;外行人看字,便说毛笔字还是黑的好看。我于中国画,也算外行,便说这石头还是大的见气势。
任意
怀强的画不是画家的画,怀强的字也不是书法家的字。怀强的画是诗人的画,怀强的字也是诗人的字。所以,怀强说到底是一个会画画的诗人,一个会写字的诗人。怀强与别的诗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与别的书画家不同的地方也在这里。
读怀强的画,就像是读他的诗。怀强的画里有一股诗人的天真之气,像是池塘边的青草,自然生成的。他笔下的山水花鸟人物,古人大都画过,他的线条好像也是古人的,但这一切由他经之营之,原本合于古人的做法,忽然又全无古人的做法了。怀强的画,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合古法(像石涛说的那样“如作野战,略无纪律”)。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人物画里,和尚多胖,道士多瘦(而且一定要加撮胡子)。胖有喜感,显得雍容大度;瘦有质感,更见仙风道骨。但你若是把道士画得肥肥的、懒懒的,意思出来了,就可以把人们的审美观念一下子颠倒过来。中国画说简单也简单,就那么一支笔,一点墨,在纸上划拉出几根线条,晕染出一团水墨。它的自由度和难度几乎是成正比的。怀强画画,用的还是前人用过的笔墨技法,這是无法跳脱的,可画画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能用陈旧的线条表达自己的新异想法。这就是对既定的审美标准的破与立。中国画之美,在于“不标准”。他把一条腿画得比另一条腿长,把一只眼睛画得比另一只眼睛大,但你看了,仍然觉得很美。我在怀强的微信上时常浏览他的画。他无论画什么都是一味笨拙,笨拙至极,即见拙趣。他是一个惜墨的人。图写山水、花鸟、人物,不求形似,约略得其神韵,就收笔。因此,就像他的诗歌语言所表现的那样,他的笔墨是精省的,线条是节制的。他画的树枝与鹤胫,形同古篆隶;他画的石头,如书法中的方笔直折。就那么几下,看上去好像都不太费力。从他的画笔里面,你大致可以看出书笔来。这就不难理解,他的画有一种写的意态:一株树的虬枝是写出来的,几道流宕的衣纹也是写出来的。线条的书写性愈强,画面的律动感也就愈强。正是一种带有逆意的“写”,再捎带上一种与心绪一并触发的“意”——这个“意”是随笔而转,随遇而化的——构成了他的写意之风。
怀强写字,也同作画,总是要尽自然之气。中国文学的表述似乎是跟着字走的。汉字打开了我们的表述空间,也限制了我们的表述。书法同然。中国书法,仿佛只有写古典诗文最能得笔、得味;写现代白话诗文,就好比用毛笔画自行车、收音机,又好比穿着唐装跳街舞,总像是少了点什么。但一个真正的书写者,是懂得笔墨当随时代的。怀强写的是现代诗,他用毛笔抄写现代诗,在形式上与传统书风隐然存异,他没有二王一脉的柔情似水,而是从古碑中来,又加了些野路子的东西,任心所至,也不怕过火。因此,怀强的笔墨语言是他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是今人的,不是古人的。把他的一幅字放在众多的书法作品中你可以拎得出来;把他的一个字放在别人的字里你也能拎得出来。我也写字,也喜欢从字里看人。看得出来,怀强的书风源自北魏造像,经过淬炼、变形,又多了一层现代气息。字里面的犄角之势,透出来的是书写者的直率性情。怀强写字,有时是意在笔先,有时是意随笔走。一个“浓”字用的是浓墨;一个“枯”字用的是枯笔;一个“醉”字歪斜着,如真的醉了;一个“衣”字有衣袂飘举之姿。他那一点,恰似字母Z(用的是圆转笔法写出来的Z),又似一只水里面的雏鸭,憨拙味十足,仿佛可以伸手捉之。他的书风与诗风是紧紧地贴在一起的,就像水草与水的关系。怀强曾引用过美学家叶秀山的一句话:书法就是书法家说话。我读他的书法,也能觉出他的笔墨间有一套自己的说法。这些话是质朴的,随意的,有时也带一点棱角的。这些话,都是他自己要说的(别人也无法代替他说)的话。在静夜,读着怀强的字,有一种与之对话的感觉。这时候,你可以忽略文字本身的内容,单是看看字,也能看出另一层意思。那些字,个个都是有生气的,密密麻麻地排布着,让人想到中国乡村的集市:那些人有蹲着的、坐着的、有叉手立着的、有背着手晃荡的、有攘臂而争的、有跌踬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并肩而行的,有让出道来的;叫卖声、喧嚷声、杂谈声、歌吹声、哭笑声交织在一起。这样的字,在电脑屏幕或印刷品上不易看出效果来,唯有挂起来,作壁上观时,视觉冲击力就出来了:乱中有序,静中有动,豪放中有温婉,粗犷间有精微,古拙中有灵动,平淡中有奇崛。
怀强写字,时而放松,时而收紧,时而恣肆,时而内敛;字有浓淡、大小,仿佛人有远近,说话的声音有轻重,从整体布局来看,近于绘画。很显然,这是现代水墨语言,有人以为狂怪,以为悖离传统背叛师门,以为恶搞炫技找抽。可是怀强想必是不太理会这些的。他曾给我寄来一幅白鹭诗的书法。有些字是淡墨写的,有些字是浓墨写的,远远看去,真同一群白鹭,一些鸟蓬蓬然飞远,一些鸟则蘧蘧然飞近。
我与怀强有过一面之缘,但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读他的字,观他的画,也从来不会问他是从哪家哪派来的。在水墨世界里,他就是江湖满地一渔翁,钓了鱼,又放了鱼,顺便把自己也放进水里,让人寻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