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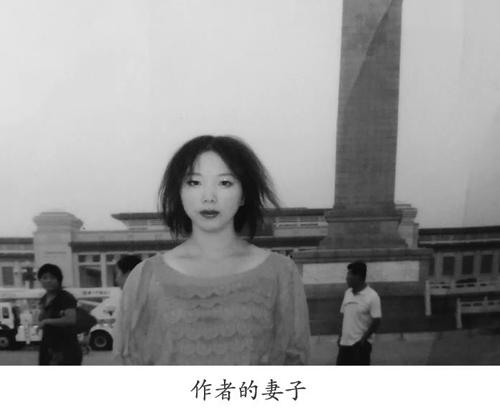

作者简介:郭文艺,84年出生,河南项城市人,文字发表于 《海外文摘》, 《散文选刊》 《散文百家》 《椰城》 等刊物。著有长篇散文自传《在黑夜与黎明前穿行》,散文集《弯弯的小路曲曲的河》。
作家史铁生是一个伟大又另类的人物,他那不停地对人间哲理的探索和独特的人间感悟,以及始终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其实人活一世,顺心顺意的日子是很少有的。各自在不同的人生路上行走,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牵绊。我们常常被一些老掉牙的旧俗困住手脚,搞得焦头烂额。
2002年退学在家后,我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中。按农村旧俗,十七八岁的孩子到了这个时节,就该是谈婚论嫁的年龄,整日里媒婆三五成群地登门不绝,那便是好人家,书香门第。要是阁里养的是姑娘家,挑选个适宜的郎君,不是难事。男孩家呢?遇此时节也是扭扭捏捏,挑肥拣瘦,故意显出他家有多高贵、多富有。
父亲那些天整日里早出晚归地劳作,回到家把锄头往墙上一靠,他就接连叹气。让他坐在灶屋里给母亲烧把火,他也低着头叹气,一把柴一把柴地往灶膛里添,火苗的舌头探出灶膛口,窜到了他的眉梢处,也不见他闪一下,母亲就用手捶捶他的肩膀头,拿眼睛狠狠地瞪他。
父亲愁容满面。
再没人能比我和母亲更清楚父亲的叹息声了。父亲是愁我的婚事,他见村里和我一样大的男孩子一个个要么考上了名校,要么去了部队当兵,但凡留在村里的,也早已经是配好了婚姻,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然而这世俗的道上终归没有太多奇迹可言的,那些日子,连一个拙嘴的媒婆也没有登过我们家大门。
秋后,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在北地出红薯,母亲仔细地用镰刀翻割秧子,成堆地放在地埂上晾着。父亲用抓钩(农具)在前面錛,我和母亲在后面捡。一个个躯肥紫鲜的红薯被我和母亲从土里掏出来,放入麻袋里。
父亲脱下了外套,只裸袒着那件破旧的秋衣。汗水浸湿了他的脊背,显出一道清晰的脊梁骨痕印。他又继续劳作了一阵,便坐下来稍些休息。
父亲背对着我,双手使劲地往土里伸,在泥土的最深处,父亲又掏出了几个小点的红薯头。
大地的体温应该是对人类最适宜的温度,是那种带着湿润和安祥的温和,这样的适宜多少使父亲感到了亲切。父亲此刻的内心好像萌生了想要向大地祈求些什么的念头。他有一阵子就仰面躺在了红薯秧上面,闭着眼睛,一只手垫在颈下当枕头,另一只手不停地在土地里继续抓着、掏着。
夕阳的光穿过稀疏的桐杨叶,照着他的脸。父亲的脸在那一刻凝聚了这世上难以言状的惆怅。
父亲一定是向大地索要了某种祈求,又急于想要在我的身上实现,那天晚上,他第一次狠狠地数落了我。以至于许多年后,我常常想起那个带月光的夜里,父亲的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含着的无限委屈和渴望。
父亲那晚喝了两大碗红薯粥,又吃了两个馒头、一碗梅豆子菜。然后就坐在灯下慢悠悠地剥起了花生。这期间,我要起身去开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在我起身去插电视线的那一刻,父亲阻止了我,示意我靠着他坐下来。父亲拉了拉披在肩膀上的破夹袄,然后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道:“你的一辈子准备咋办呢?和你一起大的男孩子都好胳膊好腿的,各自养活一家子没问题,原本指望着,上学是你唯一的出路,不想你也荒废了。叫你跟村东的刘裁缝学缝纫,你又坐不住,就是求人家媒婆赏脸,能给你提个啥亲呢?我和你母亲百年后,谁来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呢……”
那晚的月亮很圆、很亮,父亲就着月光说的掏心话远远不止这些,一些让我听着心颤的句子现在却怎样也记不全了。
总之事情的结尾是:父亲想要送礼请一个媒婆上门来给我寻一桩合适的婚事,他为此不惜卖掉了刚刚打下来的芝麻、挂在墙头上晒干的玉米棒子。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周全,又精心准备了两条纸烟、两瓶烈酒,还在一个红包里卷上了剩余的钱。
我非常心疼父亲的这些举动,在心底一百个抵制他这样用世俗的手段去做这些伤财的事情。但父亲对我说的话似乎又都那么合乎常理,让我纵然有一万个不情愿,当着他和母亲的面,也反驳不出一个字来。
隔天半晌午,家里进来了一个矮矮的、黑瘦黑瘦的老太婆。她的小脚一踏进门,父亲就满脸虔诚地搬凳子、倒茶,母亲慌忙着去包饺子、炒菜,我躲在西屋的书桌旁,只听见灶屋里锅碗瓢盆相互碰撞的欢快之音,父亲的细声细语和老太婆嘹亮的嗓门形成的高低调。
午饭很是丰盛,但我没上桌。豫东千百年的习惯,长辈们谈事情待客人,做晚辈的远远地躲着些好。
将近下午三点多,老太婆才起身告辞,腋下夹着烟,抹着油漉漉的嘴朝大门口走去。父亲和母亲连忙往外送,我随在二老身后。送至老旧的柴门外,老太婆拿机灵的三角眼斜视了我一下,回头对父亲说:“放心吧,包在我老太婆身上,过几天就叫他们见见面,保证你今年腊月娶媳妇!”
父亲欸欸地应和着,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的几天里,父亲似乎是到了度日如年的地步。他干着庄稼活也跟母亲小声嘟囔,这老太婆咋还没个信呢?夜半睡不着,他叫醒母亲不住地问:你说她会不会撇咱(骗咱的意思)?父亲三番五次的疑问,惹得母亲也无法断定,跟着瞎着急起来。
终于,那个媒婆还是来了。
那天下午,老太婆骑着三轮车,三轮车帮上坐着一个女孩子,大约十七八岁,和我年纪相仿。一身红衣,脸蛋白净,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
看着怪赶时髦哩!
村里人都围着看,私下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父亲激动得直搓双手,脸上的肌肉都随嘴唇颤抖着。他在由邻人组成的方阵前头走着,小跑着迎到了村口。
父亲在前面带着路,直接把媒婆和女孩让到了堂屋当门。女孩轻巧地下了车,媒婆牵着她的手,引她坐在了藤椅上。当看热闹的众人都哄散在院子外,我和那个女孩便相对着坐了下来。
按照风俗,男方是要先前一步讲话的,我就问起了她的年龄、家住哪村、爹娘如何等等。她也不含糊,一五一十地答了。如我所问,她把我的事也问了一遍。两个人便低了头,各自想心事。又过了一会儿,我试探着说:“你看,我腿脚是不方便的,生活里是需要一个人长期照顾的。”女孩抬起了头,脸上瞬间起了道绯红:“没关系,其实我也一样,打小眼睛就看不清事物的,互相照顾吧。”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所有的交流仿佛一下子冷却了。接下来说了些什么话,我不再记得了。我只记得媒婆带她离开时,父亲的脸上是欢欣的、令人鼓舞的表情。显然,父亲对这门亲事是满意的。女方也留了话,对这门亲事没啥意见。
也许,在父亲心里,这样的机会是求之不得的,全是那个老太婆带来的恩惠。晚饭时,父亲欢喜地拿出他的酒盅,就着辣椒萝卜丝喝了一盅又一盅。父亲认为,儿子能讨一个这样的老婆,就是全家人的幸运。
但我死活不同意这门婚事,这是父亲不能料到的事。起先我和母亲在一边讲,父亲他慢慢收了喜悦的脸,闷着头就着馒头喝闷酒,一声不吭。后来他见我一个劲地絮叨,便仰脖饮了一盅子酒后,火气腾地窜了上来,父亲红着眼,平生第一次对着我咆哮,像发怒的、受了箭伤的狮子一般:“你想气死我吗?啊?你也不想想,咱就这个家境,你身体又这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又实诚的姑娘家,你又这般挑拣,你自己本身连个锄头都拿不了,还想娶个什么样的呢?你非要混成光棍汉不成?”
父亲越说越恼,他几次欲哭无泪,胸口窝了一股子气发泄不出来,憋得他大口大口地喘息。母亲也在一旁劝说我,认了吧,找个这样的能凑合着伺候你吃穿,你爸的心病到底也算痊愈了。你千万别犯傻,到头来惹得一头没一头。
但我终究还是没能了却父亲的心愿,僵持到半夜,父亲都把好话讲尽了,我就是不同意,给出的理由只有一个,我自己本身就不方便,再娶个不方便的女孩为妻, 到底是谁照顾好谁?这无非是给二老添些乱子,这样的组合对谁都是伤害。但父亲却没能想到那么多,他只想着他还年轻,这个姑娘刚好也需要照顾。想盼着我娶了她,两人有个后代,他哪怕当牛做马,也要给我撑起一个家。
我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但同时又排斥这些看似合理又世俗的安排。
那一夜,我和父亲一样睡卧不安,开始学着父亲唉声叹气起来。
这样的结局免不了使父亲受尽了尴尬。他在集市上两次碰到老太婆,那个爱翻三角眼的婆子当着卖肉的、售酒的的摊主,半开玩笑地催着父亲下聘礼,父亲就那样在人群中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站也难堪,走也不妥。
我心里一百个愿意那个姑娘立马能找到一个好婆家,赶紧嫁个壮实能干的好小伙,这样,于我,于父亲,于那个姑娘,都是一种解脱般的皆大欢喜。我不愿意娶她,凭良心讲,不敢存半点嫌弃之心,不出意外,她亦如我内心一样,是希望各自都能找个健全的人扶持,这样才能在未来无数个风霜雪雨的日子里,有个身全的人儿为各自残缺的身体抵挡些严寒。不至于在家庭琐事面前,搬动重物、搭衣晾被之时,去求他人来家中帮忙。
这只是我较着劲不愿意娶那个女子的一万个理由中的一个,父亲显然没有觉察到这些。甚或,贫苦的生活、繁重的担子迫使父亲过早地消除了敏锐的洞察力,对于我的这些细微又粗犷的反抗,父亲只是一惯地理解成不听话、心太高的举动。这促使父亲在每一个劳作后的夜晚,更平白增添些苦恼的唉声叹气。
我知道这样下去,是无论如何都化解不了我们父子之间的一些矛盾,便找了个理由,和在省城工作的六叔通了个电话,在一个寒雾弥漫的早上,拎包踏上了开往郑州的大巴车。
车出县城,我扒着窗户看外面的万亩麦田,久久地看着。
太阳出来了,照得人身上暖暖的。
从那一刻起,我暂且把母亲的叮嘱、父亲的叹息,一股脑儿全甩在了身后的村子。
在省城无非也就那样,吃饭、睡觉,每天忙些无关紧要的事。当然,过度地指望这些琐事能抵消装满心头的大大小小的思想包袱,是不现实的。我有几次都想要在灯火稀疏的街上找个电话亭,给父亲打个电话,听听电话那端故乡的声音。但一想到父亲又是那声让人措手不及的叹息,和难免又要讨论起我的婚姻大事来,所以几次上街溜达,我都刻意地绕过了电话亭。
日子在风平浪静的状态下消磨着。我跟着六叔一起管理着一所大学的微机房,顺便也能向维修电脑的刘老师学些维修电脑的知识。我原本打算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展:学几年维修,回家乡小县城开个电脑维修部,守着个摊位,守着二老,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
若按这般推理,一辈子单身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就在翌年的春季,一个女孩(我现在的妻)闯入了我的生命里。她当时读大一,家住省城以北的郊外。女孩个头不高,脸皮白净,平时不怎么爱讲话。但她十分有责任心,爱帮助人。
我实在讲不出她和我的交往有什么好处,至少对她完美的身材、大好的前程而言。
她常来上网课,久而久之我们就搭讪了,开始熟悉了。那时春天刚上柳枝头,冬冷似乎还未褪尽,我的脚上冻伤的部位还在火辣辣地疼。我不经意间告诉了她这个事情,我想她也就听听而已,转身就忘记了,并不会放在心头。但她却记得牢牢的,隔了两日,下午放学后,她请求大门口保安给开了大门,去了趟外面的药房,给我带回来了一支冻伤膏。
我在心头始终当她是普通朋友,母亲没有闺女,我就想认她当妹妹。相当一段时间,我们保持着一般的交往。
对她,我至少在她大学期间,我没有对她有其他的念想。
暑假两个月,她和她的两个室友都没有回家,在省城各自找了份临时工,为下个学期的学费忙碌着。偶尔闲下来,我们喜欢去省体广场散步,看人家放风筝,风筝有蝴蝶、老鹰、蜈蚣,各式各样。有玩无人机的一帮人,穿着怪异,肩膀上刺着字。也有许多老年人打陀螺,还有妇女大妈跳广场舞。走累了,我们就选个草地的一角,看这些人各自的表演。
日子,很平常地流逝着。
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雪厚。她感冒了,躺在宿舍里。街上所有的车辆都无法通行。我踏着积雪走了几里路,为她抓回几副草药。归时,膝盖不断磕摔在冰天雪地上,整个人都快僵硬了。
也许,打那一刻起,女孩子特有的细腻敏感的心思就悄悄地起了变化。
此事不知怎樣被乡下的父亲知晓了(六叔常给父亲通电话)。父亲如坐针毡,开始三天两头地睡不起觉。我想,父亲是自打接到六叔捎话的那一刻起,便在老家过得糟糕透了。他像一头刚从冬眠中醒来的北极熊,先听此事觉不出详细,而后慢慢引发了他思维的一系列的混乱,他既欣喜又苦恼,脑海便跳出这样那样的疑问:女孩怎样?儿子在省城如何?他们的交往会不会影响到女孩子的学业?此事女方父母是否知情?学校方面会如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