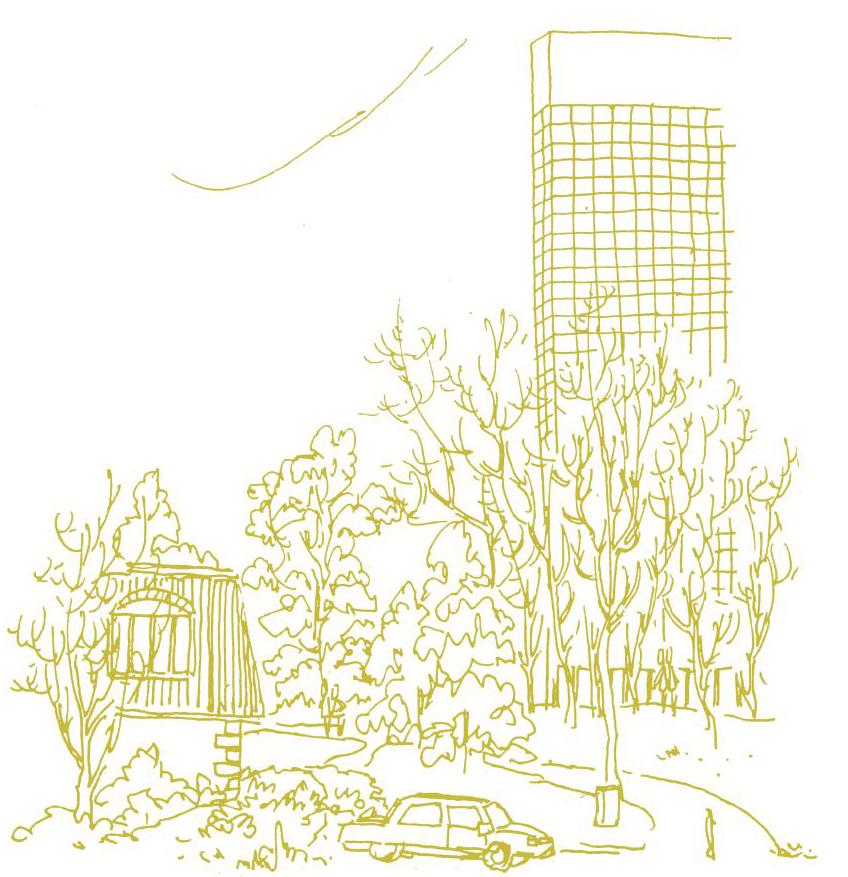
“民谣太贵了,听一曲就要一根烟三瓶酒,外加无数伤心回忆和一晚上的苦涩。”
——题记
清晨五点十分。他背着吉他又来到了地铁站。早起上班的人零零散散,偶尔经过几个穿着校服急速奔跑的学生,脚上的白耐克鞋晃得他睁不开眼。睁不开就睁不开吧,反正她也不会这时候出现,这么一大早有多少人肯起来啊,他这么安慰自己。
清晨六点。
赶时间上班的人多了起来,大部分人都睡眼惺忪地往前走着,时不时咬上一口抓在手中的早饭,他们看地铁还没到站,稍稍喘口气,从容吸一口豆浆或是牛奶,轻咳一声,跺跺脚继续等车。他握住吉他呆呆看着这些人,才想起来他今天早上还没吃早饭呢。权当减肥吧,他摸了摸自己空瘪瘪的肚子,咽了一口唾液,忍不住地幻想着,不远处有一个和自己一样没吃早饭空咽口水的她,如此想着,他傻傻地笑出了声。
清晨七点半。
地铁里呼啸着风声。
他挂在脖子里的吉他终于慢悠悠地晃出了声音,一声半响的在嘈杂的地铁里很快就被湮没了,他并不急,拨动琴弦的手若有若无地抓着空气,一会张开,一会闭上,手心里渐渐冒出了汗,他也不在意,只管低下头,轻轻拨动着琴弦。
早晨八点。
“北方的村庄里,住着一个,南方姑娘。”他终于开口唱起了歌,大概是几个小时没有喝水,所以声音更加沙哑,他低着头,把嘴唇凑近摆在前面的话筒,“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
唱着唱着,他唇边的弧度越来越往上扬,节奏也越来越快,整个人容光焕发,像是醒了一般。他把帽子随便丢在一边,长长的刘海倾泻,盖住他所有想要流露出来的表情。从远处看来,他还是清晨那个没睡醒的青年,漫不经心地弹着吉他。
“啪啦啪啦。”
“锵——”
他的吉他声骤然停止,扭头看向发出噪声的源头。
现在是八点四十分。
“Hey。”她對着他挥了挥手后继续收拾她的画具。他把吉他从脖子上拿下来撑在地上,手臂压在琴头上,又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今天怎么这么迟才来啊。”
她不说话,只是耸了耸肩,匆匆支起画板后一屁股坐在地上,点燃一支烟。烟雾袅袅升起,伴着笔尖与纸的摩擦声,像是给他伴奏。他没有动身子,依旧是那个姿势撑在吉他上。
临近九点的地铁站人又散了不少,只是偶尔经过几个年迈却步履匆匆的老人,他们的双手背在后面,斜挎的背包中有的插一把大红扇子,有的露出老式收音机的一截天线。老人们就好像集体从公园锻炼刚结束,准备借地铁站的空间休息一下。看着手中不断冒着烟雾的她,他们的步履变得缓慢而狐疑,一脸“孺子不可教也”的表情。
“哈哈哈。”在收到无数个老人对她的白眼后,她却笑出了声,手里的炭笔一顿一顿地画着各种神情的老人们,画完了随手丢在画包里。他一直关注着她。见她满脸笑容也跟着扬了扬眉毛,又弹起了吉他。她听见琴弦声又响起,头也不抬,默默整理着手里的画稿。地铁里风大,她需要按住才能保证画稿不跟着风走。
突然,纸张飞扬。
他扭头,看见她牵着一个孩子走了过来,那孩子哭得抽抽搭搭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她便抱着孩子坐在自己腿上,从外套里抽出衬在里面的衣角给孩子擦着鼻涕。孩子被她安抚好了情绪,擦干眼泪鼻涕后开始扭着身子要去找妈妈,她却抱着孩子蹲在地铁门口,任凭孩子如何挣扎也不松手。
他握着吉他走到她跟前,她对他投以一笑,有些尴尬地说道:“这孩子怕是和父母走散了,留在原地等才是最好的办法。”他点头,蹲下来摸了摸孩子的头,轻轻地说了声:“好乖。”
不一会孩子的妈妈找了过来,看见她抱着孩子,也不客气,一把夺过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并不恼,用手梳了梳凌乱的头发,便蹲下身子开始捡着画稿,他跟着她一起捡着,捡着捡着,他突然站起来说道:“我给你唱首歌吧。”
“不用了,”她依旧蹲在地上,“我只有一根烟,还要过一天。”
他笑了,还是唱了起来:“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她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哎呦……”
她蹲在地上不言不语,头也不回。
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西贝的《路人》中的几句话:“我的宿命分为两段,未遇见你时,和遇见你以后。你治好我的忧郁,而后赐我悲伤。”地铁呼呼行驶,大风起兮,她挑染的金色头发在不太通亮的地铁过道里竞熠熠生辉。
他转身,偷偷拿了一张她的画稿塞进口袋里。
她是温柔的南方姑娘,可是在烟雾缭绕中,谁又知道她本心向蓝天。
他笑意不减,唱着那首《南方姑娘》。
他耳边喃喃地响起了她与他第一次在地铁站里遇见时,她念的诗:“忧郁和悲伤之间的片刻欢喜,透支了我生命全部的热情储蓄。想饮一些酒,让灵魂失重,好被风吹走。可一想到终将是你的路人,便觉得,沦为整个世界的路人。”
“知道吗?你就是我的南方姑娘!”他在心底咆哮。
“风虽大,却只是绕过我的灵魂。”她在心底感叹。
加州橘郡风光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有一城市名Orange Coun-ty,直译应为橘郡。虽是严冬季节,然满眼苍翠,鲜花盛开,一派春意盎然之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