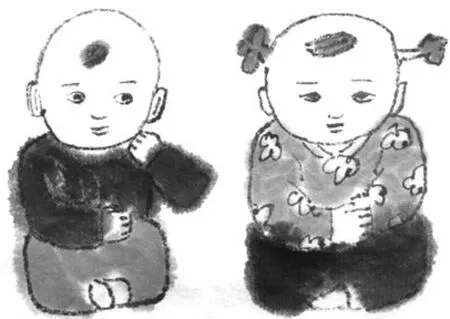
我的娃娃亲定于上世纪70年代初。
那时,家乡“学大寨,赶烽火”;“赶烽火、奔小康”。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浮夸口号,吃大锅饭,社员没有劳动积极性,再加上天灾,使本来就贫瘠的黄土高原百姓的日子雪上加霜。
我家七口人,上有70多岁的婆(奶奶),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弟,父亲久病卧床,只靠母亲一人挣工分养活全家,日子相当艰难。
家乡有个习俗,贫困人家的女娃一般都早早订亲,这样,男方要一直负担女娃吃穿到18岁结婚。为了支撑这个家,亲戚、邻居都给我们出主意,要给我张罗一个好人家。
在大姨的撮合下,定了一户合意的人家。男娃的父亲已去世,母亲改嫁去了县城,家里只有老婆婆带着男娃兄弟俩,希望有一个媳妇早点过门操持这个家。
记得那是一个严冬的早晨,黄土高原北风凶悍,窑洞外漫天的大雪把路掩盖的白茫茫的,原野上连一只麻雀都看不见。大人娃娃都没法出门了。我们全家每人喝了一碗包谷糊糊,几个娃娃像一群小鸡偎在老母鸡翅膀下一样,蜷缩在炕上围在我婆身边取暖。母亲说,梅娃,跟我走亲戚去。
我看看窗外,又看看因冻疮而溃烂的双手直摇头,不去。母亲说,是去你大姨家,她家有白面馍,你玉珍姐还要给你花毽子哩。长这么大,我才吃过两次白馍,记得那白馍酥酥的味儿香的不得了!现在母亲的话让我馋涎欲滴,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我去!
母亲用水打湿毛巾,给我擦了脸,把我稻草样凌乱的黄毛梳理了,用头绳扎好。母亲看着我干净的小脸说,要是有雪花膏给梅娃抹一抹多嘹(好),我女子好看着哩!我婆张开没牙的嘴笑着说,以后会有人买,你别熬煎!母亲用头巾裹住了我的头和脸,只露出两只眼睛,往我手上溃烂的地方撒了点炉灰,把我的双手塞进一个缝好的棉筒筒里,拽着我的胳膊,踏着厚雪、迎着刺骨的寒风,踏上了去大姨家的路。
70年代初,我们那里的农村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几十里的雪路,我和母亲走走停停、跌跌拌拌的走了一上午,也不知道怎么到的大姨家。
大姨家还坐着一个姨,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好看,像城里人穿的那般排场。这姨把我拉到跟前,摸摸我的头,给我一颗水果糖。大人们说着话,还不时看着我笑,说着什么我也听不懂,就自己跑到院子玩耍去了。
雪已经停了,太阳暖暖的。大姨家院子里拉着一根铁丝,上面晒着一条床单。一个男娃站在单子后面,掀起一角看着我,他的眼睛乌黑发亮,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赶紧用单子挡住了脸。他是谁呢,难道他也想到我大姨家混白面馍吃吗?我赶紧把那位姨给我的糖舔了一下,攥在手心里,我可不想给他!
可我想看看那双大眼睛。等我走近时,他干脆用单子遮住脸躲起来了。我悄悄的、轻轻的绕着单子走,我发现他也时不时窥视我,我就学着他的样子用单子把脸遮起来不让他看。我们绕着单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觉得挺有意思,最后都嘻嘻笑起来了,一不留神,就把单子扯掉在雪地里了。我吓得大哭起来,因为我大姨厉害着呢。可是,大姨听到哭声,并没有责骂我,安抚着哄着我们回到了屋里……
回家的路上,母亲问我,那个男娃好不好看?我说好看。母亲又说,那就是给你寻的女婿,那个姨就是他妈,这娃额看着也心疼,人又老实,你以后不受熬煎。我不知道什么是女婿,只想着能有白面馍吃就好。
到了订婚那天,因为我俩都要上学,两家大人就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回来时,母亲给我带了几身衣服的布料,还有两袋粮食。
那年他9岁,我8岁。
从那以后,逢年过节他经常来我家,还给我家带来一些物品,有时也帮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他不仅长得好看,而且人老实、勤快,我们全家都喜欢他。
暑假,他家让我表姐带我去他家玩耍,婆说,你就去吧,那娃的婆也是个好人,过几年要在一搭过活哩,早点熟了也好。妹妹仰着小脸问:去了有馍吃吗?婆说,有,黄馍,白面馍都有唻,还有哈水面!妹妹闹着说,我也去,我要吃馍!我说,我想吃哈水面!母亲说,记住,到了人家那里要懂事,要听话,要帮着你婆做活,有眼色,以后过门了光景好过些。
他家年迈的婆领着弟兄两个过活,主要靠她改嫁到县城的母亲接济,日子也很艰难。婆对我很好,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一会儿我们就不害怕了,与婆也很亲热。到了中午,婆问我:额娃在家能做甚?我说念书。婆说念完书回来坐甚?我说,看娃。婆说可会做饭?我说不会,都是我婆与妈做。婆说,娃,你已经8岁了,做饭可要学唻,婆老了,年纪大了,过几年你过门,这个家就指望你操摸,不会做饭咋行唻,婆今个就慢慢教你做杂面馍。婆先教我和面,可我比案板高不了多少,使不上劲,婆就拿来一个小板凳让我站上去,手把手教我放多少白面,放多少包谷面,放多少黑面,还有一点野菜,放多少水,一一给我示范。然后说,额娃试活(试一试),婆来烧火。我手在盆里抓来抓去,面与水就是不听话,和不到一起,急的我满头大汗,手上,胳膊上白的、黄的、黑的到处粘的都是,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揉,人晃来晃去从凳子上摔下来,装水的碗啪的一声被我带到了地上,成了碎片。我连惊带吓,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婆忙从灶火旁站起来,扶起我说:不哭,不哭,额娃不会慢慢学。我偷偷瞄一眼碎碗,怯怯地说:婆,碗碎了,额没抓牢……婆用手抹掉我的眼泪说:碎了就碎了,只要额娃没跘疼就行。又说,你来烧火,额和面,婆又给我教了烧火的要领。我坐在灶火旁,抓起一把麦草就往炉膛里塞,麦草有些潮湿不好燃,一股股烟从灶火口往外弥漫,呛得我直咳嗽。婆说,用那个棍棍把麦草挑一挑,用嘴吹吹火就旺了,我把头伸向灶火,用尽力气噗噗噗吹起来,忽的一下一股火冒出来,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一下,听得滋拉一声,紧接着一股焦糊味,我的刘海、眉毛被烧掉了半截,我赶紧用手去摸,既伤心又委屈,眼泪噗噜噜往下掉。婆赶紧说,看来额娃真的没做过这些个,你先起来,以后婆慢慢教你,然后就让我“女婿”烧火来了。
那时没有地种菜,一般人家赶季节到田间地头、坡地、沟畔等地方挖野菜。有天上午雨过天晴,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泥土香,青草香。田野里、沟畔上到处青青绿绿。婆让我们四个娃娃提上筐子到坡上拾地软软(地皮菜)、到渠道边、河畔挖雀雀菜。我们刚到坡上捡了半筐地软软,走到一道沟里,我一抬头,望见沟上头几丛酸枣树上挂着一串串红艳艳的酸枣,那酸酸甜甜的酸枣多好吃呀,一瞬间,口水不自觉的在口腔里漫延,就对他们说:看,酸枣!妹妹举着小手说,我要吃酸枣!我说:我也想吃!只见我“女婿”立马放下筐子,手抓乱草与土缝隙,往沟上爬去。我们三双眼睛齐刷刷都盯着他,快要够到酸枣树的时候,他脚没有蹬稳,只听“啊”、“扑通”,我“女婿”从沟畔上摔了下来,我们几个娃娃都咬着手指头愣愣地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他。过了片刻才明白过来,吓得哇哇大哭,一同扑过去摇他,他弟弟边哭边喊:哥,哥,你不能没(死)呀,你没了谁跟额给家里抬水呀,你没了,额一个人上学路上害怕!我跟妹妹也大哭:哥,你不要没,额不吃酸枣了,咱回家吧!我们三个围着他又哭又叫,我跑到路上想找个大人帮忙,突然悠悠的传来:
羊啦肚子手巾哎三道道蓝
咱们见啦面啦容易,哎哟拉话话难
一个在那山上呦一个在那沟
咱们拉不上那话话咱们招一招手
瞭的见那村村呀瞭不见那个人
哎哟泪蛋蛋抛在那个沙蒿蒿林
隔山呀隔水隔不住心
哎哟哥哥心里只装妹妹你一人
我顺着声音眺望,从坡上过来一个老汉,手拿鞭子赶着一群羊,一边走一边唱。我对他弟弟说,柱柱,快看,来了一个老汉!柱柱一看高兴的说,是五保爷,说着就向老汉跑去,边跑边喊:五保爷,五保爷,快来呀,麻达了,额哥没了!老汉听到喊叫声也急急的往我们这边跑,说,娃,咋啦,不急,慢慢说!我们都哭着说,额哥没了!五保爷来到我“女婿”身边,摸摸这、拍拍那,对我们说,麻达没有,是昏了。又伸出手用指甲掐掐嘴上,然后把他抱起来解下自己的水壶,扳开嘴巴灌了几口水,一会儿他睁开眼睛问,额咋啦?我说,你刚才没了,是五保爷救的你!他说,哎,额都快够上酸枣了!五保爷一听,说,是为了够酸枣呀,你几个碎脑娃娃还没有柴火棍棍高,刚下过雨这沟坡滑,又陡,你咋能爬上去唻,看爷的!说着,举起鞭子,只听得“啪哈儿”、“啪哈儿”几声清脆的鞭声过后,一颗颗红嘟嘟、圆溜溜的酸枣带着青绿色的叶子扑刷刷纷纷落下,羊们咩咩叫着抢食枣叶,我们一边赶羊,一边在地上拾起滚落的酸枣,还不时往嘴里塞,似乎把刚才的一幕忘得一干二净。五保爷用他头上那灰不溜溜的羊肚巾抹了抹脸,扬起鞭子赶上羊:
你给谁纳的一双牛鼻鼻鞋
你的那心思我猜不出来
麻柴棍棍顶门风刮开
你有那个心思把鞋拿来
一座座山来一道道沟
我照不见那妹子我不想走
远远的看见你不敢吼……
晚上,我们几个娃都坐在炕上,围在婆身边,把今天的事向婆进行了诉说。我问婆,五保爷的衣裳可脏可烂了,腰里系着个麻绳绳,精脚(没穿袜子),鞋也露指头了,屋里的为啥不给他缝一下?婆说,五保爷是五保户。我说啥叫五保户,婆说就是没有婆娘,没有娃,光棍棍一个,就一孔破窑洞,啥都是队上管。婆又说,五保爷人好,虽然老了,但队上的羊没人放,他就主动给队上放羊。队上给他分的东西他经常接济娃多的人家,自己受穷。我说,五保爷为啥没有娃?婆说,没有婆娘哪来的娃!我们都问,那五保爷的婆娘哪达去了?婆说,五保爷家里精光精五个小子,他是老大,碎娃的时候,家里从很远的大山里给他定了一门娃娃亲。那女子到咱队上来过,长长的大辫子闪在腰眼里,脚片子大大的,一双毛眼眼忽闪忽闪的,可心疼人了。那女子也是个苦命人,家里姊妹七个,没一个男娃,上上下下加起来十一口人,都是吃饭的。五保爷去过几回,回来说,深山旮旯的,穷的七姊妹只有三条破裤子,谁出门谁穿,其余就在炕上围着破棉絮坐着。你五保爷与那女子可对上眼哩,两人心里都欢喜的不得了。快16岁的时候,两家思谋着正月里给过门。没梦想到那女子在来五保爷家的路上饿的不行,摘了路边的野果、野菜吃了中毒,没了(死了)。
从此,你五保爷疯疯魔魔的,白天晚上游逛,满嘴里唱调调,几里路都知道。家里穷,再没能力给他说上媳妇,就这样耽搁了,哎,可怜呀!
我说,婆,五保爷唱的调调可好听,你会不会唱?婆说,好,那额就给娃们唱一个:
娃娃你睡觉觉,娃娃你睡觉觉
山上下来个老瘦猴,嗯——
娃娃你睡觉觉,山上下来个老道道
脑上戴着个草帽帽,身上还系个草幺幺,嗨——
哎,老道道,草帽帽,哎呀——
小伙伴们后来知道了这事,经常打趣我说,梅梅女婿来了!我虽然不知道女婿是怎么回事,但也慢慢隐约知道这事羞人,就大声反驳他们:谁是女婿?有胆大的娃就说,女婿就是你以后要当人家的婆娘,晚上一个炕上睡觉,还要养一大群娃!然后他们就哈哈大笑,还说羞羞羞!
我又羞又气,哭得伤心,觉得没法见人。
那时,冬天有闲的时候,人们圪蹴在门口向阳的地方,靠在墙边,有的双手揣在袖筒里晒太阳;有的解开衣服捉虱子;还有的围在一起谝闲传,讲段子,算是在苦难的岁月里苦中作乐聊以自慰吧!有次放学,我和亚玲从他们身边走过,有个晒太阳的后生看见我,就怪腔怪调唱到:
一对对绵羊并呀么并排走,
哥哥能什么时候拉着那妹妹的手?
你要拉我的手,我要亲你的口,
拉手手呀么亲口口,咱二人圪崂里走。
拉手手亲口口,
圪崂里盛不够,
妹妹你呀不害羞
……
他故意把妹妹的音唱成梅梅,还对着我喊:拉手手,亲口口,梅梅,你的碎哥哥来了没,你们拉了手手亲了口口没?他旁边的人也跟着起哄大笑。我羞恨不已,觉得他们很无聊,是在羞辱我,眼泪不听话地流出来了,就从地上捡起一块胡基(土块)向他们扔过去,边哭边骂,伤心的不得了。
这时,一个姨过来安慰我,说,梅梅别气恼,他们与你耍笑,没有哈(坏)意思,又对那几个后生说,你几个哈怂以后不要在梅梅面前谝这些个,梅梅还是个碎娃,知不道个这!你看把娃羞成啥咧!
从那以后,我再不到他家去了,他来我家,我就躲在灶火圪崂里不见。
11岁那年,我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父亲去世了,后来又有几位亲人意外离世,他说要来我家帮着干力气活,可是一个12岁的娃娃能干什么活呢!很不现实。
七十年代中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是男多女少,政府鼓励男职工回老家找媳妇,不但给落户,还可以分到住房。我的继父就是这样回到家乡,经人介绍与我母亲结了婚。听继父说他一个月有38.92元工资(天啦!太富有啦!我们村一个工分才几分钱,我家一年到头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还有白面馍吃,还有面条子,饿不着人。母亲就决定带我和妹妹去新疆投奔继父。至于我那个“女婿”,他才13岁,正上中学,弟弟也小,家里一个小脚老婆婆,即使我过门去了他家,也是没法生活的啊!母亲没有办法,就把家里仅有的麦子卖掉,给他家赔了部分彩礼,算是把我的“婚约”给解除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新疆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一切都顺理成章,但童年那段娃娃亲,总是若隐若现的出现在我记忆力,他那双亮闪闪的大眼睛和朴实勤快的模样,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母亲有时也会提起我的娃娃亲,她说,那娃是个好娃,长得好看,手脚勤快,人也老实,每到春天播种,他都跟老师请假,说要给老丈人家拉肥料,老丈人家没劳力……哎,那时他才十一、二岁,还是个娃娃呀!也不知道他们一家现在日子过得怎样了?
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想起我的娃娃亲,想起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他家给予我们的帮助,帮我们度过了多少难关。在灵魂深处,时常有个声音在回荡、在发问: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你那纯真的神情忘不掉
你的帮助对我一生很重要
......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偶而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
......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
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
一直到老……”
人生是一场无法预测的旅行,在生命的列车上,乘客们上上下下,来来往往,有的注定成了过客,正如我和我的娃娃亲,就这样匆匆了断了。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滚滚红尘中,我们曾经相遇过,而最终劳燕分飞、不再有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