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失了四个多月的母狗沙拉回来了,它意兴阑珊地来到廊檐下的窝棚里,横躺下身子。尾巴反复敲打着地面,它似乎在跟自己的女主人打招呼。刘小巧溜了母狗一眼,拎起木桶大步走进猪棚。
那一群群的肉猪闻到食物的香味,哗啦啦地挤到猪槽边,仰起了硕大的脑袋“咕噜咕噜”叫个不停。刘小巧撂起瓢子在它们的猪头上轻轻敲打着,嘴里呵斥着“去去去,谁闹不给谁吃!”她来到里间的三个猪圈,“哝哝哝”地叫唤着。几只吊着大肚子的老母猪“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爬起来,晃晃悠悠走了过来。
刘小巧提起木桶把搅拌好的饲料倒进猪圈外特制的漏槽里,又用瓢子往里面捅了捅。母猪稀溜溜地吸着,而后开始大口大口地嚼起来。刘小巧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欠身摸了摸母猪胀鼓鼓的肚子。母猪边吃着饲料,边哼哼哈哈地表示答应。
此时,外边圈栏里的肉猪叫声更加尖锐了,它们甚至齐刷刷地把前腿搭在水泥栏上。刘小巧立即拎上一桶又一桶的饲料,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喂上了全部的猪。她站直了腰,浑身的衣服都让汗水给浸透了。趁着猪猡吃饱了睡着,她得赶紧下到圈里推粪。这样,可以让它们睡一个晚上的清凉觉,猪吃饱睡足了才长得快。
最近,猪价像发了情的母狗一样乱窜。听说到年底,猪肉的价钿还得往上爬。刘小巧退掉了厂里的活儿,扔下了两个月没有发的工资,下定决心养猪!
这些年来,村子里的年景变了,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生意,发着自己的财。有门路的在自己的屋子里办起了家庭小工厂,没有门路的起早摸黑地找活干。大家都很忙,忙到隔壁邻舍半年难得见一次面。熟人见了面,最要紧的问候就是你一年挣多少钱。说少了吧不好意思,说多了吧又心虚,只好不多不少装装门面。天天在那家家庭小工厂干着套扣的活儿,受老板的剥削,有时还要在你身上蹭点便宜。你得忍气吞声,一辈子都出不了头。刘小巧想着,看来,要想跟上潮流,还是得靠养猪。我累点苦点没关系,我做不了“养人”的老板,就做个“养猪”的老板。
一连三天,刘小巧都整夜候在母猪的圈外,等着它们生小猪。她在潮湿的地面上铺了层厚厚的稻柴,开了吊扇,点上蚊香。刘小巧累得全身上下的骨头好像都已经散开了,闭上眼睛就能睡着。在猪圈外面躺了半个多月,刘小巧成功地给三只老母猪接了生。她仔细数了数,一共生了45只小猪。如果当秧猪卖的话,每只小猪可得200块钱,她一下子就收入9000块。可是,刘小巧舍不得,她想把小猪养大,当肉猪卖,赚更大的钱。
那天走进猪棚,母猪发出了凄厉的长嚎。刘小巧立马赶过去,看到有一头母猪艰难地趴起来。小猪则疯狂地往它的肚子底下钻,叼着乳头不松口。原来小猪太多了,母猪的奶水不够。如果买奶粉的话,成本太高。刘小巧就拼命给母猪灌糖水,可是奶汁变得清汤寡水,没有营养。有些小猪甚至拉起了肚子,搞得刘小巧忙上加忙。
刘小巧扒拉着一碗油乎乎的康师傅泡面,坐在廊檐下的秧凳上。九月里的天气依旧是闷热,天空灰蒙蒙的好像沾满了油腻的抹布,似乎永远都绞不干。灰白色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了晒谷场上,它时时提醒着女主人,家家都要通汽车的。路上偶尔滑过一辆收购废品的三轮摩托车,或者慢悠悠地晃过买羊的脚踏车。唉,这潮流还是要跟上的。她想着以前做姑娘的辰光流行买辆凤凰牌自行车,到了做妈妈的年纪就要买屁股后面冒烟的摩托车了,现在倒好,时兴四个轮子了……潮流是一定要跟上的,不然儿子连对象也找不到,人走出去都没脸了。
咕咚,灌下了一口面汤,浓重的胡椒味直冲脑门,刘小巧忍不住狠狠地打了几个喷嚏。廊檐下的狗窝被惊动了,里面传出了“呜呜呜”的怪叫声。刘小巧这才想起自家的母狗沙拉已经回来了,奇怪的是沙拉没有声息地睡了十几天,看到陌生人也不像以前那样不要命地叫唤。现在,躲在狗窝里不知搞什么名堂。她放下饭碗,扒开狗窝,看到里面黑乎乎地趴着一窝的狗。原来,沙拉回家待产了。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同时生了一窝猪和一窝狗。可是,那几个黑不拉几的狗头越看越模糊,嘴巴宽阔地叼着狗奶头,如同一把铲子。四条腿犹如四根长歪了的老桑条,脚趾特别长。短促的尾巴粘在屁股上,瘦小的后腿紧紧夹着。
“可怜的沙拉死了老公,成了寡妇。它倒也痴情,挺着大肚子,硬是找了几个月。真的要生了,还记得回家?”刘小巧喃喃自语。四个月前,沙拉的爱侣,也就是邻居家的公狗黑鱼被套狗贼套走了。黑鱼惨烈的叫声惊动了窝棚里的沙拉,它挣脱铁链追上去。黑鱼在灰白的水泥路面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沙拉一路嗅着,一路找去……后来,有人说沙拉呆呆地站在一条河边。有人说它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游荡,饿得瘦骨嶙峋。有人说它在荒芜的矿山里乱窜,还有人说它被打断了脊梁,扔进了臭水沟……想不到,沙拉居然回来了,回来后还产下了一窝什么东西。
趁着沙拉起身出去找食的机会,刘小巧立即用蛇皮袋装了小狗,扎紧,还在上面绑了一块石头。来到河边,两岸都是数不清的野草,开着各种不同颜色的花。浓郁的花香里透出一股沉重的臭味,河边有好几个新建的养猪场,灰褐色的粪水肆无忌惮地排放到村中的河港里面。长长的狗尾巴草挠得人腿脚发痒,桑树的枝条时不时地抽到脸上。蛇皮袋沉甸甸的,挂到了一个树桩上。里面的两个小东西开始不安分起来,叽里咕噜叫个不停,乱窜。刘小巧停下了脚步,她想起了自己十月怀胎的情景。那个时候,孩子也是这样的在肚子里闹腾。顿时,她的心软了下来。唉,毕竟是两条活生生的命啊!
沙拉在什么地方吼叫了几声,刘小巧心里一惊,一甩手,噗通,蛇皮袋砸进了门前的河港里。河港里的水黑黝黝的,全是猪粪。有几只灰白的鸭子浮在上面,爆炸似的逃离开去,然后,又回过头来好奇地看着她。
逃也似的回到家,刘小巧看到水泥路上的沙拉正在吧嗒吧嗒地往回走,母狗肚子下胀嘟嘟的粉红色乳头直直拖到了地上。她的心中一亮,一个绝妙的主意在心头闪过。她立即钻进猪棚,从里面抱出了三只黑色毛皮的小猪,塞进了狗窝。狸猫换太子,哈,一换一个准。刘小巧不动声色地搅拌着猪食,暗地里斜着眼睛瞧。
沙拉垂着眼皮钻进窝棚就横着躺了下来,还伸出舌头舔起了小猪。很快,它们找到了滋润的奶头,巴扎巴扎地吮吸起来。嗨,那个,行!刘小巧捂住了嘴巴直乐。当然,她也没有亏待沙拉,剩菜剩饭全给了它。有时,自己吃半碗,给母狗留半碗。她要养着狗奶妈,好让它多出奶水。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小猪在狗窝里长得飞快。要命的是,沙拉的乳头被它们咬得伤痕累累。好几次,它愤怒地咆哮着。在乡下,但凡小狗小猫长大后,母狗母猫会十分讨厌。有时甚至会把狗崽猫崽引出去放掉。刘小巧见了,立即把小猪抱回猪圈。
看到一窝小猪慢慢长成了,刘小巧快活地睡了一个好觉。老公朱连荣也恰好换成了长日班,晚上,两个熟悉的陌生人终于又睡在了一张床上。朱连荣抱着老婆打趣:“侬一日到夜困在猪棚里,臭烘烘的,像只老母猪。”刘小巧一翻身,把老公压在了身下说:“叫你尝尝老母猪的厉害,亏得我养猪,猪价还在涨。看来,到年我们可以挣到这个数了。一年养一批猪,儿子读大学的钞票就有了……唉,嗨嗨……四个轮子的小轿车也会有……”她挥舞着两只大手,大汗淋漓,畅快地笑着。
“小巧,唉……你得担着点。我看那三只小猪不对劲,老是跟圈里的猪猡吵架……”朱连荣说,“好像是车间里新来的三个外地人,不怎么合群。”
刘小巧连连扭动腰肢,喉咙里踟躇着:“哦……哦……晓得了,晓得了,就你会看猪?”
深夜,猪棚里发出了凄烈的惨叫,沙拉也直起喉咙乱吼。刘小巧猛得推开朱连荣,披上衣服,穿着裤衩就奔到了猪圈。猪群爆炸了一样,尖声叫着,仿佛要把整个黑夜撕裂。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蚊子在成群飞舞着。拉亮了灯,那三个圈的成年肉猪已经跳在一起,喘着粗气正在乱挤乱撞,好像在逃避着什么。刘小巧赶到小猪圈,差点儿晕眩。三只黑色的小猪露着长长的牙齿,它们来回跑动,狂躁不安,疯狂地和其他猪崽撕咬。其他的猪仔围成一圈,对着三只小黑猪大声嘶叫,好像是面对着什么异类。刘小巧惊叫着,疯了似的抡起扫猪粪的长柄竹耙打过去。三个黑鬼退了几步,眼睛血红血红地盯着她看着。又低低地吼着,忽然跳出了猪圈,拱开了木门,风一样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虚开的木门拍打着墙壁,刘小巧惊骇无比,一颗心跳到了嗓子眼里。她转身跑出猪棚,迎面与老公朱连荣撞了个满怀。她语无伦次地喊着:“猪……狗……猪……狗……”朱连荣一把捂住了老婆的嘴巴,压着嗓门说:“不要喊,不要喊,你再喊,我们这窝猪可卖不出去了!”
靠在老公的胸膛上,刘小巧渐渐平静下来,打着寒战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朱连荣在各种各样的家庭小工厂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积累了一肚子的歪门邪道。他推开老婆,坐在门槛上点燃了一根香烟,不紧不慢地吸了几口,说:“那些咬死的猪崽挖个坑埋掉,千万不能扔到河里,免得丢人现眼。那些咬伤的猪崽明天给擦点黄药,说是得了瘌疮,便宜卖掉算了。我们最要紧的是保证那三十头肉猪没有事情,只要安稳到年底,我们还是能赚上不少!”
朱连荣的一番话讲得刘小巧心里慢慢有底了,她忍不住又问:“那三只黑猪怎么办?它们跑到哪里去了?如果到时候再回来,我们怎么对付?”
朱连荣吐出长长的一口烟说:“谁奶大的崽就念谁的情,我想畜生和人都是一样的。你把沙拉养在猪棚里,一天三顿喂足了,管保没事。”
沙拉懒洋洋地来到猪棚里,被刘小巧拴在粗大的廊柱上。它忧郁地看着猪群,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它涨大的两排乳房直直地挂下来。哪些猪在沙拉的注视下也变得安静起来,趴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第二天一早,刘小巧拎着猪食来到猪棚,发现沙拉已经不见了。廊柱上只留下一段咬断的绳索。她这一惊可不小,立即抄起手机给老公打电话。在一片机器的嘈杂声里,朱连荣喊着:“这该死的母狗,肯定是去找自己的崽去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村子里的怪事渐渐多了起来,那些家养的鸡鸭总是莫名其妙地丢失。还有,地里种的瓜果蔬菜也常常被糟蹋。本来这种事情根本算不上事情,但是事情偏偏撞到了宝强奶奶的枪口上。
一大早,宝强奶奶就找上门来了。
“小巧,我看到你家的狗了,两排奶子拖着地……”
“肯定是你老人家看花眼了,我家的狗,半年没有回家了。”
“狗偷鸡,活活地咬死了……满地的鸡毛……血……”
“狗怎么会咬鸡呢,又不是狼……”
“千真万确……两排奶子拖着地……”
……
宝强奶奶却是出了名的不吃亏,以前有过一回,她家养的刚生蛋的几只母鸡钻进柴垛里过夜的。有一天早上,宝强奶奶起来“咕咕咕”地叫唤着,然而母鸡却不见踪影。她急了,亲自钻到柴垛里掏,没有。出来后,她顾不上粘在头发的稻柴的碎屑,开始破口大骂。宝强奶奶的骂声尖锐,在村子里的每个角落回响。此时,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接口的。因为,你接了口,你就是撞到了枪口上。不是你偷的,你出什么头?
宝强奶奶指桑骂槐地骂了个够,见没有声息,就回家抄起电话拨打了110。谁知110说记下了,抓到小偷会通知她的。见没人帮她找鸡,宝强奶奶一狠心,倔劲上来了。她甩下一句话:“我养的鸡我认得哩,我到街上找去,我就不信找你不到。”她在县城的几个集贸市场进行了地毯似的搜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只还没卖出去的芦花母鸡。芦花母鸡也认出了她,扑棱着翅膀跳过来。宝强奶奶乐得敞开了怀,紧紧搂住芦花母鸡,一个劲儿地亲它的嘴。摊主不干了,他跳出来拉住宝强奶奶,说她偷鸡。
宝强奶奶瞪圆了眼睛吼道:“贼喊抓贼,什么世道?”两人拉拉扯扯,互相说对方是小偷,芦花母鸡也没有闲着,扑棱着翅膀咯咯大叫。市场里乱套了,大家围拢过来,都笑嘻嘻地看热闹。保安循声赶来,叫他们安静下来。
宝强奶奶大喊:“这鸡是我养的,它认得我哩。昨天夜里被小偷偷了,今天又找着了。我把鸡放下,只要在外面唤一声,它肯定跟我走。”
保安就让她试试,谁知宝强奶奶刚到大门口“咯咯咯……”一通叫唤,家禽市场里有好几只母鸡疯了似的拍打翅膀,朝门口跳去。原来,小偷贪方便,把母鸡都销赃给了这里的贩子。结果,宝强奶奶在保安的监督下,大摇大摆地找回了丢失的母鸡。后来,宝强奶奶的事迹被县报记者报道了。一时之间,她成了“名人”。
最近,宝强奶奶的芦花鸡又不见了。她跟随一路的鸡毛来到村后的横山,早晨雾霾霾的山上杂树乱生,西北方炸掉的山头张大了巨大的嘴巴,好像恨不得一口吞下整个村子。什么地方发出“呜呜呜”的奇怪叫声,平日里,这里人迹罕至。沙拉在山间懒洋洋地走动,阴郁的眼睛盯着宝强奶奶。
开山采石的那年,李宝强与老婆黄翠英刚结婚。会上,大队长问了声:“谁去放雷管?”
“我去,我去!”李宝强就跳了出来。
结果,随着一声巨响,李宝强翻滚着从山顶跌到了山下。从此,黄翠英成了寡妇。她几十年来未曾嫁人,成了村里著名的宝强奶奶。
两人的吵闹声吸引了很多人,大多是一些不去厂里上班的老人。他们在家里照例是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田地里的农活,邻里之间的来往,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琐事……
面对老邻居质问的目光,刘小巧心虚地说:“可能是我家的死狗回来了,黑鱼被人套走了,它就成野狗了。唉,我有什么办法呢?它又不听我的话。你们叫我怎么办?”
“马松老爹,来,来,来!你能装陷阱捕野兽的,快,你来讲两句。”还是宝强奶奶眼睛尖,她一下子发现了平时不大出门的老猎手。传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在山上抓到过狐狸。
马松老爹咬着烟嘴慢悠悠来到前面,“吧嗒吧嗒”吸着烟,良久才说:“捕啥兽,现在还有啥个兽?连山都快要炸平了。不就是一条狗么,不就是偷了一只鸡么,还搞那些陈年的劳什子做啥?大家都散了吧,连荣家的,你平时多唤着狗,喂饱点,不让它出去牵头皮……听我的,大家散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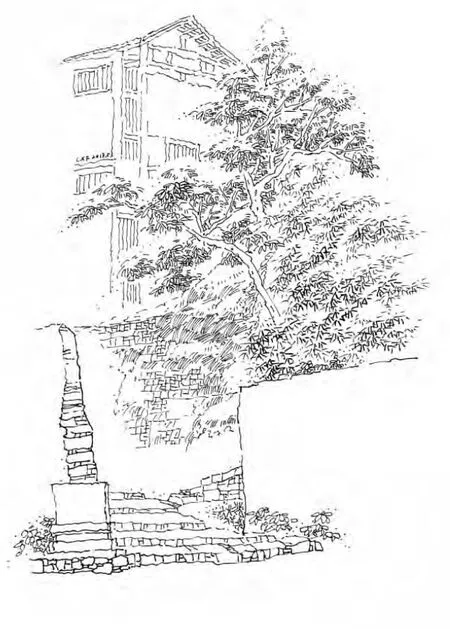
看着马松老爹趿拉着拖鞋远去,宝强奶奶只能打落的牙齿往肚子里吞,憋着一肚子气回家了。
“一阵风样地刮进来,看见点啥就拱点啥!”
“只看见两团黑影,也不晓得是啥东西。”
“遭了殃了,冲了秽物了。”
“腥,跟死鱼一样臭……”
马超的花木大棚给什么野物给拱了,泥地上姹紫嫣红,满目狼藉。这下,大火可烧到了马松老爹自家的院子里。他急急地来到大棚里,安慰了孙儿几句,实地查看了一番。最后,他看着苗圃里乱七八糟、深深浅浅的脚印不发一言。
广袤的田野里扎满了各式各样的棚子、毡房、简易屋子,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鱼塘虾塘。绿色的田野被分割成不规则的块状,白色的塑料薄膜,黑色的燃烧过后的灰烬,黄色的喷过草甘霖的草,艳丽的反季节的蔬菜和花朵……大家放弃了祖传的春耕秋收,一心做着发财的梦。宝强奶奶背着草篰走过,幸灾乐祸地看着马超。马超哭丧着脸问:“爷爷,你讲到底是啥东西?”
“野猪!”马松老爹咬着牙齿吐出两个字,全场的人顿时像被冰雹砸中一样,个个缩紧了脖子。
在村子的历史上,野猪始终是最恐怖的记忆。相传,村后的横山上生活着一窝野猪。它们藏在很深的洞穴中,平时很难找到。风调雨顺的年代,野猪拱着山上的冬笋、红薯,还有树上的蜂蜜、果子。它们在山上自得其乐,很少下山,似乎不喜欢熙熙攘攘的村落。
野猪下山只有两个原因:发情和饥荒。到了发情期,山下的村子里家家户户看紧了自家的圈里的猪,提防它们与野猪发生关系。如果谁家的母猪不慎被野猪奸污了,只能被斩杀。家猪与野猪交配后产出的猪凶悍无比,它们会不断地袭击家畜。还有,雌性的野猪释放出浓重的腥臊味。惹得村中的公猪发了狂地乱窜,有的甚至冲破了栏栅,跟了那些野猪跑到横山上,一去不回。
民国廿三年大旱,庄稼蔫了,山下的人家靠着地窖中储存的红薯勉强度日。野猪在山上掘地三尺,连竹园子里的鞭笋也掏着吃了。饥饿是一副看不见的毒药,发作的时候连石头都会咬上一口。乘着夜色,野猪一窝蜂地下了山,看见什么咬什么。它们的鼻子特别灵敏,很快就找到了地窖中的红薯,洗劫一空。人们惊恐万分,竟然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野猪吃饱回山后,村子里到处都是腥臭的粪便,混乱的脚步。
人们来到马松家的泥场上,日头如同一块浓稠的痰贴在灰蒙蒙的天空。大家个个面黄肌瘦,气喘吁吁地盯着马松的爹马三枪,他可是村中世传的猎手。他家有一杆历代相传的老枪,山上的猎物除了野猪都作了抢下鬼。马三枪背着双手说:“野猪不是寻常的猎物,皮厚肉坚,一枪打不死,就会有大麻烦。它还会记仇,打了野猪,我得准备搬家。除非……斩草除根。”
看着满脸菜色的人们,马三枪摸着咕咕作响的肚子说:“用老鼠药,野猪肚子饿了,肯定还会下山……”
一窝野猪倒在了村外回山的路上,个个瞪大了眼睛,紧缩成一团,铲子样的嘴巴里喷出了红色的液体……它们的头齐刷刷地朝向山上。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马三枪咬着烟嘴来到山脚下,对着一行远去的新鲜脚印陷入了沉默。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马松重复着当年父亲的那句老话。他们家传的老枪早已被政府收走,老鼠药也无处可买。思虑再三,马松决定上山去铲几个陷阱。
第二天清晨,焚过香,喝过烧酒,马松带领几个村子里精壮的汉子扛着工具来到横山脚下。雾气中,横山自东向西黑魁魁地蹲着,如同一头狮子。在辽阔的平原地带,这涌出地面的狮形山体天生就是奇迹。每一个晴天,橙红的太阳总是在狮子头顶缓缓下沉。狮子张大的嘴巴好像含着一枚火球,此时,整个横山通体火红。如今,狮子的头部已经炸掉,露出一个黑洞。远远望去,如同被一把看不见的利刃砍去了。
山坡上盛开着黄色的野蔷薇,一丛丛,一片片,晃得耀眼。浓郁的香气灌入鼻腔、口腔,让人沉醉、麻木。狗尾草长长地摇摆着,在九月的阳光下显得很不真实,痒痒地撩拨着人们的纤弱的神经。绊头根草在看不见的地面上蜿蜒,冷不防会狠狠地让你栽个大跟斗。前些年的松树已经被人砍伐,留下坚硬的树桩埋在地上,长出各种黑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蘑菇。鬼蜡烛草泛着橙黄的色彩,它的枝干近乎透明,渗出丝丝黑色的汁液,诡异地伸着懒腰。一阵风刮过来,云遮雾罩,四下里一片沙沙沙的声响。大家打了个寒战,不知该往哪里走。
“找到野猪的粪便就好办了。”马松压着嗓子低低地吼着,“我们要抓紧时间,趁着日中太阳大,野猪正在睡懒觉,快点寻。”
大家握着橛子在草丛里探寻着,缓慢地移动身体。转过一处山坳,前面是片开阔地带,雾气散尽。有人发现前面的有一块灰白的岩石在转动。仔细一看,惊得大喊:“沙拉,连荣家的雌狗,一排奶子拖着地,怎么会在这里?”
沙拉从那块洁白的岩石上站了起来,它拖着沉重的一排奶子,俯瞰着山坳里的那些黑色的人影。它看上去非常消瘦,褪了毛的脊梁如同锋利的刀刃,直刺灰色的天空。
马松觉得眼前的天空似乎抖动了一下,他伸手拉住两边的同伴,喊着:“别动,野猪可能就在后面的石窟里。看来这是一头公猪,它忍耐不住,竟然勾引了连荣家的雌狗。”
话音刚落,岩石后面忽而爆发出了几声尖锐的猪叫。马松他们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蹲在地上,不知所措。马松悄声说:“幸亏我们是在下风口,千万不要冲撞了野猪。听我口令,慢慢后退,下山再想办法。”沙拉冷冷地看着他们,而后,它转过身钻进了岩洞中。
昏黄的太阳在残破的山头上落下去了,好像被什么东西一口咬掉了。吃过晚饭,村里的人开始往刘小巧家赶。刘小巧喂好了猪食,正在乘它们吃食的当儿推猪粪。
“小巧,小巧啊,你出来一下。”马松老人苍劲的声音穿透了猪们稀里哗啦的捣食,直打在刘小巧的耳膜上。
刘小巧磨磨蹭蹭地提着猪食桶走出来,迎面就喊:“哦,原来是马松老爹呀,您这是去喝早茶?还是在村子里溜达?”
马松砸吧着嘴巴说:“小巧,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就别跟我瞎猫糊了。你家的雌狗牵头皮,勾引了野猪闹事,你可得管管。”
刘小巧心里一个凌子,嘴上却说:“唉哟,老爹,如今的狗都被摩托车给套走了。哪里来的野狗?怎么都算在我的头上?”
马松老人自顾自地说:“这狗还得靠你收,不来的话,村子里的损失都得叫你造。我们还是好好合计合计,该怎么收拾。”
沙拉是刘小巧捡来的,那个时候,她刚刚嫁到横山村。有一天,刘小巧赶集,翻过横山才能来到外面的机耕路上。回来路过山坳口,听见一阵呜咽声。初听,还以为是个孩子。她想,谁这么不要脸,生下孩子丢掉。刘小巧循着声音找去,发现在不远处的茅草丛里有动静。她紧走几步,拨开乱草,看见一只黑白花色的小狗趴在草窝子里喘着粗气,正在一只瘦骨伶仃的母狗身下拱奶。刘小巧是新嫁娘,心肠子软,她蹲下身捉住小狗的前腿。谁知,小狗伸出舌头舔了舔她的手指。潮湿、温暖的感觉唤起了她天生的母性。肯定是饿坏了,刘小巧赶紧掏出一包饼干,用水泡软了送到这对母子口边。谁知,母狗艰难地摇了摇头,盯着小狗摇着尾巴。刘小巧明白了它的心思,她把饼干全部送到了小狗的嘴边。
刘小巧在树下的石头上坐着,四下里一片寂静。清明时节,杨柳扯出了一缕一缕白色的絮。蒲公英不甘心落后,稍微有点风,就蹦散着去寻找自己的家。一对对喜鹊飞舞着,叫着“恰恰好,恰恰好”,时不时地站在枝头摇摆着,交着尾。如果它们衔着树枝,就欢喜地回到半空中的窝里加固,准备着下蛋孵化小喜鹊。风暖暖地吹过来,送来了各种花的香。小巧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面没来由地痒痒的,身体里一股潮湿泛了起来。她想,我得要个孩子!
刘小巧又给母狗喂了点水,心想明天再来看它们吧。她折了些树枝,给它们搭了个棚子,上面铺了些竹叶。又看了一会儿,就走了。回到家里,刘小巧发现自己的钱包掉了,里面可是一个月的工资呀。她急得满脸通红,翻遍了皮包也找不到。怎么办呀?她来来回回,坐立不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娘家的母亲生病得买药,结婚时还欠下一笔钱……脑子里快速转动着。刘小巧心慌意乱,出了门沿着来路找去。当她来到山坳口,又听见一阵呜咽声。她发现母狗趴在刚才坐过的石头上,正看着她轻声叫唤。刘小巧疑惑地走近,谁知,母狗咬住了她的衣角不放。她坐在母狗身边,它努力地翻过身,石头上赫然躺着粉红色的皮夹子!原来,它发现了刘小巧遗留在石头的红色皮夹子,怕被人捡去,就一动不动地趴在上面,等待着。
此时,母狗猛地抽动了几下,就垂下了沉重的脑袋。刘小巧的心也抽动着,长时间地静默着。蝴蝶还在花丛中飞动着,蜜蜂来来回回采花蜜。一切还是刚才的样子。她把母狗埋在了一个石洞,外面用野花遮住了。来到棚子跟前,小狗还在沉睡,刘小巧俯下身,轻轻抱起了它。
“你在前边走,我们跟在后边。你只要呼出母狗沙拉,野猪就在它身后。一有情况,我们就射击。”马松老人向村里汇报了情况,打了证明,去镇里的派出所领回了老猎枪。
刮了一夜的大风,山下的田地里铺满了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花瓣。雨横风狂三月暮,横山上的泥沙汇成了小溪,缓慢地注入到村子里。褐色的泥沙混合着各色鲜艳的花朵,构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山上的杂树也吹得东倒西歪,乱糟糟的,如同一个疯子长年不洗的头发。
在风停的间隙里,刘小巧摸索着来到了上山的路上。一路走,一路呼喊着“啧啧啧,沙拉,啧啧啧,沙拉……”声音在山谷里不断地回荡着。来到百丈岩口,刘小巧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她诧异地发觉周围的一切怎么会那样熟悉,那一棵树,那一丛花,还有不远处的一个棚子。哦,原来这里就是当年刘小巧遇到沙拉母女的地方。草棚里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分明看见沙拉摇晃着尾巴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沙拉,真的是你吗?沙拉?”刘小巧绽开了笑容,这一刻,仿佛时光倒流。她站起来,忘记了此行的使命,等待着沙拉扑向自己的怀抱。轰,一条长长的火舌射向沙拉。数不尽的霰弹打在了岩石上,刘小巧的双腿瞬间软下去,整个人瘫倒在地上。沙拉全身震动了一下,嫣红的鲜血从前腿流出来,它不顾一切地冲到女主人的跟前。
“走,快走!”刘小巧忍住疼痛,随手抓起几块碎石,奋力掷过去。沙拉没有躲闪,盯着她看着。
“小巧,趴下,我再给它一枪!”马松老人沙哑的声音再度响起。
刘小巧抓着树枝站起来,声嘶力竭又扔过去一把碎石。沙拉跺了一下前脚,转身隐没在荒草丛中。
一阵怪风从山谷里旋转,轰隆隆,崖顶滚下来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向躲在树后的马松老人他们。“野猪拱石!”马松怪叫着扔掉猎枪,双手抱头,率先滚下山坡。幸亏石头被树挡了一下,随着闷响,砸向了悬崖。
一个小时后,马松组织了一批身强力壮的村民,敲打着铜锣,燃放着鞭炮,招摇着灵符,声势豪壮地爬上山来。刘小巧被他们抬下山去,送到镇卫生院检查。幸好只是皮外伤,包扎上厚厚的纱布,回家静养。连荣看到自己的老婆受了伤,直起喉咙要找马松老人算账,还嚷着今后一窝棚的猪谁来养?
第二天一大早,村后又传来呼天喊地的声响。村子里的人一窝蜂似的全涌过去,原来是驼子关强的羊被什么东西咬死后拖走了。地上一条血线,从羊棚里延伸到村外……
“有小偷杀了羊拖走的。”连荣嘀咕着,想澄清真相,“沙拉奶了猪仔逃到了山上,没有野猪……”
看到连荣,马松伸出枯树枝般的手指点着他的额头说:“你家养的什么狗?勾引野猪,下流污秽……我们差点让野猪砸死……我看根本不是狗,是一头狼……”
“我家的鸡又少了两只。”
“我家的鸭不回窝棚了。”
“一头狼,一头狼。”
“还有野猪……不要脸。”
“什么年头,狼跟野猪搞到一块了?”
连荣的气焰立即被大伙儿的口水给浇灭了,他蹲下身,一根连着一根地吃香烟。最后,大家拥护着马松老人拿个主意。马松阴郁的眼光扫着大家,每个人被他看到时都会不由自主地一阵寒冷。他苍凉的声音再度响起:“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放火烧山!”
“放火烧山?”
大家心头好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放火烧山!”马松不慌不忙地说,“狼狡猾,野猪凶残,它们杂交后产下的东西叫做狈。狈比我们人还要聪明十倍,恐怕到时候我们村子就要遭殃了。放火烧山,斩草除根。”
“放火烧山,斩草除根。”大伙儿的心又被莫名的火焰点燃了。
各种野花的香味在黑夜里酝酿着,横山村全体村民出动,在马松老人的指挥下,人人背了一捆柴火。山脚下堆好了干柴,要道口,岔路上也塞得满满的。最后,大家看着马松老人不说话。他细细长长地抽完了一根香烟,挥了挥手。几个精壮汉子各自拎着汽油在山下洒了一周,然后,又远远地退了开去。马松老人又点燃一根香烟,猛抽几口,一抖手,划出了一道火星。
轰,蓝色的火焰腾空而起。逼啵逼啵,红色的火浪排山倒海。满山呜咽,黑色的浓烟比黑夜更黑。瞬间,整个横山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夜空也被烤得通红,颤抖着,好像要马上掉下来。众人被逼得倒退出100多米远的地方,站着,火焰给每个人镀上了金色的光环。
接连不断的狂吠声,尖锐地猪叫声,各种鼠类的吱吱声。几只喜鹊从睡梦中惊醒,怪叫着,带着燃烧的翅膀飞行,然后重重地砸向地面。还有数不尽的虫子,在烈火中爆裂着。好像焖着爆米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看,沙拉……”
众人抬头看见在横山北部炸掉的狮子头上,沙拉站在上面,纹丝不动。身后,还有三个黑影,紧紧地靠着它。
“狼……野猪……”
“它们逃不掉了,它们逃不掉了……”
在烈火的映衬下,沙拉浑身雪白,宛若一头真正的草原雪狼。它低头看着众人,忽然,仰头对着夜空,一阵狂嚎。声音如同冰雹,砸向每个人的心头。接着,沙拉缓缓退后几步,一个俯冲,跳下了悬崖,跳向黑沉沉的夜空。身后的三个黑影,如影随形……
一阵狂风吹来,火势转向,对着村子蔓延过来。
文学港 2014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