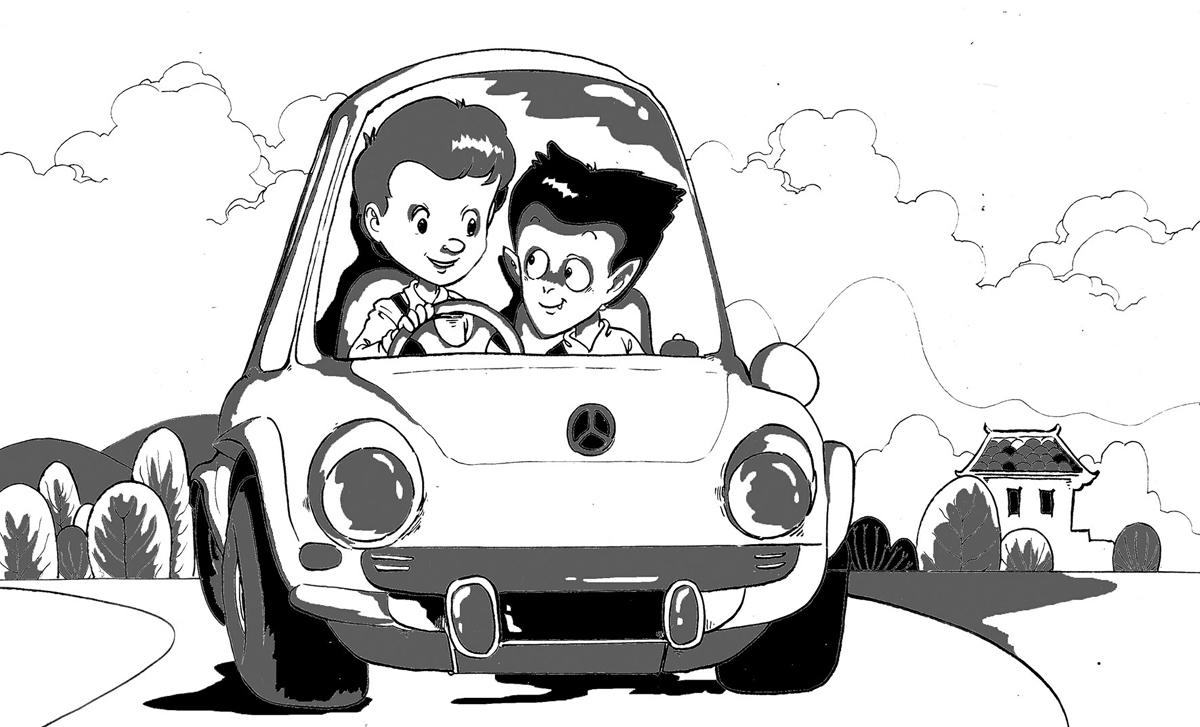
我买了一辆新车,一部大功率的宝马3.3Li,意思是说3.3升,长轴距,燃油喷射。它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129英里,加速度快得惊人。车身是淡蓝色的。车内的座位是深蓝色的,都是皮制品,真正的软皮,最最高级的质量。车窗都是用电开启的,车顶也是如此。当我打开收音机时,天线自己竖起来,关掉的时候,天线自己消失。大功率的发动机在低速度的时候,发出轰隆轰隆的吼声,但是到达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轰隆声停止了,马达发出愉快的嗡嗡声。
我亲自驾车到伦敦去。那是一个美好的七月天。田野里正在翻晒干草,公路的两边也都是毛茛。我正在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下轻轻地自言自语,背舒舒服服地靠在座位上,用不到兩个手指头轻轻靠在驾驶盘上让它驾驶平稳。我看到前面正有一个人伸出大拇指,要求搭车。我碰碰刹车,让车停在他身边。我常常为搭车人停车。我知道站在乡村公路边,眼巴巴看着一辆辆车子在你面前经过,我恨那些驾驶员假装没看见我,特别是那些开着大车子,车子里还有三个空位的人。那些豪华的轿车难得停下来。倒是那些小车、生锈的旧车、已经挤满小孩的车子会让你搭车,那司机会说:“我看我们还能乘一个。”
那人从打开的车窗外探进头来说:“老板,到伦敦去吧?”
“是的,”我说,“上来吧。”
他上车了,我就开走了。
那人长着一张老鼠脸,一副灰色的牙齿。眼睛黑黑的,像老鼠眼睛一样骨碌骨碌转得很快。耳朵上方看上去有点尖,他头上戴一顶帽子,身穿一件浅灰色的夹克衫,上面有几个大得出奇的口袋。那件灰夹克,加上那骨碌骨碌的眼睛,尖尖的耳朵,无不使人觉得他像一个巨大的人形老鼠。
“你想去伦敦什么地方?”我问。
“我要穿过伦敦,在伦敦那头下,”他说,“我要到埃普索姆的赛马场,那里今天举行德比赛马。”
“没错,”我说,“我希望我能跟你一起去,我喜欢赌马。”
“我从不赌马,”他说,“赛马的时候,我看都不看。这些都是愚蠢透顶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到那里去呢?”
他似乎并不喜欢我问他这个问题。他那张小小的老鼠脸白白的,坐在那儿眼睛看着前方,一声不响。
“我想你是在赌博机之类的东西方面帮帮忙的。”
“干这种事情岂不是更傻吗?”他回答道,“修理那些蹩脚的机器,好让它们卖票给那些傻瓜,那算什么活儿!任何笨蛋都能干!”
好一会儿谁也不说话。我决定不再向他提问。我记得过去我打车的时候,司机不停地问我种种问题问得我很烦躁。你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去?你是干什么的?你结婚没有?是不是有了女朋友?她叫什么名字?你多大啦?诸如此类的问题问个没完没了。我往往很讨厌人家这样做。
“我很抱歉,”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不关我什么事。问题是,我是一个作家,大多数作家都特别爱管闲事。”
“你写书?”他问。
“是的。”
“写书能行,”他说,“这是一个我称之为有技术的行当。我也从事一个有技术的行当。我看不起那些人终身做一样千篇一律令人讨厌的工作。这些行当根本没有一点技术可言。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生活的秘诀,”他说,“就是成为非常擅长的人,做非常非常难做的某些事情。”
“就像你一样。”我说。
“完全正确。你跟我都是这样。”
“是什么使你觉得我擅长我的工作?”我问,“我们周围坏作家可有一大堆。”
“要是你干得不怎么样,你不会开这样一辆车。”他回答道,“这辆车一定很昂贵吧。”
“果然不便宜。”
“它开足能开多快?”
“每小时129英里。”我告诉他。
“我敢打赌,它到不了这个速度。”
“我敢打赌,它一定到得了。”
“所有汽车制造商都是吹牛皮大王,”他说,“你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任何一辆车,可没有能开到制造商在广告里所说的速度。”
“这一辆能行。”
“那就开起来,证明它能行,”他说,“说干就干,老板,快起来,让我们看看,它能快到什么程度。”
恰尔韦德·圣彼德那儿有一段环形路,过了这段路,前面马上是一条笔直的双向车道,很长很长。我们开出环形路,上了双向车道,我的脚踩紧油门,我那辆大车子便朝前蹿去,好像有什么叮了它一口。不到十秒钟,我们已经达到每小时90英里。
“棒极啦!”他叫道,“干得好!继续开!”
我把油门一踩到底,并且一直不松开。
“100英里!”他叫道,“105英里!110英里!115英里!加油!不要松劲!”
我正开在外车道上,我们飞快地掠过几辆车子,好像它们全都纹丝不动地停在那里——有一辆绿色的微型车,一辆奶油色的雪铁龙,一辆白色的路霸,一辆有货厢的大卡车,一辆橘色的大众小公共汽车。
“120公里!”我的乘客大叫大嚷,身子蹿上蹿下,“加油!加油!让它开到129英里!”
这个时候我听到了警笛的尖叫声。声音非常响,好像是在车子里边发出的。然后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赫然出现,沿着内车道超过我们,举起手示意我们停下。
“哦,我的姑奶奶!”我说,“这下完蛋啦!”
那警察超过我们的时候一定开到了每小时130英里,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慢下来。最后他停靠在公路边,我停在后面。“我不知道摩托车竟能开这么快。”我有点不以为然地说。
“那一辆能行,”我的乘客说,“它跟你的车子一个牌子。它又是一辆宝马R905,最快的公路摩托车。他们如今就用这个牌子的车子。”
警察从摩托车上下来,把车子的撑脚架撑在路边,然后他取下了手套,很小心地放在坐垫上。这个时候他不慌不忙。他迫使我们停下,停在他要我们停下的地方,这点他很清楚。
“这下真遇上麻烦了,”我说,“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不必要的话,不要跟他多说,这点你也清楚,”我的伙伴说,“坐得稳稳的,保持沉默。”像是一个刽子手走向死刑犯,那警察踱着方步向我们走过来。那是一个粗壮的大个儿,挺着一个大肚子,蓝色的警裤紧紧绷在硕大无比的屁股上。他的护目镜拉在他的头盔上,露出一张宽宽的红脸,冒着怒火。
我们坐在那里,像是两个犯了错的小学生,等他走上前来。
“留心这个人,”那乘客低声说道,“这个人看上去报复心很强。”
那警察绕到我打开的车窗前,把一只肉鼓鼓的手放在窗框上。“这么着急干吗呢?”他说。
“我没什么可着急的,警官。”我回答道。
“是不是后座有个妇女要生孩子,急着要送医院?是不是这回事?”
“不,警官。”
“要不就是你家房子着了火,你要赶去把家人救下楼来?”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阴险的嘲弄。
“我家的房子没有着火,警官。”
“那样的话,”他说,“你让自己陷入了糟糕透顶的困境。你知道这个地区限速是多少吗?”
“每小时70英里。”我说。

“那你介意不介意跟我说说,你刚才开的准确速度?”我耸耸肩膀,什么也没有说。接下来他说话的声音突然提得高高的,吓了我一跳。“每小时120英里!”他大声叫道,“超过限速每小时50英里!”
他转过身吐了一大口唾沫,它落在我车子的侧翼上,开始从我漂亮的蓝漆上淌下来。然后他再次转过身,仔细打量我的伙伴。“你是什么人?”他很不客气地问。
“他是一个搭车人,”我说,“我让他搭乘一段路。”
“我有没有做错事?”我的乘客问。他的声音软得像油光光的发蜡。
“样子挺像,”那警察说道,“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见证者,我回头来处理你,驾驶证!”他伸手来向我要,声音很严厉。
我把证件给了他。
他解开紧身短上衣的左胸袋,取出一本让人畏惧的罚单簿。他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我那驾驶证上的名字和地址,然后把证还给了我,他又踱到车子前面讀了车牌号码,记了下来。他再填上日期、时间和我违章的细节。接着,他撕下罚单簿最上面的一页,在递给我之前,他又跟复写纸上印下的各项仔细核对一遍。最后他将罚单簿放回胸袋,系上扣子。
“现在轮到你啦!”他对我的乘客说。他绕到车子的另一边,从另一个胸袋里掏出一本黑色记事本。“名字?”他凶巴巴地问。
“米歇尔·菲什。”我的乘客说。
“地址?”
“卢顿温德-索尔胡同14号。”
“给我一样东西,证明你的姓名和地址都是真的。”那警察说。
我的乘客在他的那些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摸出一本他的驾驶证。警察核对了姓名和地址,还给了他。“你干什么职业?”他突然问道。
“我是一个泥灰工。”
“什么?”
“搬运泥灰的小工。”
“怎么写?”
“搬运水泥灰浆的小工。”
“那就行啦,泥灰工做些什么,我倒要问问。”
“警官,那就是运水泥灰浆上扶梯,递给砖瓦工。他们搬的是一个灰浆桶,有一个很长的柄,上面有两块木头,钉成一个角度……”
“行啦,行啦,谁是你的雇主?”
“一个也没有,我失业啦。”
警察把这些都写在黑色的笔记本上。然后他把本子放回口袋,系上扣子。
“回到所里,我要对你进行一番小小的调查。”他对我的乘客说。
“我?我做了什么错事?”那个长着老鼠脸的人问。
“我不喜欢你的脸,就是这么回事。”那警察说,“说不定在我们的档案里正好有你的一张照片。”他又踱回我的车窗前。
“我看你也知道,你惹上了一个大麻烦。”他对我说。
“是的,警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再也驾驶不了你这辆时髦的车子了。至少在我们没有给你了结之前。说不好,有好多年,你再也不能驾驶任何车子了。这也是一件好事。我希望他们另外还关你一段时间。”
“你的意思是说关在监狱里?”我有点慌张,赶紧问道。
“完全正确,”他咂咂嘴说,“关在牢里,铁栏杆后面,跟其他违法的罪犯关在一起,另外还要缴一大笔罚款。没有人比我更乐意看到这个结果。我会跟你们两个在法院见。你们会收到出庭的传票。”
他转身走开,走向摩托车,用脚拨开撑脚架,抬腿跨上坐垫,踩了踩发动器,便在公路上开走了,一会儿工夫,就不见了踪影。
“嘿,”我喘了口气,“这下完蛋了!”
“我们被抓住了,”那乘客说,“我们被抓住了,被抓个正着。”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被当场抓住了。”
“可不是吗?”他说,“现在你准备怎么办,老板?”
“我直接上伦敦去,跟我的律师谈谈。”我说着发动了车子,上了路。
“他跟你说,要把你关进监狱,这种话你千万别信,”我的乘客说,“因为超速,他们不会把谁关在铁栏杆后面的。”
“你能肯定?”我问。
“完全肯定,”他回答道,“他们会拿走你的驾驶证,敲你一大笔罚款,这就到头了。”
我觉得大大松了口气。
“顺便问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对他说谎?”
“谁?我?”他说,“是什么让你以为我说了谎?”
“你告诉他你是失业的泥灰搬运工,但你说过你是属于高级技术行当的。”
“我确实是,”他说,“什么都跟一个条子说不值当。”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啊,”他躲躲闪闪地说,“是不是一定要说?不说行吗?”
“是不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不可告人?”他叫了起来,“我,工作不可告人?我还要为它感到骄傲呢!在整个世界上不是谁都能干这个工作的。”
“我并不在乎这个行当那个行当的。”我跟他扯了一个谎。
他那狡猾的老鼠瞥了我一眼。“我看你在乎。”他说,“我在你脸上看得出来,你以为我从事一种非常特殊的行当,你一心想知道究竟是什么。”
我等着他继续说。
“你看,因此我谈到它格外小心。比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另一个便衣警察呢?”
“我看上去像个条子吗?”
“不,”他说,“你不像,也真的不是。随便哪个傻瓜都看得出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听烟丝、一包香烟纸,开始卷起一支香烟来,我用一只眼睛的眼角看着他,这个活儿比较困难,但是他完成的速度快得叫人难以相信。不到十秒钟这支烟就卷成了。他的舌头在纸边一舔,烟纸就粘住了,噗的一声,香烟就叼在他的嘴唇上。然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只打火機出现在他的手里。火光一闪,香烟就点着了,打火机就不见了。这一整套表演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谁卷一支香烟卷能那么快。”我说。
“啊,”他说着深深吸了口烟,“这么说,你注意到了。”
“我当然注意到了,快得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他背朝后一靠。我注意到他卷烟的速度非常快,这使他非常开心。“你不想知道为什么我能做到这一点?”他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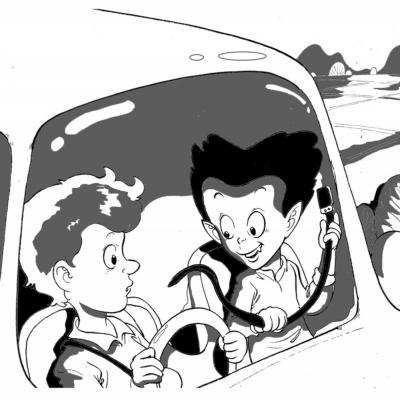
“那就请说说吧。”
“因为我有灵巧的手指,这些手指只有我才有,”他说着把手高高举起在他的面前,“它们比世界上最出色的钢琴家的手指还要灵巧。”
“你是钢琴家?”
“别开玩笑啦!”他说,“我的样子像吗?”
我看了看他的手指,它们果然很美,又细又长,有模有样。看样子这种手指头不可能属于其他人,只可能属于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或者钟表匠。
“我的工作,”他继续说,“要比钢琴家演奏难上一百倍。任何傻子都能弹钢琴。如今你走进家家户户,差不多总有一个个矮矮的小孩在弹钢琴。这是事实吧,是不是?”
“多多少少是那么一回事。”
“当然是事实。但是一千万人里,没有一个能学会我手上的活。一千万人里也没有一个!你怎么看?”
“惊讶极啦!”
“你惊讶极啦,这就对啦。”他说。
“我想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我说,“你是变魔术的,是一个魔术师。”
“我?”他哼着鼻子表示轻蔑,“一个变戏法的?你能想象我在那些挤满孩子的讨厌晚会上混日子,从大礼帽里变出兔子来?”
“那你是一个玩纸牌的行家,你让人家进赌局,你用你那了不起的一双手出老千。”
“我?一个人人讨厌的爱出老千的人?”他叫道,“那是一个可悲的营生,如果这也算是一种营生的话!”
“好吧,那我实在猜不出。”
现在我让车慢慢地往前开,每小时不到40英里。我们不得不开上伦敦到牛津的主干道,走在开往丹哈姆的下山路上。
突然我的乘客举起手中的一根黑皮带。“见过这根皮带吗?”他问道。那根皮带有个设计特别的扣子。
“嘿,”我说道,“那是我的皮带,是不是?从哪儿弄到的?”
他咧嘴一笑,轻轻晃了晃皮带。“你以为从哪儿弄到的?”他说,“当然是从你裤腰上弄到的。”
我伸手摸了摸我的裤腰,皮带果然没有了。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驾驶的时候,你从我裤腰上取了下来?”我问,有点目瞪口呆。
他点点头,一直用他黑黑的老鼠般的小眼睛看着我。
“那不可能,”我说,“你得解开扣子,把整根皮带从裤腰扣里抽出来。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总会看见的,就算没看见,也总会有感觉的。”
“啊,但是你没有,是不是?”他洋洋得意地说。他把皮带丢在膝盖上,这时突然有一根棕色鞋带从他的手指上荡下来。“对这个你怎么说?”他大声问,晃了晃手中的鞋带。
“这是怎么回事?”
“谁丢了这根鞋带?”他又咧嘴笑了笑问。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鞋子,一只鞋的鞋带没有了。“真是奇怪!”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根本没有看到你弯过腰。”
“你什么也没有看到,”他骄傲地说,“你甚至,没有看到我移动过一分一寸。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
“知道,”我说,“那是因为你有十只灵活得叫人难以相信的手指头。”
“一点不错,”他叫道,“你的理解相当准确,是不是?”他背朝后一靠,吸了一口自制的香烟,在挡风玻璃上吹了一股淡淡的烟。他知道他的两个小把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使他很开心。“我不想迟到,”他说,“现在几点啦?”
“你前面就有一只钟。”我告诉他。
“我不相信车上的钟,”他说,“你的表上是什么时间?”
我撩起袖口看了看表,谁知表不见了。我看看那个人,他回看我一眼,笑了。
“你把表也拿走了?”我说。
他举起手,我的表躺在他的手掌里。“这东西不坏,一只好表,”他说,“质量很高,十八克拉金表。很容易脱手,高质量的东西脱手从不麻烦。”
“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要回来。”我气鼓鼓地说。
他小心翼翼地把表放在他面前的皮盘上。“我不会捞走你的任何东西,老板,”他说,“你是我的伙伴,你让我搭车。”
“我很高兴聽你这么说。”我说。
“我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他接着说下去,“你问我靠什么为生,我就做给你看。”
“你还拿了我一些什么东西?”
他又笑了,开始从口袋里掏出一样样东西来。这些东西全都是我的:我的驾驶证,钥匙圈,四把钥匙,几镑钞票,几个硬币,一封出版商的来信,我的日记本,一截又短又粗的铅笔头,一只打火机,最后还有一枚镶珍珠的蓝宝石戒指——那是我妻子的东西,因为珍珠掉了一颗,我要拿到伦敦的珠宝店去修理。
“现在还有一件可爱的宝物,”他边说边在他的手指上转动一枚戒指,“我要是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十八世纪的古董,国王乔治三世在位时候的东西。”
“又给你说对了,”我毫不惊奇地说,“一点也不错。”他把那枚戒指跟其他东西一起放在皮盘上。
“这么说来,你是一个扒手?”我说。
“我不喜欢这个字眼,”他回答道,“一个粗俗的字眼,扒手只是一些粗俗的人,只做一些容易做的业余活儿,他们在瞎老太婆身上扒钱。”
“那你怎么叫你自己呢?”
“我?我是一个手指匠。我是一个专业的手指匠。”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非常严肃,相当骄傲,好像他正在告诉我他是皇家医科大学校长或者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一样。
“我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我说,“那是你发明出来的?”
“当然不是,”他回答道,“这个头衔只给予达到职业顶级的人,你听到金匠银匠的头衔吧,他们都是金子银子行业的专家。我是手指行业的专家,我叫手指匠。”
“那一定是一个有趣的行当。”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当,”他回答道,“非常美好的行当。”
“这就是你去赛马会的原因?”
“赛马会上最容易到手肥肉,”他说,“你只要到处走走,到处站站,看着那些走运的人排着队取钱。当你看到有人领了一大包钞票时,你只消跟着他,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但你千万别误解我,打赌输的人身上我分文不取。穷人那儿我也分文不取。我只从丢钱丢得起的人那儿取钱。”
“那是你想得周到,”我说,“你多久才给抓到一次?”
“抓起来?”他气愤地叫起来,“抓到我?只有扒手才被抓到。手指匠永远不会被抓到。听着,只要我愿意,你嘴巴里的假牙我也能拿到,而且不让你抓到我!”
“我没有假牙。”我说。
“我知道你没有,”他回答道,“要不我早就取下来啦。”
我相信他,他那些细细长长的手指似乎什么都做得到。
往前开了一阵子,两人都没有说话。
“那警察要调查你一番,”我说,“你就一点也不担心?”
“没人会调查我。”他说。
“他们当然会。他在那个黑色本子上仔仔细细记录下你的名字和住址了。”
那人又给了我一个老鼠般狡猾的微笑。“哈,”他说,“你这么说,他是写了下来。可我敢打赌,他根本没有写下来,也没能记住。我从来就不知道一个警察能有还算不错的记忆。他们有几个甚至记不住自己的姓名。”
“这跟记忆力有什么关系?”我问,“他写在本子上了,是不是?”
“是的,老板,他是写下了。但麻烦的是,他丢掉了他的本子。还一丢丢了两本,一本写着我的名字,一本写着你的名字。”
他洋洋得意地用他右手修长的手指举着两个本子。那是从警察手里拿来的。“那还不是伸手就来的事情?”他骄傲地宣布道。
我突然一个转向差点撞在一辆送牛奶的卡车上。我太激动了。
“那个警察在我们身上什么也没有捞到。”他说。
“你真是天才!”我叫道。
“他没有捞到姓名、地址、车牌号码,什么也没有捞到。”他说。
“你真是才华横溢!”
“我看你最好尽快离开主干道,”他说,“然后我们燃起一把篝火,把两个本子烧掉。”
“你是一个非凡的家伙!”我惊叹道。
“谢谢你,老板。”他说,“有人赏识总是件快活的事情。”
选自《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明天出版社2014年4月版。
罗尔德·达尔,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剧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曾获爱伦·坡文学奖、白面包儿童图书奖、英国儿童图书奖、世界奇幻文学大会奖等。代表作有《女巫》《好心眼儿巨人》《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