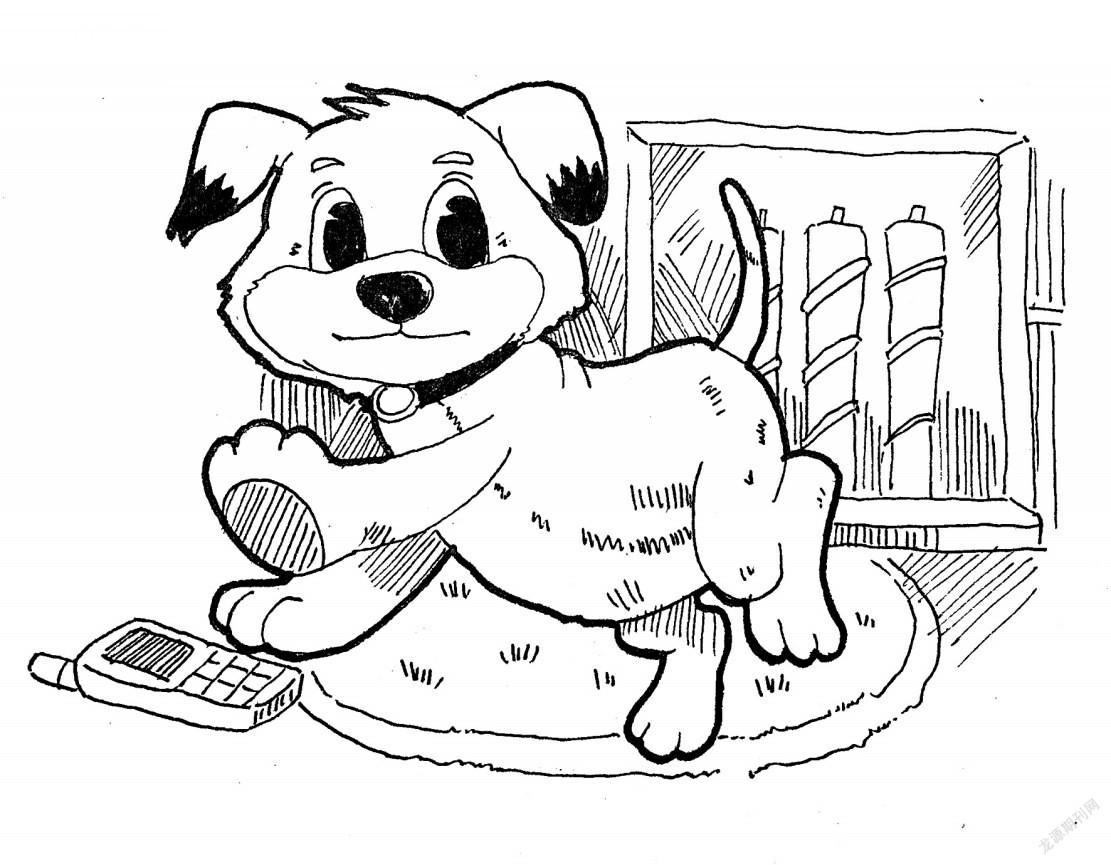 1
1银子是一条白狗。
银子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有的,为了便于叙述,我们一开始就把它叫银子吧。
土狗银子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同胞四个,三个纯白,就银子不很纯,两个耳尖是黑的,像顶着两个黑三角,蛮任性的样子。
出生不久的小奶狗大部分时间是趴着的,人称“趴泥小狗”。江南童谣这么念:“嘭嘭嘭。啥人?隔壁张小二。啥事?领只趴泥小狗。小狗眼睛没张开呢。嘭嘭嘭。啥人?隔壁张小二。啥事?领只趴泥小狗。小狗眼睛腿脚还软呢……”这是对话,要两个人来念,一个扮狗主人,另一个是讨小狗的邻居。这么一句对一句浪声浪调地念,好玩。念着,你就觉得人与人之间很融洽,人与狗之间的关系也挺温暖。
小奶狗银子被一个城里男孩领走了。男孩付了一元钱——这是老规矩,领狗不能空手领,得象征性地付出一点什么。男孩是骑自行车来的,把装小狗的草篓子挂在后座上。主人抓一把狗窝里的柴草垫在草篓子里,这是安慰小奶狗。当时狗妈妈不在家,回来时一定会很伤心,因为这是它最后一个孩子了。
银子本性文静,还见过三个兄姐被领走,知道抗议没有用,喊了几声妈后就安静下来,趴在草篓子里看风景。
公路沿着山脚盘缠,一边是山景,一边是水景,银子看新鲜看得很忙,觉得两只眼睛不够用。自行车后座的另一边还挂着一只篓子,里头是两只鸡。两只鸡见小狗这么镇定,也就安静了下来,镇定是能传染的。
暮色好像是从山坡上淌下来的,又像是从水里蒸腾起来的。暮色就像饥饿,看不见,却非常真实。男孩粗心,又急于赶路,没发觉狗篓子掉落到了路边的草地里。银子大声呼喊,可男孩的耳朵里塞着耳机,根本听不见。等银子从篓子里爬出来一看,嗨,男孩早没影了。
一辆大卡车驶过来。银子害怕这个轰隆隆的大家伙,赶紧钻进灌木丛躲起来。它不知道怎么办,就在灌木丛里一声一声地哭。一辆辆驶过的汽车一次次打断小家伙的哭泣,很粗暴。天光暗下来,亮起的车灯更使银子惊恐不安。那些刺目的、很快移动的光经过灌木的切割,闪烁不定,十分凶险。小家伙忽然很想念妈妈,很想念那个有夜饭花丛的院子。
灌木丛有刺,不友好,银子逃出来,重新钻进草丛里的竹篓子,把那堆软软的、带着妈妈气味的乱柴拢在胸前。这么做,银子胆壮了点,不怕轰轰驶过的汽车了,后来甚至敢冲着汽车怒吠了。原来发怒是可以驱除恐惧的。
罗木匠就在这时骑电瓶车到了竹篓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只敢于抗议汽车的小白狗。罗木匠停车等了一会儿,等不来寻狗的人,就把篓子挂到电瓶车上,把银子带回了家。
走进家门,罗木匠喊一声:“哈哈,我捡到银子了!”
就这样,小白狗有了一个吉利的名字。
当晚,银子吃饱之后就在罗家灶膛门口的柴堆上不顾一切地睡着了,经过一番折腾,小家伙累坏了,累得连想一想、哭一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天快亮了,公鸡一声声地啼。恍惚间,银子以为还在老家。灶间的门开着,银子滚过门槛就到了院子里。
罗木匠家的院子和老家的院子很相像。院子里居然也有一丛喷香的夜饭花。银子一眼就看到了倒在花叢边的竹篓子,赶快跑过去嗅嗅,心里踏实了一点。
罗木匠今天不出工,一转手就用板条做成了一只狗窝,还很贴心地把狗窝安置在靠近夜饭花丛旁边。银子明白这是它的窝了,把竹篓子里的柴草衔进去铺好,趴着试睡了一会儿——很好,很好。
罗木匠在院子里打家具。银子对推刨口吐出的刨花感到很惊讶。刨花一卷一卷地成了堆,银子就在刨花堆里拱来拱去玩。新鲜的木材是香的——很好,很好。
院子里有一群母鸡,它们对刨花早见怪不怪,发现这只小白狗欢天喜地玩刨花,挺不屑,在一旁嘀咕:咯咯,可笑,真可笑!
玩累了,银子想回窝眯一会儿,却发现新窝被一只黑母鸡占领了。银子刚探进头去,头皮上就挨了一下子,耳朵里被刺进一个尖锐的声音:去!
这只黑母鸡一贯搞特殊,从不肯在鸡埘下蛋,偏喜欢在这个角落下蛋,它可不管狗窝不狗窝的!
新来的银子底气不足,不敢和母鸡对抗,装作不在乎,跑去和刨花继续玩。
罗木匠看得分明,对银子说:“你啊,你啊,你怕鸡啊?”
银子知道主人在和它说话,咕哝道:“汪汪汪。”大概是“好男不和女斗”的意思。它是公狗,是纯爷们呢。
黑母鸡事毕,走出来大声报喜,嗓门大得像炸鞭炮。银子受不了,钻进刨花堆避难,唉,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等母鸡走出院子,银子把鸡蛋衔出来交给罗木匠,结果被教训了一番:蛋是不能动的,被狗叼过的蛋多恶心啊!
银子去夜饭花丛里拉了一堆屎,又错了,被罗木匠抓住颈皮拎到院子外芋头地那边荒草地上,示意那儿才是方便的地方。银子扒了一下土,唔唔几声,表示它已经明白了。狗的颈皮那儿有点“木”,天生就是让狗妈妈叼来叼去用的。
银子跟着罗木匠回院子,跟得很紧,鼻尖几乎触到主人的脚跟,生怕被主人丢下了。
下午,罗木匠做了一个微型的木门,安装在院门左侧下方,专供狗狗自由进出。说“自由进出”不准确,一到晚上,这门就被闩住了,只能出不能进。银子对这个“半导体门”研究了好久,终究没研究明白。
只几天,银子就和母鸡们搞好了关系。如果黑母鸡去狗窝下蛋,银子就在窝门口守卫。下蛋是件严肃的事,不可以打扰的噢。
主人故意没给银子另设水盆,银子只能去鸡埘那边的水盆里蹭水喝,鸡们没意见。鸡们去院子外觅食,银子就在一旁守护,它总得找点事干干呀。当然,它隔一会儿就会奔回院子去看看有什么情况,看看罗木匠在不在。两头兼管,银子就有点忙。
一个多月过去,银子成了半大狗,跑起路来刮风似的,管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小菜一碟。
罗家有三口人:罗木匠夫妇和独生女儿。罗木匠夫妇说这小白狗挺乖的,罗家女儿说小白狗挺萌的。
罗木匠的电瓶车后座上附有一个装工具箱的铁皮条篓子。每当看见主人清空篓子,银子便会兴奋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主人要带它去青螺镇玩了。篓子一清空,银子就迫不及待地跳将进去,坐舒服了,招呼主人:汪汪——行了,出发!
罗木匠去青螺镇东园茶馆喝茶。茶馆也是工匠行业接业务的处所,同行业的会自动坐到一起,像公园里的英语角那样,形成木匠角、瓦匠角什么的。喝过几泡茶,罗木匠会“叫”来一碗面条当早饭,总是双浇面——排骨加焖肉。罗木匠象征性地咬一口排骨,便抛给守在桌子下的银子吃。银子一口接住,衔着去茶馆外找个安静处享受,哎呀呀,这里的肉骨头真的很香噢!狗的嗅觉太发达,语言太简单,它们是完全没法用语言描述它们的味觉世界的,挺憋屈。享受完了,银子就去找同类自由自在地交往一番。它会自己回来,很准时,就像它戴着手表或带着手机。
这样的狗日子真是好过。
这天,罗家来了个客人,是罗木匠未来的女婿,粗壮,长一头乱蓬蓬的卷发。罗木匠让女婿把黑母鸡杀了。黑母鸡老了,生蛋稀了。卷发人就在院子里杀鸡。
黑母鸡的头被粗暴地别在翅膀下,露出来的脖子被扯掉毛,然后就是亮闪闪的刀和鲜红鲜红的血。黑母鸡徒然地挣扎,刀割后屏息了好一会儿才放了血……
银子惊惧地目睹这一幕,先是向罗木匠求救,不见效,知道奈何不得了,便躲到香椿树后去,露出半边脸,露出的那一只眼睛泪汪汪的,充满了恐惧。
这天,罗家的饭桌很丰盛,有好多肉骨头什么的供应银子,可银子没胃口。银子躲在窝里,盼望卷发的家伙快快离去。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卷发人离去时竟把银子也带上了。他在镇上开了个“毛头服装店”,让银子去帮助看店,罗木匠答应了。
银子的苦日子开始了。
小服装店只一开间门面,总面积不足十五平方米,里半间堆满了货包杂物,前半间的墙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廉价服装,卷发坐在衣裳堆里做生意,身旁站着一男一女两个穿得花里胡哨的塑料模特儿。这两个整天不动、一声不吭的模特儿让银子疑惑了好多天,心里很疑惑。
白天,银子被囚在门口的铁丝笼子里,徹底失去了自由,整天在嘈杂的声响中闻着汹涌的人味车味怪味,看着人来人往车流滚滚。
卷发人是个粗糙生硬的家伙,从不对银子说一句温软的话,从不让银子出来活动一分钟,一天中除了给两次剩饭外,连个水盆都没给银子备一个,而他自己却整天捧着个大茶瓶子咕咚咕咚喝茶。
真渴啊,真渴啊!银子冲着大茶瓶怯怯地吠叫,恳求给它一点水喝。卷发人不耐烦了,猛踢铁笼,骂:“住嘴!再不住嘴打死你!少喝少撒,你懂不懂!”
银子滚倒在笼子里,很委屈,轻轻地哭,眼睛涩涩地流不出泪来。真渴啊!真渴啊……
一天到晚,笼子前走过许多许多人,唯有一个男孩走过时会关注一下银子。男孩十多岁,每天早晚背个书包走过这里时,他会蹲下来和银子说几句话。书包的侧面有个小网兜,里头插一个玻璃水瓶,里头的水清清的,晃来晃去诱人。
“嗨,小白,小白,你几岁啦,你的耳朵尖怎么是黑的啊,你想假扮熊猫对不对……”
银子知道这是在和它说话,可它太渴了,没情绪领会这些话的意思,眼睛死死地盯着水瓶子,唔唔地轻哼——求你了,给一口水吧,给一口水喝吧……
男孩子不懂狗语,逗一会儿狗就走了,功课多,他不能耽搁太久。
一天早上,男孩吮着一支雪糕走过来,见小狗贪婪地盯着雪糕,就咬一截雪糕吐进笼子里。银子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吞吃,因为吃得太急而呛得咳个不停。
卷发人很不满,恶声恶气地把小男孩轰走。银子很气愤,冲着卷发人汪汪抗议。坏脾气的卷发人大发雷霆,连连猛踢笼子,银子在翻滚的笼子里跌来滚去的,被摔得浑身疼痛,眼冒金星。
到了晌午,卷发人左手夹着一支香烟,右手不断往嘴里扔牛肉干粒子。牛肉的香味逗得饥肠辘辘的银子好难受啊!忽然,卷发人开恩了,给银子扔了一粒牛肉,银子没接住,牛肉粒落在地上。银子看看卷发人并没发火,小心地捡吃了。卷发人又抛几粒牛肉,银子每次都用嘴接住了。银子正为挽回了一点面子得意时,就中了卷发人的圈套——它用嘴接住了一个燃得正红的烟头!银子的惨叫逗得卷发人很开心:“哈哈,狗东西,这烟头好吃吧?”
嘴里辣辣地疼,银子往后退,想摆脱这个疼,可它无处可退,只能张开嘴唔唔地哼哼。
白天怎么会这样漫长啊!
天光一点点暗淡,终于,白天过去了,可银子的苦还没熬完。
卷发人把银子从笼子里放出来,随手用细链子扣住银子的项圈,胡乱给一点吃的,就出门把卷帘门哗啦一声拉下来,骑摩托车噗噗噗走了。留银子在店里值夜,是他把银子从岳父那儿弄到店里来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他只关心钱和他自己。
小小的店堂没有窗户,卷帘门拉下后屋子里立刻一团漆黑。都说狗能在夜间视物,但还得有一点点光才行呀。没有光源,狗照样两眼一抹黑。
等待银子的是深重无边的黑暗和寂静。在这种密闭的黑暗中,无助的小白狗只能哀哀地哭泣。哭累了,银子慢慢进入半睡半醒的迷糊状态。银子会梦到它的妈妈和兄妹,梦到罗木匠那个堆满香喷喷刨花的小院……
这种千篇一律的苦日子延续了将近两个月,银子从一条胖嘟嘟的小奶狗变成了一条瘦骨伶仃的半大狗。银子憔悴,原本晶亮活泼的眼睛变得呆呆的,原本瓷质的白毛干枯得就像冬天里的芦絮。
卷发人赌博输了钱,要把小店卖掉。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转行大用卖,全场服装一折起”。他把“甩”字写成“用”了。
卷发人已经先把两个模特和铁丝笼子卖掉了,现在只能把银子用细链子拴在店门口。银子身旁竖了一块硬纸板,上面写:“出售纯种白狗,贱卖两百元。”
风一吹,硬纸板倒在地上。卷发人过来踢了银子一脚,骂:“狗东西,看住这块牌子!”经历几番折腾,银子明白了卷发人的意思,一次次扶起牌子靠在墙上。它不知道这是一块出卖它的告示。
一个肩膀上有文身的汉子过来,说:“这狗什么种啊?”
卷发人文不对题,说:“是纯种哎,你看看,一身白毛,多纯啊。”
花肩膀撇撇嘴:“拉倒吧,你干脆说是白博美得了,没看见狗耳朵上有黑毛啊!”
“不是只一点黑么?”
“有一根杂毛就是杂种,懂不懂啊,还纯种呢,还两百块呢。”
花肩膀一走,卷发人把火撒在银子身上,一把扼住银子脖子,用一把生锈的剪刀把银子的两个耳尖剪了。
银子惨叫,本能地摆出攻击的姿态,可它不知道怎么攻击人,最后逃到一个小椅子后面躲起来。它想舔舔流血的伤口,可它怎能舔得到自己的耳朵呢?只好把脑袋弯过去,弯过去,将耳尖子贴在自己的肚皮上……
第二天,卷发人继续让银子看守硬纸板,固定硬纸板只是举手之劳,但他就是要折腾白狗,发泄自己赌场失败的怨气。为了冒充纯种狗,他为银子拭掉了耳尖上的血痕,还破天荒地用洗洁精给银子冲了个冷水澡。
银子一次次惶恐地扶起硬纸板的情景,让一对逛市场的老夫妇看得很心疼——哎呀呀,这眼泪汪汪的小白狗多像旧社会头插草标自卖自身的穷孩子啊!
银子扶起硬纸板时把硬纸板弄颠倒了,它不识字,不能怪它的,可卷发人是不问情由的,咒骂着又要踢银子。
老先生忍无可忍了,大声说:“住手!白狗我买了!”
老先生姓丁,就住在青螺镇老街上。
“毛头服装店”在镇西新街上,而老街在镇中心,是个蛮有名气的旅游景点。老街有三里多长,是条半面街,一边是店铺,另一边是一长溜的石驳岸。
丁先生牵着银子刚进老街,银子就认出了这是它熟悉的地方,挣扎着要下水栈喝水,急迫地拉扯让腿脚不便的老先生脱开了手中的链子。银子蹿过石级,前爪踩在水里,急吼吼地大口喝水。可怜的银子已经很久没能这么畅快地喝水了。
丁家夫妇把银子带到家里,好好地款待了一顿——红烧肉汁拌米饭,几块带肉的骨头,外加吃剩的半碗茭白炒蛋。银子大口吞食,风卷残云般把一大盆食物吃个精光。吃完,舔凈盆子,银子才想起来表示它的感激。它仰视两位老人,努力摇着尾巴,把整个屁股都带动了。
丁家夫妇款待了银子三天,到了第四天,等银子再次享用过美食后,丁先生蹲下身子解开了狗项圈,说:“好了,二百五,现在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走吧,走吧。”丁先生买狗付过二百元,临走时卷发人又加要了五十元,说是项圈和链子的钱,幽默的丁先生就把银子叫作“二百五”。
银子眨眨眼,不懂丁先生的话,回头向着丁太太。
丁太太抚摩银子的背,说:“小白狗,是这样的,我们老了,过些日子这个店就关门了,我们要去城里和儿孙一起过了。我们不便带你走的,你呢,就回老主人那儿去。我知道你有老家的,对不对呢?”
银子听不懂人话,但它能从人的语气神态约略猜出人的意思。它明白,这里的人不要它了,这使它不解。在服装店那么多日子,银子整天目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居然大概弄明白了人类的“交易”。它看见丁先生交过钱,然后卷发人把狗链子交给丁先生,知道它就得跟新主人走了。可是,今天没有“交易”呀,新主人怎么就让自己离开呢?
没了项圈的银子愣着,心里慌慌的,不知怎么办了。
丁家开的是花烛店,叫“老丁家花烛店”。这时,有几个游客进店来了。有一个年轻人也是个卷头发,弯下身子来想摸一摸银子。银子本能地闪开,一跳就出了花烛店。它害怕卷头发的人,非常害怕。
丁先生见银子出了店,挥挥手:“好的,好的,走吧走吧。”
银子见丁先生只顾做生意,不理它了,只能离开,走了一段路,回头时,看见老先生站在店门口看着它。银子想往回走,可丁先生又挥手了——让它走。走一段路,银子再回头时,店门口没有了老先生。银子有些失落,想一想,抬起一条后腿,在墙脚撒了几滴尿,再想一想,想不出什么了,只能茫无目的地小跑起来。
说“茫无目的”不对,银子是有目的的,他一径到了东园茶馆。可东园茶馆在下午是关门的。银子这才真的茫无目的了。他想回到罗木匠家去,可它每次跟老主人来镇子都是乘电瓶车来的,不认得回去的路。
3
银子沿着青螺河走,不久就出了镇子。一抬头,银子就看见了坐在远处的一座青翠的山,心头一亮,眼睛都放出光来了——呀,家就在那儿啊!
银子狂奔在山间公路上了。浑身发热,它吐出舌头散热,舌头上不断滴着水。狗不流汗,用舌头散热。山间公路窄,路边的树茂密,就像一条深深的绿色长廊。银子跑啊,跑啊!
银子很幸运,它选择的这条路还真能去罗木匠的家。银子很不幸,山路上噗噗地来了一辆摩托车——骑车的正是卷发人!这家伙也要去罗木匠家。
卷发人一轰油门,把摩托拦在银子面前,跳下车,半蹲着张开双手,亲热地说:“嗨,银子,来,来,过来啊,我是你主人啊……”
银子最不想见到的就是这个卷发人。谁说狗愚忠,会无条件地追随主人?不对,狗肯追随的主人那得像一个主人。主人可以穷,可以骂它打它,甚至可以没有理由地骂和打,但不可以无理由地折磨它,不可以深深地、反复地践踏它的自尊。日复一日无休止的折磨,会让狗鄙视你,怨恨你,反抗你。
不管卷发人怎样笑容可掬,言语亲热,银子还是感受到此人的心怀叵测。只要不被过度宠物化,狗大多拥有一种微妙的感知人内心的直觉。都说看家狗“狗眼看人低”,会排斥衣饰不整的人,其实狗排斥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感受到了这个人内心的庞杂和不安。
银子站住,冲着卷发人决绝地怒吠:“汪汪,汪汪汪……”意思是:走开,别靠近我!卷发人靠近时,银子毫不犹豫地闪进路边的树林,飞奔而去,尾巴一划就不见了踪影。
白得两百元的好事没成功,卷发人懊丧,却并没有灰心,他断定银子会自动找回他老丈人家的,到时候,银子还是会投到他手里。
经过这番折腾,银子不敢走公路了,就在山坡上沿着公路伸展的方向走。不多久,它遥遥望见了凸出在山顶的白色的消防瞭望塔——好了!这就对了呢!它知道这个白色的建筑就在罗木匠家附近。
银子觉得有点渴,就下到山谷去找水喝。还没走到谷底,一声奶声奶气的狗吠就把银子带进了危险之中。
在谷底的一块巨石上,一条小黑狗正冲着银子大声呼救。银子四顾,不见其他活物,这么小一条狗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山谷有点蹊跷。忽然,银子发现对面山坡上的一个灌木丛在晃动——莫非那里有小狗的妈妈?
从灌木丛里钻出来的不是狗,是一头身材硕大的野猪!在罗木匠家的日子,银子看见过乡人们合力逮住过一头野猪,认得这种凶猛的野物。
野猪是由小黑狗的吠声引来的,不吭声,它悄悄转移到黑狗的侧后,确认处在上风处后便向谷底的黑狗直扑过来。不好了!
银子冲着小黑狗用狗语发出紧急警报:汪,快跑!快跑!
小黑狗发现了敌情,赶紧向银子这边跑。可是,野猪的速度很快,小黑狗怎么能逃得掉啊?银子紧张四顾,发现离自己和黑狗之间有几块平躺的巨石,巨石下面有黑洞洞的缝隙!
银子一边向巨石跑,一边呼喊小黑狗朝它这边跑。
野猪在冲击途中滑了一跤。就靠野猪的这一个延误,小黑狗才得以钻进了它到达的第一个缝隙。来不及纠正小黑狗了,银子在野猪赶到之前,钻进了另一个石隙。
野猪赶到,发现它的尖吻和爪子都没法够到石板下的狗,气得嚎叫起来,两条狗吓得发抖。
坏脾气的野猪冷静下来后,发现它还有成功的可能——其中一块石板的下面是山泥,它完全可以扒开山泥扩大洞口,够到黑狗!野猪欢叫一声,立刻撅起大屁股开挖起来。猪的掘土本领好生了得,它很快就能得到它的猎物!
银子是安全的,这边的石板下也是石板,野猪是没法开挖的。
小黑狗发现身处险境,惊恐万状地吠叫求救:“汪汪呜,汪汪呜……”凄惨的喊叫让银子头皮发麻,脑门刺痛。哎呀,怎么办呢?
两块石板几乎是并排的,专心挖土的野猪的大屁股就暴露在这边的石隙外。银子鼓起勇气冲出去狠咬一口猪后腿,又迅速退回。野猪狂叫一声回头向这头攻击,可它发现它在这边没有机会,气得嗷嗷叫。叫一阵,它又回头去开挖。
为了及时退回洞中,银子的攻击很潦草,未能咬破猪腿。银子的第二波攻击就厉害了——攻击目标是野猪后胯之间鼓起的阴囊。可惜,这大阴囊绷得太紧,银子还只是潦草地冲撞了一下,但这已经把野猪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个要命的部位啊!
拼命三郎再次狂怒,跳上银子这边的石板四处寻找开挖点。
这是个机会!银子冲着对面的小黑狗喊:汪汪!快过来!快过来!
小黑狗的腿吓得软了,挣扎了一会儿才颤巍巍地站起来。银子嗖一声冲过去,咬住小黑狗脖子硬是把小黑狗扯了过来。
谁说银子软弱可欺?关键时刻,银子一点也不含糊!
4
出猎失败的野猪暴跳如雷地闹腾了一番,最后还是无奈离开。
银子离开时,小黑狗跟上了它。银子冲着小家伙咆哮——去,别跟着我!
小家伙噙着泪,愁眉苦脸地望着银子,从喉咙深处发出轻轻的呜咽声——大哥,收留我吧!
傍晚时分,银子灰头土脸地回到了罗家村。死里逃生的小黑狗一步不离地紧跟着,小家伙走投无路,只能死跟这个大师兄了。
走到院子外头的芋头地,银子停下来拉了一泡屎。小黑狗举起后腿想撒几滴尿,却怎么挤也没挤出一滴。它还没有从惊恐中完全缓过来。
银子从芋头地出来时,发现院子门口停着一辆摩托车——呀,这不是卷发人的车么!银子心头一紧,慢慢移动脚步,探头往院子里看——卷发人果然在院子里,正光着上身在井台那儿哗哗地弄水呢!
银子重新回到芋头地里,趴下,两眼睁睁地等着卷发人离开。小黑狗不知情由,乖乖地趴在大哥身边。
院子里传出来卷发人的声音和母鸡们的唠叨,就是没有罗木匠的声音。两只饥肠辘辘的狗焦躁难耐,可它们无计可施,只能这样趴着死等。
漫长的等待。
卷发人终于走出院门来了。可他并没骑车离开,反而把摩托车推进院子去了,停妥車后又回身关上了院子门。他是罗家的上门新女婿,这里就是他的宿处。
现在,小黑狗是无家可归,大白狗是有家难回。
夜深时,村里的黄毛母狗嗅着气味寻到芋头地里,把两条流浪狗领去老孟家的豆腐坊偷吃了一肚子豆腐渣。豆腐渣是新鲜的,还不算太难吃。
第二天,银子带着黑狗在村外转悠了大半天,直到晌午时分才见卷发人出来锁上门走了,没骑摩托车。银子让黑狗在芋头田里等着,自个儿从它的专用小门进到院子。它的突然回家引起母鸡们的激动——咯咯呀,小鲜肉回来啦!呱呱呀,小鲜肉怎么成大白狗啦……这些善于遗忘的母鸡竟然还记得银子,算是奇迹了。
银子没情绪和母鸡们叙旧,在院子里、屋子里到处寻找老主人罗木匠。它毫无计划地奔来奔去,舌头长长地垂在嘴角,焦躁、仓皇的样子真让母鸡们受不了。咯咯呜,这白狗疯了还是怎么啦?
院子里没有老主人的气味了!老主人留在屋子里的气味也已很淡很淡……银子沮丧万分,双耳耷拉,尾巴死命地嵌在屁股沟里。呜呜,主人啊,你去哪儿啦?
罗木匠在县城承包了工程,遥遥不知归期。
这时,院子门外有了动静——是开锁的声音。
银子的鼻子灵,一嗅,就知道门外是卷发人,它赶忙躲进夜饭花丛,等到卷发人进了屋,才往院子外跑。卷发人透过玻璃窗看到了往外跑的银子,从窗子里跳出,呼唤着追出院子来:“银子银子,别跑别跑,回来回来,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银子哪肯理他,冲进芋头田,领着小黑狗往村外跑。
5
青螺镇老丁家花烛店虽然小,却是有名的百年老店,自产自销的花烛可不是一般的蜡烛,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工艺品,专用于婚礼庆典场合。“洞房花烛夜”中的“花烛”正是这种造形独特、制作精美的蜡烛。随着婚庆礼仪的西化,青螺镇上仅剩的这家花烛店也将关门歇业。
这天早上,丁家老夫妇正在店堂闲坐,忽听得柜台外有唔唔的狗吠。丁先生探头一看:“呀,这不是白狗二百五么?“
丁太太说:“啊,啊,小白啊,没找到家是不是啊?可怜可怜……”
银子听不懂话,却分明感受到了两位老者的善意,抬起头,轻声呜呜,表示它的感动。
两位老人走出柜台,发现白狗身旁还蹲着一只小不溜丢的黑狗。
丁太太说:“小白,这是谁啊?”
小黑狗怕人,躲到银子身后,怯怯地细声细气地轻吠,卖力地摇着小尾巴,小眼睛里满是哀切和不安,活脱脱像一个和亲人失散的小孩子。
丁先生说:“小家伙在发抖呢。”
丁太太说:“看它们肚皮瘪得没形了,一定是饿坏了。来吧,跟我去后院吃点东西吧。来啊,来啊……”
丁先生看妻子领着两条狗去了后院,感叹道:“这白狗还认定这里是它家了呢。可惜,我们要关店离开了……”丁先生有点伤感。
两条狗在后院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白狗不见了,只留下了小黑狗。银子是通过一口倒扣在院墙旁的大缸,越过院墙悄悄离去的。
银子认定它的家在罗家村,主人是罗木匠。
银子留下小黑狗是为小家伙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家,还可能有报答老夫妻的想法。这是有可能的,因为银子是懂得一点人类“交易”的。这里的人花钱买了它,自己跑了,不就亏欠人家了吗?
接下来的日子,白狗银子在青螺镇和罗家村之间来回奔波。进了罗家村,它并不会贸然走进罗木匠家,就在罗家周围活动,苦苦等着老主人的回来。在青螺镇,银子只去老街,不去服装市场,尤其忌讳那些轰隆作响的卷帘门。银子去老街先会去东园茶馆转一圈,再去花烛店看一看,然后很快离开。银子到花烛店时,老人会给它东西吃,银子很客气地吃一点点就不吃了,表示它是能养活自己的,表示它并不是流浪狗。它来这里只是想用脸颊倚一倚老人的膝盖,想让老人捋一捋背,摸一摸头。小黑狗欢迎银子来,频频和银子碰鼻子,可它不再跟银子走,它在这里过得很好。
就这样,银子成了一条流浪狗。
这句话你别对银子说,它不承认这个,它会说:我不是流浪狗,我的家在罗家村,我的主人是罗木匠。
过些日子,老丁家花烛店关门了。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银子明白老夫妻已经离开了,但银子去青螺镇时必定还会去东园茶馆找一找主人,还会去老丁家花烛店门口坐一会儿。银子现在已是一条成年狗了,身上挺干净,毛有瓷质的光。坐在花烛店门口看街景的银子神情庄重,一脸沧桑,若有所思。不知它在想些什么。有主人家的大狗总是挺从容的,从容地走路、伫立,一般不苟言笑。
罗木匠还是没有回家。
半年后,花烛工艺被省里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丁先生被镇里请回老家重开小店,并让他带徒传授手艺。
银子发现花烛店的门开了,还见到了丁先生,只是丁太太和黑狗没见到。
后来,有一条“生意狗”在青螺镇旅游点出了名,还在旅游网上成了网红。
丁家花烛店没雇营业员,银子文文静静地坐在店堂玻璃柜台后的椅子上,两只前爪学丁先生那样交叠,优雅地搁在柜台上,爪子旁还煞有介事地放着一只手机。手机是弃用的货,摆摆样子的。喜欢搞笑的丁老先生还在银子身旁竖了一块蛮大的告示牌,上面這样写:
我叫二百五,店主人在后屋作坊忙碌,由我守店。开架的花烛每对十元,往玻璃盒内付款后自己取货即可。如想买玻璃柜内大型花烛,请击掌三下,我会去后屋叫主人出来接待您。谢谢光临!
这个被称为“二百五”的家伙就是银子。如果有客人忘了付花烛钱,它会轻声哼几声提醒一下。如果客人击掌,它就会奔进里间去让丁先生出来接待顾客。
有一天,有个客人击掌三声,银子却没有反应,庄严地坐着,连看都没看那人一眼。这人就是卷发人。银子每天早上都去一次东园茶馆看看主人有没有在,每天傍晚都去一次罗家村,看看主人有没有在。
小巷子里有小孩子唱童谣:“嘭嘭嘭。啥人?隔壁张小二。啥事?领只趴泥小狗。小狗眼睛没张开呢。嘭嘭嘭。啥人?隔壁张小二。啥事?领只趴泥小狗。小狗脚头还呒么力呢……”
“嘭嘭嘭”是敲门的声音。
罗木匠还在县城里做木门。
选自《少年文艺》2019年第4期
金曾豪,儿童文学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长篇小说《青春口哨》《魔树》,中短篇小说集《小巷木屐声》《九命树》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