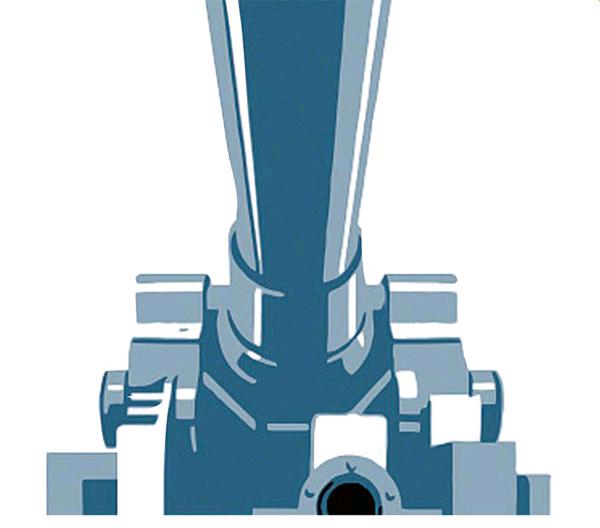
百余年来,化学武器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大于其军事意义。如今,国际社会就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达成一致意见,其中一个原因是,化学武器的实战价值不断降低。
自从化学武器首次被应用于战争以来,世人已在它的阴影下度过了一个多世纪。这期间,无辜平民因化学武器受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2017年4月初,在敘利亚伊德利布省的汗舍孔镇,一次导致数十人死亡的沙林毒气袭击令世界震惊。消息传出后,英国《每日镜报》以加粗的通栏标题“叙利亚儿童再遭毒害”,描绘出化学武器给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带来的恐慌。
细心人发现,这则新闻的字体、遣词造句和排版,与该报102年前报道史上首次化学战时的情况相似,当时,《每日镜报》使用的标题是“魔鬼,你的名字是德意志”。
首次参战引发巨大恐慌
1915年4月22日下午,埋伏在比利时城市伊普尔附近战壕里的法国士兵,发现一股黄绿色的烟雾正向自己飘来。他们以为这是掩护德国步兵前进的烟雾,于是开始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事实上,那是德军从6000个密闭容器中释放的氯气。
随着毒气像幽灵般卷进战壕,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立竿见影——最先接触到烟雾的法国士兵发疯似的用手猛抓喉咙,纷纷倒毙;更多的士兵惊惧万分、落荒而逃。很快,头戴防毒面具的德军冲了上来,没费太大力气,就在这条久攻不下的防线上撕开了缺口。
这是通过工业手段制造的有毒气体首次被有计划地应用于大规模战争,其带来的精神冲击力大于实际杀伤力。有当事人心有余悸地回忆当时的情况:“头部剧痛,肺里好像被扎进烧红的针,仿佛被人掐住喉咙,无法呼吸……”化学武器的“首秀”导致5000多人丧命,更多的受害者在此后几十年间被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后遗症折磨,痛苦不堪。
美国Politico网站在回顾化学武器的历史时指出,虽然化学武器的原理和制造技术如今已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神秘,但它的每一次登场都会造成舆论地震,进而引发意想不到的政治效应。此次叙利亚毒气事件发生后,美国特朗普政府迅速改变了对叙利亚当局的态度,对疑似储存有沙林毒气的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了军事打击。
在美媒看来,特朗普立场的“反转”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对化学武器为何如此敏感?在叙利亚内战中丧生的数十万人,大多是被常规武器夺去生命的。世人为何对化学武器如瘟疫般严防,而不把机枪和路边炸弹等导致更多人死亡的武器一并禁止?答案或许有些出人意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化学武器的军事价值在不断降低。
《日内瓦公约》有漏洞
几乎在化学武器被用于战争后的第一时间,各国军方对它的反制就已开始。1915年,同盟国为前沿部队普遍配发了防毒面具。随着交战双方争相引入毒性更强的化学物质,效果更好的反制手段也在不断跟进。另一方面,化学武器的破坏效果很难控制,在阵地前沿释放的毒气被风吹回己方而引起伤亡的案例屡见不鲜。
美国军事史学家马克·佩里援引统计数据指出,“一战”期间,共有9.1万名军人死于化学武器攻击,不到死亡总数的一成。机枪、飞机、坦克被证明比毒气更高效。然而,化学武器引发了在民间蔓延数十年的恐慌,为战争添加了更多的野蛮色彩。
曾在英国军队服役的诗人威尔福莱德·欧文的诗作《为国捐躯》,反映了化学武器给公众带来的不安:“如果你能听到鲜血从污染的肺叶中喷出,这个肺就像患了癌一样恐怖……”绘画大师约翰·辛格尔·萨金特的作品《化学战》,展现了一队被毒气致盲的士兵蹒跚前行的景象,令人联想到宗教仪式。战争结束多年后,各国文学家笔下仍经常出现遭受过毒气袭击的老兵形象:他们坐在地铁的伤残军人专座上,脸上布满被化学品烧伤而留下的疤痕。
另一方面,参加过实战的指挥官们普遍承认,化学武器的威力不如想象中可怕。即便如此,当时也没有正规的国际公约禁止各方使用毒气。德军在伊普尔首次发动化学战,令时任英国西部战线指挥官的约翰·弗伦奇爵士大为恼火,他称这种作战方式“是对为人所熟知的文明的战争手段的蔑视”。之后,英国人的回应令外界大跌眼镜。弗伦奇宣布:“鉴于敌人在进攻我方阵地时一再使用窒息性气体,我军将‘被迫采取类似的战法。”
直到“一战”结束,各大国才就杜绝毒气攻击这种“不够光明正大”的作战形式达成基本共识。1925年,《日内瓦公约》明文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的战争手段”。耐人寻味的是,该协议最早的签字国都是那些使用过毒气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美国直到1975年才对该公约开绿灯。如今看来,90年前的《日内瓦公约》存在一个刻意为之的漏洞——并未禁止生产和贮存有毒物质和化学武器。公约的主要签字国此后仍在研发威力更强的毒气。
“希特勒不用毒气”之谜
近年被披露的档案资料显示,国际公约的存在与舆论的一致谴责,不足以打消各国使用化学武器的念头。决定毒气是否被用于实战的主要因素是交战各方的技术水平。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专著《世界大战》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英国曾在伊拉克使用毒气镇压库尔德人起义。学术界对此存在争议,但时任英国战争部部长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番言论提供了旁证。“我搞不懂反对者的神经质,”他曾在非公开场合表示,“我个人非常赞成使用毒气收拾那些野蛮人。”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持相似立场,1935年末,他批准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军队使用芥子气,导致近10万人伤亡。
“二战”时期,用化学武器“以防万一”是交战各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1944年,已是当时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敦促将军们“认真考虑这个(使用毒气)问题”,他在备忘录中提到:“上次大战时人人都用它,也没听说道德家有多少抱怨……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考虑道德不道德,实在荒唐。”丘吉尔甚至认为,希特勒不敢对盟军使用毒气的唯一原因是害怕报复。
值得关注的是,就最近的叙利亚毒气袭击事件,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搬出了纳粹德国的先例,称“即便是希特勒,也没有恶劣到使用化学武器的地步”。很快,他就因“出言不当”而被迫道歉。《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关于纳粹德国为何不愿把毒气用在战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希特勒在“一战”时被毒气伤害过,“不想在别人身上看到同样的恐怖”;但更多人相信,真正的原因在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很清楚化学武器的局限性。
英国《每日邮报》指出,没有哪支军队愿意禁用威力强大的武器,同意禁用的往往是不好用的武器,化学武器属于后者。“它反复无常,可能对使用者反戈一击,”美国陆军退役上校保罗·休斯告诉该报,“之所以容易通过谈判加以禁止……是因为它毕竟不像常规火炮那样高效。”
好用的武器很难被禁
同其他一些有争议的武器进行对比,人们就可以看出国际社会一致禁止化学武器背后的玄机。Politico网站提到的一个例子是地雷,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强烈支持将使用地雷列为非法武器,但這方面的努力屡屡在五角大楼和国会山碰壁。反对禁止地雷的军方重量级人士主张:这种武器在朝鲜半岛等特定区域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若就此退让,会创下“危险的先例”,即“军方可以被民间组织施压,从而削弱自身的防御能力”。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集束炸弹。这种武器在20世纪末的巴尔干地区被大规模使用,并被曝因为哑弹遗落而持续威胁平民安全之后,“挺禁派”和“反禁派”就在各种场合争得不可开交。军史专家马克·佩里曾在瑞士旁听一场军控会议,看到台上有一位挪威外交官情绪激昂地呼吁与会人士通过禁止集束炸弹的条约。台下的一名英国军官面露鄙夷之色。“为什么挪威人赞成禁止集束炸弹?”此君自问自答,“因为他们没有。”
真正好用的武器很难被禁用。正如英国《独立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到的,一方面,162个国家签字同意禁止使用地雷,108个国家签署了旨在禁止使用集束炸弹的公约;另一方面,最可能使用这两种武器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和印度,至今不同意在相关协议上签字。
相比之下,各国政府对禁用化学武器的态度高度一致,最大的受益者是平民百姓。在1993年发起的《化学武器公约》中,毒气被排除在“战争武器”范畴之外。包括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也多次表态接受这一公约的核心内容。
因此,按照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的说法,当叙利亚再度传来有关化学武器的新闻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起初十分怀疑,这是否真是叙利亚当局所为?后者为什么走如此冒险的一步,甚至不惜挑战国际共识?
埃及中东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哈桑·哈桑分析认为,无论袭击是哪一方实施的,始作俑者的目的都不只是制造恐慌,他们试图借助化学武器的恐怖向民众释放信号:国际社会并不在乎汗舍孔镇发生了什么,谁都不要奢望外界能提供多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