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有木兮木有枝
◎莘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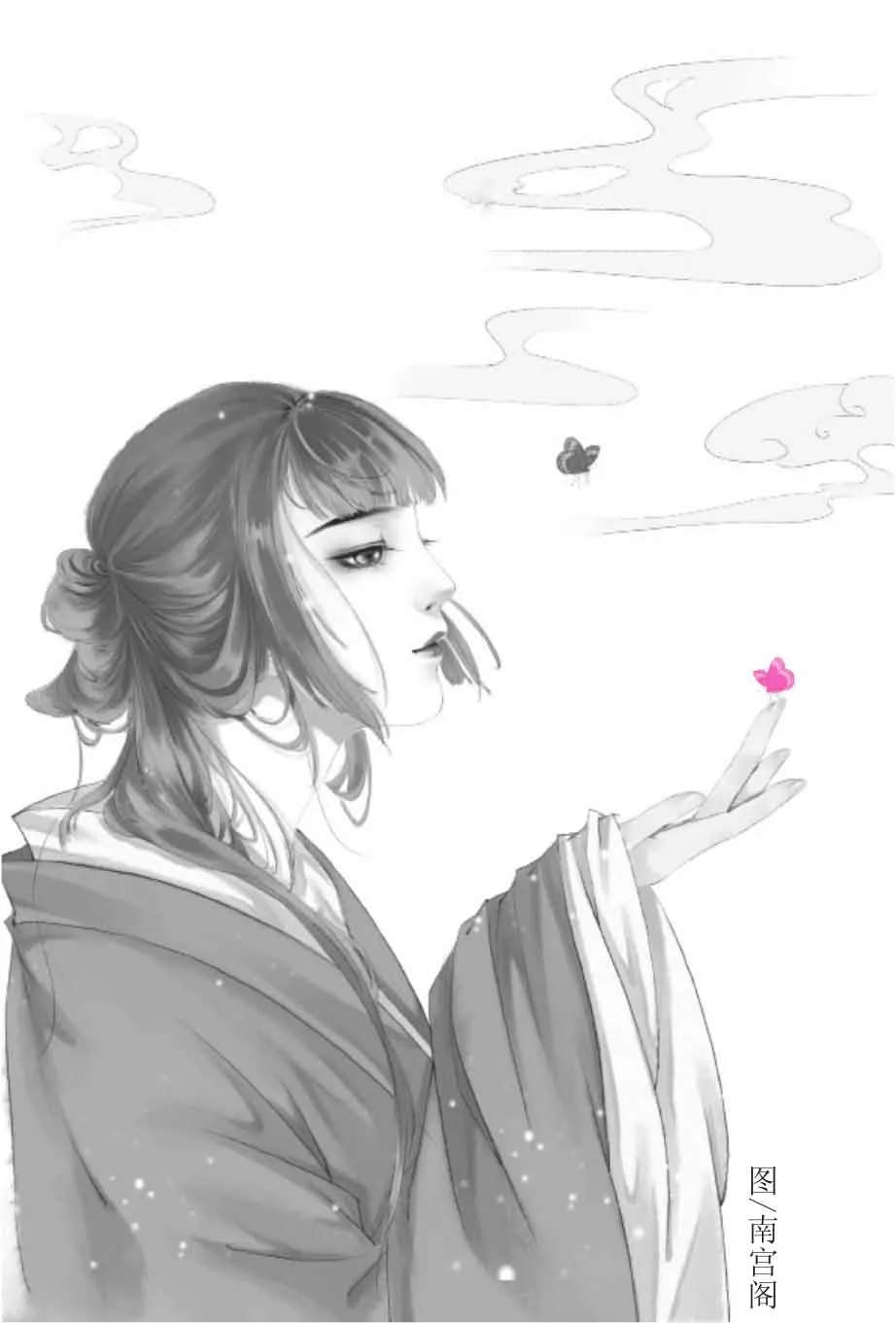
图/南宫阁
夜色醉人,星子闪烁像楚楚动人的泪眼。
楚服身着玄色巫袍以怪异的姿势默立于漆金榆木桌前,宽大袖口处露出一截雪白皓腕,腕上系着一条细细红线,白皙交织着鲜红,衬得她华丽又邪魅。缭绕的烟雾模糊了楚服的面容,让人看不清她眼底的情绪,隐约只有一张苍白清秀的脸和诡异的神色。
她身侧跪坐着一名女子,绛色宫袍以华丽金线勾边,裙摆绣着一只凤,长长的凤尾隐在衣衫褶皱间,发髻繁复,沉重的凤冠未曾摘下,姝丽的容颜满是憔悴,她跪坐半晌后终于向楚服问道:“还需几次祭礼?”
“禀娘娘,还需两次。”楚服恢复了正常站姿,弯身行礼,“娘娘莫急躁,这厌胜之术最忌讳的就是如此。”
绛衣女子对着楚服挥了挥手,示意她退下,楚服弯着腰慢慢退至大殿门口,正准备离开,女子突然叫住她:“楚服,你说阿彻真的会回心转意吗?我听说,那卫子夫又有孕……”
“娘娘莫担忧,厌胜之术便是为挽回陛下的心而施,只要此术一成,陛下心上便只有您一人。”楚服低头答道。
女子好似早知她会如此说,面上期待与惶恐交织,然后又闭上眼,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睁开双眸,“楚服,你可有心上人?”
楚服的脸瞬间苍白无色,华丽衣衫也掩不住疲态,她顿了顿身子,道:“奴婢没那个福气。”
女子却好似听不到楚服的回答,喃喃道:“阿彻是世上最好的男子,他儿时便许诺我,要造金屋子给我住……”女子忽然笑出声,眉目间满是回忆的柔情。
楚服没有应声,静静听着女子的诉说。
楚服回屋时夜已深了,换下华服,她把蜡烛拨亮了些,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枕边那只木盒,拿出一只小小的巫偶,巫偶由是梧桐木雕成,微凉如玉。它眉峰英挺,一双凤眼细长,薄唇有些细微的弧度,笑眯眯的模样,颈间一条纤细的红绳,相似的面容让楚服想起了杜言之。
杜言之是椒房殿的侍卫,眉目俊朗,身量挺拔,每天都笑意洋洋的。这晦暗的深宫也因这几分笑意暖了起来。
楚服抱着一堆衣服在回廊里小跑着,在转弯处撞上一堵肉墙。“哎呀!”那人一声惊叫,被撞倒在地。楚服连连道歉。那人也没生气,赶紧上前帮忙捡起衣服。楚服抬眼就撞进了那笑意暖暖的眼眸,少年笑道:“你是不是叫楚服?我记得你,下次小心些。”楚服默默接过衣服,低着头跑远了。
“楚服,你怎么总有这么多衣服要洗?”
“楚服,你这鸳鸯绣得歪歪扭扭,真丑。”
“楚服,你笑笑好不好,你笑起来最好看。”
杜言之就以这样奇怪的方式靠近楚服。在他看来,这个沉默寡言的姑娘太好欺负,每天洗着好多人的衣服,做着数不过来的活儿,却从来不吵不闹,让他想要保护。
渐渐地,楚服像一个美好年华的少女般有了温柔的笑意和软糯的嗓音,也会戴着她最好看的发簪在这深宫角落为他跳舞。
他总说,你跳得真难看。
又是夜浓,楚服再次披上那件华服,推开了椒房殿的门。
门后的青石地板上,躺着一名宫女,身上伤痕累累,衣服破烂不堪,她拼力睁开被血渍糊住的双眼,用细微的声音说:“娘娘饶命……”
楚服认得,那是新进的小宫女莞绿,长相可人,性子活泼,对着楚服总是叫姐姐。不多时,那双曾经明亮的双眸灰暗下去,渐无声息,一会儿便有人上前将她拖走。
楚服什么都没问,只是俯身行礼,待得那人应声才起身。
陈皇后眼角微红,想是刚哭过,身着丹红凤袍,即使深夜,凤冠亦未取下,只是翱翔九天的金凤在这深殿烛火的映照下多了几分落寞。
陈皇后已命人摆好东西,品质极佳的檀香燃起,楚服跳起了奇怪的舞蹈,祭礼开始。陈皇后艳极的脸孔在缭绕的烟雾中渐渐扭曲,愤怒、委屈、祈愿变形地交织着。待楚服舞蹈结束,便又听见陈皇后歇斯底里地问:“阿彻有多少日子不曾来过椒房殿了?一月?还是三月?不,本宫记得,整整168天了……而如今,一个小宫女也敢欺负本宫了,我要杀光这些看我笑话的人!”
在对畜禽养殖过程中饲料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在对畜禽进行管理过程中常常发现很多畜禽指标不合格的现象发生。畜禽得不到充足的饲料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自身生长发育不健全的现象发生,很多畜禽养殖户一般都使用青饲料来作为补充畜禽的重要营养物,然而,这种饲料的转化率却非常低,长时间使用这种饲料在一定程度上对畜禽的健康生长将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饲料营养不充足在一定程度上对畜牧养殖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应该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心态积极创造更多创新型、高效的管理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畜牧业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楚服恭敬地跪着,看着近乎疯癫的陈皇后,直到她不耐烦地一挥手,才惶恐退下。
深夜的椒房殿因莞绿的死,不再死寂一片,几名宫女行色匆匆,低头疾行时不忘对楚服指指点点,无非是“帮凶”“不得好死”之类的话。她仍记得言之说过,这世上最无用的便是流言蜚语,做人但求无愧于心,何须在意他人说法。可是,言之,你不在的日子里,我便是靠流言蜚语活在这深宫里。
“她就是楚服,听说她和那杜言之已私订终身了……”
“是吗?怎么会……”
我守着和你有关的只言片语,苟延残喘。
楚服总是好奇,杜言之谈吐大方,容貌俊朗,为何只在宫中做一名小侍卫。
他点点她的鼻头,“我家是巫蛊世家……”
楚服一脸惊讶,巫蛊……在新帝继位后就被禁传,所有传蛊者不是处斩就是流放。
杜言之一脸淡然,悠悠道来,“新帝继位后,我家为避难早早分族,没想到还是没逃过灭族的宿命,我身为罪人之后,自是不能再为官,而我又不甘终生从农,索性进宫做侍卫……”
楚服轻轻拉着他的手,不知如何相劝。
少年的忧伤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就笑眯眯地在楚服腕上系上红线,白皙的手因多年劳作已不复娇嫩,还有些许粗糙的茧痕和伤疤。他细细抚着楚服腕上的疤印茧痕,有些不着调地说:“这红线我可是施过巫术的哦……”
“我这辈子只学了一种巫术,叫‘情’,这条小小红线就能牢牢绑住你这笨姑娘的心!”
“哼,我才不信,我偏不理你。”
“别别别,你同我说说话,我就好欢喜。”“有多欢喜?”
“整个长安城也装不下的欢喜……”
天边还擦着几抹绮丽的红,楚服提早来到椒房殿,远远便看到陈皇后站在殿前,面前跪着一群瑟瑟发抖的宫女和侍卫。
“陛下还是不来!让你们请人,你们请到哪里去了?给本宫杖责一百!让这群奴才长长记性!”陈皇后歇斯底里地吼着,宫女侍卫们哀求声一片,陈皇后只是甩甩衣袖,转身进殿。
楚服的身形晃了几晃,还是跟着进了殿厅。
“娘娘,今日便是最后一次厌胜之术。”
陈皇后闻言面上闪烁着喜悦,却没有急着让楚服施术,抬手取过一旁的杯盏轻呷一口茶,鲜红的丹蔻刺目非常,笑着问楚服:“你这丫头可有中意的人?若有,本宫可为你做主。”
楚服僵着脸,俯了俯身:“禀娘娘,奴婢没那个福气……”
“没有就罢了。”
楚服出椒房殿时,漆黑的夜空看不见半颗星。不多时便起了风,夹杂着潮湿的空气扑打着楚服的面颊,她没回屋,而是转身往甘泉宫的方向行去。宫外密林处,有两人等在那里。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卫子夫扶着侍女的手,即使有了身孕,黑暗中她仍旧清丽动人,不同于陈皇后的娇艳不可直视,她的美柔弱而清贵。
“是,只待陛下亲临椒房殿,大事便成。”
“开始时你就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你不后悔?”
“奴婢,不悔。”
楚服永远忘不了那个清风徐徐的午后,杜言之兴冲冲跑来,揣着小小的木偶,“楚服,你看这像不像我,我雕了好久,坏了好多个才成这一个!”
楚服摸了摸那只巫偶的发顶,“以后你不在就让它陪我。”只是她没想到,此后那么长时间里,就真的只有这木偶陪着她打发这枯燥的日子。
远处同行的侍卫催促着杜言之:“皇后娘娘遣我们去请陛下,再不走就迟了!”楚服站在椒房殿长长的台阶下目送他远去,风卷起他的衣袍,温柔又缠绵。
夕阳如血,椒房殿门前又在处罚侍卫,楚服听陈皇后嘶吼:“打死这群不中用的东西!”
她的指甲深深扣进掌心,铁鞭落在身上的击打声,言之的惨叫声,让她眩晕,她猛地起身要冲到陈皇后面前,本已奄奄一息的言之却高喊:“奴才办事不力,请娘娘责罚!”
陈皇后冷笑道:“重重地打!打死为止!”
楚服,我的笨姑娘,快退下。
日后,你要坚强,不要总被人欺负,不要在冬日里洗那么多衣服,手会冻伤;天暗了就点灯,不然刺绣时会伤眼睛;我们养在冷宫里的那只猫,我偷偷叫它阿服;还有,其实你跳舞时,美极了……
温柔的少年远远望着她,终于在铁鞭下闭上了眼。
胆小的楚服一夕之间褪去懦弱,披上复仇的巫服,自荐施术。卫夫人安排好一切,直至流言四起,帝遣人搜查。元光五年,陈皇后于宫内大行巫蛊之术,帝震怒,遂废后,巫女楚服传施禁术,即刻问斩。冷宫中,陈皇后哭喊着恳求陛下原谅,那人却不愿再看她一眼。
楚服被处决时,心里很平静,她的胸口还放着那只巫偶,手腕因为被捆绑多时早已红肿,却依旧系着那条红绳,摩挲着与杜言之最后的一丝牵连,楚服轻轻地笑了。
断头刀落,血洒刑场,小小的巫偶掉落,眼角一滴血划过,像是落泪般,笑着的面容莫名染上了悲戚。
“我这辈子只学了一种术,叫‘情’,这条小小红线就能牢牢绑住你这笨姑娘的心!”
“哼,我才不信,我偏不理你。”
“别别别,你同我说说话,我就好欢喜。”
“有多欢喜?”
“整个长安城也装不下的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