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不及纪念
◎ 孙 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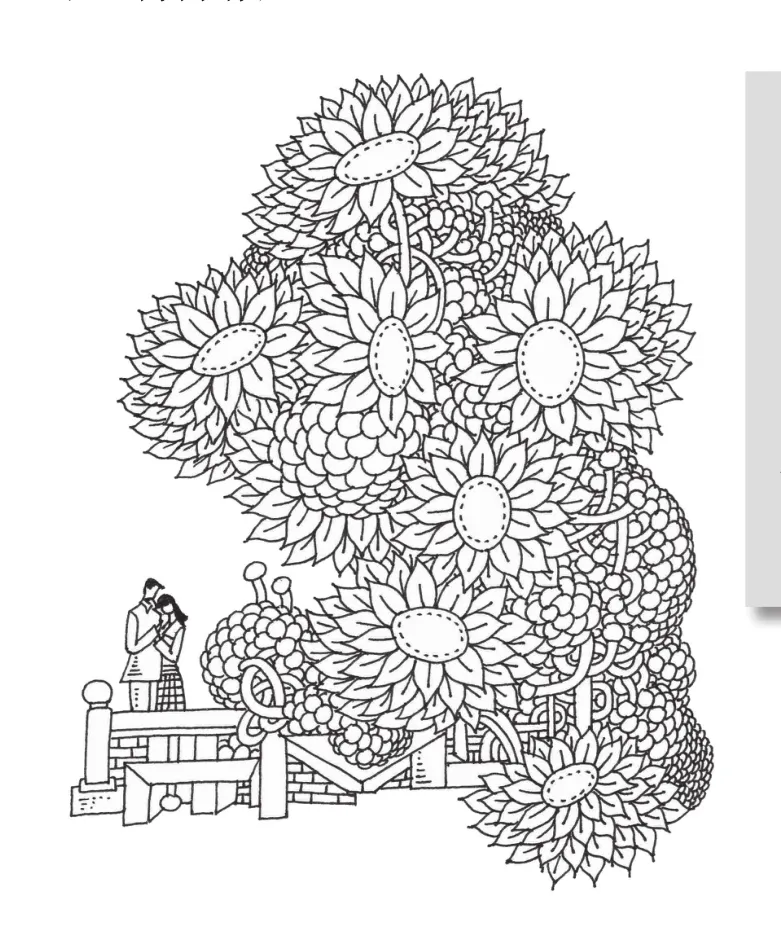
一位老朋友、老邻居,近几年来屡次建议我写写“大嫂”。因为她待我太好。
老朋友说:“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我当时答应了下来,但一直拖延着没有写。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去世。有时,我的脑海里也会出现一些闪回: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梦中相遇而不可得;如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
我还记得一些清晰的断片,让我对她的怀念愈加深刻。
有一天,母亲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
母亲问她:“试试,看你背得动吗?”
她弯下腰,挎好筐绳,猛一站立,因为北瓜太重,把她弄了个后仰,沾了满身土,北瓜也滚了满地。她站起来哭了,母亲倒笑了,自己把北瓜一个个拣起来,背到家里去了。
后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家境越来越糟,我又不在家,她带着孩子们下农场、下地。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梁,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粜卖。对于经历的这些,她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
我们那村庄,自古以来兴织布,但她不会。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就下决心学,从纺线到织布都学会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
我们的几个孩子,也都是她在战争岁月里一手拉扯长大的。农村少医药,我们12岁的长子竟以盲肠炎不治死亡。每逢孩子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
在她生前,我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你们若不记得我,也不妨事,但母亲把你们拉扯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
我们结婚40年,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摘自《当代散文鉴赏》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图/傅树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