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陈军的《“郭、老、曹”与北京人艺 ——戏剧文学与剧场的关系研究》,是最近戏剧研究的重要成果。它动态地以郭沫若、老舍、曹禺三位经典作家作为个案,将文学剧本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二度舞台艺术创作进行综合性、比较性的研究;之于世界范围戏剧创作重视“剧场性”贬斥“文学性”以及中国“探索剧”的实验现状,具有文化反思与“反刍”的现实意义。“不注水”的踏实、“论文”化的严谨、理论支撑的厚重,是戏剧学者的品格呈现;该专著的文学与舞台关系研究的互动话语,是开拓戏剧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新课题研究。
上海戏剧学院的陈军教授,继《工与悟——中国现当代戏剧论稿》《专与钻——戏剧与文学论集》等学术著作“亮相”之后,最近又推出 《“郭、老、曹”与北京人艺——戏剧文学与剧场的关系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的研究成果。这是戏剧文学史交叉延伸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为了本文叙述的方便,我将其书名简称为《“郭、老、曹”与北京人艺》。
此著的雏形,是作者于2004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老舍与北京人艺的互动关系》(指导教师为董健教授)。在此论文基础上,作者花15年时间、用学术钻研的钉子精神、以文学与剧场的互动关系为视角,逐步深入与放大,孜孜不倦、反复琢磨,终成现在“亮相”的、十五年磨砺的“一剑”。
我读完此著,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命题独特的视角。当年答辩专家丁罗男教授评价陈军的博士论文说:“作者较为全面地深入地掌握了文学与戏剧的基础理论知识,并且特别重视演出作为沟通文学与戏剧的桥梁,强调舞台是完成戏剧的最终表达之所在,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本身体现了避免陷入‘纯文学’或‘纯戏剧’偏途的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丁教授明确地指出了陈军论文构思的独特视角,是“难能可贵”的新的研究思维。实际上,他关注与读懂了席勒与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莫里哀与法兰西喜剧院、莎士比亚与英国环球剧院,以及叶芝、辛格等人与爱尔兰阿贝剧院等等剧作家与舞台剧院这一道特殊的文化景观,而产生了自己的构思。过去的话剧研究的内容,往往是话剧经典作品研究、经典剧作家整体创作研究、话剧团体思潮流派研究、中国话剧史研究、中国话剧的接受史研究等。而陈军却另辟蹊径,从话剧剧本到舞台演出,动态地将一度文学文本创作与二度舞台艺术创作进行综合性、比较性的研究;而且以郭沫若、老舍、曹禺三位经典作家作为例证,因人而异,分别对个案进行描述与厘析。应该说,关于郭、老、曹的话剧创作研究,论文与著述已经很多,方方面面的论述也已经很充分,还有什么可以再研究?陈军的回答是“ 有 ”。而他的这部专著就是他开拓创新的一个具体回答。
早在1978年,牛津大学巴勒克拉夫教授就说过:“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家对1945年以前占优势的那种历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动,至少对于年青一代历史学家来说是如此。对于20世纪上半叶支配历史学家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怀疑的趋势,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1]巴勒克拉夫在这里强调,史学研究要有责疑的思想与方法。文学、文艺的学术研究同样须要如此。从这个意义上看,陈军对当下戏剧创作与研究的现状提出“怀疑”,是值得我们予以赞扬和思考的,因为“怀疑”需要激情,更需要胆量与勇气。
巴勒克拉夫所说的“怀疑”,就是“责疑”。“责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最具有灵魂的批判精神。任何时候做任何一项学术性研究,都须要有责疑的立场、态度和相应的研究方法。面对世界戏剧创作重视“剧场性”贬斥“文学性”、而被台湾戏剧家姚一苇指称为“新形式主义戏剧”的“戏剧浪潮”,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探索剧”的探索现状,陈军是非常清醒的。他在《绪论》中开诚布公地说出了他研究的“缘起”:“探索戏剧重视剧场本无可厚非,也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文学核心精神的缺乏则可能使戏剧华而不实、空洞无力,因为剧院演出的好坏需要高质量文学剧本的支撑。同样,20世纪90年代,中国话剧也逐渐从‘Drama’时代走向‘Theatre’时代,致力于消解文本,解构文本与舞台的关系,以一种不破不立的态度突出剧场美学价值。”他的导师董健先生则很明确地认为:“客观地说,先锋戏剧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其试验也在某些方面丰富了戏剧表现的可能性。但是,否定文学在戏剧中的重要地位,重表演而轻文本,戏剧叙事的表象化,有时则掺杂过于激进的政治偏见,所有这些都使得它们缺少深刻的内涵。先锋戏剧虽然对传统的‘解构’尖锐犀利,而自身的精神建构和美学建构则明显不足。因此,它们主要聚集在京城,大都是个人制作而难成气候,到世纪之交也同样走入困境。”[2]惟其如此,《“郭、老、曹”与北京人艺》就是以剧作家与舞台演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证明给太过“先锋”的探索者看,旨在强调说明:文学剧本的文学性,作家给予导演、演员这一文学力量的强大支撑,永远难以消解与抹杀。当下戏剧忽视文学性,是一个必须讨论、必须解决的问题。陈军就是带着这个“问题”的责疑意识与使命,而开始他的学术研究;而且很平静地用剧作家与舞台演出的互动关系的学术叙事,表明他的学术思想、责任和隐忧意识。
我认为,学术研究与学术讨论切忌简单粗暴的批评与批判,应该摆事实、讲道理。陈军对当下“新形式主义戏剧”思潮泛滥之现状,不是直接对新时期以降的先锋“探索剧”说三道四,进行一些得失方面的评论,或者进行金刚怒目式的批评;而是通过自己独特的“戏剧文学与剧场的关系研究”,写成关于郭沫若、老舍、曹禺的文学经验,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称“北京人艺”)如何运用剧作家的语言文字符号变成舞台戏剧视听符号的经验——俨然是他的一份“学术调查报告”,告诉读者这是新文学传统戏剧的一份应该借鉴和传承的财富。人抓起自己的头发想离开生存根基的地球,这是徒然的痴心妄想。我们实践戏剧的创新性的探索,借鉴外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必须的,是发展我国戏剧事业所必须的“破体”,本无可厚非;但太多“失范”、太“转基因”,甚至完全置换成外国后现代主义的“骨血”,就有害无益了。目下,先锋小说家马原说“小说死了”、诗人兼评论家杨铁光说“散文病了”,罗兰 · 巴特也曾宣称“作者死了”云云,我认为它(他)们有“病”没“死”,失“度”就会产生或“病”或“死”的必然结果。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必须掌控。这个“度”怎么去掌控?我以为就是“执两用中”的儒家“中庸”哲学,这是研究一切问题、防止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而陈军的《“郭、老、曹”与北京人艺》,就是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中庸”的哲学态度告诉我们,用“中庸”哲学来节制、调和、归正,和谐地处理好“守成”与“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处理好继承传统与艺术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要忘了新文学的戏剧传统经验给予我们的自信,更不要遗忘与舍弃传统戏剧的文化基因之“根基”。这是陈军这部著作的“问题感”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下戏剧研究的现实意义。
唐代刘知几于 《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应具史才、史学与史识的“史家三长”。“史才”,主要指“辞章之学”的文才、文采。“史学”,主要指专业知识与理论基础的学养。“史识”,主要指识见、义理;即是以科学价值观发现并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文史不分家,研究文学同样须要研究史学方面的“三长”。陈军的这部著作,证明其学术研究三方面的知识结构是完备的。且显而易见,“三长”中间,前两“长”是做学问的基础,最重要的是第三方面的“史识”。“史识”的发现与建立,不仅要有驾驭文字的才能与专业理论的厚实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下苦功夫去做考据、研读、辨析等把握资料方面的工作。陈军正是在这方面下了真功夫。暂不论他对三位剧作家作品与研究资料的占有与细读所花的精力,仅看他在舞台演出资料方面的准备和梳理,就下了死功夫。北京人艺有完整的舞台演出的资料,对此,陈军数次去北京人艺进行科研调查,对北京人艺博物馆的“展示篇”“社教篇”“科研篇”“典藏篇”,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访问,尤其查阅了大量的“艺术档案”,包括每个剧目的演出档案,细致到作者修改剧本、导演分析主题、演员讨论角色、排演场的谈话、演出后的总结、座谈会的记录、报刊评论文章、说明书、宣传海报等等资料,甚至还有布景、服装、灯光设计图、化妆造型、音响声带、全剧演出实况录像。这些第一手原始资料的积累与研究,支持着《“郭、老、曹”与北京人艺》的最后完成。林非先生“泡”在北京图书馆,完成了《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与《中国现代散文史稿》;范伯群先生“泡”在上海图书馆完成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同样,陈军 “泡”在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馆,查找、细读、记录、辨析,才有他自己的发现与个人的见解,也才会有现在这部结实的专著。做文史方面的学问,就是靠资料的实证说话,就是在资料的占有与辨析中发现并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现在年轻的一些学子比较浮躁,沉不下心来,坐不住冷板凳,往往忽略了“考据学”的基本功夫。这就常常让他们写出空洞的“高蹈讲章”。所以,我期盼年轻学子应该多向陈军老师学习,学习他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走上归正的学术研究之路。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所谓“德”,就是章先生所说的“心术”之正。文史研究者本人,必须讲究从事学术研究的品格,认真、严谨,绝对不做伪学问。现在有些中青年学者喜欢“炒冷饭”,吃别人“吃过的馍”,抄抄拼拼,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库里实施“拿来主义”,就变成了自己的论文、著述。还有的人全然不顾中国的文论传统,生搬硬套外国的现代主义的名词、概念、观点,以西方学者为圭臬,常常引用福柯、苏珊·朗格怎么说,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戴卫·赫尔曼的“叙事学”如何讲,追逐新潮,盲目照搬,加上中国文学的一些原料,就成了自己的文章。说得明确一点,这是学风不正,做的是虚伪的“假道学”。而陈军的《“郭、老、曹”与北京人艺》,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当代文学学者应该有的“文德”。而这部书的“文德”的呈现,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从这方面看,除了前文涉及的相关内容之外,陈军还有几个学术品格的特点。
首先,是“不注水”的踏实。“不注水”是作者的夫子自道。他在《后记》里据实地说明:本书的写作不是博士论文的简单的“扩充”,而是“再起炉灶”,由老舍与北京人艺的研究,转向郭沫若、曹禺与北京人艺的研究。论文不停留在一般的描述上,所有的论证都有剧本的细读基础,也有关于戏剧表演过程的实证。在此基础上梳理、比较和把握“郭、老、曹”与北京人艺之间的复杂的动态关系,厘清不同风格特点的作家与剧院互动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中蕴涵的规律性,为戏剧文学与剧场关系的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例证,并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作为读者,我读完这部新著,感觉作者是很自觉地进行学理论述,围绕着“互动关系”的主旨纲举目张,重实忌虚,实事求是,在详实资料梳理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提升与观点的阐述。陈军的这种“不注水”,就是他做学问的踏实、老实与结实,用他自己的关键词说,是完全靠资料梳理之后的“实证”与“厘清”,没有一点空话、大话、废话的闲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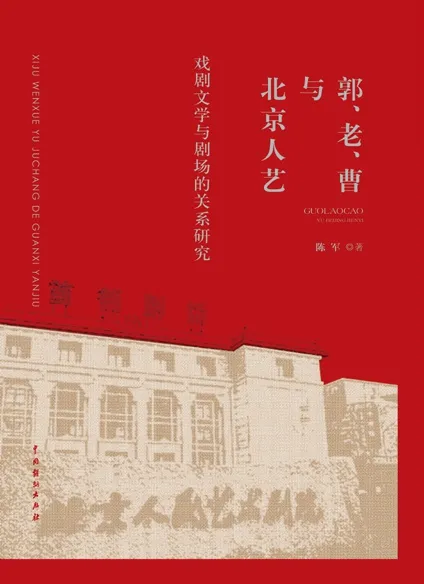
陈军 《“郭、老、曹”与北京人艺 ——戏剧文学与剧场的关系研究》封面
其次,是“论文”化的严谨。一般来说,学术著作的写作是将一篇论文“放大”了写,可以摆脱篇幅限制,自由漫论,甚至可以像写散文那样,不受任何约束地引经据典,并且进行相应的说明与引申;于是在另一方面,常常会产生许多芜杂的“水分”,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是故意拉长篇幅的泡沫话语。可是,陈军的这部著作却将常见的“论著”“缩小”了来写,即是将每章每节当“论文”写。正如他自己所说:“尽量把书当成论文来写。在写作时,我延续了当初博士论文写作的风格和要求,尽可能把书当成论文来写,不满足于内容的拼凑和材料的堆砌,而有内在的逻辑理路和间架结构,追求写作的层次感和递进性,尤其是尽量使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篇论文的规制和品质,合起来是一本书,拆解开来可以分成一篇篇论文拿出去发表。”几乎全书所有的章节,都经过学术刊物“三审制度”的严格审查,先后分别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戏剧》《戏剧艺术》《戏剧文学》等等全国著名刊物上发表。从文体学上说,全书既是学术论著的框架,又是一篇篇论文有机的整合,故而充满了严密逻辑论证的理论色彩,论说语言中没有任何的泡沫与渣滓,让读者觉得学术品位很高。归根结蒂,它是“论文”化的严谨写作。
第三,理论支撑的厚重。这部专著里,陈军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戏剧批评的理论世界。一是,他在从传统“戏剧”时代到“后戏剧”时代的宏观背景下,将中国的戏剧发展与流脉进行历史的定位,从而进行中国三位著名剧作家与北京人艺之间“互动关系”的叙事;宏观背景的把握,使论说提升到文学史的认知与史识。二是,陈军的专业戏剧理论的积累是厚实的,掌控着西方亚里士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的“诗学”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理论,英国盖·霍普特曼和德国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1t Brecht)之后的“新形式主义”戏剧理论,李渔等中国戏曲理论家传统的戏剧理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戏剧导演观及林兆华的“先锋”思想等等。作者对这些方方面面的专业基础理论,熟知于心,用起来得心应手,很有理论穿透力地支撑着他对论述对象的深层理解与感悟。即便在很多微观问题上的论述,也能够获得理性的自觉。如中篇第一章“跨文体写作与老舍戏剧的独特性”,抓住老舍小说创作中的“戏剧性”与戏剧创作中“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进行两者的比较研究,其论述就很有新意。再如,在对林兆华“先锋”思想得失的解读中,作者对其去“莎士比亚化”的批评很透彻且很到位,是很令人信服的个人学术观点。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论支撑,使该著又具有学养的厚重品格。
《“郭、老、曹”与北京人艺》的《结语》,以两万字左右的篇幅,对全书“互动关系”研究进行了总结,其中关于“文学与剧场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戏剧文学与剧场之间……在于高水平创作与高水平演出的相辅相成”“成功的戏剧艺术是作家、导演、演员三者的有机结合”“谋求文学与剧场双赢格局的形成”等四个方面“启示”的归纳,是作者言说历史与言说当下的建设性之学理感悟,是全书归趋的价值之所在,对当下戏剧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理论性的设计与想象。这是我推介全书诸多理由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建议读者对这一内容,进行细细的品味与思考。
【注 释】
[1]〔英〕杰里弗·巴勒克拉夫.当前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6.
[2]董健,胡星亮主编.中国当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280—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