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山水画未来发展的几点构想
崔遨然
如今,全球化的信息世界给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环境,也迎来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的艺术活动,毫无疑问地也要发生一些变化和联系。这就需要中国艺术家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文化身份的自我认识得到加强。由20世纪初的立足本土的变革,变为如今的面向世界的对话,这其中所蕴含的审美价值观变化,正构成中华艺术崛起的历史背景。
早在1918年,康有为就在上海中华美术专门学校主办的《中华美术报》上发表《万木草堂藏画目》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呼唤“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1]的到来。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画坛,一直是在改革的呼声中,不断地进行着艺术实践,与此同时,还进行了多次关于中国画发展方向的讨论,其中心一直是如何解决创作中的中西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中国画的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所以,山水画和风景画的比较研究,就成为解决以上问题的又一理论工具,它不仅能让传统中国艺术精神中的文化特质以及传统绘画作品中的独特表现形式、方法,在新的创作体验中重生,而且还能在认识西方艺术之后,再结合中国传统的艺术精髓,为我所用。
今天对传统绘画进行“再发现”的艺术思潮活动决不意味着墨守陈规,而是在经过了艰辛的历史征程、血与泪的崇高审美体验之后,人们辩证地期望着在对立的基础上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在更新层面上高级的“天人合一”。即,如果说古代内外和谐,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朴素的“田园和谐”,那么现代的和谐,就是生发于现代科技文明基础上的精神家园。就像徐恩存评价卢禹舜先生那样:“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敏感到人们焦灼的精神和审美的需求,他把自己的艺术框定在精神层面的高度上,着力以笔墨语言、意象符号去营造一个精神家园,去慰籍焦渴的审美心灵。”[2]因此,在这个历史主义的视野中,面向未来的精神家园,首先应该是回归传统,我们对历史要尊重,对大师更要学习,尊重传统是我们国画创作者应有的最基本态度,有一些经典是值得我们终身研究的,如: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图1)、《溪山行旅图》,南宋李唐《万壑松风图》,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明代沈周《庐山高图》等,我们应力求从传统佳作中找寻精神,在精神层面进行宏观把握,深究其精髓,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绘画加以改造、升华,把那些能引起现代人心灵共振的、富有艺术生命力的因素加以吸收,并发扬光大。其次,基于上述思想,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来光大传统艺术的文化品质;在积极而不是守持的开拓性实践中,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通过现代审美的精神沟通,正如石涛《画语录》所言“笔墨当随时代”。这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一种带有许多机遇的挑战,这是当代创新的必经之路。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对外开放,西方艺术思潮冲击中国画坛,李小山在《江苏画刊》上刊登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提出了“中国画穷途未落论”,“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及“传统中国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它植根在一个绝对封闭的专制社会里。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纲常,……无论从形式或从内容上看,中国画从形成、发展到没落的过程,基本上保持着与社会平衡的进程,几乎没有出现什么突变与飞跃。”到“传统中国画发展到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的时代,已进入了它的尾声阶段”。[3]这反映了一部分艺术青年迫求思想解放和艺术创新的急切要求。
此文引发了中国画界的巨大反响和讨论,中国美术开始积极地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元素,有责任感的画家们都在认真地思考自身艺术发展的前途。如吴冠中、张仃的关于中国画的底线问题之讨论,同时也回答了笔墨问题的关键点。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这场两位艺术家的辩论逐渐升级为美术界的大讨论,影响范围由此扩大。在当时中西融合的呼声中,还有一些盲目的画家,靠一些间接的文化交流渠道引入东拼西凑的文字来了解西方当代艺术,从而造成他们对西方艺术理解的片面化,这种吸收不仅不会给中国画界带来根本性优化,相反变成发展的绊脚石。所以,中国当代国画家需冷静下来,面对“西学东渐”,既不能盲目否定,也不要全盘西化。没有参照,没有其他文化对比,文化差异性所带来的特征,都无法清淅地展示出来。一定要把风景画中对我们有利的东西,为我所用。要看到,在西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西方现代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弊端,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的艺术评论家,提出了震惊当时整个欧洲画坛的新论点,客观犀利地指出西方现代艺术已走到尽头: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艺术不断个性化和不断求新求变,并越来越脱离社会大众,造成艺术与社会大众的矛盾和对立。这些危机使西方艺术家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艺术中所体现的智慧和技巧,特别是中国山水画中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有很重要的补偿作用。现实生活中失去的精神世界,在艺术作品中可予以弥补,艺术中呈现的精神世界,将带给人们以启迪和教育,使之更真诚地对待自然。又要看到,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文化符号流传下来,中国画的材料和笔墨语言形式符号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特质,是其它艺术材料或语言形式符号所无法互换和替代的。也正因此,中国水墨艺术现代形态的创新历程自然就更为艰难。当然,谁都无法预测中国水墨艺术在21世纪中存在的笔墨语言形式符号,但经过了艺术思潮变革过程,中国现代水墨艺术既体现出吸纳各种门类现代艺术观念与形式语言的优越性,也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在我国当前艺术大环境下,开放地吸取部分西方当代艺术的美学因素、创作理念,是颇为有益的,而这与继承传统并不矛盾,因为我们所说的现代新和谐对传统的否定,其实是一种包含着肯定的否定。中国艺术追求的方向与西方艺术追求的方向到底是有所不同,还是殊途同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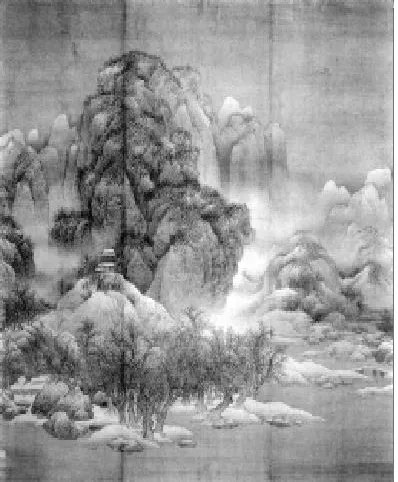
图1 范宽《雪景寒林图》
那么,我们就来构想一下,当代山水画创作者要在西方艺术中寻找哪些长处为我所用呢?
首先,要把目光投向自然生活,将主观情感与自然景物和谐地融合为一体,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状态,这是使画面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只有这样我们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笔墨语言符号才能有用武之地和不断创新的可能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谈到:“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毕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躁所受,躁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搁笔”。[4]此意不仅指出了“外师造化”的重要性,还提出了外师造化是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掌握自然规律,扩大内心容量,才能表现出造化之美。虽然这是中国国画的优秀传统,但自清末以来,山水画家很少到真山真水中去洗涤陶冶自我,满足于在前人的笔墨程式中徘徊自赏,山水画的发展历程一度陷入摹仿前人不求突破和发展的怪现象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提倡“天人合一”,到自然生活中去,吸收自然给予画家们的无限信息,使之从其内心深处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那无疑将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应恢复传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理念,但在表现的过程中对自然生活的感悟表现要多于对自然生活的写实表现,试看笔者创作的《遍地柳花香》(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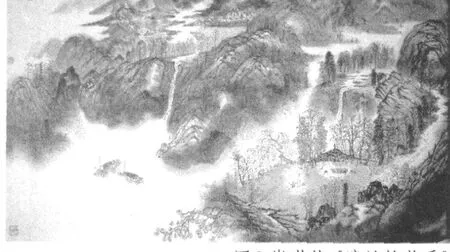
图2 崔遨然《遍地柳花香》
其次,西方风景画对近代中国山水画家的启发是对造型的关注。中国传统山水画讲神韵,讲传情,把极为普通的山村、乡野、田园、树林等自然景物与诗性浑然一体,这是十分可贵的。“神”与“情”之表现,在传统山水大师中决没有离开真实和相应的造型,以形写神,以形传情。笔墨之美之力,不是为了写形,但也不能完全离开最基本的形。否则,便使笔墨趣味失去具体实在的艺术感染力,失去画面应有的视觉效果,就成了笔墨游戏。这是近代中国山水画衰退的原因之一。当然,关注形的表现,并不是要把风景画的写实方法简单挪用到中国画中来,而是要求山水画家笔下表现得是真实的、可感知的山水,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假山假水。80年代后期,一些画家多次赴欧美进行考察,跳出了形的束缚,形成了新思维,创作了一批强调形式的作品,从而与写实山水拉开了距离,突显了视觉张力,成为革新山水画的代表。
第三,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平面构成特征和装饰性也给予山水画家一些启示。例如,1979年,吴冠中先生明确提出:“在造型艺术的形象思维中,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形式思维。形式美是美术创作中关键的一环,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5]他力求探索运用中国传统材料工具表现现代形式、精神美感,并一直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他的水墨画构思独特,布局别致新颖,善于将诗情画意通过点、线、面的交织而表现出来。他喜欢运用构成形式方法强调装饰性,简约概括表现对象,以半抽象的形式语言表现客观自然物象和主观心理感受。既有东方传统诗情画意,又有时代气息,如一丝春风拂过画坛使人耳目一新。这与西画的的点、线、面三个基本的造型因素有着相通之处,所以,也可以把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平面构成特征和装饰性等方法加以改造、转化,尝试着打破真实空间再重组画面空间,化物理空间为艺术空间重建秩序之美、景象之美。
再者,西方风景画的明暗与色彩的表现力,不能不对中国水墨山水产生某种刺激。西方风景画一直是色彩的世界,用色彩表现风景画是欧洲绘画的最大特征。而西方的色彩观,是将色彩与科学结合起来,将形、色、光三者和谐结合在一起,在画面上将色彩、光影、造型和透视进行完美结合。而中国山水画的色彩观念一直保持固有色的观念,“随类赋彩”是中国山水画设色的理论和方法。无论怎样,中西方的色彩观念都是关于对客观事物的直觉感知与看法认识。因此,色彩表达了山水画与风景画的视觉特征。但在分析各自表现特色的同时,适当吸收西画的科学客观的、丰富准确的色彩关系,与笔趣、墨韵相结合,来改进和扩充中国画自身的表现语言,增强色彩方面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则不失为明智之举。
如今,中国山水画多元共生的审美文化格局已逐步形成,它意味着不同层次、不同趣味、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之间所构成的审美文化生活景观。人们的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都需要与时代同步的艺术,传统文化给人以民族的归属感,赋予传统文化的新生,会获得时代的共鸣,为百家争鸣的创作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对于每一位寻求充分发展的个体来说,关注整体艺术大环境发展的新动向、新思潮,善于兼收并蓄,才能不断超越自我,抵达人与人、人与自然新和谐沟通的审美境界,这才是精神活动的理想境界。
注释:
[1]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丛刊》(2),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93页;
[2]林彦:《卢禹舜艺术研究》,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3]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江苏画刊》1985年第5期。
[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5]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美术》1979年第5期。
责任编辑:李 雷
崔遨然: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