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山的地理和心理
——评《观音山》
杜庆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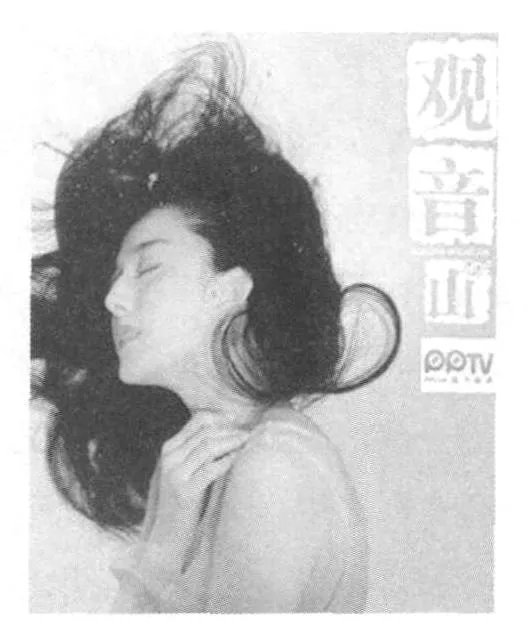
一部电影是复杂的,目前的中国电影生产状况更是让文本的复杂、甚至内在分裂演绎得格外充分。一部电影总是承担了过多的纠结和看似难以统一的欲望,然后它或许只以一种侧面在这个时间点上被过度讨论。如果说,姜文的《让子弹飞》是一个CULT电影却演绎为大众宣泄的狂欢,那么,李玉的《观音山》却注定被言说成文艺片的市场成功样报。按照可信度比较高的艺恩咨询的数字,截止到2011年3月27日,《观音山》的票房是上映25天,总收入6860万元。一部这样的电影可以获得如此的成绩自然感谢范冰冰,范冰冰也送导演李玉一辆汽车作为在东京电影节上拿奖的回馈,算得上功德圆满了。但是,这部电影更为复杂的面向是如何构成的呢?除去这些物质性的数字背后,还可以讨论一个精神图景的复杂性吗?
观音山作为地名,也作为一个行为的场所出现在片中。作为地名它提供了火车行进的地理依据,那些在火车道上行走,或者在火车车厢被风吹拂的青春的脸庞,成为这部电影里最根本的一种调性,一种文艺青春的调性。而观音山作为一个行为的场所,却提供了一座被地震摧毁的寺庙的重建过程,人不多庙很小,言谈却很深沉,这个维度拉抻出一种中产阶级在这个时间点上的宗教需求。当然,在剧情中间的段落中,“观音山”其实才真正完成了剧中两组人物的扭结,也就是创作者才最终将这些人生放在一处了,这种安放其实远远超越了租房这种编剧层面上的技术手段,而成为一种精神性的征兆。总之,《观音山》就是上一代的青春期(主创们的青春肯定已经消逝了,这里的青春其实不是现在时的,而是充满了一个追忆性的氛围),一个丧子之痛的母亲的典型戏剧形象(幸亏这部电影没有找一张对这种形象典型演绎的演员的脸孔)和观音山的组合,一个文艺青年的自我怀念、一个家庭伦理基础上的女性创伤心理,叠化成一位女性导演的双重扮演,而最终在观音山上混合为这个时代的带有宗教性消费的自我灵魂安顿。更直接地说,这是一种文艺青年的个体记忆、文艺中年的灵魂需求和通俗叙事的戏剧套路的粘合,最终转为观音山带出的隐喻性的姿态。铁道上的姿态,青春美丽的光影消逝在远方,连接着一个创伤中渴求安宁的灵魂之肉身的消逝,这里面带出了一个心灵历程的游走痕迹。
我愿意更琐碎地讨论影片的结尾段落。有些观众——这些观众肯定超越了看范冰冰的欲求层级,讨论结尾处张艾嘉的“跳”或者“不跳”,但是我觉得这根本扭曲了创作者的欲望。创作者在此处恰恰不想涉及或者说根本规避了这个人的选择的视觉呈现,这种视觉呈现也可以说是“确认”,也就是创作者在此处不想确认经历可以造成何等抉择,而自动选择一种“超越”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艺术上可以被修辞为“空灵”,实际上本质的描述就是“她不在我们看见的视野里了”,而且“她也不在剧中人物的视野里了”,“她”消失了,在她看见并且参与了观音庙的复建之后,在“她”和宗教对话之后,她就可以这样了。但是创作者肯定还没有这样,于是我们必须重新面对青春的脸孔在轨道上行进,重新面对迷惘青春的姿态。
对于一种姿势的着迷构成了这个电影的姿态,所以也留下了很多需要打磨的毛边,也就是我很难将剧情和这种内在姿态化合成一体,它不断地造成我观影的断裂,也造成了我在影院时,前排观众不断聊天状况暗示的出戏状况。譬如,演和尚的演员显得过于临时而不经意,而这一点却足够伤害这部电影能否完成真正扭结的观音山的质地。同样,这部电影使用的香港明星无法和地域真实感与大量叙事性段落的写实性的镜头相容,但这又是文艺片努力获得市场回报的无奈结果。或者说,这部电影在精神上的自我指涉之外,还充满了各种现实自我的策略性,这些策略性选择也许因为制片周期都变得有所唐突,比如地震和迈克尔·杰克逊元素的引入都带来了一种误点的感觉。再譬如,这种两个不相容世界的人相处一处,在作息习惯、饮食等等方面的喜剧性的暗示,却被创作者对于人生悲剧和人生残酷的思维习惯不断击碎,当然,这样造就了这部电影对于创作而言难得的松弛感。
总之,《观音山》这部电影在试图成为一个带有戏剧性的电影,或者说它试图成为一个有故事、在市场上可以剧情作为卖点的电影。这些剧情设计是相当唾手可得的便宜的桥段引用,让两个世界的人相遇而成戏。迷惘的青春期的年轻人,为生活打拼,也被情感和欲望折磨,他们因为租房遇到了一个沉浸在丧子之痛的老年女性,并且他们窃取了她的金钱,当然,他们是准备归还这些金钱的。我们自然知道故事的写作肯定是相互的救赎的诉求,但是影片在并不认真地提供了两个世界的人物相互接纳了的剧情的同时(这种接纳的故事像无数遍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一样出现在电影的历史中,这次也出现了),影片最终完成了透露出自己真相的使命——还是两个世界,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这座山被命名为观音山。也就是说本片的创作者以自我为桥梁,在电影之外连接这种断裂,就是“我的青春”和“我的想象性创伤的中年”在文艺中青年的姿态性中完成了融合,或者说范冰冰在这个片子真正要感谢的也许不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角色的内心深处和创作者的精神关联性。这种姿态无法在剧情的故事层面以有着充分说服力的人物以及戏剧桥段来推动剧情的发展,音乐和阳光一样弥漫的状态性画面彻底揭开了自我想象的真相,青春的美丽、青春光泽消失后的魅力,这些才是超越人生历练的沉淀的真实痕迹。在此,电影作为痕迹的意思也许完成了它的使命。
责任编辑:唐宏峰
杜庆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