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典与本土新作
——第39届香港艺术节点评
林克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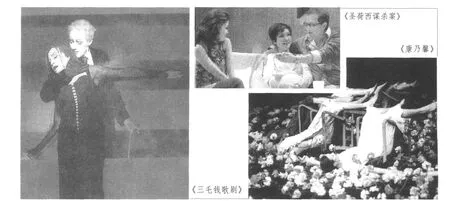
第39届香港艺术节于2011年2月17日至3月27日举行。本届艺术节规模盛大,演出及活动超过200场次。节目包括世界级经典与本土新作。歌剧有莱比锡歌剧院演出的《崔斯坦与依索尔德》,这是理查德·华格纳写于1865年的三幕歌剧,是该剧面世近一个半世纪后,首次在亚洲演出。舞蹈有纽约市芭蕾舞团带来的、包括“美国芭蕾舞之父”乔治·巴兰钦编舞的《小夜曲》、《三乐章交响曲》等七部镇团舞码,皮娜·鲍什乌珀塔尔舞蹈剧场的《康乃馨》。音乐节目有莱比锡布业大厅超豪华阵容演奏的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舒曼的《春天》交响曲等名曲,当今世上最优秀的花腔女高音塞西莉亚·芭托莉和英国第一代摇滚闯将、以沙哑迷人的嗓子独树一帜的玛丽安·费思富尔的独唱音乐会。戏剧则有罗伯特·威尔逊导演、柏林剧团演出的布莱希特名剧《三毛钱歌剧》。
属于创新赞助计划委约的本土新作有香港话剧团资深演员潘灿良编导的《重回凡间的凡人》和三度公演的《圣荷西谋杀案》。同样属于新作赞助计划的,还有两岸三地联合制作的、用摇滚、流行音乐伴奏的另类京剧《水浒108忠义堂》等。
香港艺术节是亚洲艺坛盛事,其声誉建立在多年不改其志的高水平经典节目展演,吸引世界各地演艺精英到此献艺并进行学术交流。另一方面,香港艺术节有计划地赞助当地及海峡两岸创新节目的创作,为探索性作品和年轻艺术家提供一个切磋技艺的理想平台。
本文不是艺术节的全面概述,涉及的仅仅是部分剧目和舞蹈剧场的零碎评点。
一
《三毛钱歌剧》改编自约翰·盖伊(John Gay)的《乞丐歌剧》,是布莱希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1928年在柏林船坞剧院首演,此后长演不衰。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后现代主义弑父一代的戏剧家们,一再指责布氏戏剧中的“社会性关照”与“情节主线”的结构模式,然而无法阻止布氏戏剧不断地被搬上各国舞台。在经历了银行高管的群体性诈骗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观众在全剧末尾,听到出自一个强盗之口的辩词:“抢劫一个银行怎能同开办一个银行相比?杀害一个人怎能同雇佣一个人相比!”观众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不能不佩服布莱希特的先见之明与博见精识。今天的戏剧,不一定非承担启蒙的重负不可,但像布莱希特关于“强盗本来是公民”一类的人文关怀,仍不失启蒙与启悟的意义。
执导《三毛钱歌剧》的,是当今炙手可热的美国导演罗伯特·威尔逊。这是一位被说成兼有戏剧奇才与江湖骗子名份的神奇人物。在他的成名作《沙滩上的爱恩斯坦》、《西·弗洛伊德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中,极缓慢的动作和并存的不同元素各自独立存在,成了他与众不同的视像呈现方式。这使他成了当今最有名气、又最富争议的导演之一。
只是这一回,由于采用布莱希特的文本,更由于有一位德国导演、两位戏剧文学顾问,一支出色的小型乐队和柏林剧团一众演技精湛的演员的通力合作,演出明显地带着表现主义戏剧那种刻意为之的形式美感与审美距离,也不难从表演者的身姿、手势、表情中窥见卡巴莱(Caburt)歌舞秀的痕迹。奇妙的是,所有这一切,均被威尔逊纳入:说书人的叙述、幕前戏、情节主线的戏剧扮演、作为间离层面的歌唱……的严整结构之中。对纯然抽象的几何图形的偏好,对包豪斯(Bauhaus)式简洁与功能性的倚重,处处不减威尔逊的个人色彩。
全剧设色大胆,对比鲜明。除珀莉小姐同尖刀麦基在马厩姑且成婚时身披白色婚纱外,其余角色的服饰均为灰、黑的冷调西服。主要人物脸部扑粉,近似歌舞伎演员水白粉敷脸的白面,在幽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耀眼,与几成剪影的群体角色构成层次分明的对比。
全剧行将结束,尖刀麦基脖子套着绞索站在行刑架下,扮演丐帮帮主的约根·霍兹(Jurjen Holtz)恢复演员身份,直面观众说道:“尊敬的观众,我们准备就绪,尖刀麦基就要被绞死……但为了不让你们以为,我们同意这一规则,我们设想了另一种结局。”此时,从前台左侧快步走出一位“信使”,身披一袭极为怪异的、后摆逶迤拖地的红色长袍,其艳异张致,夸诞而虚妄。随着警察局长宣布:“女王在她的加冕典礼之际,命令释放麦基上尉”,并赠送他一座城堡和一万镑终身年金。在一片欢呼声中,一整幅猩红、奢华的古典式的丝绒大幕倏然从天而降。布莱希特在关于《<三毛钱歌剧>的排练说明》中写道:“如果骑马使者不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舞台上,资产阶级文学就会降低为单纯描绘社会状态的水平”,故意作假的、可笑的结尾,一举两得,既是对警匪一家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批判,也是对矫情造作的资产阶级传统歌剧的嘲讽。
全剧表演最出色的是扮演丐帮帮主皮丘姆、年近八旬的老演员约根·霍兹。皮丘姆统治着一个庞大的乞丐王国,将贫穷当做商品出售。他老成闲肆,身段柔软,在与警察局长布朗斗法时,语调平缓,不动声色,其威胁来自轻描淡写的话语后面利害关系的暗示上。在收取穷乞丐费尔希(乔治·齐万诺格鲁扮演)行乞许可的定金时,皮丘姆/约根·霍兹、费尔希/乔治·齐万诺格鲁一同僵立在舞台左侧,前者伸出胳臂,手心向上,后者伸出胳臂,手心向下,音响效果长时间传出金属钱币掉落钱罐时哗哗啦啦的撞击声,两人身体不断抖动……此刻,演员表演完全背弃了现实主义的似真性,两位人物的特定关系,从具体场景中剥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意义,成为一种表现性的舞台意象,一种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漫画化的常规图式。演员在角色与角色的扮演之间灵动转换,在规定情境的真实体验与夸张、变形的肢体形态之间巧妙地滑动,使表演的间离,在强烈的主观性表现与细致的内心体验之间,获得微妙的平衡。
此次柏林剧团演出的《三毛钱歌剧》,导演是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戏剧家罗伯特·威尔逊。人们在领略何为叙述体戏剧、何为表演间离的同时,也一窥了布氏戏剧与后现代主义(观念与技法)碰撞时所产生的火花,促使人们更深入地去思索戏剧变革与历史承传的复杂关系。
二
《水浒108忠义堂》,是受香港艺术节委约、台湾当代传奇剧场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戏曲学院联合制作的新编京剧。主创人员是知名演员吴兴国、文学好手张大春、流行音乐人周华健。
全剧从《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开始,采用回溯手法,跳跃式地叙述:武松夜走蜈蚣岭、花荣大闹清风寨、秦明夜走瓦砾场、浔阳楼宋江题反诗、众将三打祝家庄、吴用智取大明府……这些片断场景几乎都属武戏,也即是武打演员身段、功架的简略展示。戏的重心放在第二幕“罗天大醮”与第三幕“菊花会”上。
“罗天大醮”表现宋江终成梁山寨主,遂令作七日大醮,祈保众家兄弟身心安乐,超度横死、被害之人俱得善道,上荐晁天王早生仙界。众人行礼如仪,渐次散去。舞台转暗,漫天飘雪,空荡荡的醮坛下,只剩宋江孤身一人。演出者将晁盖的灵位置于舞台后区正中的高台上,此时狂风大作,身披白袍的晁盖跃身而起,直陈“贤弟呀!你我还是你我,这山寨么——却不是昔日的山寨了!”“毕竟是宋公明,算尽机关,运筹帷幄,将才无二,能把江山坐!”听此言,宋江惊出一身冷汗。尽管他一再辩解,“窃钩者诛,何如窃国者侯?”毕竟有些心虚。编导者将晁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恨与宋江机关算尽志未酬的惆怅,作了鲜明的对照。编导者更加着力的一笔是,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脸颊上中一毒箭,此时,面对钓江山、猎公侯的昔日弟兄,视千秋伟业如枷锁的晁天王,唱罢“今朝一醉今朝酒——我不问千秋”,放声大笑,挥手拔去脸上之箭,弃绝而去。
菊花会,本是秋高气爽,重阳节近,宋江大摆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原以为座次已定,各守其位,开怀痛饮,等待招安。不料一提招安,武松、李逵等一众下层将领,捶胸顿足,踢翻桌,冷了心,李逵更迸出一句“招他个鸟安!”来。鼓乐声中风吹雪飘,场面凌乱。此时,从舞台深处走出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含笑不语,自左而右,穿场而过。一曲“一片残阳水上月……笑英雄,笑英雄……”的轻柔女声,同时而起。戏剧场景之妙在于编导者不再拘牵于儒的忠义与侠的忠义两相对立的思维定势,引入禅的角度与女性视点,以众语喧哗的多元视域,为当代观众提供多种可资选择的思考角度。
牟宗三以禅解《水浒》,认为武松、李逵、鲁智深为“无曲者之典型”,而以宋江、吴用为“有曲者之典型”。无曲,即纯直无曲,义之所在,生死以之,当下即是,洒然自足。他由是认为“《水浒传》是禅宗”(《水浒世界》)。牟氏的见解异于前人,自成一家之言。观众何妨将在台上无牵无挂、无忮无求、四处游走的和尚,看作禅之灵光一现。
全剧人物设置,最精彩的莫过于在一种勇武狠斗的亡命之徒中自如行走的女性角色——孙二娘。剧中的孙二娘,婀娜多姿,温婉柔媚,全非小说中那个眉横杀气、眼露凶光、卖人肉的母夜叉。在罗天大醮与菊花会之间,以及全剧终了,她两度从台唇与前台之间的花道登台,款款而行,一曲“笑英雄、笑英雄……”“笑你怕进温柔乡,笑他不识红粉妆,笑尔曹尽夸英雄冢,笑儿郎眼波真懵懂……”将假道学的江湖世界揭个底掉。
全剧最大胆、最富争议的探索,恐怕是将摇滚乐引入京剧舞台。贬者认为京剧文武场加摇滚乐、尤其是让吉他手登台独自演奏,有些不伦不类;褒者认为摇滚乐、流行歌曲入戏,有助吸引青年观众入场观看演出,也拓宽了戏曲音乐的路子。我倒是注意到歌曲在全局构成上的另一种作用。周华健为此剧专门制作的《三打祝家庄》、《饮酒歌》、《菊花会——笑英雄》等歌曲,通俗易懂,委婉动听,为全剧增色不少。假若前两首歌曲,作为群体合唱,还只是渲染场景气氛,传递人物情感而已;那么,一曲女声《菊花会——笑英雄》,意义更为深远。演唱者孙二娘/刘津,此时已不全是角色(孙二娘),也不单纯代表演员个人(刘津),而是化身为编导者从女性视点出发、又超越女性立场的代言人,成为戏剧演出的所有参与者,包括编导、演员、观众,对血肉杀夺、江湖忠义的一种评判。我不知道,这其中,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编导者的理论自觉,但在戏剧美学上,它确实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技巧在戏曲舞台上的成功运用。
三
今年是皮娜·鲍什谢世后乌珀塔尔舞蹈剧场首次访港,也是舞团第四度在香港艺术节上演出。前三次是:1997年3月的《抹窗人》,2001年3月的《热情马祖卡》,2008年2月的《月满》。
受艺术节邀约,1996年秋天,皮娜·鲍什和她的舞者在香港逗留几周,兴致勃勃地去了解、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情。她们将对香港的人、事、环境的感受,编成舞码,这就是次年3月演出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抹窗人》。
《抹窗人》舞台上放置了一座由无数鲜红的香港市花——紫荆花堆成的移动“花山”。演出末尾,川流不息的人潮,从舞台一端涌向另一端,登上花山,隐没在黑暗之中。几个月后,香港这座殖民城市即将回归祖国。登上花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群,是个玄机内藏或一无心机的晦涩隐喻,将其当作引发家国之思的戏剧性场景也未尝不可。
花是《抹窗人》最主要的舞台意象,一如《蓝胡子》的满台枯叶、《热情马祖卡》的黑色火山熔岩、《月满》中的水……构成别有深意的舞台景观。在《康乃馨》中,花的规模更宏大,意涵更复杂,浪漫情怀与冷冽嘲讽的并置与对应,让人感受到皮娜·鲍什和舞台设计师彼得·帕布斯特加诸“花”的力量。
《康乃馨》首演于1982年年底,此后经过多次修改加工,一直成为舞团巡演时的重要舞码。《康乃馨》的舞台场景极为壮观,台上密密麻麻地插满约八千朵粉红色康乃馨。一群穿着套头连衣裙的男舞者嬉戏其间,或四肢着地如兔奔鼠蹿般地撒欢,一片童稚无忌的欢乐、和平景象。突然间跑上一位身着笔挺西装、脸色阴沉的男子,追逐、驱赶众人,逮到一位枯窘的来不及逃脱者,狠揍其屁股,并严厉苛斥:“护照!”舞台右侧同时出现两条被皮带勒住的虎视眈眈的德国牧羊犬。充盈童稚游戏气息的花海,陡然变成严厉管束的权力场。
另一个场景是:五、六个男人在一排长条桌子上跳舞,一群妇女躲在桌子底下蜷曲肢体,跳着局促、滑稽的舞步。同是被管束、被压迫者,男人与女人竟然分出等级。更有甚者,这群男女不断围攻、欺凌一个体弱力衰的老者。弱者将迫害加诸更弱者,人性的丑恶,以此为甚。舞蹈剧场呈现的是,无所不在的残忍与恐惧,以及弱者在强权、暴力之下的无助与叹息。
男女舞者不断地涌向台口,向观众诉说各种极其可笑的自己为什么成为舞者的理由;不断地走到台下,与观众拥抱、交流……这些在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极具挑衅性的表现手段,在今天看来,已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但不要以为舞蹈剧场的舞者只是像业余演员一般地随意、松脱,其实他们都是技艺精湛的舞者,我们已在《热情马祖卡》、《月满》中,见识了男女舞者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独舞和形态各异的多人舞蹈小品。也不要以为皮娜·鲍什舍弃舞蹈技巧。在《康乃馨》中,舞者快速奔趋、蹦蹿、突兀转身的爆发力,群舞者斜坐在椅子上全身舞动的韵律与力道,从一位女舞者开始、推衍至在场所有舞者双臂上扬、微微摆动宛若微风拂柳的轻柔身姿……其编舞手法,部分源于德国表现主义舞蹈的理念与传统,部分来自美国后现代主义舞蹈的影响。
皮娜·鲍什将儿童游戏、自传体独白、杂技的特技技巧、普通人的日常姿态与动作、尤其是多焦点并列与戏剧场景的张力……引入舞蹈剧场,极大地拓宽了现代舞的表现力。但她从不对自己的作品强行索解或故作深沉。有人将《康乃馨》中那两个巨型的金属框架,说成边境的守望塔;有人将满台被砸烂的纸箱,说成是现代启示录之后的废墟……其实各种读解因人而异,重要的是舞台呈现什么和如何呈现。无边的花海被巨大的金属塔架和大堆纸箱所占据、挤压,舞者的空间被压缩在台中的一小片地盘和台沿附近,舞蹈与杂技两种不同的演艺并置于同一台面,被践踏、被损毁的断枝残叶同演出开始时整片明丽、鲜艳的花海的对比……这些场景、视像已足以让人获得无穷的启悟与遐思。
最令我思索再三的是,皮娜·鲍什不仅对古典芭蕾盛丽艳魅掩盖下的苍白,对现代舞优雅自恋的眩技逞能,嗤之以鼻,而且对舞蹈(艺术)在后现代(消费时代)能做什么,心存深深的疑虑。一位女舞者沮丧地对观众说:“不要怪我,是鲍什女士要我这么跳的。”更多舞者则追问自己、也对观众发问:“我们还能跳什么?”皮娜·鲍什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舞台上呈现生命的严酷、世界的荒诞、男人与女人无休止的战争……然而却无法或不吝将其化解。一如她自己所说:“我跳舞因为我悲伤”,或如约亨·施密特为她所撰写的自传所起的书名:《皮娜·鲍什——为对抗恐惧而跳舞》。
皮娜·鲍什对当代舞蹈、戏剧等艺术的影响难以估量,她编导的一系列作品:《春之祭》、《穆勒咖啡馆》、《康乃馨》、《月满》……已成新古典。然而有谁能深入理解这位舞蹈剧场第一夫人沦肌浃髓、痛彻身心的悲伤与恐惧吗?
四
此届艺术节上演的两台本土话剧:一是资深演员潘灿良担任编导的《重回凡间的凡人》,一是青年女剧作家庄梅岩的《圣荷西谋杀案》。
《重回凡间的凡人》采用回述方式,将整个演出包容在一连串的回忆或梦境之中。戏剧开始时,主人公黎志宽平躺在台板上,喃喃自语,叙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漂浮在太空中。从太空回望地球,感觉到四周非常安静,安静得令人害怕。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平淡、平实,平实到没有多少戏剧性,以不事渲染的凡人俗事的日常场景取胜。许多时候都是在某一片断的末尾,主人公站在台中,把自己内在的个人感受直接诉诸观众。这些片断,这些琐琐碎碎的回忆,其意义主要建立在祈望相互理解、守望相助的人性及人伦的价值层面上。
黎志宽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已经不很年轻的年轻人。他的工作要经常往返于香港与深圳之间,偶尔也会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他的女友——“琪”——是一位空中小姐,居无定所地穿梭于香港——加拿大之间。他们都属于“无根的一代”。对他们来说,此地与他乡,分别不大。“宽”的生活,就是上班,吃饭,与女人约会,到深圳泡澡堂……对人对事一贯漫不经心,无可无不可,从未想到要对家庭、社会承担什么责任。突然有一天,“宽”的父亲病故了。于是,他的心情、甚至性情,随之大变,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从前那种表面闲散、平淡的生活,其实是安静得令人可怕。《重回凡间的凡人》与香港回归前夕那些探询港人身份、建构香港意识的“九七剧”不同,其关注的重心已转移至个人(凡人、普通人)对当代都市生活的感受。但在对友情、亲情的珍重,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婉转、沉重的背后,仍沉潜着对“此处是他乡”的不安全感。
《圣荷西谋杀案》于37届(2009年2月)香港艺术节首演,受到广泛好评。同年八月重演。此次是该剧第三度公演。《圣荷西谋杀案》写了两桩谋杀案:一桩发生在序幕,一桩发生在全剧末尾。戏剧叙述:崔巧玲、邓少昌因偷情事发失手杀死崔的前夫,从此邓少昌冒充崔的丈夫,两人隐居在圣荷西(S a n jose)人烟稀少的郊区,刻意回避与外人接触。有一天,崔巧玲儿时的女友、美丽、热情的Sammy(张咏儿)专程从香港来访。张咏儿的到来,不仅带来往昔的回忆与亲情,也成了点燃崔、邓两人深潜的矛盾的导火索。最后,为了“生存”,崔、邓两人再次狼狈为奸,杀死了已知内情的张咏儿。
张咏儿是一名为歌星演唱会伴舞的舞蹈员,因与老板有染,事发导致老板娘跳楼自杀。张咏儿其实是为了远离是非之地,才千里迢迢从香港来圣荷西投靠崔巧玲,不料却陷入另一个深渊。
戏是在传统的镜框式舞台演出的。编导者将剧情限制在一个写实的封闭空间中,演员表演也采用近乎自然的写实手法。除开首的命案(发生在序幕)和末尾的凶杀(发生在戏剧场景之外),全剧全无侦探片、惊悚片悬念、惊吓一类的踪影,只是一切都显得有些异样:张咏儿搭顺风车到崔巧玲家走错路、第一次进屋的张咏儿遗漏了一件行李、崔家仅有的一次聚
会却烫伤一位客人……
全剧发生在一间海外华人的居屋。这是他们的避难所,也是禁锢的牢笼。无论他们做什么、怎么做,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生存的残酷与荒诞,好像是一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或无从选择。这是一则漂流异国与城市异化、人性异化的故事。
上述两剧均属于比较传统的、比较严肃的作品,虽然也借重明星效应与市场操作,但与当前香港演艺市场中大量通俗、搞笑的演出不同。在编导者、演出者不动声色的演绎中,碰触的仍是离乡背井的精神危机与此地他乡的不安全感。
责任编辑:贾舒颖
林克欢:国家一级评论员、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