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运的武松
⊙ 文 / 李约热
李约热:一九六七年出生,广西都安县人。现供职于广西文学杂志社,系“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创作岗”团队成员。作品曾获《小说选刊》奖、《北京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出版小说集《涂满油漆的村庄》《火里的影子》《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李约热卷》,长篇小说《我是恶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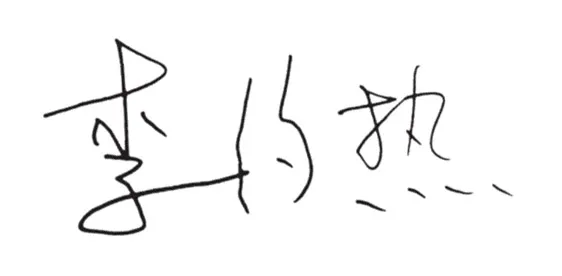
这些年来,我每隔三四十天就回一次老家,除了春节、清明节这两个传统的节日是回乡的“规定动作”外,我回乡的“自选动作”全是我哥给定的。
可以自豪地说,在往老家跑这件事上面,我比我的好兄弟黄骥强多了。
我和黄骥同一天进副刊部,他胖我瘦,他高我矮,我曾跟他开玩笑:黄骥,跟我走在一起,你的虚荣心是不是很容易得到满足?他笑呵呵地回答:这个城市治安不好,站在你身边,我像不像一个不离不弃,随时为你挡刀的保镖?除了长相比较“搭”,两人都不思进取,不喜欢咧着嘴对领导笑;喜欢夜酒,喜欢啤酒炒粉烤串,喜欢给各地不知道漂亮还是不漂亮的女作者打电话:你好,你这篇散文如果去掉一些形容词就更好了。……他娶护士,我娶医生,都是医院的家属,在这个城市,都有些人模狗样。一口气憋久一点,腰杆子绷直一点,猛一看就像“中产”。
对,我们是那种不禁看的“中产”。
看到我经常往老家跑,黄骥觉得不可思议:你也真是的,老往乡下跑,难受不难受啊,是想把你哥的土鸡土鸭吃完?你跟你哥哥,真的那么亲?
我说,真的那么亲。
我父母已经故去,俗话说“长兄为父”,我哥跟我说什么,就是我爸跟我说什么。
有一次,我哥说,弟啊,最近我老梦见妈妈,你回来吧,我们给她烧烧香。我把手中的香烟摁灭,出了办公室的门。感觉一缕烟雾还绕在唇边,而我的车已拐出《邕城日报》的大门。
妈妈的脸模糊不清。我三岁的时候妈妈没了,我只记得妈妈死后,我们几兄妹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天上打雷下雨,一道道闪电抽在我们身上。后来,我只记住闪电,妈妈的面孔记不住了。
关于妈妈的记忆,全在我哥那里保存。
我妈妈死在县城的医院里,那时候没通公路,没办法回乡安葬,就葬在县城附近的土岭上。
我们那个地方,一个人死了,要安葬两次。第一次是临时安葬;等肉身羽化,只剩下骨头,就把骨头洗净放到坛子里第二次安葬,算是永久性的安葬。也不能算永久性的安葬,如果谁家诸事不顺,会被认为是亲人在那边过得不好,那就要去“探坟”。所谓探坟就是去看亲人的骨头好不好,如果干燥、泛黄甚至发红,那就没事;如果潮湿、惨白或者发黑,那就得重新找地方第三次安葬。
我哥十五岁的时候,跟他的好朋友世荣去县城的土岭上,把我妈妈的骨头捡起来放到坛子里。当时我妈妈几乎是躺在水里,我哥哥一面哭一面拿酒精拭擦,在坟边生一盆火,把妈妈身上的水汽烤干,再小心翼翼地把她装在坛子里背回家第二次安葬。后来,他又怕我妈妈在那边过得不好,几年后又去探了一次,是最好的那一种,便从此心安。
因为妈妈过早去世,她成了我们几个孩子在人世间最大的牵挂和念想,想必妈妈也一样,她走的时候我们多小啊。
家里神台上常年香火不断,案前三个酒杯,第一杯酒给妈妈倒,第二杯给爸爸,第三杯给所有的祖宗。哥哥是那个守在家里的人,是经常在神台前倒三杯酒的人。所以他说,弟啊,最近我老梦见妈妈,你回来吧,我们给她烧烧香。我二话没说就回来了。
烧了香倒了酒,哥哥的一帮好朋友来到家中,其中就有世荣。他的脸已经皱了,越来越像树皮。当年他带我哥去县城旁边的土岭上捡我妈妈的骨骸,刚二十出头,我哥哭,他也跟着哭。我每次回家,哥哥都叫他来吃饭,他很少说话,默默地喝酒,他们说好笑的事情,他也不笑。他的酒量是越来越小了,一桌子的人,每人一瓶“丹泉米酒”,以前我回家,世荣还能喝一瓶,后来,一次比一次少,现在二两他就醉了。他不喜欢说话,什么时候醉根本看不出来,喝着喝着突然就歪倒在饭桌边,没有一次不被人抬回去。每次回乡跟哥哥的朋友们喝酒,世荣什么时候醉,是最大的悬念。我曾跟哥哥说,他每次都这样,那他不知道提前回去吗?非得每次都被人抬回去。哥哥说,他就喜欢这样,如果提前劝他走,他会有意见的。
看见我,世荣点头笑了笑,转身去帮我哥摆桌子,他手上得有活儿,这样在我家才显得从容。他独身,在街上做“花窗”卖,所谓花窗,就是水泥做的窗户,图案是万年青,我曾去看他做花窗,一个正方形的木框,镶上万年青的模子,然后拿水泥浆去填。他叼着一根烟,乜斜着眼,拿铲刀在模子里插、抹,漫不经心的样子。十分钟不到,一个花窗就做好了。他的师傅是他哥哥世新。世新脾气大,经常打弟弟,水泥浆灌少了,一个拳头就擂过来,有时躲得开,躲开了也没用,反正躲开了还有第二记;有时躲不开,打在胸脯上,世荣就拿手去揉,满脸都是委屈。世新烦心事太多,以前打弟弟是因为娶不上老婆,后来打弟弟是因为超生,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后他没有收手,谢天谢地,第三个是儿子。工作队怕他再生,要拿他去结扎,他害怕,心烦,所以经常打弟弟。后来世新去找卖草药的志宏,求吃了能让血压升高的药。真求到了。吃了几服药,血压就上去了,在我们那个地方,高血压根本就不是个病,但是工作队不敢不把高血压当病,他们叫世新躺在手术台上,一量血压,只好让他回家。工作队不甘心,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找上门来,带他去医院,每次量血压,医生都不敢动刀。世新为此得意了很久,经常拿来炫耀,说自己对付工作队有一套。
后来,他死于高血压引起的心梗。他老婆带两个女儿改嫁,儿子炳坤由世荣带着,现在已经长大。有一次炳坤半夜肚子疼,在地上打滚,世荣以为他家门口的那棵碗口粗的树冒犯了神灵,连夜叫我哥跟他一起砍树,我哥说先送炳坤去医院,然后再砍树。我嫂子和街上的几个女人负责送炳坤去医院,我哥和世荣负责砍树。天亮的时候,树砍倒了,炳坤依然在医院的床上哭爹叫娘。镇上的医生说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意思是赶紧回家给炳坤准备后事。世荣瘫在地上,脑子突然就错乱了,一下子哭一下子笑。我哥给我打电话,我说赶紧送炳坤来邕城,不要耽误了。街坊阿富开他的柳州五菱送炳坤来邕城,我哥和世荣跟着。医院床位紧,幸亏我是医院家属,炳坤一到医院就住进病房,就有好医生过来诊断。他很危险,得的是胰腺炎,幸亏送来及时,要不就没命了。世荣对我很感激,在酒桌上经常只说一句话,那就是,幸亏有小果,要不然炳坤就死了。
小果就是我。
一桌子的人吃饭,因为是我哥哥梦见我妈妈我才回来的,所以桌子上的话题就跟我妈妈有关,跟我家的事情有关。
他们问我,你还记得你妈妈的样子吗?
我说记不得了。这时候我心里马上掠过一道闪电。根据他们的话,我慢慢拼贴出关于我妈妈的一些事情。
枪一响,她就抱着你往后门跑。这是我哥说的。一九六七年,我出生的那一年,镇上武斗,经常有枪声响起。
我哥说,我们家以前没有后门,就是为了躲,才挖了一个后门。
我家的后门歪歪地开在靠山的那一面,那是一条逃生的通道,枪声一响,我妈就披头散发,疯了似的往后门跑。
她原始人一样。
她唱歌很好听,哄你睡觉时就哼歌。野马镇没有一个女人哄孩子睡觉时哼歌,都是拿鬼来吓小孩子睡觉。你妈妈真是太好了。在旁边看我们喝酒的八婶说。
她从来不跟街上的人红过一次脸,跟人讲话细声细气,怕惊着脚底下的蚂蚁。八婶说。八婶很夸张,她怎么知道人的声音能惊着地上的蚂蚁?
我已人到中年,我找不出我作为一个孩子缩在母亲怀里睡觉的感觉。更多的时候,我感觉我小时候缩在母亲怀里睡觉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了;更多的时候,一想起这个画面我身上就起一层鸡皮疙瘩。同时,我也想象不出我妈妈她哼歌的样子,她说话的样子。我对她一无所知。野马镇唯一一个唱歌给孩子听的女人,他们说得怎么具体,听起来好像说的不是我妈妈,说的是别人的妈妈。
你姐姐长得像她。八婶说。
我姐再怎么长得像我妈妈,我都不能把她往妈妈身上靠。妈妈就是妈妈,姐姐就是姐姐。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这样想:我是一个冰河里的孩子,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有哥哥姐姐。可他们也同样是冰河里的孩子啊。还有在座的很多人,包括世荣,他们都是冰河里的孩子。
他们说到我爸爸,他在外地工作,每个月寄十五元钱回家,我都已经长大他才回来。
……
他们更多的是说我哥哥,他们说他,了不起的一个男人,你们家的顶梁柱。没有他就没有你的今天。
我哥说,喝酒喝酒,废话少说。
后来我就喝醉了,我比世荣先醉,他还没倒在桌边,我就醉了。
为了给妈妈烧个香,每次我都回家,所以我比黄骥强。
这一次,我哥又叫我回家。这一次回家不是烧香,而是打架。
我哥不是武大郎,我也没有一个漂亮的、名叫潘金莲的嫂子,但是我哥把我当武松了。
我身体这么单薄他还把我当武松,估计是被逼急了。
我哥说,我被人欺负了。
我说,谁?
韦海。这回你要回来帮我打他。你行不行啊?他说。
韦海,他以前是我哥的好朋友。
我以为我哥喝多了,叫他慢慢跟我说,韦海是怎么样欺负他的。以前我回家,家里的饭局还有韦海,后来就没韦海了,有一次我问韦海怎么没来,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他果然跟我哥反目成仇了。
我哥没喝酒,他清醒得很,在他坑坑洼洼地叙述中,我理出了他要我回去揍韦海的原因。
韦海以前跟世荣一样,蔫,话少,每时每刻都像做错了什么事那样,不敢跟人对视。他做木工,手艺不错,我哥结婚用的柜子还是他打的呢,现在还在用。当然这是以前的事了。后来他去县城帮税务局的人事股长打家具,人事股长又推荐他帮税务局长打家具,局长见他手艺好,又老实,就留他在饭堂干活。勤快、老实、穷,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勤快、老实、穷,这还不足以打动局长,在局长周围,看起来勤快老实的人多了去了,谁真谁假局长根本懒得去判断。韦海之所以能在税务局立足,是他为局长立了大功。局长的爸爸患阿尔兹海默综合征,老是记不得回家的路,有一次走丢了,税务局的人以及局长的亲朋好友,几乎把县城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个遍,两天两夜都没有找到。局长高血压住进医院,所有的人都心灰意冷,私底下都认为凶多吉少,都希望出现奇迹。果然奇迹出现,第三天傍晚,韦海把局长的爸爸背了回来,那场面,简直是王者归来。这个韦海,别人找局长的爸爸是沿着大街小巷找,他呢,是去县城周边的山上一个岩洞一个岩洞找,这跟他是木匠有关系,在我们野马镇,他经常被请去山上看木头,哪棵木头能打什么样的家具,他心里清清楚楚,所谓的匠心独具,说的大概就是韦海那样的人吧。局长的爸爸失踪,很奇怪,他首先想到的是老人家会不会爬到哪个岩洞去了。他想跟别人说,但又怕万一不是在岩洞里找到,那样他们会小看他。他避开所有的人,踩着自行车一座山一座山转,一个岩洞一个岩洞找,终于在县城附近绿岑山的岩洞里找到已经两天没吃饭,饿得发抖的老人。局长问他爸爸,爸呀,你怎么跑到岩洞里去了?局长的爸爸说,我上楼梯、我上楼梯,我们家的楼梯好高啊。弄得大家都笑起来。这个山洞,别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后生仔爬上去都很费劲,局长的爸爸“上楼梯”也真算是件了不得的事情。更加了不得的是韦海,他立了一大功。从此,他成为局长家饭桌上最重要的陪客之一;从此,他的人生开始滋润:先是工人编制,然后是干部编制,局长全给他办了。后来,他坑坑洼洼地扯了张党校文凭,穿上制服,就收税去了。我记得当时回家时我哥还拿他来炫耀,他的好朋友中终于有人在衙门里耀武扬威了。
我哥说,这个野仔,他以前多穷啊,我们家的碗,都被他拿得脱了一层皮。
我哥的比喻很生动,没去县城之前,韦海经常来我家吃饭,他喜欢跟世荣坐在一起,两个人性格一样,酒量也一样。两个人的命不一样。
我哥说,以前裤子都可以换着穿,现在来收拾我。你说,他该不该打?
韦海收税,开始是在其他地方收,大概他沾染上吃、拿、卡、要的坏毛病,调到家乡野马镇之后,这种毛病毒瘾一样改不了了。凡是给他好处的,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凡是没给他好处的,他就往死里收。我哥开了个商店,仗着以前跟他是好朋友,什么好处都没给他不说,还经常喊他的小名,他以为韦海还是以前那个把我们家的碗拿得都脱了一层皮的人。他不知道韦海现在已经不跟我哥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吃饭了,跟他吃饭的人,都是派出所的人、工商所的人、医院的人。我哥曾在背后说他,如果日本鬼子还来,韦海肯定是第一个到街头给日本人带路的汉奸。我哥说这话是有原因的,在野马镇,干部是干部、平民是平民,两个阶层之间,很难喜欢上对方。韦海当干部后不理睬我哥这样的老朋友,就像宋朝时刚刚进宫的高俅不理睬以前的拜把子兄弟一样,他自然就被我哥当成叛徒来看。这话传到韦海耳朵里,他生气了。我哥好处没给他不说,还经常喊他的小名,还说他是汉奸。对待我哥,他开始铁面无私起来,我哥的税,他就往死里收。说往死里收也有点夸张,只不过一样的铺面,我哥的收得多,其他人收得少。我哥不交,他威胁我哥要叫执法队来拉我哥的东西。我哥以为他只是吓唬吓唬,不敢动真格的,没想到,韦海真的叫来税收执法队,把我哥的半车鞭炮,拉去当税了。
我哥说,拉去的鞭炮,他们几个人转身就给私分了,春节的时候,韦海家的鞭炮是镇上烧得最多的。他烧掉的鞭炮,全是我的,你说,他该不该打?
我哥埋怨我,当初让你去当领导秘书你不去,偏要进什么报社,如果当领导秘书,韦海敢欺负我吗?他敢上我们家的楼拉走我的鞭炮吗?
当初我在县里的广播电视局当记者,县府办想调我去给领导当秘书,我喜欢文学,有点清高,看不上那份工作,就没有去。后来《邕城日报》招聘记者编辑,我考上了,离开了县里,我哥还觉得我很牛逼,四处跟人炫耀。
在我哥不停地问我韦海该不该打的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一伙人在我哥楼上搬鞭炮的情形,以及他们转身就把我哥鞭炮分了的情形。这些乡村恶霸,现在欺负到我哥头上了。欺负到我哥头上,就是欺负到我头上。
我的血往头上涌。我扔掉手中的香烟,走出了办公室。我要马上回乡下,我要替我哥出一口恶气。
还在正月里头,天上飘着细雨,楼道里的人没精打采。没听到这个消息之前,我也跟他们一样,整个人懒懒散散。很多天一直都在饭局里泡,脑子花里胡哨。现在,坏消息给了我一记耳光。我因为搬家,在新房子里过春节,没有回乡下,所以不知道我哥被韦海欺负的事情,我哥之所以没在节前告诉我这件事是想让我先过好春节。可以想象,他的这个春节过得多么的窝囊。
我非常难过。
高高大大的黄骥迎面走来,他的手里提着一袋龙眼,龙眼应该是夏天才成熟,现在有了大棚技术,春天就可以吃到龙眼、西瓜、梨。他发现我不对劲,问我,你怎么啦?脸色很难看。
我哥被人欺负了,我要回去打架。我说。
一个中年人口中说出打架这两个字,效果就像赵本山念政府工作报告一样。尽管这个时候我胸中有一团怒火。
果然,黄骥笑了起来。
打架,可是需要本钱的哦。他说。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我突然觉得灰溜溜的,好像韦海带人当着我的面抄我的家而我无能为力恰巧又被黄骥看见一样。我不满意地瞟了他一眼。我上一次打架还是在广播电视局当记者的时候,在夜宵摊,县城街上的一个小混混儿欺负我们单位的摄像记者,我当场敲烂一个啤酒瓶,抵住他的喉咙。
一晃二十年了,我打起精神,怒火像头怪兽一样又驻扎在心里。
黄骥高大的身躯挡在我前面,我说,闪开!
他闪开,我气呼呼地走着,感觉后面跟着一个人,没等我扭头,黄骥在我身后说,打架,我跟你去。
真是我的好兄弟,关键时刻站了出来。要知道,他很少回老家,他父母双全,如果他想他们了,就叫他弟弟把父母带到邕城住几天。我曾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去,他说,有事情才回去,没事情回去简直就是扰民。他说他一回家,爸妈就紧张,生怕他吃不好睡不好,问这问那,把他当成远方来的客人,每一次返城,他妈妈都哭。这我理解,黄骥少小离家,爸妈已不习惯有他在身边,他一回去,就是件大事,搞得全家很紧张。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弟他妹过得不好,过去他一直没少支援他们,建房啊、侄儿外甥读书啊之类需要用钱的事情,他一直都不含糊。但是后来他媳妇小苏慢慢地就不高兴了。他曾经跟我说,回去也不能帮他们做些什么,索性不回去,没脸回去。这个高大的男人说这话时眼含泪光,可以看出他和他弟弟妹妹的感情也非同一般。
他说打架我跟你去,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有他在,我的底气和信心一下子爆棚。我也不跟他客气,直接就说好。他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他提着那袋反季节龙眼,上了我的车。我一踩油门,车子就拐出《邕城日报》的大门。我火气大得很,车开得飞快,一面跟黄骥说韦海是谁谁谁,他先前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为了跟黄骥说明,韦海是一个值得我们走一百九十五公里高速,再走五十公里机耕路去痛打的一个坏蛋。为此,出城的时候我闯了一个红灯,黄骥也不劝我,任由我左冲右突。出城需要半个小时,我滔滔不绝地说了半个小时,说到我妈死得早,全是我哥把我带大,我们家怎么怎么样……我都说不下去了。
黄骥接过我的话,他说,这种人你还真不能跟他讲道理,这种人就该用最原始的方式收拾。小果,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就他妈为民除害的感觉,我感觉自己特别悲壮,我发现自己终于能为这个社会做点好事了,你知道吗?
黄骥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为民除害的程度,让我始料未及。开始我以为他这么说是要我打消欠他人情的顾虑,毕竟,帮人打架跟欠人钱不一样。后来觉得不是这样,我感觉他一下子亢奋起来了,听口气就像是感谢我给他找了一个当义工证明自己还有爱心的机会。
黄骥说,我都觉得自己过得太窝囊了,行尸走肉。现在,我觉得我还有一点点的用处。
他说的用处就是跟我回乡揍韦海。黄骥以前写诗,他有那种很浓重的自我批判情结,经常在自己的诗歌里批判自己,后来不怎么批判了,就改写情诗。他跟我说他自己过得很窝囊,让我感觉以前那个喜欢批判自己的黄骥又回来了。
我跟他两个人经常喝夜酒,有时候,两个人一晚上都不说一句话,啤酒的泡沫在杯中破灭,疲惫的身体在夜色中暗淡。喝完夜酒各回各家。有时候也聊天,聊什么呢?聊我们报社的种种不堪。聊媒体上的“软暴力”(在这个方面,电视台尤其严重,有一次在电视上,一位出镜记者在介绍一起车祸,她把车祸遇难的人比喻成“夹心饼”,看到这里我非常的愤怒)。聊我们未来的老年生活:黄骥说,如果能活到七十以上,假如到了需要人照顾才能吃喝拉撒的地步,那好,绝不麻烦儿女亲朋,马上启动“自动销毁程序”,就像一些机密档案馆里安装有自动销毁装置那样。跟黄骥不同的是,当我们谈论社会上的种种不堪的时候,我慷慨激昂,就像说别人家的事,而黄骥呢,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垂头丧气,“恨不抗日死”。他比我有情怀。更多的时候,我们混在一群文人中间,感觉是在一个被抽空空气的容器里,吹牛聊天,兴奋得面孔变形。是的,一个大大的被抽空空气的容器,是文人的主场,也是一个时代的夜场。
黄骥说,我们这个群体,是这个社会最没有用的群体,最没有活力,最没有创造力,最他妈势利、最他妈委曲求全的一个群体。
黄骥说的“这个群体”我知道是指什么。这个群体,就是像我和他那样的人。
黄骥这样说之后,我觉得这一场架非同小可,是关系到光明能否战胜黑暗,正义能否战胜邪恶的大事,是挽回“一个群体”岌岌可危的声誉的大事。是证明我们“还有一点点用处的”的事情。我受黄骥的情绪所影响,此时也感到悲壮起来,高速公路的风景飞快地往后退,我的车现在是一架出征的战车。我和黄骥,这次不单单收拾欺负我哥的西门庆,连危害乡里的蒋门神也顺带一起收拾。今天,西门庆和蒋门神是同一个人。
黄骥说,勇气比才气更重要,当时代需要文人的才气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弱,但是当时代需要我们的勇气的时候,我们人在哪儿呢?
黄骥说,我们缺勇气,为什么这样,除了贪生怕死,人世间太多的诱惑消磨了我们的斗志。当然,这也不能怪我们,人各有志,比如说革命,革命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多数人都是向往富贵温柔乡……小果我跟你说,我他妈就想当少数。
我说,你是少数,那我至少也是觉悟者吧。
黄骥说,你不算很纯粹的觉悟者。
为什么我不算?

⊙侯立远·江净舟静
本期插图作者 / 侯立远:一九六八年出生于浙江乐清,早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现为《求是·红旗文摘》艺术顾问。作品发表于《美术》《新美术》《美术报》等百余种专业刊物。画作被BIG SHOT、GESHAN、美国彼岸艺术学会、中国保利艺术博物馆、刘海栗美术馆、浙江博物馆、台湾国父纪念馆等艺术机构收藏和推广。
黄骥说,你是为了你哥,如果你哥没被人欺负,你会觉悟吗?
也对,如果我哥不被人欺负,我干吗觉悟啊,吃饱了撑的。
我说不会,我还是向往温柔富贵乡。
黄骥说,我早看出来了小果,你也没什么错。对了小果,我告诉你,今天真出了什么事都跟你无关啊,我只不过搭了你的便车。我现在马上写一份声明。
黄骥从包里掏出纸和笔,哗哗写了起来。
黄骥说,我的声明很短,只有一句话:黄骥打人和任何人无关。小果,到时候你告诉我谁是韦海,就行了。
他这么一说,我开始担心。我担心我控制不了黄骥,我原来的意思是回去揍一顿韦海,既帮我哥出口气,又可以显示文人的血性,仅此而已,最多被拘留十五天。而现在黄骥把自己当革命者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偏离我的初衷。特别是他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这就更加不简单了。我知道黄骥,关键时刻他是豁得出去。我怕他跑到野马镇,一面打韦海,一面高呼打倒土豪劣绅,那事情就闹大了。黄骥啊黄骥,他大概写情诗也写烦了,今天这件事情,突然就点燃了他胸中的野火。
黄骥,你不能那样,我现在后悔把你带回去了。我说。
哈哈哈哈,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到前面服务区,你可以放我下去,你不带我去,我不会自己找车去吗。黄骥说。
他这么一说,我就更加害怕了。不行,我得阻止他。我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对韦海的愤怒,变成怎么阻止黄骥前往野马镇。
我想了几种办法都觉得不好,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我提前下高速,沿着一条不知名的二级路走了一段,然后又拐上一条机耕路,让黄骥觉得,我正在把他带回野马镇……
一直折腾到天黑,我才对黄骥说,黄骥,我们迷路了。
……
野马镇这边,我哥准备了一桌菜等我,菜都热了好几回我都还没到,期间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没打通,当时我正带着黄骥,在不知名的机耕路上颠簸。我哥非常失望,招呼几个朋友吃饭,一面吃一面骂我,劝都劝不住。
那天夜里,十点多钟的光景,韦海就被人捅了,捅他的人是世荣。世荣体力不支,打不过早已肥头大耳,一身横肉的韦海。他拿着做花窗用的铲刀,一捅就捅破了韦海的肚子。
在这之前,他去找他的侄儿炳坤,他要炳坤去教训韦海,替我哥出一口气,炳坤不敢,他就自己动手了。他动手的时候,我的车正陷在泥坑里,等待过路车辆的救援……
后来,世荣被判十年,我和黄骥去看他,他苦笑着看我们,什么话也不说。
黄骥的妻子小苏有一天对我和黄骥说,好险哪,你和黄骥真幸运啊。黄骥说,闭嘴,我欠了人一笔大大的人情。小苏说,凭什么你欠啊,要欠也是小果欠。小苏当着我的面对黄骥说,以后你少跟小果来往,他是个危险分子。黄骥没有听老婆的,我们依然经常在一起啤酒炒粉烤串。我们很多时候不说话,啤酒的泡沫在杯中破灭,两具身体在夜色中暗淡。
后来,韦海伤好后被调往县城,不敢再收税,专门管饭堂。
后来,我哥不再叫我回乡,我主动回去,他对我也非常的冷淡,好像我不是他的亲弟弟。
一直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