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忘记了,从哪儿得到了这样的启示,这个启示像一颗青稞的种子,在我脑海里顽强地生长起来,我被它诱惑着,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压抑着这个启示带来的热情,然而,就在我遇见神女的那个晚上,那种热情像是压力超标的锅炉蒸汽,终于不可遏制地冒了出来。
神女的大名我早听说过,一般来说,她是一个诗人,虽然她的诗我从没看过,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我心目中的诗人形象。不过,意想不到的是,那个晚上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却告诉我,她是个画家,喜欢画油画,她家已经差不多是个专业的画室了。这让我很迷惑,我想追问一下,却及时刹车了,因为我们并不熟悉。我沉默了,保持着礼节性的微笑。
沉默令人痛苦。神女大名鼎鼎,自然身边不乏谄媚者,其实我也渴望成为那样的谄媚者,但遗憾的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在关键时刻我怕自己会变得张口结舌、毫无乐趣,因此,我蛰伏在人群的一角,暗暗关注着神女,等待着突如其来的机会。
那天吃完晚饭已经很晚了,但大家热情不减,面对着残羹冷炙还喝了许多酒下肚,直到饭店打烊,我们才被迫离开了战场,八九个人在大街上像酒鬼一样晃荡了很久。然后有人提议去唱卡拉OK,大家纷纷叫好,好像第一次知道有此等好事。
大家保持着伪装出来的热情向KTV走去,但是在半路上,出现了状况。神女站住了,她转头对大家说:“我就想在这里唱歌!”
说着,她便坐下来了,她的身后便是经过园丁定期打理过的城市绿化带。这一刻,我的心情是兴奋和复杂的,因为这落实了我对她的判断——她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画家,画家中自然也不乏自由率性之人,但这种情怀是属于诗人的……至于说复杂,是因为我隐隐预感到有机会了,却还不知道这种机会的踪迹在哪里,又如何去把握。
“好啊,”我当机立断,也站住了,看着神女大声说,“这个提议太棒了,我非常赞同,太有创意了!”
她看了我一眼,很高兴有人响应她,让她对自己的影响力有了一个确证。这时候人群开始骚动,看来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率性而为,因为他们都不是神女这样的诗人。挣扎、辩论与协商的结果是,队伍分裂了,一部分继续向KTV进发;另一部分人和我一样,选择了和神女待在一起,留在街边当流浪的吉卜赛人,为这个城市守夜。尽管,留下来的人不少,但毕竟比刚才少多了,我数了一下,正好有五个人。
我紧挨着神女坐下来了,神女望着我露出调皮的笑容,她不但美丽还有种激情。我知道她是在鼓励我,我的胆子略略放大了些。我对她笑着说:“你再怎么伪装,诗人的本质还是露出来了。”她捋捋头发,笑着,不置可否,突然对我说:“可惜这里没有酒,有酒的话就完美了,比KTV完美多了。”这话对我宛如懿旨,我马上义无反顾地说:“这有什么?我马上就去买。”她撩了撩头发说:“你一个人行不行?”我壮着胆子说:“也许需要你的帮忙,要不我们一起去吧?”她吐了吐舌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走!”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有些张皇失措。
有人问:“你们去哪儿?”神女头也不回地说:“都不许走,等着!”
我们走了几条街,才找到了一家快要关门的士多店,一路上我们所说的话并不多,都集中在如何才能买到酒这个话题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尴尬导致的结果,我显得有些没话找话。她倒是一如既往的态度,率性地走在黑暗的街道上,一辆又一辆车稀稀拉拉地驶过,车灯一次次照亮了她,让她周身长满了光的绒毛。
她要了一箱啤酒,我抢着付好账,然后抬起箱子就往回走。神女跑到我前面,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两瓶啤酒来拎在手中,一手一瓶,我们对视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鼓足勇气,我又说:“你真的画画儿吗?我非常好奇,很想看看。”她挥舞着酒瓶说:“好的,没问题,以后有机会一定让你见识下,到时你别害怕就好。”“害怕?为什么呢?”我诧异了。她说:“反正你到时见了就知道了。”她的自信让我暗自歆羡,她是一朵跳动的火苗,走到哪里,夜色就在哪里被劈开。
那帮人看到我们回来,欢呼了起来。神女负责分发啤酒,把这种绿色的玻璃炮弹递给每个人。
神女举起瓶子,有点儿凶猛地喝了几大口,然后她提议大家讲故事,每个人都讲讲自己生命中的一个故事。这样的游戏形式的确很老套,但不管神女说什么,我都会第一个响应,而且发自内心。在座的五个人,除去我和神女,还有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很文静,一点儿也不像神女这样飞扬跋扈,因此她得到了另外两位哥们儿的格外关照。
“要讲生命的故事?从谁开始?要不神女你先来吧!”大家听了她的提议,面露难色,尽管有夜色的掩护,隐私还是像缩头乌龟,畏首畏尾的。
神女的魅力就体现在这样的时刻,她坦率自然,一点儿都不像要刻意表现自己,她说:“好吧,我先说。”
她喝了一大口啤酒,静静呆想了一会儿,说:“我生命中最核心的故事全部和一个人的死有关。”
那是四年前,神女怀孕了,当然,那时候她还没离婚,有个完整的家庭。那是她幸福的年头,她是一个好妈妈,而不再是一个好诗人。本来,这样过下去也是非常幸福的,但是有一天,她在下楼梯的时候,突然感到下腹一阵绞痛,她靠着墙,打电话给120,等到她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没了。据说那是个男孩,只要再等上一个月就有活下来的可能。神女的男人——一个在政府工作的公务员,匆匆赶到的时候,也没看到那个孩子,他被医院以最快的速度处理掉了。男人尽管只是个小职员,但所在的部门不错,收入还是比较高的,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保障,但同时,男人的情怀也是小职员式的。他不能面对和接受这样的情况,他觉得自己各方面做得都接近完美了,但是孩子却说没就没了,而且还找不到什么原因——只不过是下楼梯嘛,怎么下楼梯也会流产呢?这个问题极大地困惑着男人。男人和医院的医生护士们较上劲了,非要问个一清二楚,他的头发几天没洗,变得油腻腻的,粘在额头上,任凭他的叫喊却纹丝不动,这让他的歇斯底里显得有些空洞。医生耐心地解答着他的困惑,告诉他这种事情是说不好的,各种因素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况且,大人也没事,休整几个月后就能重新要孩子了。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不知道,下次极有可能重蹈覆辙啊,这次我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男人不依不饶地追问着,他十足的认真中蕴含着一股按捺不住的急切。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尽善尽美的事情,尤其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身体尤其如此。”医生说。
“这个,我当然明白,但是,凡事都有因有果,即使没有直接的原因,也会有间接的原因吧?间接的原因你也得告诉我啊。”一种绝望感从男人的胸间涌起,他看起来变得可怜兮兮的了。
“间接原因太多了,真的太多了,也许没休息好什么的,都有可能。”
“不可能!我问过她了,她说她休息得很好,这个,其实不用问她我也是知道的,因为我晚上被她的呼噜声吵醒了,早上我起床去上班的时候,她还在继续睡觉呢!”
“所以说嘛,间接原因太多了!没休息好只是其中的一种假设……”医生越来越无奈,在男人穷凶极恶的追问下,他支支吾吾的态度反倒显得是在刻意遮掩什么似的。
神女看着这一幕,她的心情是复杂的,刚开始她也很想知道原因究竟何在。一个诞生于自己内部的生命就这样去了,总是需要一种解释的,没有解释,她的心是非常不安的。她一想到那个小身体待在带血的纱布与破碎的药瓶当中,她就感到自己要疯掉了,她有种强烈的负罪感,仿佛是自己没有照顾好他,是自己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但是,男人歇斯底里的质问看起来很傻,医生的为难也反映了这个世界在某种本质上的缺失。她边看边想,就像是看着一部电影,终于,她想到也许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也许不是所有的答案都是真实和存在的,答案也许可以是一句诗、一个词,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什么东西。想到这里的时候,她突然间就脱口而出:“重力!”
男人和医生回过头来不解地看着她。
她眨巴了几下好看的眼睛,面无表情地说:“都是因为重力。”
这句话让医生惊愕的脸部肌肉逐渐松弛了下来,他推了推沉重的黑框眼镜,喜笑颜开地说:“是的,是的,没错,是因为重力,无处不在的重力,导致了这次的不幸。”
“重力?” 男人的脸上浮现出一层雾样的困惑。
“是的,重力!”神女和医生异口同声道。
男人走到病床边的椅子前坐了下去,陷入了某种沉思的状态。医生不失时机地跟过来,说:“你看,连你这样的正常人站久了都会觉得累,都要被重力拉扯着坐下来,那么女人的腹部要承受多大的力你知道吗?一不留神,孩子就会被重力给拉扯出来了。”
“胡扯!”男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神女叹口气,对男人说:“你不觉得重力是最好的答案吗?只有它才可以解释这一切的悲剧。”
男人抬起头,看看神女,不再说话。
他们出院了,回到家门口的时候,男人盯着楼梯使劲看,说:“难道真的是重力?楼梯放大了重力的作用……”神女没有理会,任他自言自语。从此,他们的生活中有了一个缺席却存在的人,这个人不受重力的作用,从天上俯视着他们,令他们越来越难以忍受。每次下楼梯的时候,男人都会不自觉地叹口气,嘴里吐出一个词:“重力。”神女也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踩在楼梯上,每下一级台阶都变得举步维艰、如履薄冰。久而久之,神女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滑坡,她和男人的生活在滑坡上没有任何羁绊,因此,那种生活便像小孩坐在滑梯上一样,滑了下来。也许,这又是重力的作用。等到这种生活滑到底端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离婚了。
重力是个完美的答案。
这件事情之后,神女就很少写诗了,她开始以画家自居,尽管见过她的画儿的人少之又少。但因为她的坚持,很多人开始迷惑了,进而,一些人就把她当作画家了,一个传说中的神秘画家。
神女的故事讲完了,大家鼓掌,有人吹起口哨,有人举起瓶子在空中碰碰,喝了起来。他们和我一样,摇晃着醉醺醺的脑袋,沉浸在对重力的想象之中。在我看来,重力是对生活的一种提醒,一种客观存在却无法理解的事物,我们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同时,我也感慨神女不愧是优秀的诗人,竟然有着这么锋利的思想直觉,她愈加吸引我了。
但是,别人也许不会想这么多,我看到那两个哥们儿在感慨一番后,便继续和文静女孩搭讪了。神女喝了很多酒,瞥了他们一眼,扭头对我说:“你不是老问我是个诗人还是个画家吗?现在你都清楚了吧?”
我说:“清楚了。”
“那我到底是诗人还是画家呢?”
“都不是,你是小说家。”
我的话让我们哈哈大笑了起来,她说:“才不是呢,我不擅长虚构的,我说的都是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实的,那么我还是得承认你是个诗人,因为你对生活的理解落脚在一些细节与意象上面。”
“就意象这点而言,我想你说得还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变成了画家,画家不表现意象,而是直接创造意象。”
我被她的话所折服,我说:“你越这样说,越勾起我的好奇心,我一定得看看你的画儿才行。”
她突然趴在我的耳边说:“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我扭头看到了她闪动着光彩的眼神,我抑制不住地笑着、点着头,没想到奇迹这么快就发生了。不过,我不知道该如何摆脱其他的三位朋友,尽管他们现在没有关注我们,但我们的离开对他们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事情。缺少了人群的遮掩,他们三个人或许会变得尴尬起来的。
神女比我聪明多了,她站起身来四处张望着。她的张望引起了另外三人的注意,他们问她要干什么,她说她想去厕所,有点儿怕,然后她就叫我的名字,叫我陪她去。我像个士兵听到命令一般,坚定地尾随在她的身后,向着某个莫须有的厕所走去。
等我们拐过街角,神女就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她说了一个地方,我们便向那里驶去。我再次陷入了沉默,假如说之前我的聒噪只是为了引起神女的注意,那么现在我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她不但注意到了我,而且还和我组成了一个新的队伍,一同行进在夜色的战场上。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下车,进小区,上楼,我想象着神女每天的路径、每天的心情,我觉得离她近了,走近一个人,就要走近她的全部岁月。来到她的门前,她开门邀请我进去。我有些紧张,站在门口准备换鞋,可她一把把我拽了进去,说:“不用那么麻烦,我这里崇尚自然,你就随遇而安吧。”我惊魂未定,却已看到了四面墙上的画儿,还有面前的落地窗,窗外灯火辉煌的城市夜景衬托着一个很大的画架,上面有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儿,但我一时还看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待我走近细看,初以为是满天的太阳,后来才惊觉这是向日葵,长在天空中的黄金般的向日葵。
“你的向日葵怎么长在天上?”
“因为它们不受重力的作用。”
我笑了起来,看到画儿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每当我们看见不可描绘的形象和无以言表的凄凉,万物的终结和极致,上帝就进入了一个人的心灵。
“这是你写的吗?”
“不是。”
“能告诉我……”
“文森特·梵高。”
对,梵高,怎么可能不是梵高呢?那些怒放的向日葵,那些在天上舞蹈的黄金。我深爱梵高的画,在我心情最阴霾的时候,是梵高的画儿给了我力量。那个赤贫的画家都有如此旺盛的生命与顽强的希冀,何况我呢?
“看来你也喜欢梵高……”我喃喃说道。
神女说:“我怎么会不喜欢呢?他太明亮了,他能搅动一切。”我心弦一颤,知音的感觉吧。我们靠在她的大画架前,面对面看着彼此。我们还是第一次这样对视,她的美有些刺目,就像向日葵。突然,她抱住我,哭了起来。
我有些不知所措,有些紧张,在她耳边问:“怎么了?告诉我好吗?”

■美术作品:卢西恩·弗洛伊德
她不说话,只是哭着,我想,也许她只是想哭了,需要一个人安慰,我便抱紧她,一动不动,她的身子抖动着,像只假寐的猫咪。难以相信的是,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她的哭泣有种强大的蛊惑力量,让我生命中的破碎翻腾而起,化为泪水,在夜色中静静流淌。很久了,我都忘记了这样的滋味,而这样的滋味让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我们哭了很久,我觉得我的心脏开始隐隐作痛了,便拍拍她的背,说:“我们不哭了。”
她伸出一只手在我前胸摩挲着,她说:“疼了吧?”
“是的。”我很奇怪她怎么会知道。
“因为太多碎片,所以我知道。”神女抬起泪眼望着我,我又流泪了,不过只是因为这一瞬她太美了,令人心碎。
哭过之后,我感到自己虚弱极了,然而同时也宁静极了,从没有过这样的宁静。此时再看那浮在天上的向日葵,我感到了一种冷冰冰的燃烧,一种没有灰烬的安静的燃烧。
“你看看我画的其他画儿吧。”她擦擦眼角,笑了,像个孩子。
“好啊,我喜欢你种在天空中的向日葵。”
她把满屋子的灯都打开了,四面墙上挂满了她的画儿,那些画儿的颜色都非常绚烂,尽管形态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倒立。就像是那天上的向日葵一般,不过因为向日葵的对称性,倒立表现得并不明显。而现在,我面前画儿里的这把椅子就非常惹眼了,就像是倒立过来看椅子一般,椅子是悬挂在天花板上的。
“都是源自你的反重力情结?”我笑着问。
“是的,重力是我的悲伤之源。”
“今晚遇见你,激发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灵感。”我觉得到了必须要说出那个灵感的地步了,而且,我觉得恰到时机。
“什么灵感?”神女有些好奇了。
“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
“好的。”
我们俩并排坐在地板上,像两个精疲力竭的装修工人。我看着周围这些倒立过来的画面,有种超现实的感觉,这种感觉令我迷醉。我说:“我小时候,每次和小朋友要告别的时候,总是舍不得,然后我们走几步,就会俯下身子,从裤裆下的那个三角形里倒看这个世界。在裤裆里和对方招手作别,没有人能对裤裆下的笑脸无动于衷的,那一瞬间真的令人开心,那种开心遮盖了离别的伤心……啊,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离别的伤心是最噬心的痛苦。”
“离别的伤心……”神女喃喃道。
“是的,万事万物最终都免不了离别,因为变化是如此的永恒,腐蚀着我们对永恒的渴望。”说完后,我觉得自己突然变成诗人了,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兀自笑了笑。
神女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说:“你的故事讲完了吗?”
“哦,还没有,不过这个故事的跨度很大。自从我迷恋倒着从裤裆里告别后,我就注意上了一种动物,那就是蝙蝠。这种古怪的玩意儿白天从不出现,隐藏在阴暗的洞穴里,倒挂在一些石缝底下睡觉,这让我非常迷惑……你说它们为什么会倒挂着呢?”
“嘿,你还别说,我真不知道,这个现象和重力的关系太密切啦!”神女兴奋了起来,呵呵笑着,她心中柔软的部分正在显露出来。
“说真的,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基本上贯穿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候没有网络,知识的来源非常单一,我就去问我的自然课老师,她说蝙蝠倒挂睡觉是最安全的了,不怕别的动物袭击它。”
“这的确算一种解释。”
“是的,但我并不满足,我跑去图书馆查资料。我都忘了自己看了些什么书籍,反正我知道了蝙蝠的腿是毫无力气的,甚至连走路都举步维艰,更别说像鸟类一样靠着腿部蹬力腾空而起。没有最初的一跃,是不可能飞起来的。因此蝙蝠便倒挂在树上,待它想飞的时候,一撒手就可以了,重力变成了它的动力……”
“这个解释不错,蝙蝠真聪明,懂得利用重力,我们的逆境是它的顺境。”神女若有所思,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是又拓展了她对重力的思考。
“蝙蝠肯定会喜欢你这些画儿的。”我看着她这些倒置的画儿哈哈大笑了起来,觉得它们好像是专门为蝙蝠而画的。
神女笑了笑,说:“你看到我的画儿,就应该明白我很想像蝙蝠那样活着。我做梦都梦见我是倒置的,我站在天花板上,那些家具向我的头顶拥来,我害怕极了,不过同时,我也觉得有趣极了。”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我的灵感便是——”我卖个关子,停住了。
“你快说啊!”
“倒立着生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方式,你想想看,你如果倒立着生活,孩子就不会掉出来了。”我半开玩笑半真诚地说道。
“是的,绝对是的!”没想到她认真了,沉浸在一种追忆带来的想象情景当中。她的样子令我伤心,我知道她的心情,一种迷惘与失落折磨着我。我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动作,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我伸出右手,放在了她的下腹,静静停在那里,似乎在召唤着什么意想不到的事物。她明白了我的意思,脸埋进了我的颈窝,悄无声息地哭着。神女的确是我梦寐以求的伴侣,我想和她生活在一起。我愿意分担她小腹传来的无尽虚空,只要她愿意,她愿意就好。
更晚的晚上,我住在了神女那里。她让我睡在客厅,她睡在卧室,我们之间的门开着,我抬头便可以看到她。她说能这样彼此看着就很好了,就能慰藉彼此的孤独了。我躺在长满天空的向日葵下面,抬头望望神女蜷缩在被窝里的身影,心里暖暖的。她说得对,这样的感觉太微妙了,强大地慰藉了我的孤独,我的早已结冰的孤独。
第二天,我们哪里也没去,就待在她的家兼画室里。我以为我们早上起来,看到彼此惺忪的睡眼会感到尴尬,但是没有,因为我早上醒来的时候,神女就睡在我的身边,像个小猫似的蜷缩成一小团,脸埋进被子里,发出均匀的呼吸。我抱紧她,几分钟后,她醒来了,冲着我笑,我说:“你装睡的吧?”她伸了个懒腰说:“你才装呢,哈哈。我是今早才来的,你正跟野猪一样打着呼噜呢!”
我们同居了,这场同居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我自从那天去她家后,就再也没出过门了。原本我干着的工作就是可有可无的,待遇相当可怜,神女知道后便劝我不要上班了,我也乐意从命。我们将身上全部的现金拿出来,居然还有千把块钱,足够我们在房间里好好住上一阵子了。
“让你住下来可是有目的的,”神女说,“你可知道原因吗?”
我挠挠脑袋,说:“总感到和重力有什么关系,你和重力较上劲了。”
“算你聪明!”她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我趔趄了一下,怀疑她的身体里是不是居住着一个男人。
她从床底下搬出一个墨绿色的工具箱,打开后,我看到了眼花缭乱的各种装修工具。她抚摸着一把榔头说:“我当初就是被他的勤劳给迷住了,我觉得这样的好男人简直绝种了。你想象不到,每逢周末,他就搬出这个工具箱,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家居,当然,我有什么要求,他也会尽力满足。”
我想象着一个中规中矩的男人,穿着旧衣服,手持工具,穿行在自己的房间里。是的,我甚至还有点儿羡慕他的感觉,因为,他像是这片小天地的王者。
“你怎么放过了这样的男人?”我低声说,若无其事的样子。
“因为他是个一定要掌控秩序的人、对细节一丝不苟的人,你知道,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没有了可能性,死亡便提早莅临了。”她抚摸着金黄色的门把手,我想,那一定是她那位一丝不苟先生安装上去的,看起来很好用。但是很遗憾,“很好用”在感情关系当中似乎并不好用。
“你现在要我怎么做?不会想让我创造一个新秩序吧?”我看到榔头的反光,在室内显得很刺目,而且危险。
“我的本意是毁灭一种本质的秩序,但是反过来说似乎也可以,也是一种建造吧。”她站在画架前,只穿着黑色的文胸和黑色的底裤,显得像是若干年后和我熟悉到脚趾缝的妻子,她指着天花板说:“我要你把上面变成下面,我们要倒立着生活了。”
我笑了起来,我知道她会这么干的,只不过没想到她如此的迫不及待。她一个箭步跳到我面前,抱住我,开始撒娇了,她说:“快点儿行动吧,我真的是迫不及待了。”
“好的,知道了,诗人同志!”我抚摸着她瓷器一般光洁的后背。
我脱掉衬衣,光着膀子行动起来了。我不知道我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唤醒神女对她前夫的怀念,我只知道自己被一种奇怪的想法所驱使,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神女的奇思妙想,同时,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一直暗暗有种期待,觉得也许倒立着生活就能挽回我破败的生活,就像当年从裤裆里告别伙伴一样,一切都变得那么荒诞和滑稽、一切都令人发笑,欢乐最终取代了悲伤,生活就改变了……是的,生活说到底不就是一种情绪嘛,对个人来说,情绪就是生活的本质。
这个工具箱太强大了,里面居然应有尽有。我用螺丝和铁片将一个椅子倒置在天花板上了,看上去诡异极了,就像神女的画儿变成了现实。神女的脸上荡漾着难以描述的微笑,像是嘲弄,又像是欣赏。她站在一把椅子上,伸出手臂抓住了头顶上那把椅子的椅背,狠狠往下拽了拽,结果那椅子纹丝不动。她大声惊叫道:“真的这么结实啊?”我仰视着她细长的双腿说:“那当然啊,你坐上去都没问题的。”她鼓掌大笑说:“太棒了,你加油啊,等你把主要的家具都倒置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住上去啦!”我摩拳擦掌道:“行,没问题,你就等着吧!”
有了安装第一把椅子的经验,接下来的工作变得简单了。神女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的力气真大,我再次怀疑她身体里居住着一个男人。她能一个人扛起桌子,让我可以心无旁骛地上紧螺丝。不过,她的力气之大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那是在安装好桌子、柜子之后,我说:“现在只剩下床了,只要装好床,一切就搞定了。”她面不改色地说:“那就装啊。”我站在高处,俯视着她,无奈地说:“我倒是想马上就动工,但床实在太大了,我想打电话找个朋友来帮忙。”她显出吃惊的样子,说:“什么?还要找人帮忙?不需要的,我可以的。”我的嘴巴张得大大的,说:“你真的可以?”她使劲点着头:“真的,可以,没问题。”
她认真的样子让人不容置疑,我无法抗拒,便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开始装床。”说完,我看着她,有点儿置身事外的意思,成心想看她的笑话。她似乎没觉察到我那点儿玩笑式的恶意,走到床边,把床垫卸了下来,然后把床板也卸了下来,现在就剩下一个骨架样的床架了,不过那玩意儿也够重的了,我看她怎么办。她迈步站在床架的中间,慢慢抬起床架的一侧,将床架翻转了过来,然后她站立了一会儿,深深呼吸着,突然,她伸手握住床架中间的横梁,大喊一声,竟然将床架举了起来。她抬脚站在了凳子上,让床脚顶在了天花板上,她闭着眼睛,声音颤抖地对我说:“好了,快点儿上垫片和螺丝!”我这才慌乱了起来,太可怕了,我紧张得双手颤抖,赶紧工作了起来,面对这个奇迹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感慨了。
神女一直坚持到最后,直到我上完最后一根螺丝钉,她还保持着举重冠军的标准姿势。我说:“好了!”她这才睁开眼睛,惊恐地望着上方,然后缓缓松了手。她望着这个不可思议的杰作,惊讶得说不话来。我也很惊讶,说:“你不该当什么诗人,你应该去参加奥运会的举重比赛!”她这才回过神来,说:“我平时真的没有这么大力,今天只是梦想给了我力量。就像是以前看到过的一个报道,一个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把重达一吨的汽车给抬了起来。这就是意志的力量。”我说:“难道你的梦想有那么重要吗?”她看了我一眼,认真地说:“有的,真的很重要。”
就这样,我们把床也装在了天花板上,一切物质性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主要人物如何倒立着去生活了。这是一切的关键……
“但是且慢,”神女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我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装饰。”
“什么装饰?”
“你仔细想想呀。”
我上下左右看着,那些生长在天花板上的家具让我有种错觉,我觉得自己现在是站在天花板上的,这让我的身体有了种本能的恐慌。我说:“我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到,不过,亲爱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像是站在天花板上?”
她也上下左右观看了一番,说:“有,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
“那我们就这样生活在房间的地板上,算不算倒立生活呢?”
她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不算!”
我吃了一惊,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地否定,我问:“为什么呢?”
“因为尽管形式上我们已经在倒立生活了,但实质上我们还是重力的俘虏,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啊,你说对不对啊?”她用麋鹿一般明亮的眼眸盯着我看,我觉得她的灵魂也一定会是与众不同的,我和这样的灵魂比邻而居是我的荣幸,我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她的话语。
于是,我也斩钉截铁地说:“对!”
她笑了,就像那晚在人群中的扬扬自得,她恢复了女王的信心与尊贵。
“但是……但是你说还缺乏什么装饰呢?”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笨呀你,假如我们要和重力做斗争的话,我们还缺少一个蓝色的星空。”
“星空自然不错,可出现在哪里呢?”
“这个还用问?就是我们脚下啊,你想想,地板成了星空的时候,你站在这里是什么感觉?”
“我会觉得我站在宇宙中,地球悬浮在我的头顶上。”
“你会不会有一种压迫感,觉得地球就要掉下来压碎你了?”
“嗯,好像是的。”
“那你再想想,同样是地板或者星空,但如果我们站在天花板上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闭上眼睛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然后大吃一惊,说:“恐怖极了,我觉得我要掉进无边的宇宙当中了。”
她却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说:“那种感觉美妙极了,那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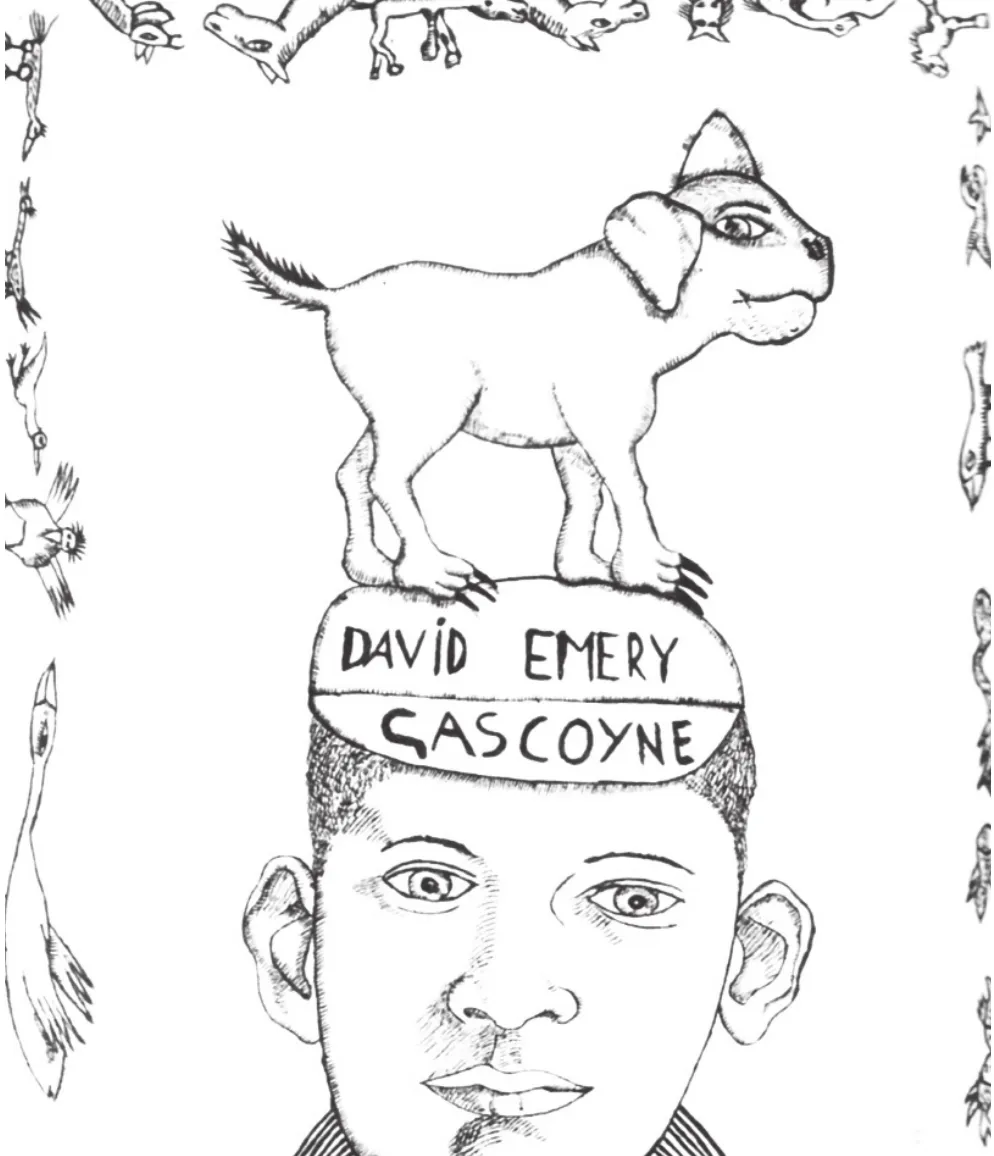
■美术作品:卢西恩·弗洛伊德
那是我梦寐以求的感觉吗?我不知道,或说我无法确定,当一件事情被置于反思的境地时,它的意义就会面临着消解的危险。我惧怕那样的危险,我曾像兔子一样跳跃着,逃避着那样的危险,现在我可不想再自讨苦吃。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感觉。”
星空的制作相当容易,找来蓝色的颜料,将地板整个儿涂抹了一遍。星星呢?用黄色的颜料勾画吗?就在我思考的时候,神女拿了一串彩灯过来,说:“这个就是亮闪闪的星星。”啊,我得承认,她太有创意了,没有什么比这些小灯泡更适合扮演星星了。
现在真的就剩最后的一步了——住到上面去。这实在太难了,人不是物体,不能靠垫片和螺丝来固定,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浑身黏满吸盘,像章鱼一样吸附在上面吗?
我思来想去,发现我们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那就是绳索。神女说:“那我们岂不是成了蜘蛛侠?”我摇着头说:“不,我们比他笨拙多了。”
尽管笨拙,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个极具物理学天分的人,我居然用有限的材料制作了滑轮升降装置,有两个摇把,一个在地板上、一个在天花板上。操作的方法非常简单,一个人先钻进“升降机”中(补充一下,那原本是一个插花的巨大竹篮,放上沙发垫之后非常舒服),然后另外一个人摇动地面上的摇把,“升降机”便徐徐上升,那个人随之到达了天花板,可以钻进特制的网状睡囊中。这时,到达天花板的人把篮子放下去,地面上的人坐进去,上面的人开始摇把手,“升降机”便再次升起了……
我在床上、椅子上都安装了结实的皮带扣,这样我们就可以“仰卧”在床上,或是“坐”在椅子上看书了。不过,那种感觉真是难受极了,全身的血都涌进了脑袋中,眼睛发胀,太阳穴的血管跳动着。要是神女坐在那里就显得更加可怕,以倒过来的视角看,她的长发完全站立了起来,像个通电的女巫。一次,我们并排“躺”在床上,她问我:“蝙蝠为什么倒着睡觉,就不怕血液涌入脑袋里呢?”我说:“这个问题真的难住我了,我们用百度搜搜吧。”打开电脑,输入问题后,出来了一大堆网页,我们点开一个开始看,上面有众多网友留下的解答,第一个人说:蝙蝠终日在外活动,挂着睡有助于血液循环和恢复体力。第二个人说:蝙蝠的饮食习惯不好,容易呕吐,所以倒着睡觉时万一呕吐了还不会吐到自己身上。第三个人说:它要证明它与众不同。第四个人说:因为蝙蝠的心脏太小了,害怕血液到不了大脑,才利用了地球的重力。第五个人说……
最后,我们看到第十八个人的话时,才觉得他的答案勉强能说服我们。他说:因为我们人类在站立的时候,下半身的血管紧缩,使下半身的血液不会聚积;蝙蝠刚好相反,它在倒挂的时候,头部的血管紧缩,使流到头部的血液不会太多,所以就不会脑充血。也许这是对的,我们的判断标准是:因为它并不可笑。但仔细琢磨下,它还是似是而非的,真伪更是难以辨别,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学与解剖学上的证据。
除却这种“血倒流”的不适,其余的一切都很新奇。看着下方的星空,神女经常对我说:“我们就像是宇宙中的两块小陨石。”我说:“你也太高看自己了,在宇宙中,咱俩就是两粒微尘。”她说:“我就喜欢微尘的感觉,因为微尘即使有痛苦,也是微不足道的。”我点头说:“对极了,但我怕消失的感觉,微尘与消失只有一线之隔。”
“消失又怎么了?”
“我怕。”
“不用怕,怕也没用。”
“好的。”
神女握着我的手,我也握着她的手。
我觉得一会儿是我俯视着她,一会儿又是她俯视着我,我感到越来越眩晕了,在这样的眩晕中我跌进了睡眠的涡流中。我似乎听到神女在叫我,但我实在太困了,因为倒立生活要付出比往常多几倍的体力,我像个操劳过度的蝙蝠,看上去也许会有几丝古怪,不过,这不正是我期待的吗?
我很想对神女说出这些,但我的嘴巴无声地嗫嚅了几下便停住了。我听到她在我耳边一会儿粗暴一会儿温柔地呼喊我的名字,我却无能为力,独自滑向睡眠的欢乐。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神女身上长满了细细的绒毛,这些绒毛让我们能像壁虎那样随心所欲地倒立在天花板上。我感到我全部的恐惧、绝望与不幸都向头顶那个星空倾泻而去,一股如星云般壮丽的宁静诞生在我的心间。
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存在还真有可能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