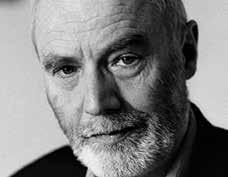
“那突然而至的夜晚……”a
那突然而至的夜晚
充满盐和松脂,双眼和双唇的恩爱,
黑暗蜷缩于灯盏的小小教堂
我的身体避难于你的身体,
在黑暗中看见。
在露珠的眼皮下
雾似的无人的瞳仁梦见,
受伤的童年潮退而去。
“在一个深渊的……”
在一个深渊的山脚
在一道闪电的斜坡,你的房子曾经矗立
活着的诗
诗就像
为心脏工作而输入的血液:
捐献者也许早已死于
突发事故,但他们的血液
活着——与他人的血流融合在一起
并复苏了他人的双唇。
“温柔……”
温柔——就像在某个废弃的房子里你发现
一缕秀发在一片裁下的纸上
一束紫罗兰凋谢在一只花瓶里
温柔存在于——通向活人未知的岛屿
那受致命伤的抵达中,
于大屠杀中一个孩子幸存的发带
有一阵子
有一阵子我注意到
当主人以口哨召唤他的狗时
多数过路人会回过头来。
失?眠?
失眠——你做的错事
你受的委屈,未实现的
梦,不能实现的梦,
所有白天,黑夜和噩梦之事,
不可避免的错误,不可弥补的错误
近的——不可感知
远的——不可忘却
也许死亡不能擦去的一切
就像雨?死海
总是将你抛到它的表面?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我只有一次生命
我也许从未生活过
在遥远的童年我便已失去信念
我从未停止过忠实
我羞愧地阅读我最近的诗
我漫步穿过它们就如雪层下的灰烬
我不想参与作伪
我不想讲半真半假的真相
虚无梳理着我的信件和文件
虚无以其油腻的手给它们贴上邮票
我几乎不能感到你是谁
这并不是我为什么
学习沉默的
理由
自白,而非一首诗
我引起沮丧当我停止
自娱的文字游戏——那奴隶的
无助的戏耍
我听到铁的笑声
和铅的大笑。在我喉头
凝固的喑哑在生长。喑哑
我听到喑哑的笑声,
它们现在
不过是伤口。
像一个梦
真的,你的生活像一个梦,
像一次火车旅行,一次沿着幸存大街的闲逛;
它不知不觉地延伸,无形中变化着:
拖延着——而且——被已知的道路
扭曲成十字——
它无情地将你带到
从前的下午
或者世代。
打?击
“打击从最意想不到的角落落下……”
所以,是时候了,开始从头清点
尘世的账目
或其他任何不可挽回之事
谁?会
谁会比你的纯种狗
更能理解你的平等意识?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寻找,
他们自己出现,奴隶们,
随时准备屈服于权力
那唯一的
拖延着我们的
爱和致命的疾病。
小林一茶
——致扎加耶夫斯基夫妇
小林一茶,我不久前才读到他
他一生受尽贫穷和剥夺
却幸福地活到了晚年,
在一首不可译的诗里,他说:
“爬呀,小蜗牛,
爬上富士山,
但要慢慢地。”慢慢地。
不要急啊,词语和心脏。
几乎全部
已是二十世纪了,所以
我上床睡觉,带着报纸,
眼镜,药丸,手表
均觸手可及;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睡着,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醒来
这就是一切。
你已经爬得很高了
你已经爬得很高了,我的小蜗牛,
爬到了紫丁香黑色的叶子上!
但是请记住:九月就要结束了。
去睡吧
恐惧,去睡吧。不要睡着。
如果其他人都睡着了,那么
睁着眼睡吧。
是的,她说
是的,她说,我们幸存了下来。
现在我面临一个
同样严重的挑战:乘上
一辆电车,
回到家里。
谁知道
如果我们一起
用我们的语言
同时呼喊:“救命!”
那么,谁知道,许多光年后
我们另一个世界
不可摧毁的堵塞的信号接收站
也许能探测到一个应答
犹如一个回声。
画掉的开头
——致兹别格涅夫·赫伯特
画掉的开头,在另外
一边:白色,
在两者之间那么多的生活,不可
描述——
——仍是一张白纸;被揉皱
在燃烧后的烟灰缸里,
一个小小的无限?什么也不是?
一点阳光和阴影
城?市
首先它奖励秩序、干净、节约:
犹太教堂变成了公共游泳池,
市场停车位一点儿看不出
犹太人墓地的痕迹。
霜
流言的白霜,绝望的化石。谁会听到
大地上正在消失的赞美诗,行星间
无声的问候,以及
星座间互致的道别。黑太阳
爆灭成
冷冷的
寂静。
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
可怜的埃及公主的木乃伊
暴露在异国人的注视下
你在这里还好吗?
在此你拥有了你的来世。
此刻,我,也是它的一部分,
正看着你。
此时再没有人来。
没有人知道
来世是否存在。
栗?子
在布拉格犹太人新公墓
我站在弗兰兹·卡夫卡博士坟前
从附近一棵栗子树上
最后的栗子落下
晚秋下午的阳光下
它有片刻的闪光
在其他栗子,
树叶,字母,
鹅卵石和石头中间。
只有雪
只有雪,
只有水和火,
只有沉重的大地和轻盈的空气,
只有携带死亡的元素,
只有死去的事物
当它们从死者中起来
或者以它们的下一个化身
重生
不受
其行为的支配
燃烧过的纸屑
燃烧过的纸屑之星星
坠落在大街上——
仅仅几年或几千年之前
你可能会想到
天堂,也可能空间不够用
不时要烧掉一些文件
它们记录了曾在地球上行走的
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动作;
你现在所感到的
既不能叫放弃
也不能叫希望之缺乏
路?过
路过郊区的一所房子
我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里瞥见
一个老人,在明亮的
桌子旁,独自吃饭。
谁给了我权利
怀疑
这个切开面包的人
为了生存
可能也曾被迫背叛
朋友或自己,
無论他的手上是否沾着别人的血,
他的脸
是否不曾被人唾口水?
你?是
你是我唯一的祖国。
你是我唯一的祖国:沉默,
你保存着所有
徒劳的词语;
喑哑的云,
呼吸,扫视,
承载一封信的信鸽
不留痕迹地离去;
你是我唯一的祖国:寂静,
尖叫
在死去的母语里;
像一场大火的受害者,
他失去了一切无用的东西,
像一个逃亡者
刚逃出营房就被逮捕
虽然我不是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囚徒,
我知道即使在流亡中
我也将留在你的里面:言语,
你也将在我的里面
像一只红肿的舌头:心跳
让我活着
直到它不能
“冒失?心不在焉?意外……”
冒失?心不在焉?意外?
一只小蜥蜴,颤动于荆棘和常春藤中间,
带我走向你,一个死者的岛屿
被蔚蓝色的墙壁和海水包围。
我欣赏你的小诗
但我不能理解你的生活。
好吧,埃兹拉·庞德。我知道得不多。
我得回去了。作为纪念
我想从小路上带走一枚鹅卵石
看上去深邃、紧闭、不言不语。
我将它留给大地和无人的沉默。
零点差一刻
你的声音在受话器里
被另一个我无法理解的
声音覆盖。也许在拨打911,也许在
告诉一个应答机“我爱你”,
或是有人,在装卸库存,或是咒骂,
抽泣。来自臭氧层外?来自大西洋
水底?零点差一刻
不属于任何人的一个时间。
普瓦捷大街
傍晚时分,下着小雪。
奥塞美术馆在罢工,附近
人行道边灰暗的一团:
一个流浪汉蜷成球状(或许是来自
陷入内战的某国的一个难民)
仍然躺着,裹在毯子里,
一只垃圾睡袋,和活下去的权利。
昨天他的无线电还在播放。
今天硬币冷却在纸上,在星座上,
那些不存在的行星和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