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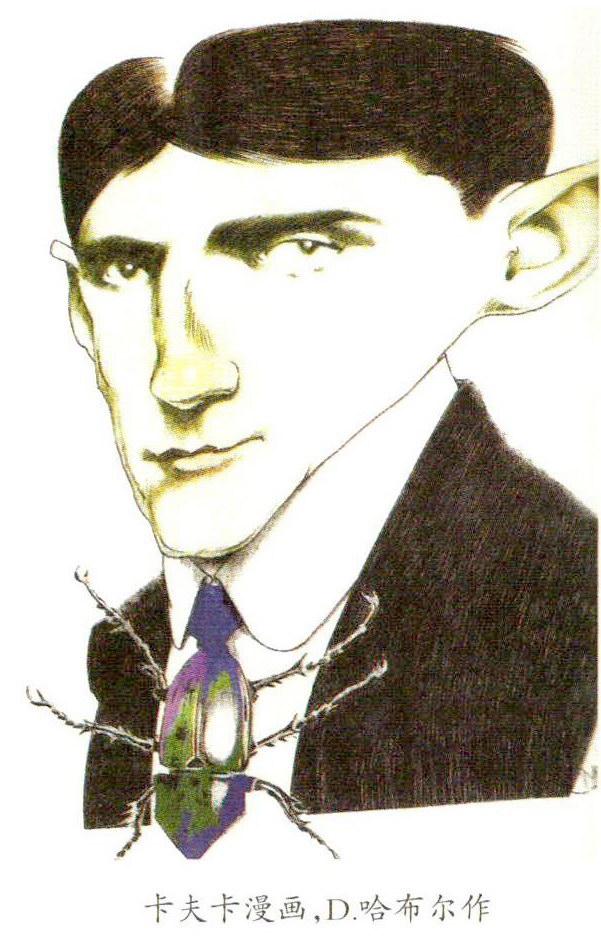
一
卡夫卡(F.Kata,1883—1924)1913年的日记,其中两则写道:“我不能入睡,只有做梦,完全没有睡意。”“我勉强入睡,做着浅梦,但并不荒诞,经常是日间主要活动的重复。但比起熬夜更清醒,更疲倦。”到1922年,情况更加严重了:“几乎完全失眠,被梦折腾,好像用针把它们镌刻到我的与生俱来的抗拒的本质上。”长梦短梦,大梦小梦,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日记、笔记中,也出现在给朋友、女朋友的书信里。与先后两次订婚的女友博埃、最后的女友米莱娜的通信,无一不谈梦。天花乱坠,离奇怪诞,却非色情梦,尽管昆德拉在《小说艺术》中,谈到卡夫卡作品中被人忽略的色情一面。被忽略,皆因点到即止,不像当代人火辣的露肉又露骨,大体是“现在……你属于我”,“我们两人都迷迷懵懵”,或者是安格尔彩笔下的裸女对着镜子搔首弄姿。王尔德有谓:“一个大梦人,只在月色底下找到他的路。在其他人之前看到黎明,是对他的惩罚。”
卡夫卡一辈子都在被惩罚。生活与梦紧密相连,更甚于周庄梦蝶的浮生若梦。梦使他严重失眠,糟蹋了他的夜,醒在黎明之前。他神思恍惚,不能忍受任何声音,音乐、歌声也不成。白天黑夜,皆游荡在一个记忆的黑洞里,在一个大概的、近似的、从来没有目睹过的、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的世界当中。现实和梦是一码事。也许只有当他返回办公室,作为一个法学博士,在“波希米亚王国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里,处理繁忙事务的时候,才能从大梦中逃脱一刻。晚上,就去追逐不为人所知的陌生世界,是他最劳碌、最珍贵的时刻。梦与噩梦只是一线之隔,就有《变形记》中的推销员萨姆沙,经过一夜噩梦折腾,次日早晨,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一打开书就见虫,先就不悦。你把它放一边,打开另一本,那是初版于柏林的“Die Scheide”出版社的《诉讼》。当时旅居捷克的法国人维亚拉特(A.Vialatte)第一个把它翻译成法文,由纪德改编成戏剧,1947年搬上舞台,比利时、瑞士、纽约也跟着上演。你相信这部书会好看些。一开始就切入主题:
肯定有人诬告约瑟夫·K,因为他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一天早晨,他被逮捕。女房东的厨子每天早上八时习惯给他送早餐,但那天早晨没有出现,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K又等了一阵子,从深陷着脑瓜的枕头上。望向住在他家对面的老妇人,她在惊奇地观望他。他又饿又惊讶,去按铃召女仆来,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一个男人走进来——一个从来没有在房子里见过的人。
约瑟夫·K,一个银行小职员,安分,敬业,独身而生活得井井有条,平日活动只限于办公室和住所之间。现在被当成罪犯,置身于两个穿着制服的人中间。他们自称是由某法院派出来执行任务的,通知K要承认自己处于被逮捕状态,行动虽仍然自由,但必须跟负责调查他的案件的法官合作。个人必须服从一种权力,按照规定准确地行动。他堕入五里云雾,因为从来没有做過坏事。最初还以为是办公室的朋友趁他30岁生日,给他开个玩笑,耍一下乐子;格鲁巴赫太太也对他说,这样的逮捕,就像在街头被坏人袭击,麻烦过去了,就没事了。但眼下只能服从命令,跟法庭合作,希望水落石出,一劳永逸地还自己清白。第一次被传上法庭时,还指望以申诉来使听众明白他是无辜的:“我是一大清早从床上被抓的……隔壁就住着两个粗鲁的检察员,如果我曾经是危险的强盗,人家可没有采取更多的防范……我问队长为什么要抓我……他啥也不回答,可能他根本不知道。将我抓起来,于他就足够了。……”在强大、无所不在、权力无限制伸展的国家机器面前,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寻找可以开脱的门路。通过格鲁巴赫太太找到的人,都不肯帮忙。有的闻声溜走。他需要找一个辩护律师,还要找一个有可能联系上调查案件的大法官的人。所有人都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但所有人都离他十万八千里;所有人都在回答他的问题,但所有答话皆答非所问,他的辩护律师跟他说的也是一堆废话。有的朋友劝他不要太顽强,要懂得“认错”,否则在劫难逃。法院一旦控告某人,就得相信这个人有罪。一位律师还向他揭露司法界的黑幕,如何徇私舞弊,藏污纳垢。也有一位谷物商告诉他,为一件案子他被折腾了二十年,倾家荡产,千辛万苦立下的状子,成了一堆无人过目的废纸。
显然,所有敲过的门都关上了。K还说,逮捕他那天,队长“把他银行的三个低级职员带到房间里来,……这些职员的出现自然另有目的,就像将女房东和她的女仆引进房间,他们的作用是传播我被逮捕的消息,破坏我的名誉,动摇我在银行里的位置”。他孤独无援,觉得整个城关起来,变成一个大法庭来审判他。他说的话,在别人眼里都成了废话。在强大的权力机器面前,在被催眠过的芸芸众生面前,他的罪状无真假可言。没有一个被解上法庭的人是无罪的!一年之后,他死在了刽子手的刀下。你作为读者,眼睁睁看着清白无辜的小职员,被法庭判成“罪人”,血淋淋地倒下,比看人变成虫更不是味道!
你去看卡夫卡,就得把仁慈、同情、公道、阳光般的笑脸,统统先存放在衣帽间。他给你讲述的,是一块破烂的抹布的故事。都说卡夫卡患了神经病,这可要医生证明,医生说没有。说他有一种颠覆倾向,就看你怎么说,他是个不眠人,通宵达旦做噩梦,又患上痨病,健康日益恶化,医药物质短缺,听天由命地活着,就以恶毒来向社会施暴,来向生活报复,一落笔就攻击现实,丑化现实,弄得一地的血污!谁对这种破事感兴趣?唯相交二十二年的好友布洛德(M.Brod),他的遗嘱执行人,难得地眼光独到,将他的作品当宝贝,卡夫卡向他朗读《变形记》时,他捧腹大笑。后来接手卡氏的手稿、书信和笔记之后,并没有按照遗嘱付诸一炬,而是保留下来,还花大量时间整理,就像高鹗续“红楼”。须知《诉讼》《城堡》《Amerika》都尚未最后完成。还得到处找出版社。为说服出版社,将作品的宗旨解释为宗教意向。必须具有超时代超现实的眼光、殊众的艺术观,敢于全面担当,才会不顾一切捍卫这个神经汉和他的胡言乱语。
卡夫卡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奥匈帝国末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老一辈犹太人尽量融入到帝国的相对宽松的生活当中。年轻一辈则不一样,感觉上依然生活在潜隐的反犹太的气氛里,他们还是“鼠民”。对父辈的“盲目”表示不满、倾向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卡夫卡,就生活在这种敌对气氛中,基本是年轻一辈的立场。但并不热衷于政治。1917年得肺病后,在日记中写道:“虚无的号角吹响了”,爱情、婚姻可以一笔删除了,工作松懈了,到乡间去喂羊,去剥马铃薯,晚间与耗子为伍。看着夕阳西下,他在日记中谈杂技,说“他走的绳索不是悬在高空,而是紧贴着地面”,泥土与他更贴近了。一战期间,因病没有上战场,但生活已彻底改变,人手短缺,上班时必须加倍工作,以至疲精力竭。朋友们都上了战场,原来就不喜欢社交生活,交友甚少,现在越发孤独了。在世时无声无息,跟远离社交有关系吧?
那个年代的欧洲,没有几个人接受卡夫卡;出版界也不例外,只有专门出版批判性作品的出版社,或有可能接受。然则,他的作品一经刊出,马上被眼光独到的人看成是文坛的新品种。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被誉为文学现象的唯一,拥有的空间是全新的。超时代,超现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大浪淘沙,又发现卡夫卡是放射性元素,是深海里的迷宫,让你迷路,让你去发挥,去结束他开始了的故事。就有超现实主义者跟他一起做梦,去神经质,去幽默;有哲学的狂热者就去寻找象征、隐喻。他们需要他,就像需要弗洛伊德、尼采。每个人都能通向卡夫卡。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的神经病、黑色幽默、大梦般的怪诞,或令人瞠目结舌的逻辑,而是因为他的既可感知又显得陌生的寓言色彩、他的象征意义以及隐晦的暗喻。你说他荒谬,只要你愿意睁开眼,现实中到处存在着荒谬;你说他超越时空,首先近在眼前。你可以从处身的时代、自身的经验,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去哭、去笑自己的命运,去感受人生的谬误。现代人批评旧世界,声嘶力竭,不堪其倦,卡夫卡不叫,不喊,不斥责,不提出忠告,却拥有风倒朽木的能力。
他把文学作为生活的主要活动,唯一的,他所需要的,又随手可得的活动。孤寂反而成为福气。一夜间或数天时间,就可以完成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一部作品。一蹴而就,纸页上没有大小交叉,横杠直杠。你说他闭门造车,缺少生活?不错,有些作家需要火辣的生活,要亲身经历战场、屠场、情场,要泡在眼泪里,或弄得混身弹痕,才能写出伟大作品,于卡夫卡好像不是:
没有必要走出家门,就坐在书桌前用耳朵去听。甚至不用听,单是等待就足够。甚至不用等待,就让自己处于绝对的静穆与孤独当中。世界就来将自己呈现在你跟前,并摘掉面具,不做别的事情,就在你面前弯腰,拜倒。
這段文字与老子的感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咱们的老子爸爸,于静夜时分,“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凭他的“道”感,来感悟宇宙的无穷尽和神秘,以现代的字眼来说,就是以“超验”来揭秘事物,道出它的所以然。你说他脱离现实,天马行空,提不出物质证据,到了20世纪,现代天体学的神秘画面,就来给他的“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等文字作证。卡夫卡这只“寒鸦”,生活在人寰,却像地鼠,老躲在洞穴里,不时将鼻子伸出洞外,这里拱拱,那里嗅嗅,就来给你说些怪异的故事、超验的故事,超出人的认识、超出时空律法的故事。你说他患上神经病、梦游症,不能说刻薄;说《城堡》中的K千辛万苦走的长路,为的是抵达天主,也说得通。如果大家一味以书论书,没有从纸页的迷魂阵中脱身而出,回到现实世界,将脚丫牢踩大地,会觉得这个脆弱、胆怯、一本正经,甚至不敢面对婚姻的人有点怪癖,不遗余力地将世事“扭曲”,又有本事使它不可逆转。你奈何不了。其实,他生活那个年代,只经历过第一次大战,跟着要来的世事,神龙不见尾首。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经历过二次大战,战后来了一个患病时代——邪恶有理,无仁无亲——大家才揉揉双眼,不无惊诧地发现:纳粹的屠杀,他预言了;极权国家的滥捕滥杀,他预言了;古拉格群岛,他预言了;监视和控制的技术、摧毁个人及个人世界的能力,也预言了。柏林围墙倒下之后,他的作品走出欧洲,到1994年,各种译本纷纷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罩着卡夫卡的罩子才被揭开。从此他被誉为文学界的“先知”“文圣”。
二
卡夫卡的风格是不追求风格的风格,他偏离了传统作家的路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统统扔出窗外。要比只能跟贝克特相比较。语言干巴巴,但透明清晰,简易畅达,不着重复杂的表意,避免“风格”,只提供画面。文字准确得一板一眼,枯燥无味。写的都是小市民,没有面孔,没有身份,没有幸福生活,但有意识,有心情,有感觉,历尽艰辛追求的,只是最起码的生的需求而已。目标却永远不可抵达。卡夫卡逝世次年,法国人维亚拉特就把《城堡》翻译成法语。当时他任职于以法语和德语双语出版的、由法国外交部资助的杂志《Revue Ph e nane》。作为杂志社的编辑,他一头栽进《城堡》里。测量员K希望在克拉姆伯爵统治的村子里落脚,以便开展测量工作。但必须找到爵爷,得到他批准。爵爷是个神秘而传奇的人物,住在山丘上的一座城堡里,静静地守着他统治的世界。里面有一大群爷们和公务员,等级分明地组织起来,开动着统治村子的行政机器。城堡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散发出神秘的魔力,将村子笼罩着,直抵地平线。K踏着雪路上访,希望亲自见到爵爷。但路上阻障重重,出乎预料之外。城堡逐渐出现,越来越像充满敌意的魔鬼机关。K听见牧歌和教堂的钟声,向它发出讯息,也得到回答,尽管是错误的回答。但通向城堡的道路都是死胡同。他非常顽固,眼睛老盯着城堡,竭尽努力要进入,但没法靠近。村民也不接受他,把他当成非我族类、一个疯子,他们都习惯了当地的法律,不觉得它荒谬、反逻辑、非人性。他唯一的功业是在入住的酒店里,勾引上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企图通过她到克拉姆跟前。这条路子还是没走通。当弗丽达拂袖而去,眼看这盘棋输定了,却偶然进入村子一间酒店,那是爷们到村子的时候,习惯落脚的地方。终于有一位公务员愿意帮助他,但他已经疲精力竭,昏睡过去,什么也没听见。故事到此中断。千辛万苦穿过路障重重,只为有一个落脚点而不得,最后赔上了小命。说卡夫卡荒诞,马克·吐温却说:“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卡夫卡以荒诞手法揭去现实的假面具,把它的实质指给我们看。要触及实质,荒诞手法就必须高于现实手法。K的目的地的不可抵达,却是另一种抵达: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小说预定的结局是:K在弥留之际得到通知,可以在村子里落脚,但不能进入城堡,这个最高的权力机关。
都说卡夫卡有颠覆和反规则意向,这种倾向成就了作品的复杂性和深不可测。你读过《诉讼》,掩卷细思,竟发现我们就是约瑟夫·K,勤恳,敬业,像小鸟衔泥做窝,一砖一瓦一梁一椽起好房子,一犁一铧一锄,开垦了荒地,正想告诉朋友:“这是我的家园,我与我的亲人就生活在这里。”谁知一场风暴来了,随即墙坍柱塌,瓦片纷飞,你的窝被兜底打翻,人与物俱亡。你循规蹈矩走你的路,忽然从转弯抹角,或一道大门后面,闪出两个穿制服的人,给你拦截了去路,让他们捕了个正着,那时候你就是一个罪人。所有被逮的人都是有罪的。从此万劫不复。事先你永远不知道躲在门后的那些事儿。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最健忘的人也不会忘记古拉格群岛、奥斯维辛;也永远不会忘记索尔仁尼琴这头北极熊的古拉格岁月,犹太人汉学家马伯乐断魂奥斯维茨。我们也是约瑟夫·K的工作单位、住所、咖啡馆、邻里的芸芸众生,都是些被催眠过的人,宁可相信约瑟夫·K有罪。目睹了很糟糕的情况,依然感觉良好,日子还过得去。更甚者,如卡夫卡的寓言:“牲口从主人手中夺过鞭子,以鞭打在自己身上来做主人。”
三
布洛德听《变形记》朗读时,捧腹大笑,是卡夫卡日记记载的。哪一个章节使他大笑?他笑什么?《变形记》是卡氏重要作品中的第一部,发表于1916年。作为神秘的现象学作品,有十年时间,在德国最具特征的作品中,占最重要地位。作者将一种怪异的现象与现实缝合起来,表达的诚恳,手法的新颖,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融和、协调,使那只虫子经历了年月存活下来。萨姆沙一夜噩梦之后,变成一只大甲虫,躺在床上起不来,老滑回原位。可悲的是脑子依然是人的思维,清醒,明晰,外形的改变没有触动内心的慈悲、对家人的温情。他首先想起的,是要乘早班火车出差,生怕耽误了工作时间。又怕公司来人找他,这副形象如何见得人?他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恐慌、焦急无补于事,公司的主任果然上门来了。威胁他说,如果不开门出来见人,就要受开除处分。在极度难堪中,用嘴扭动锁匙开了门。这时,主任惊叫,母亲昏倒在地,父亲怒火中烧,号啕大哭。但,这条虫唯一想到的,还是他的工作,请求主任在公司面前说好话,好保住他的职位。但主任吓得三级当一级下楼,逃走了。盛怒的父亲随手拎起主任匆忙中遗留下的手杖,扔到虫儿子身上,导致他大量出血。
为什么变形?噩梦使他变形。从人变成虫。无须达尔文同意。为什么连夜噩梦?为生活的压力,父亲五年前生意倒闭,一家四口的生活担子就落到他肩上。为应付工作,为保住职位,他小心翼翼,从来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沉湎在一百种小心眼的忧虑当中,无尽的烦恼重压般落到身上。但对家人有刖处,他很珍惜。变成甲虫后,外形惹人厌恶,虫性使它吃垃圾,喜肮脏,怕阳光,自惭形秽而躲避家人的视线,老躲在床底下。他对家人依旧充满柔情,反而招来灾难,逐渐感觉到他们的厌恶,老在回避他。连他准备资助学小提琴的妹妹也不例外。盛怒的父亲还把一只苹果扔到它背上,陷进体内,甲壳一块块脱节,活得很苦。一天晚上,他听见外边传来小提琴声,非常感动,这可是他所渴望的养料啊!忍不住偷偷爬出房间,去参与那场聚会,妹妹在房客的要求下表演小提琴。但他的出现使房客惊叫,小提琴声遽然刹住,父亲连忙将房客疏散回房间,他们很生气,耻于跟一只虫生活在一起,很快全部搬走了。妹妹表面仁慈,到某种时刻比谁都冷酷,她发声了:“事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当虫返回房间,听见有人从外边闩起门,上了锁。他陷入静默的沉思,空空如也的沉思。到时钟敲响三时,便孤独地、无声无息地死去,让仆人扔在垃圾堆里处理掉。家人如释重荷,随即乘车到郊外闲逛。
故事与其说可怕,不如说催人泪下。你不禁要问,灾难是自身的懦弱招致的?是荒唐而难以捉摸的现实强加到我们身上的?《诉讼》经历过20世纪的风风雨雨,变得容易理解,小民白白得个罪名,白白丢了小命,何罪之有?莫须有。《城堡》也不难理解,小民企图在社会中得到一个落脚点,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无能为力。悲剧在于国家机器与小民的不协调。《变形记》呢,西方译本既然多,理解角度各有不同。人变虫?卡夫卡要说的是啥?“可能是对基因的
卡夫卡漫画,D.哈布尔作不断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遗传学的天才,像卡夫卡向我们叙述的故事那样,使之产生意外事件。那些新种的人,里软外硬,在它们的背上种上腐烂的苹果,可以作为跟自然最高的接触点,让人感知到大自然。”小说家迪马耶(P.Dumayet)以科学观点来解读,颇贴近时代。笔者不懂科学,只觉得这是一个人从里到外、从精神到肉体,皆丢失了自我的悲哀,人最可悲的处境。荒唐的变形影射了人的困惑。一个永远的当下故事。你的解读对口径了吗?《变形记》的出版并不一帆风顺,曾经被拒绝过。一旦出版了,却马上引人注目。构思、语言的新颖,整体的高质素,都不可忽略。但卡夫卡要说的是什么?天晓得!有人惊诧于作者的膽色、他的创新;有人企图把它跟传统文学挂钩,也有人指出作者独立特行,拒绝模仿生活。因此,距离生活很远,望迷了眼。
变形从来不曾停止过对文学、艺术的骚扰。人的身份很脆弱,与其他动物有太多相同的基因。自身的欲望也不会规矩地驻足于“不可能”的观念上。《太平广记》中的《吴堪》篇、《计真》篇、《板桥三娘子》等都在人兽之间“变”得不亦乐乎。西方有奥维德(Ovide)的《变形记》,其中讲到雕塑家皮革马利翁(Pygmalion)爱上自己的作品,美之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使他如愿以偿:“回到家里,皮革马利翁走近他创作的少女雕像,俯首向床亲吻她,感到她的肌肤变得温热了。”还讲到希腊神话中的猎神戴安娜,为报复阿克蒂翁(Act e on)偷看她沐浴,把他变成一只鹿,让50只猎犬将他撕成碎片。变形为的是爱情、天意,或惩罚。唯卡夫卡的变形深奥得很。你要进入他家里,他老人家大门紧锁。你敲门,他不应;撬门进去,他在家,但绝非在等你。一双半阴半阳的大眼梦深沉,沉浸在自己当中,迷失在孤寂当中。你跟他对话,他的语言你不懂;你听在耳朵里的声音,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你收到的讯息是海豚发出的超声波。维亚拉特曾说,普鲁斯特嘛,“他的烦恼是地上的,他勇于叩门的保险箱,只是塞满了大地的时间、茶杯里的茶、掺上杂质的灵魂、尘世的密码。而卡夫卡的保险箱里面塞满了天空”。
一个塞满了天空的保险箱掉到我们头上来了,就有一股砸保险箱的探索热。一股卡夫卡现象迅速地漫延全球,醉汉般的逻辑、空穴来风的异象、神经汉般的反思维、超现实的感觉、文学上从未出现过的描画……被无制约地诠释、投射、折射。既然一切皆是谜,或处于未完成状态,任你用锤子再敲,也毁坏不到哪里;任由你明偷暗窃,也不能说你什么。只要拾取卡夫卡随手扔下的一个人物、一个几乎没有被发现的情节,就可以创造另一个故事。眼下就有不分远近国度的借题发挥:《卡夫卡和少女们》《卡夫卡的埃及》《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卡夫卡在布拉格的生活》……改编成的戏剧、电影无数,都醒人胃口,票房纪录都不错。一部厚达2048页的《卡夫卡传》也出现了,作者斯塔克(R.Stach)赔上20年时间,将数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却分散在各地的资料收集起来,写成传记,2014年发表了最后一卷。
重新译成法语也变得有必要,读者需要再读。都说,维亚拉特的译作不理想,篇幅不长的《变形记》中,可以找出800个字没有翻译出来,700个字额外加上去,60个翻译错误,基本上是改写。某些作品标题翻译有误,原意“失去踪迹的人”,译成“Amerika”。译者未能将简单、清晰的文字翻译得准确,太多文学化的手法,破坏了原著的面貌。译文也显得过时、老化了。研究卡夫卡的先驱们,又总是将观点强加到读者身上。
2019年初,从德文翻译成法文的《卡夫卡全集》的第一、二卷(计划出四卷),其中包括通讯和日记,由伽利玛出版社的珍本丛书(Pl e ade)出版。重译的文字比较清晰、通透、准确,去掉文学化和矫饰风格,给读者一片更开阔的想象空间。旧译中大量的注释也去掉了,更方便读者阅读。卡夫卡变得更现代了。
像卡氏这样拥有深广度和体积的作家,他的日记、笔记、通讯,都可以作为他的“作品”,比作品更能反映真相。他交给布洛德的大量资料,当初存放在特拉维夫。其中也包括布洛德的信件,他跟卡夫卡通信,跟其他作家和知识人的通信,信件总数在15000—20000封之间。1912年前后的布拉格,通讯条件和设施极其有限,联络不方便,拥有座机、手提电话、手机的当代人难以想象。想拨个电话,必须先到总邮局挂号,进入等候室,等候时间不会少于30到40分钟,最后进入一个小问,通话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书信来往是主要的联络方式。卡夫卡给女友博埃的信件达400封,已经结集出版;给米莱娜的书信也不少,亦已出版。这些信件一如作品,是可以深挖的矿藏。经过资料的收集、作品的重译,信件、笔记、手稿的发现、付印,卡夫卡及其作品又来了一次更新、演进,一个半逃跑或误解了的世界,被追捕回来了。
四
柏林墙倒下之后,笔者曾经到布拉格“朝圣”,去看大梦人的故居博物馆。抵j步后连日滂沱大雨,更煞风景的是,冒雨进入只能步行的旧城区,看到的只是一问面积很小又极其简陋的单间房子,与其说博物馆,不如说小书店;架子上的书籍寥寥可数,柜面出售的只有几张图片,跟大名鼎鼎的作家名不相符。你一身湿淋淋,一肚子的火。布拉格慢待了卡夫卡,又搪塞了我们这些远道而去朝拜的人。最后到城外的犹太人墓园去瞻仰他的陵墓,环境倒安静,满眼浓荫,古木被长青藤千缠万绕,藤缠树,树缠藤。时值盛夏,却连日暴雨,阴气弥漫,颇有卡夫卡的阴森味道。静寂中,连鬼影也不见一个。遑论去瞻仰的人。墓地除了墓碑没有任何饰物,跟别的陵墓大致相同。身后的世界一律平等。看过墓碑上几行字,知道他跟父母家人同一墓地。之后,便逃之夭夭,不再回头看一眼。
时隔多年,博物馆情况否改变?现在谈起卡夫卡,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当初说他的作品都在逝世后才出版,不对,《变形记》1916年就出版了;说他用德语写作,但德国人对他视而不见,不对,在世时候,《Revue Rh e nane》的评论文章将他归入德国的“表现主义”潮流,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德国文学史一早就给了他一个位置;说他当年默默无闻,不对,1924年他逝世,至少有20份报纸刊登了讣告,最著名的刊物都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法国方面,《变形记》于1928年分三期在《法兰西文学评论》发表,1938年集成书本出版。《诉讼》《城堡》也先后于1933年和1938年出版了。传说中他社交生活甚丰,经常进出剧院、电影院,到酒吧寻欢作乐,逛窑子,尤其喜欢流连咖啡座,不对,他从来不参与特殊圈子的聚会。来往比较密切的所谓“布拉格圈子”,只有他与布洛德,及另外两位朋友,总共才四人。偶或跟别人到咖啡馆见面,总是早早离席,据作家若阿内(U.Johannes)记载:“卡夫卡永远不会在咖啡座上长久逗留,离开前他起来向每个人礼貌地躬身致意,告辞后随即迈开长腿远走,消失在越来越深沉的孤独中。”
经过近百年的资料搜索及研究,卡夫卡怎么样了?浮在水面上的船身都看到了,沉在水下的部分依然是个谜。还有不少已收集的书信、日记、手稿尚未整理、刊发。据一位德国裔的美国作家帕维尔(E.Pawel)在作品中透露,卡夫卡最后的伴侣多拉(D.Dora)于1933年被盖世太保没收的财产中,有20本卡夫卡的笔记和35封信件,记载了卡夫卡最后的日子,眼下可能深藏在欧洲某个尘封的档案室里。更重要的是,当年布洛德从卡夫卡手里接过的资料,体积超过16立方米。想象一下吧,超过16立方米白纸黑字的资料!估计其中有卡夫卡信件、手稿、亲手绘制的图画。他一辈子没有停止过画画,跟朋友聊天时,习惯手不停地在纸页上画。估计还有刊登过他的小说的以色列日报《Haaretz》,有布洛德的私人日记,可能从中找到传记作家们所欠缺的卡夫卡的童年生活、日常生活,和最后日子的记载。为拥有这批资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和德国马尔巴克(Marbach)城的文学档案馆之间,曾经长期纠缠在官司里。布洛德逝世后,这批文献落到他的女秘书埃丝特手里,不管是赠送还是继承,都必须有凭据,依法处理。但1988年,她以200万美元的高价,将《诉讼》的手稿出售了。在101岁上逝世后,资料就落到她的女儿埃娃手上。经过三场官司,最后由最高法院将资料削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埃娃被责令将所有资料交出。但这些宝贝都锁在特拉维夫和苏黎世的保险箱里.埃娃尚未来得及亲自办理这件事,于2018年夏天逝世。但这批文献目前已经运到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相信只有研究过那批纸头,才能更进一步了解,大甲虫、测量员K、约瑟夫·K、《地洞》中的地鼠、其他作品中的异化现象,要跟我们说的究竟是什么。能否帮助我们思考21世纪的难题?为什么我们眼下的世界,就像卡夫卡的幻觉付诸实现:邪恶有理,真理破产。奥登(W.H.Auden)曾说:“卡夫卡之所以于我们重要,皆因他的困惑即现代人的困惑。”是这样吗?也许不该过早把他固定在一个框里,将他情绪化。已经问世的传记、林林总总的文章,将来也许需要修改。上个世纪文坛的恶作剧,逝世几近百年,依然在骚扰着我们。面对着他谜语般的作品、堆积如山的资料,多少卡夫卡迷和學者,不得不成为另一种不眠人。
2019年3月
责任编校 邓沫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