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写情书,是写给我最好的兄弟H。
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情窦未开,文思先涌,每逢写作文都爱兜售一些酸不溜丢的句子。偏偏语文老师很吃这一套,多次拿我写的文章当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同学们虽然心里泛酸,表面上还是对我钦佩有加,尤其是我的女同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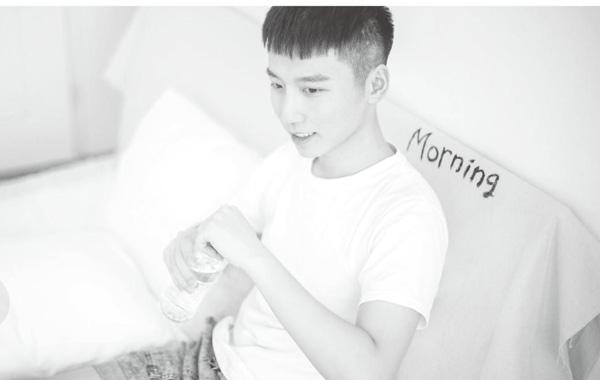
联系上下文不难猜到,我的女同桌迷上了我的好兄弟H。那时候,初中生还比较单纯,或者说比较穷,还相信情书这种老土的东西。女同桌决定给H写一封情书来表达心意。无奈文采有限,尚不能接受“我很喜欢你,我们交往吧”这种简洁的告白便条,所以就拜托我捉刀。
一开始,我是不太能接受这项委托的,总感觉这事儿有点突破道德底线,而且在文字里幻想如何与一个男同学谈情说爱,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但女同桌对我说:“这件事你能做,理由有三:第一,情书夹叙夹议,你的记叙文、议论文都写得不错,不在话下;第二,文学都有虚构成分,女生视角你总要尝试一下吧,这是一次练笔的好机会;第三,你是最了解H的人,给他的情书,你不写谁写?”
说实话,她的这三条理由事后想来都是胡说八道,应该被归入教唆犯罪的范畴,但当时我被触动了,尤其是第三条。
用了两节课的时间,我写出一封深情款款的情书,以一个直男的视角把H从头到脚夸了个遍。我至今记得,最后一句是这么写的:
“我常常想象,已是情侣的我们手牵着手,走在夕阳下的放学路上。”
你看我这贫乏的想象力,约会限定于放学,互动止步于牵手,实在是愧对“青春”二字。
女同桌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誊抄全文,郑重地署上自己的名字,我这篇原名“记一次爱情”作文的版权就转让给她了。
临放学,她托我将情书转交给H。H默默地看完,什么也没说。我心想,好歹你得有个表示吧,就问:“你觉得怎么样?”他面无表情:“我又不喜欢她,能怎么样?”我说:“不是,你觉得写得怎么样?”他说:“酸得很。”自以为妙手著文章的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差评,还来自朝夕相处的好友,真是自取其辱。
最后还是由我向女同桌转告了这一噩耗。我说:“你还是太着急了,我们才初二,还年轻得很嘛。”她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这个傻瓜,还不是因为你写得太烂!”
这事儿在写作上给了我两点教训:第一,女性视角的东西不好写,直男要慎重;第二,轻易不要当乙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时不时还会写点女性视角的小说,以至于被某些读者误会性别;为了糊口也还在接受剧本委托创作,天天被作为甲方的制片人和導演折磨。两点教训我都没有吸取,女同桌说得对,我就是个傻瓜。
爱情跟写东西发生联系,在我的写作生涯里至少有三次。第二次开始写故事,是为了我的前女友。
刚开始追她的时候,我经常翻她的微博,看到她发过一条,写的是“征一个能讲睡前故事的男朋友,在线等”。
睡前故事我讲过。在很小的时候,我在奶奶家过暑假,一家人躺在天台上望着黑漆漆的天,这时候我会复述白天在广播里听到的方言笑话,其他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唯独奶奶会认真听完,并且夸我“讲得好”。
有这等辉煌的过去,我自然信心爆棚。我和前女友都上晚班,下班就十一点了,所以我自告奋勇送她回家,在路上搜肠刮肚把以前的所见所闻都说给她听,添油加醋,眉飞色舞。听得她最后不想回家,我们就坐在通宵营业的快餐店里,一聊就聊到凌晨两三点。我说:“你该回家睡觉了。”她说:“不要,你继续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催更”,顿觉通体清凉。
在一起之后,也许是见识太少,经历又过于匮乏,我已经没有真实的人生故事讲给她听,江郎才尽,过快地掏空自己,反而在热恋期间有点没话找话,横生尴尬。于是我就开始编故事,编上古神话,编逸闻野史,编奇妙物语,编怪力乱神,写在我们两个的博客里,只给她一个人看,她看得开心,我也写得乐意。
有一个文学观点说,作者就像开车的司机,读者是这辆车里的乘客,他们只会坐一段路,总要下车的。前女友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也是那时候我唯一的读者,所以,我们分手之后,这辆空荡荡的车就漫无目的地开在路上,不知道该去哪里。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她不要私家车,我还不能开公交车了?
于是,我把那些故事通通发布到网上,然后有了我的第一本书。
后来,我喜欢上了一个不喜欢我的女孩。
在那场暗恋里,我默默地喜欢她,竟然学会了写诗,就像另一个人格在身体里苏醒了一样。他借着我的手,写下“星辰常在,苍穹不老”;写“我迷恋的现在,是你浅浅的微笑,是相遇的下一句,道别的上一秒”;也写“星河在上,波光在下,我在你身边,等着你的回答”。
你看,多肉麻。
为了隐藏这些诗,不让熟人知道我如此肉麻之后嘲笑我,我又把它们包裹在了十几个故事里,署名“莱特昂·布兰朵”,有了我的第二本书。
我的公交车里不仅稀稀拉拉地坐了些乘客,车身上还刷了押韵的句子,想起来也挺酷的。
事到如今,我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才能躲在“已经有些爱不动”的世界里告诉你们,大胆地爱,就算爱不出一段故事,也能爱成一首诗,不也挺好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