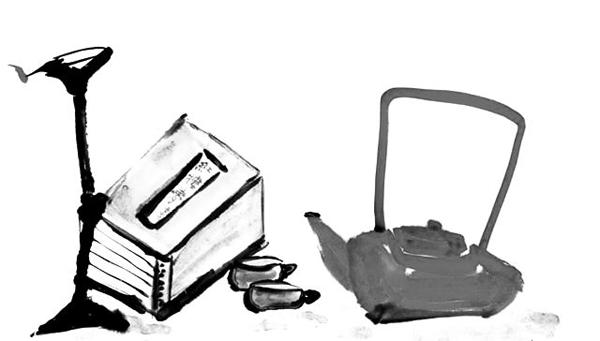
刘莉:走出体制后,知道你尝试过很多工作。记得有一次去你家,你的长篇已写了16万字,当时我特别惊讶。也许人在变动当中才有那股劲吧,是文学给了你力量吗?
薛喜君:很榮幸能与刘莉有这样的对话。说起来,我们就像两棵树,尽管“站姿”不同,但“树种”相同;尽管我们从小的生活环境不同,但我们的年龄相同;尽管我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我们同在一个地域工作和生活。尽管你是地地道道的石油人,而我不过是后来的“迁徙者”,但我们同是写作者。所以,我们注定彼此相望。
为文之道,要先于生存。一直以来,我不认为“责任”是男人的专利,而一个有担当的女子要时刻牢记自身的使命。但不管我尝试哪项工作,哪个行当,我从来没离开文学。说到变动的“劲”,我不是因为变动才有“劲”,而是因为憋着一股“劲”,才去变动的。无论是盲目还是轻率,已经做了,就坦然地接受现实。但是,现实和追求是有距离的,所以,我用身体安抚现实,用灵魂打理追求。尽管会很辛苦,但这也是人生的一个经验。
说到底,是文学的力量。
刘莉:一个写作者走到一定程度,都会对自己有怀疑或者质疑。今天,你再回过头去看,与自己的初心有距离吗?
薛喜君:是的,写作者一定会对自己有质疑,而且不同时期,质疑也不会相同。当然,质疑的时间有时会长,有时也会短。早在2007年以前,我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沉浸在质疑中。那时候不只有生存的压力,工作也特别繁忙,但我依然挤出时间写作。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早上六点就到办公室,晚上办公楼里都没人了,我才回家。其实,我是想用写作来冲刷质疑。当然,我也会与家人和朋友交流我内心的质疑和焦虑,他们都给予我由衷的鼓励。所以,2007年,《中国作家》一连给我发了两篇散文,当年还拿到小说笔会一等奖。很多时候,认可是解决质疑和焦虑的一副良药。到2015年,我又开始质疑自己了。我突然觉得肩上有很多责任,是关于文学的。我不敢说话,更不敢写字——甚至,我都不会叙述了。而且,我那段时间也正好筹备写长篇,这个题材又是我生活经验以外的,我要大量地看资料,记笔记,那时候身体也欠佳。我用各种方式想让自己走出来,比如围着太湖走,在浙西大峡谷里听瀑布,盯着水流从山顶摔下来时,绽放出壮观的“水花儿”,没黑没白地阅读……但只要一回到熟悉的生活,质疑和焦虑就疯狂地涌上来。刚好,省文学院和哈师大文学院的老师们,对我进行了研讨和跟踪。那一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开研讨会。乔焕江院长给我定义的标签是——地平线上的爱欲与生存——薛喜君的底层书写。还有老师以《诗性的抗争》为题,对我的作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等等。面对专家和学者的批评和表扬,我突然意识到了,我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小人物就要有了快感就喊,有了悲伤就哭。文学就是表达生活,所以,我很快地完成了长篇的写作。
回头总结创作的路,与初心没有距离,因为,从没忘初心。
刘莉:有人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只有作品才能留下。可是,在苍生人海中,个体太微不足道了,即使留下也是重复别人的人生。那么,为什么还要留下?
薛喜君:首先,我在创作过程中时刻告诫自己,作品一定要有品质。因为有品质才会有生命力。但这个生命力不是指“留下”。至于作品是否能留下,我没想过,但我拿出作品时,不想让自己脸发烧。说到这里,我也突然意识到,作品能经久流传,像《红楼梦》,像《呼兰河传》等等,无疑是一件好事。至少是对作者潜心写作的一个告慰,无论作者是活着还是死去。
再者,人各有命,作品也一样。能不能流传也取决于它的命运。当然,还取决于它出生的时代。我想,作品流传,是每一个作者的心愿,至少给子孙留下。
关于重复别人的人生,我不能苟同。因为,我留下的只是我的人生足迹。每个人的人生体验不会相同,个体文本中的表述也不尽相同。每一滴水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生命力之短更是令人咂舌。但是,大海,长江、黄河、湖泊都是滴水而成的。所以,做好自己这“一滴水”,也不枉生命一场。
刘莉:文学在你的生命当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薛喜君:文学在我心里有很重要的位置,甚至与生活一样重。所以,写作,是为了生活;生活,又是因为写作。
我的生活和写作不发生冲突,当有冲突时,我会为写作让路。比如,我不会去参加以文学名义,夹杂其他东西的任何活动。家人和朋友都说我是独行者,即便偶尔走到边缘,也只是向热闹的地带望一望,也止于看看而已。这样不入世的性格,很难被人接受,更不被人理解。也会为此失去很多看似有用并且适用的东西,比如热闹非凡的聚会,或者更直白地说:机会;再或者,没有朋友等等。但我确实更喜欢在一个纯粹的文学环境下,这样,我会非常自在。我认为,写作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职业,不需要人云亦云,更不能随大流。好像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孤独是生命的繁华。我非常认可,并且极其享受这种繁华。
再说,有个性的作品,才是优秀的作品。
刘莉:死亡是每个生命都要面对的,但看不到死亡的时候,死亡经常是不存在的。一个作家可能就不同了,他们是清醒的。在你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有一种死亡或哀伤的气息,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你是怎样把握的?
薛喜君:是的,死亡无处不在,只是没有逼迫到个体的生命前,我们常常忽略死亡的存在。在我看来,死亡也是一种美好。我觉得,死亡无非是开启另一段的生活。而且,我还幻想,当我开启另一段生活时,希望自己还能是一个写作者,我要记录另一个世界的温暖和悲凉。
如果死亡给我机会,我一定为自己写悼词。我不喜欢别人给我的敷衍,这是对死亡的不尊重。
我在作品里表现出的哀伤,是对个体的生命而言。因为,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会有哀伤。是的,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死亡没有关乎到自己时,我们或许还有点幸灾乐祸。我在一篇随笔里说过:无论生命是高贵还是卑微,都经不起死亡的光顾。作为一个写作者,不但要勇于面对死亡,更要在活著时,勇于把自己撕开,撕得见血见肉,体会死亡。这样,才能懂得另一个生命的喜怒和悲苦。而且我固执地认为,生命中最感人的不是哈哈大笑,而是微笑着流泪,无论是感动还是哀伤。所以,我在文本中都尽量表现出生命的凄美。至于厚重与否,是读者的事儿。
刘莉:关于小说,有人会因为某一个机缘,觉得自己忽然开窍了,作品由此迈上了一个新高度。你有类似的事件或机缘吗?
薛喜君:这是我最钟情的话题。小说就像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因作者的笔力而异,也因作者对生活的认知而异。小说的存在,也有多重可能性。对于我而言,小说仿佛从我记事儿那天就开始了。我一直在写,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力求改变,也一直在思考——当然,初期写作时总是虚构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离奇的故事,认为这才是好小说。而写着写着,突然意识到了更多的问题,比如文本中的故事,场景,结构,人物的内心、气韵以及叙述时的语言等等。这些在文本中如何分配?如何运用?包括如何使用那些被日常磨损的语言?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困惑,面对这些困惑或者焦虑时,我会与朋友探讨,也会在经典阅读中寻找,哪怕是蛛丝马迹。但是,即便是寻求到了一些方式和方法,要想运用到实际的操作中,还是需要笃定的心理素质和扎实的功夫的。我在每一个文本的开篇,都对自己说,不能按照习惯写作。
又如关于文本的故事和生活的比重,我和朋友探讨了好多年。开始,我不能接受他对我心目中经典作品的评论,但是,就在去年,我们再讨论这个话题时,我突然顿悟。于是,我就探索地写了几个中短篇。昨天,我给吉林作家于德北写评论时,就说了这样的话:谁说没有故事的小说,就不是好小说。因为他的叙述,他语言的运用,他对人物心理的把控,直可以让我泪流满面。
这就是一个优秀作家的真本事。亦或是,这些也是我的机缘吧。
刘莉:我们都是长期失眠的人,在心理医学上可能会认为是某种心理障碍,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这种障碍在写作者身上很常见,也反应了这个特殊群体的某种心理特质,比如敏感,脆弱等等。写作是劳动,也是一种心理活动。近年来你作品的产量很高,那么写作是否对失眠症有影响?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还是维持原样?为什么?
薛喜君:这是个看似与文学无关的话题,实际上又紧密相连。我承认失眠是一种心理障碍,但也有身体的原因。比如亏气亏血,脾胃不和。就我个人来说,一种是心理的,多思多虑,也有你说的敏感和脆弱;一种是身体的,除了气血不足,还有脾胃虚弱。我还真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失眠归罪于写作,因为我从小就失眠。但我的朋友说,“一个艺术家他的准备工作在童年就完成了,正常的童年九岁、十岁结束。艺术家可能延长到十五岁、十六岁。”或许,我还在婴幼儿时期,就为成年的写作打基础了吧。也或许,命该如此,失眠是为了写作,写作注定要失眠。尽管我不是艺术家,但我是一个一直朝着“艺术家”努力的人。
我还真说不清了。反正,我的失眠从一出生就开始了。
我的失眠依旧没有改善,但我学会与失眠相处,如果失眠来了,我就友好地接纳它。读书、看月光、浮想联翩——也就是说,我与失眠和解了。要说原因,或许老了的缘故,也或许是达观了,都不怕活着,还怕失眠吗。
刘莉:你每天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听说还在工作岗位,签约作家每年是有发稿任务的,怎么兼顾工作和写作?
薛喜君:其实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前面我说过,当生活与写作发生冲突时,生活会给写作让路。还好,现在的工作不是很忙,领导和员工又都特别支持帮助我。但是,我会把每一项工作做好。这与觉悟无关,与性格有关。四年的发稿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写作不挑环境,一支笔几张便签就可以。也由此,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文学,感谢小说。因为写作抚慰了我精神层面上的困顿,拯救了我生命中诸多的无奈和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以微暗之火,温暖世间苍凉。迎着太阳走,途中可能会遭遇黑暗,那是太阳正在穿云破雾。
感谢刘莉,更感谢我身边所有的文学挚友。因为你们,我对写作更有信心。

注:
薛喜君,女,1963年生人,现居大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21届学员,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
刘莉,女,1963年生人,现居大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18届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