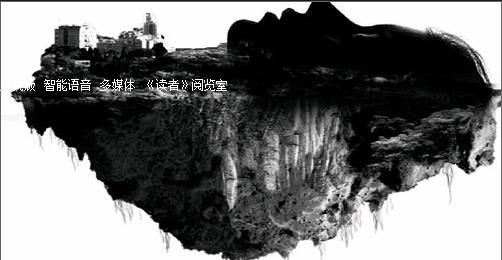
故乡的土地是雌性的,河流是雌性的,人们是雌性的。故乡的父亲是雌性的。虽然他常常跑去镇上找女人,但我和母亲都知道他是雌性的。也许他在故乡是雌性的,一旦到了镇子,见到喜欢的女人,就会变成亢奋的雄性;也许他在旱季是雌性的,一旦到了雨季,雄性特征就会被浇醒,长大,膨胀,喉结凸出,茂密的胡须一夜之间袭占他白净的脸。父亲在雌性和雄性之间来回变换,也许就像我的故乡。
故乡只有雨季和旱季。半年雨季,半年旱季。
逢雨季,雨没完没了,头顶的太阳,总是湿淋淋的。连阳光都是湿的,抓一把,攥得出水来。难得天气放晴,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会儿回来,拨弄着头发,说,晒湿了啊。她躲进里屋洗澡,背冲向我,身体颤栗着,喉咙深处发出压抑的痛苦并且快乐地呻吟。雨季将故乡浇透,将各种各样的种子催出芽苗,将所有的河流灌满,却从不溢出一滴。雨水湿了所有的女人,她们的脸色有了光泽,声音变得水淋淋的,体态曼妙轻盈。无论她们走到哪里,头顶都会伴随着一团淡粉色的若有若无的水汽,身体深处都会散发出一波又一波好闻的青草气息。这时的女人需要男人。这时的母亲需要父亲。这时的父亲每天都会去到镇上。父亲吹着口哨,推着自行车,趟过一道沟渠,涉过一条河流,走过故乡的桥。父亲去镇上修伞,扯起京戏小生般的嗓子喊,修伞啦!惊得女人们放下手里的针线,又将指尖伸到嘴里去吮。一把伞能用很多年,父亲的生意并不多,所以除了修伞,父亲还给镇上的女人们开药方。不收钱,医好再给。这绝对是无本生意——没医好,女人们认为正常。医院里都医不好,父亲怎会医好呢?何况父亲是免费的,医院是收费的;万一医好了,就认为父亲是民间神医,就会用尽她们的一切来感谢父亲。后来父亲告诉我,他开出的方子都是补品。世上总有一些病,看似没救了,其实等一等,便可不治自愈。父亲聪明得过分。
到了旱季,故乡不见一滴雨星。松软的砂土层让雨水很快渗下去,河流和沟渠,迅速变得干涸。阳光抖一抖,甩尽最后几滴水,变成另外一副样子。它暴烈,狂躁,恶毒,走进它,你会感觉它正在吮吸你身体深处的水分和血液,直到把你变成一副僵尸模样。受难的首先是女人。她们变得皮肤暗哑,嗓音嘶哑,粉红色的水汽消遁,身体深处散发出骡马饱嗝般的难闻气味。又有风,肆无忌惮地刮,赶跑太阳,故乡成为风的故乡。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故乡变得混沌,天地不再分明。风是一只怪兽,全副武装: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尖锐的指甲和牙齿,分出叉的芯子和蝎尾上的钢针……你能想到的一切,风里全有。风柔软,能够钻进故乡最狭窄的缝隙;风坚硬,能够劈开故乡最稳固的建筑;风锋利,让故乡人的手和脸,多出一道道狰狞的血口。那是地狱般的故乡,一马平川,千疮百孔。
这时母亲并不需要父亲。每天她坐在床上,守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室外天线被狂风刮得踉踉跄跄,电视上的画面被刮得踉踉跄跄,床上的母亲踉踉跄跄。父亲缩在墙角看书,书没头没尾,父亲看得津津有味。一会儿父亲抬头,瞅瞅母亲,说,你说咱们生活的地方是不是一粒沙子?你说咱们是不是沙子上的一群蝼蚁?沙子滚来滚去,就有了风和雨。母亲不看他,歪起身子,与电视里倾斜的画面保持一致。父亲丢下书,看看旁边的我,扳倒母亲,粗鲁地脱掉她的裤子。母亲的身体干燥并且粗糙,即使白天,我也能看到幽蓝的火星在她的皮肤上蹦跳闪烁。一起蹦跳的还有父亲灰色的阳具,它灰头土脸,呆头呆脑,完全没有雨季时的壮硕蓬勃。我听到母亲发出猫般惨烈痛苦的号呼,我听到皮革磨擦皮革的声音,石头磨擦石头的声音。这时的母亲并不需要父亲,或许这时的父亲也并不需要母亲,可母亲毕竟是女人并且是年轻的女人。漫长的旱季里,父亲只能将母亲想象成镇子里那个妩媚病态的女人。
旱季里,即使父亲去了镇上,那个叫雨的女人也不会服侍他。仅那么一次,在堆满盆盆罐罐的狭小木屋里,父亲强行将雨摁倒。雨挣扎着,反抗着,骂着父亲,眼睛紧闭,私处紧闭。那天父亲终未成功。后来父亲坐在一个脸盆上抽烟,问她,攒这些东西干啥?她说,想开个杂货铺。父亲轻哼一声,没说话。父亲和雨都是胆子很大并且能够预见未来的人——那时候,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将土地承包到户,但这里的生产队还没有彻底解散。
雨季里,几乎每一天,父亲都会去镇上。他去镇上,也许只为雨,也许还为别的女人。那时的雨并不在乎,她知道父亲并不应该属于她或者并不应该仅仅属于她。修伞和药方对父亲来说是借口,对她来说或许也是。她和父亲残忍地将潮湿的母亲扔在沟渠纵横的故乡,任母亲在孤独与虚无之中一天天老去。有女人劝母亲,说她可以随便找个男人,说雨季的男人个个都是蛤蚧,累不倒的。母亲不说话,我看到淡粉色的水汽在她的头顶聚集,竟有了光环般迷人神圣的色彩。一天午后,正睡觉的我被母亲的抽泣声扰醒,发现家里多出一个男人。男人正在低头穿鞋,母亲裹一条毯子,缩在墙角。那是父亲读书的位置,此刻却蜷着我的母亲。毯子破出两个洞,母亲两只粉嫩并且饱满的乳头高调地露出并且扬起。乳头淌下汗滴,连那汗滴也是粉红色的。母亲捂住脸,我听到两根睫毛被她长长的指尖“啪”地掐断。我听到男人说,你。我听到母亲说,滚。我听到男人说,你应该。我听到母亲说,滚吧。男人穿好鞋子,回身拥抱母亲,却被母亲赏了一记狠辣的耳光。然后便是母亲长达十几分钟的嘶嚎,似乎挨打的是她。男人是父亲在故乡唯一的朋友,有微卷的头发、直挺的鼻子和微驼的后背。他们常常聚到一起喝酒,父亲对他说,朋友妻,不可欺。
我一直不知道那天到底是母亲勾引了男人还是男人勾引了母亲,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过真正的性爱。待我稍大些的时候,我想问问母亲,那时的母亲,却早已不在。
母亲一直有病。她曾不止一次让父亲给她开方子,都被父亲拒绝。父亲的理由是那些方子是骗人的,母亲却坚定地认为父亲是为了省钱。母亲是在雨季死去的。这样的季节里,故乡的女人如同不会死去亦不会老去的妖精。母亲是第一个死在雨季的女人。
父亲总想逃离故乡。他向往小镇,渴望到小镇定居。他曾与母亲商量,母亲坚定地摇着头,不。然后,对着雨,或者风,或者太阳,发呆。我想母亲怕了。她怕离开这里,她怕去小镇。然我总是认为父亲不过随口说说罢了。尽管他会修伞,会给女人开方子,但离开土地,父亲很难生活得很好。何况那时候,搬家会牵及很多。
又一个雨季,雨将临街的屋子收拾出来,摆上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香烟白酒,父亲帮她在木墙上用油漆刷上“雨姐杂货铺”,钱就来了。那是什么都好卖的年代,一个雨季过去,雨就变得阔绰。她会买很多好吃的,有些是为自己,有些是为父亲。每天父亲都要去镇上找她,骑着自行车,来回四个小时,父亲并不嫌累。后来,父亲甚至会住在镇上,宿在雨的木屋。镇上很多人都认识父亲,去雨的杂货铺,不喊雨,只喊父亲。伞,给拿包烟!他们称父亲为“伞”,父亲很满意这个外号——伞与雨是一对矛盾的存在——有雨才会有伞——伞抗衡雨,离开雨又毫无意义,失去自我——父亲美滋滋地拿烟收钱,将泡在故乡雨里的母亲和我忘得干干净净。
翌日黄昏时分,父亲回到家中。走进院子父亲就闻到铺天盖地的死亡气味,如同皮革发霉、稻草发酵,气味在院子里翻滚,险些将父亲灌倒。父亲扔掉自行车,叫着“毁了毁了”,跌跌撞撞地冲进屋子。他见到身体冰冷的母亲。母亲直直地挂在房梁,一只鞋子滚落床前。年幼的我抱着那只鞋子,表情呆滞地研究着鞋面上的图案:两朵荷,两只戏水的鸳鸯。
死去的母亲让人恶心。自缢前她扎紧裤腿,试图死得干净,结果却变得更脏更臭。父亲用了整整一夜才将她冲洗干净。冲洗干净的母亲变回一朵洁净的莲,我重新闻到她的芳香。
我对父亲充满憎恨又充满感激——父亲让母亲在雨季里自杀而死,却把我送进县里最好的学校。后来我考上师范,学音乐,认识了鑫,与鑫有了刻骨铭心的恋情。鑫学的是体育,却精通琴棋书画。鑫仪表堂堂,又高又壮,敢与牛比力气。鑫迷恋我的身体。他表达迷恋的方式就是不停地画我的裸体。一张又一张,姿态各异。然他从没有要过我。
母亲死后,父亲再去镇上,只能将我托付给邻居。故乡很大,很散,沟渠与河流将平坦的土地切割得如同杂乱无章的蛛网。最近的邻居距我家足有三里之遥,父亲丢下我,对邻居说,麻烦你。
邻居不怕麻烦,因为父亲总会塞给她一点钱。父亲说这些钱是给妮买奶粉的,但邻居总是将钱昧下,然后用她的奶喂养我。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她的乳头:左边大,右边小;左边淡红,右边暗红。当她的女儿也想吃奶,我和她的女儿就会一人一个乳头,“吧嗒吧嗒”地咂。那个雨季她被我们咂得很瘦,身体却仍然水灵,乳房却仍然饱满。我还记得她叫采菱。这是一个应该出现在戏曲里而不是出现在故乡的女人的名字。
旱季时,采菱乳汁干涸,父亲也不再往镇上跑。他缩在墙角看书,我咧开大嘴,“嗷嗷”地哭。父亲烦躁地丢开书,凑近我。饿了?我哭。渴了?我还哭。父亲往手指上吐一口唾沫,笑着抹上我的嘴唇,然后继续看书。杀死父亲的想法正是那一刻在我的心中扎根,然后越长越大,开出花,长出果实,结出种子,将我的脑子和身体变成复仇的森林。每天我驮着森林走路,吃饭,睡觉,唱歌,跳舞,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现实中与木做爱,意念中与鑫做爱,我倍受折磨。
我成了父亲的累赘,所以父亲曾一度想把我扔掉并终于付诸行动。过完年,父亲决定搬去镇上,他将所有东西收拾妥当,盯着我抽烟。父亲一连抽掉五根烟,抱起我,走出村子。他走出很远,将我放进一条沟渠,旁边,一只死去的狐狸正被一只鹰开膛破肚。父亲又抽掉一根烟,在我脸上摸了摸,捏了捏,掐了掐,起身离开,没有回头。我看到他越走越远,风和黄沙让他变得越来越模糊,终于彻底不见。身边的狐狸已成一副白色骨架,现在鹰盯紧我,喙上血迹斑斑。我知道我大限将至,因为我看到小鬼。小鬼们纷沓而至,皆奇形怪状,一身红袍。它们挤眉弄眼,嘻嘻哈哈,我想它们一定在商量是烤了我还是煮了我。然后,小鬼之中,出现父亲。父亲赶走小鬼,抱我入怀,他的胸膛比我的身体还要冰冷。一滴泪未及落下,便结成冰,冰珠砸上我的脸,如玉击盘。父亲亲着我的眉毛,哭着说,妮,去镇上。
我的一个脚趾被严重冻伤。那伤伴我一生。连同我对父亲的仇恨,以及感激。
搬到镇上的父亲不再修伞和开药方。都说父亲有钱了,不屑再做那些事情,但我知道是雨不让他做。父亲可以迷倒雨,也可以迷倒别的女人,雨不想给父亲太多机会。或者说,以前的父亲是放养的,现在的父亲是圈养的,以前的父亲没有主人,现在的父亲必须听话,这大不同。每天父亲守着杂货铺,抽着烟,眼里偶见故乡的轮廓。雨坐在他的身边,往嘴里丢着瓜子,嗑出满屋香气。幼时记忆里,雨总在不停地嗑着瓜子,这让她的两个门牙之间磨出一个明显的凹糟。那凹糟非但没有减损她的美丽,反更增添她的妩媚和慵懒,有时父亲与她接吻,就会不停地用舌尖弹击着她牙齿间的那个凹糟。我听到清脆的“啪嗒啪嗒”的声音,就像一个小鬼在啃食一个孩子的手指。我迷恋那种声音。
父亲总会见缝插针地溜出杂货店,到镇上闲逛。镇子不大,一条叫做“红水河”的河将小镇分成镇北和镇南。“红水河”最初叫“清水河”,是鲜血将它染红。
据说解放以前,住在镇南的都是有钱人,住在镇北的都是穷人;解放以后,没过几年,镇南和镇北就变得一样穷。四九年旱季,国军赶走共军,将绑得像粽子的俘虏拉到河边,让他们面朝河水跪成一排,然后从第一个人开始,一枪一枪地打;到了雨季,共军打回来,赶走国军,同样将五花大绑的俘虏拉到河边,让他们跪成一排,从第一个人开始打……那年雨水很大,洪水泛滥,水中裹挟了大量的泥沙,河水混浊不堪。然待洪水退去,河水却并没有返清。便有人说,死人太多,血水渗进河床下面了。又有人说,死的那些人,都成了鬼。鬼每天拿根针扎自己的脖子,河水就成了血水。两种说法都不可信,毫无道理。可是后来,从来不见荷花的河里竟然长出荷花,事情就变得诡异并且恐怖。起初荷花们老老实实在河水里生长,后来就蔓延到岸边,甚至蔓延到人行道上。人行道上的荷花完全变异成向日葵的习性,它们迎着太阳,并不理会干燥坚硬的街道上不见一滴水。最初的花苞是粉红色的,然后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到它完全绽放之时,迎向阳光,几乎可以看清花瓣上错综复杂的血管。当花朵们受伤,就会流出深红的黏稠的微腥的血。夜里,有时候,河水深处会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和哀求之声。曾有个参加过枪毙国军的镇上男人终忍受不住,在有月的夜里投河而死。有人见过他投河的情景,说他至少在河面上狂奔二十余步才慢慢沉下去。沉下去之前,他甚至从容地■一杯河水,一饮而尽。然后月光如血,红水河散发出阵阵血腥。这件事越传越邪乎,所以后来,很少有人再敢在夜里去红水河边。包括胆大如牛的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