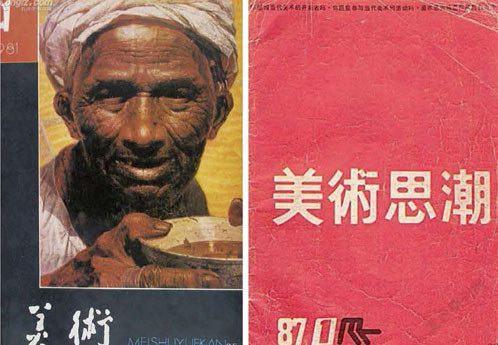


地标,是个舶来词,源于中世纪英语,特指用来标记边界、疆界的物体;发展至19世纪60年代,用于指代在风景中容易被注意到的物体;直到1959年,词典对该词的注释除上面提及的两点外收编入新释义,亦可用于指代在历史上被认为重要的事件。从地标一词的词源及词意演变过程可见,地标最初仅仅指代自然之物或人为之物,“地”与“标”二者并重,词意取二者的结合点,故而二者不论何种,皆为实际可感之物,并与地理范畴有一定联系;而后地标一词在演变过程中词意“地”与“标”二者逐渐分离,并将地标一词的词意重心转移到“标”上,强调的是“标”“标识”“标杆”这种“突出”“显著”的词意,故而“地标”一词的含义从有限的地理范畴走出来,较之前更加宽泛了,从物质层面拓宽至精神层面,即不单指地理范畴上的标杆物体,亦可指代同一范畴内的标杆物体或标杆事件。
恰如此,“地标”一词才具备成为本次展览名称的可能性。嘉德艺术中心酋展推出“地标”,由此可见策展人深谙该词词崽,一词多指:其一,展览选择当代艺术中具备“地标”性质的艺术家:其二,展览选择创作主题与“地标”相关的艺术作品;其三,一语双关,希冀新嘉德艺术中心如展览所说成为首都文化新地标。其中,对于第一条所涉及的艺术家“地标性”地位,单位艺术家的地位且不是一篇短评及一人之言可以言之,更妄论十五位艺术家,故而第一点不作为本文的探讨对象。对于第三条的美好希冀,自将交与时间留待日后去定夺,故而本文亦无须作探讨。对于第二条展览主题与参展作品的关联性,从地标一词的广度及艺术作品的创作多样性角度而言,似乎仍有一定的探讨余地。
其实不论狭义的地标,即早期还未与地理范畴脱离关系的地标;还是广义的地标,即后期用于泛指标识性事物的地标,其形成过程皆为特定时期下,一定时间内,某事物以其某一特定方面先天的突出或后天的塑造成為集体关注的对象,并在时间作用下成为一段特定集体记忆的寄托、纪念或代表。所谓集体记忆,一般指一个群体所其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物。因此地标通常要求事物具备一种标识性功能,为群体所其同认可,普遍认知。这种“标”指向“集体”,故而早期的。地标”更多的指向一种时间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背后隐没的是权力阶层的选择以及拥护阶层对于选择的认同,二者的意识所达成的其识,换言之也是“集体记忆”。至于后期的“地标”,本质上与早期无异,二者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后期的“地标”可供权力阶层选择的可能性更加广泛一些。
由此可见,地标与集体记忆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地标多数时候相对应地指代一种物质性存在,而集体记忆则多为指代一种存在于大脑崖面的精神性存在,地标往往是一段集体记忆的物质性投射。记忆是虚妄的,会随着记忆群体的逝去而消散,历史之所以留存是因为有记录,有文字记录,有物体佐证,有痕迹佐证;同样的,集体记忆亦是会逝去的,故而地标对于集体记忆而言,其意义就在于记录、纪念、寄托。故而从这种集体性及记录性而言,地标并非个人的选择,而是集体的选择。就这点而言,关于参展作品是否与本次展览主题相关联,可将集体记忆作为评判依据及关键点做出一点客观的评判。
徐冰《鬼打墙》的创作对象是长城,长城在古代中国是巍峨的坚强的军事后盾,而在作品中艺术家用纸的柔软性去对抗其固有属性,颠覆了长城在集体记忆中的固有形象。黄永砅《嗡嘛呢叭咪哞》在藏传佛教的转经筒上刻三种不同宗教的经文,这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有悖集体记忆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企图虚构集体记忆的无力。刘建华的《义乌调查》则是通过体嚣堆积的视觉冲击直接唤醒观者对义乌的集体记忆。喻红的《她——宝塔山姑娘》试图通过刻画一个个体的、渺小的、轻松的女性形象去消弭宝塔山在集体记忆中历史的、国家的、革命的、严肃的宏大形象。刘驜的《爱它,咬它No.3》同样采取一种有意为之的有悖集体记忆的方式,通过扭曲塌陷的地标建筑去抵消建筑本身的华丽、宏伟属性。
以上提到的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地标建筑、宗教物品或地名等具备社会关注焦点的物体进行创作,实际上艺术家选择对象的同时考虑的是与该对象相关联的精神性投射内容。艺术家选定对象以后对其采用颠覆、虚构、弱化等手段,人为地弱化甚至阻断观众观看作品时所产生的集体记忆的关联性纽带,从而达到迫使观众思考与反恩的目的。以上所述,艺术家对于某段具体集体记忆的选择及相对应的物质性投射对象的选择和再创作,是这个“地标”展览中作品创作方式应共同具备的本质特性。
展览“地标”的选择标准已经明了,并非表层上的地标建筑,亦非表层上的地理方位,而是在于那些与之相关的并且能够令人产生共鸣且思考的对象。故不得不提出一点质疑,即未提及的作品中;与地标的关联性体现在哪里?未提及的作品之所以构成上述疑问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作品的叙述方式是个人化的,如果抛离文字叙述单就作品本身而言,观众难以得出与艺术家最初设想一致的解读,其中的原因在于个人的不可控性所造成的解读多义性,追根究底是脱离了集体记忆作为作品创作、思考的线索与依托;其二,作品创作所选择的对象是鲜活的,时下正在发生的。地标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在于,先有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在时间的作用下自发生成一个地标作为精神性投射;抑或由权力阶层主动选择一个地标,然后开始发生关于该地标的集体记忆。鲜活对象的问题在于,主体可能未经历时间的选择和洗礼,未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共识,或者主体已形成集体记忆但尚未发展到自发选择地标的阶段。即其鲜活性注定了主体达不到集体记忆选择地标所需要的时间维度,实际上是对于集体记忆与地标关系的一种被动性的无意识脱离。这些作品对于集体记忆和地标二者及其关系的脱离最终导致了其作品与展览主题——“地标”的关联性不强。
“地标”一词立意甚好甚巧,同时主题性展览的力量理应源自于所选作品的本质统一性,作品无论是在直接或象征意义上,或就其社会性的效果,都如同地标一般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和面对现实。这些地标塑造了我们的过去,也在创建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