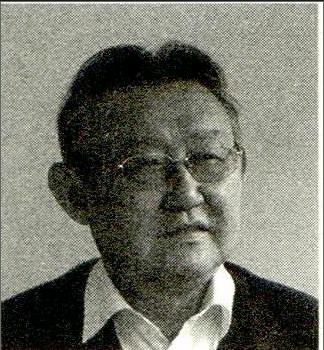
七年前的那个夏天,朝克巴特尔将一百来只羊托付给邻居萨仁其木格,自己用马车驮着重病的父亲赶往旗为父亲治疗。那年他十八岁。那次他是实属无奈,在这片小谷地上原本住着五六户人家,可其他住户都先后搬走了,只留下萨仁其木格和朝克巴特尔两家。连年干旱,草场退化是那些人搬走的一个因由;邻村的人们时时来毁坏铁丝网,偶尔还发生斗殴也是他们搬走的原故。所以,没能力搬迁的朝克巴特尔父子和单身女人萨仁其木格三人只好留在这里,现在朝克巴特尔要送父亲去看病,只能将羊群托付给萨仁其木格。
萨仁其木格家就在朝克巴特尔家西南两三里的地方,所以朝克巴特尔走出屋子站在门口就能看见她家。他常看见胖墩墩的萨仁其木格总是忙得屁颠屁颠地走在自家巴掌点大的草场上,或在进进出出地忙碌。出发前的晚上,朝克巴特尔向萨仁其木格家走过去。他走在旱年零星生长的草丛间,临近萨仁其木格家时便看出单身女人生活的艰难和力不从心。她家后边已经形成了一弯沙丘,从沙丘到房屋的这点距离扔着诸如一截烂绳子、一只破旧的鞋子、一截锹把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萨仁其木格的丈夫几年前就和她离婚,弃她而去,她唯一的儿子在旗里上小学,所以,萨仁其木格独自生活,忙得焦头烂额,什么都顾不过来。
朝克巴特尔对萨仁其木格提到去旗里的事,说:“要烦劳嫂子您了。”朝克巴特尔从小就称呼萨仁其木格为嫂子,萨仁其木格管朝克巴特尔的父亲叫大哥。因为萨仁其木格比朝克巴特尔大十七八岁,朝克巴特尔的父亲比萨仁其木格年长十几岁,所以他们如此称呼惯了。
萨仁其木格说:“巴布哥的病情加重了?唉,可怜啊,从春天开始,他脸色就憔悴了……你的羊群你放心,我替你放着,你带巴布哥好好治病。真可怜啊……”说到这里,她的嗓音开始嘶哑。她略微思索后,从里屋拿出两百元,说:“春天剪的羊毛还没卖出去,除了这些,我也无能为力了……”说话间,她的双眼溢出泪水。
朝克巴特尔急忙说道:“给父亲看病的钱我有。”
萨仁其木格生气地说:“你虽有点钱,但这些还能够贴补点呀?”说完把钱硬塞给朝克巴特尔,说:“我明早去你家,把你的羊赶过来。”
朝克巴特尔在旗医院待了十几天后,只好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父亲带回家。于是,萨仁其木格也把自家的羊群赶过来,住在朝克巴特尔家里,将两家羊合了群,还给他们父子熬茶做饭,有时还伺候料理卧病在床的巴布老人。晚秋过后,朝克巴特尔的父亲去世了,萨仁其木格帮朝克巴特尔安葬了父亲,哭得比他还厉害。
此后,萨仁其木格时时过来帮忙朝克巴特尔,提醒他管理羊群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又给他缝补撕破的衣服,有时因怀念朝克巴特尔的父亲而哭泣。还有时,萨仁其木格一受到邻村人们的欺负,便来他家诉说心中的酸楚……
邻村的人们很霸道,根本不把朝克巴特尔和萨仁其木格放在眼里。他们在萨仁其木格的草场边开荒,还在朝克巴特尔门口放羊,肆意破坏掉他们两家的铁丝网。萨仁其木格、朝克巴特尔两人去跟他们吵架理论时,对方却似乎对他们不屑一顾,似乎将他们的怒吼声当做耳边风,若无其事地为所欲为。有一次,萨仁其木格忍无可忍,向前冲去抢夺对方的犁杖。掌犁的壮汉却毫不理睬她,一手扶犁,用另一支手冲她拨拉了一下,胖墩墩的萨仁其木格便如风中飘起的破烂衣服一般甩出很远。她躺倒在地,昏迷几分钟,清醒时只见那壮汉还在若无其事地犁地。有一次,朝克巴特尔抽打赶走在他家门前吃草的羊群,没过多久,从邻村来了三个年轻小伙子对他说,你打伤了我的几只羊,要赔我们,就从朝克巴特尔的羊群里抓了一只大羯子,扬长而去。朝克巴特尔和萨仁其木格被逼无奈时,就去找嘎查书记那玛海告状。那玛海却总是挠挠头,笑着说:“这事我们不仅上报到了苏木,还报到旗里也很久了,就看他们怎么处理吧。我是拿他们没办法呀。”萨仁其木格喊道:“那如果他们也没法子,我们怎么办?”
“你们只好自己小心谨慎喽。”
“你们当领导的就不为群众做主吗?”
“难道我去帮你们和他们打架吗?”
萨仁其木格一来气就大喊大叫,可朝克巴特尔越生气就越说不上话。萨仁其木格说:“我们在那里没法活了,让我们搬迁吧!”
“现在草场都各有其主,你们如果商定好在谁的草场上居住,当然可以。”
“嘎查不是有剩下的草场吗?”
“不是大家商定那是全嘎查的打草场,不能住人家吗?”
“可是巴音琪琪格在那里居住了呀?”
“旗里一位当官的同意巴音琪琪格在那里居住的。那位领导给苏木打电话,苏木的领导又给我下达的命令,我们也只好答应。如果你和旗里的某个领导有交情也行啊。”
萨仁其木格、朝克巴特尔从那玛海家出来。返回家的路上,萨仁其木格走一路骂一路。看着萨仁其木格恼怒的样子,朝克巴特尔怜悯之心顿生。朝克巴特尔刚才注意到,那玛海说起巴音琪琪格时,是何等的笑逐颜开!那一丝笑颜背后显露着一层意思:人家巴音琪琪格年轻貌美,你一个年近四十的胖老婆子还妄想和巴音琪琪格一样占大便宜?朝克巴特尔想到,萨仁其木格也可能察觉出那玛海的想法而倍感憎恶,于是怜惜萨仁其木格之心油然而生。
那天,朝克巴特尔跟着萨仁其木格去她家后,大献殷勤,弄来柴火,煮起奶茶,千起杂活。他想,通过这些举动,能稍许慰藉这位女人。萨仁其木格上了炕,翻过身躺了一会儿后,忽然猛地起身说:“你杀一只羊,今天咱俩喝口新鲜的羊肉汤。”
朝克巴特尔怔住了,说:“为什么想起要杀羊?”
“吃自己的羊,想杀就杀,想吃就吃,谁也管不着。等什么时候都吃光了再带着木棍讨饭去。”
于是,朝克巴特尔宰羊,萨仁其木格包饺子,那天晚上他们俩像过年一样,来了一场饕餮大餐。
萨仁其木格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
“还要……喝酒吗?”
“怎么不喝?难道我们不是人吗?人家享用的东西,我们也享受一番,怎的?”
从来不喝酒的朝克巴特尔在那天晚上初次喝醉,萨仁其木格不久便唱起歌。因那一晚太过闷热,萨仁其木格敞开门窗,解开领扣,不时擦拭汗水。萨仁其木格嘶哑的歌声飞出窗外,消失在黑暗中。
萨仁其木格说:“我们小时候,流行过这么一支歌。”说完,整了整嗓子唱开:
半圆的月亮
幽幽悬挂在苍穹
呼唤彼此的骏马
在荒野上嘶鸣……
朝克巴特尔不由用醉眼凝望萨仁其木格,觉得她变得年轻漂亮许多。她那圆嘟嘟的肩膀,撑起衣服的奶子都近在咫尺。朝克巴特尔望着萨仁其木格的奶子,想起一件事,不由想笑。早在朝克巴特尔是孩童时,萨仁其木格已经嫁人生子。有一次,朝克巴特尔放羊,碰见萨仁其木格在自己的羊群旁给儿子喂奶。朝克巴特尔跑到她面前,她就抓起奶子对着他说:“想吃奶吗?”不知是被那大奶子吓着了,还是害羞了,朝克巴特尔撒腿就跑,还听见萨仁其木格在背后哈哈大笑。
萨仁其木格说:“我们年轻时不知疲惫,虽然整天为牛羊忙碌,晚上还到彼此家里喝酒热闹。儿子还小时,我用布腰带把他背着赶场子,从不曾落下。”说完,她又唱起歌。
朝克巴特尔想,谁都曾拥有青春岁月,所以萨仁其木格也肯定常常忆念起自己的青春时代。谁能忘却自己劳碌而欢乐,时常感到满足又时常觉着委屈,但又不愿意示弱的青春岁月呢?
萨仁其木格眯缝着醉眼说:“朝克巴特尔,你现在已经十八岁了,十八岁的小伙子应该追着姑娘跑。可你怎么是垂头丧气的?没听说过十八岁是一团火,二十五岁就像一头发疯的公牛吗?”
朝克巴特尔支吾着说:“我……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只觉得,他俩都醉了。
“那时,我和我的男人还没结婚。若三两天看不见他,我在夜里就睡不着。后来,我们俩结婚,我才放下心来,觉得相恋的男人属于我了。其实,我想错了。如果我们没结婚,仍保持那种关系,我就不会那么可悲喽……”
左邻右舍都晓得,萨仁其木格的丈夫几年后不再喜欢她,弃她而去。朝克巴尔特忽然觉得,如若那个男人不曾抛弃她,她不会如此受苦受累。
“过去我男人不喜欢我,现在儿子也不喜欢我了……”萨仁其木格说着,快要哭出来,又说:“我这是开始胡说什么呢?还要唱呀……”
接着,她又唱起了《半圆的月亮》。朝克巴特尔从小就听过这支歌,但不会唱。如今萨仁其木格一唱起来,让他感到十分动听。
明亮的弯月
幽幽悬挂在天空
寻觅至爱的鸟儿
在辽阔原野上鸣唱
最后,朝克巴特尔朝着自己的家踉跄走去,中途却倒在野外睡着了。《半圆的月亮》的歌声依旧萦绕在他耳边。乍一想,似乎萨仁其木格站在身旁唱歌,又一想,觉得自己在唱。
翌日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光芒分外耀眼。他坐起来,只觉全身瘫软,冒出冷汗,不由作呕。为什么喝那些苦水呀?他非常懊悔,站起身一看,萨仁其木格家就在附近。他想人一喝醉就难以自控,昨天自己是否在萨仁其木格面前胡作非为,丢掉脸面?于是觉得再没脸见萨仁其木格。
但是,萨仁其木格望见了他。
萨仁其木格说着:“嗨,你倒在路上睡了吗?让你在我家过夜,你偏不要,一个劲儿地要回家。”便来到他身边邀他到家喝热茶再走。
朝克巴特尔跟着萨仁其木格到她家,把茶喝得直渗汗。萨仁其木格的眼睛虽然红肿,可还是欣喜地谈笑风生。
“昨夜咱俩为什么醉成那个样子呀?”萨仁其木格笑着说。
“是呀,真是的。”
“有空就来吧。”
“好的,好的。”
从此,萨仁其木格更频繁地出入朝克巴特尔家,还隔三差五,就叫朝克巴特尔来自家吃饭。朝克巴特尔两日不见萨仁其木格,就倍感孤独。那些日子里,朝克巴特尔似乎快乐许多,萨仁其木格也穿戴起漂亮衣裳。
虽然有诸多的艰难和不如意,但他们也有欢乐。他们的欢乐就好比穿过厚厚的云层缝隙照射的阳光,虽不常有,但也是实实在在。光阴荏苒,不知不觉间过了七年,朝克巴特尔到了二十五岁,萨仁其木格已到四十三岁。
大前年的一天,在旗里维修电器的莫日根特古斯在摩托车上驮着酒来看望朝克巴特尔。莫日根特古斯的家也曾在这个谷地,他和朝克巴特尔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个班级学习。后来,莫日根特古斯家搬走,他在旗里一家维修电器的小铺子里当学徒。
“我就想看看你过得咋样,就骑摩托跑来了。”莫日根特古斯笑着察看屋里屋外,还往羊圈瞅了瞅,说:“过得还不算太差,勉强活得像个人。”
朋友的到来让朝克巴特尔高兴不已。当年临近高中毕业时,莫日根特古斯他们俩在私下里悄悄谈论“能不能考上大学。”其实,他们彼此都知晓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的命,可偶尔谈论起来,还感觉挺美好。当然两人只是悄悄一谈,唯恐别人听见。如果同学们知道,可能会嘲笑说:“这两个没出息的家伙还妄想考上大学,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他们想,癞蛤蟆都想吃天鹅肉,只有暴露意图的癞蛤蟆才被人们嘲弄。
朝克巴特尔熬奶茶给朋友喝,又煮起干肉。
莫日根特古斯毫不客气地仰卧在炕上,问道:“邻村的人们还来捣乱吗?”
“还是那样!真拿他们没办法。”
“上旗里打工也比这里受苦受累强啊。”
“我这不是舍不得这块巴掌大的草场和百十来只羊么?”
“把这些都卖掉,再走呗。”
朝克巴特尔觉得,这也算是一条出路,可是他走了,萨仁其木格怎么办?这两年以来,朝克巴特尔和萨仁其木格一直互相帮忙,为彼此操心。有一次,朝克巴特尔为挣钱,要出去打工二十来天,萨仁其木格给他整理行装,还再三叮嘱他注意事项。二十来天过后朝克巴特尔归来,他远远望见萨仁其木格站在谷地北边等他。也许她每天都这样等我的吧,他这样想着,不由心头一热,快步朝她跑去。
“天啊,你变黑变瘦了……”萨仁其木格叹了一口气说:“我想你今天可能回来,特地给你炖了肉。”
俩人有着谈不完的话语,一路欢笑畅谈。朝克巴特尔一进屋,便从包里拿出一件衣裳和手上涂用的一小盒防冻油,说:“这给你买的。”
萨仁其木格高兴得将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看几遍后说:“你真会买东西。这种结实的衣服对我们这样干粗活的人最合适不过。”她又凝视着防冻油说:“这对我有用,一到冬天,我的手皮肤就会裂开。”
萨仁其木格端上肉,邀他吃喝,还问道:“工钱都拿到了吗?”说话间,她满面红光,很明显为朝克巴特尔的归来欣喜不已。
“拿到了。只要不怕苦,看来出去打工还是能赚到钱的。”朝克巴特尔说,“以后有机会我还出去,你照看咱两家的羊,我再赚点钱回来,也能添补点咱俩生活不是吗?”
“可外出打工太辛苦了。”萨仁其木格说。
想到这些,朝克巴特尔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萨仁其木格。于是,他扭转话题问莫日根特古斯:“你是住在旗里的人,有女朋友了吗?”
“自身难保的家伙哪有那种痴想。城里的姑娘看不上咱。”莫日根特古斯叹气,将杯中白酒一饮而尽。
“不会全是那样吧。”
“不挑剔的姑娘也碰不见。我也没办法呀。如果找个女朋友,买冰棍还不得多买一根吗?可是我要买一根冰棍,还得先考虑考虑兜里的钱够不够。”莫日根特古斯继续说:“你是住在乡下的人,可以找个憨厚老实的牧民姑娘,一起过呗。”
“你不知道,现在的乡下已经没有姑娘了,别说姑娘,年轻一点的少妇都跑到城里,不是当保姆就是当饭馆的歌手。”
“我怎么不知道呢?留在乡下的那些小伙子现在只能找比自己大的寡妇一起生活,没办法!无论如何,比起单过好,好歹彼此有个照应呀?”莫日根特古斯说完,忽然间似乎想到什么,说道:“萨仁其木格不是在你跟前独自生活吗?其实,她虽为中年妇女,姿色较好,为人也好……”
朝克巴特尔面红耳赤,急忙说:“你胡说什么呢?萨仁其木格的儿子吉日嘎拉图比我才小七岁。”
“那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吗?”
“你觉得无所谓就没一点关系。”莫日根特古斯继续说:“在我们小时候萨仁其木格还是个大姑娘,偶尔和我们嬉戏追逐。现在想来,觉得她在那时还算漂亮。时间过得真快呀!”
到晚上,两人已喝得烂醉如泥,躺在炕上鼾声大作。翌日,朝克巴特尔醒来,发现莫日根特古斯已经走了。他回忆起昨天跟莫日根特古斯谈过萨仁其木格,夜里又梦见了萨仁其木格。他清楚地记得,梦中的萨仁其木格变得愈加年轻美丽,笑靥如花地朝自己款款走来……
朝克巴特尔走到外面,看见萨仁其木格走在家附近。他想去和她见面,可一想,昨天和莫日根特古斯围绕她胡吹一番,夜里还梦到她,感到害羞,犹豫不决。
自从南方养蜂女来了之后,事情变得有些复杂。
莫日根特古斯走后的第二天夜里,朝克巴特尔听到汽车声渐行渐近。他虽被惊醒,但没当回事,又睡过去。翌日早上,他起床走到外面看见一位穿着蓝衣裳的姑娘走来。
奇怪呀,从哪里冒出这么个姑娘?朝克巴特尔伫立思索时姑娘已来到他面前,笑容满面的像鸟似地啁啾一番。朝克巴特尔费力地理解到她在问:“你的井在哪里?”
“你问井干嘛?”
姑娘继续啁啾后,朝克巴特尔再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他放羊时才看见自家的左下边有一顶帐篷和几十个蜂箱,才晓得昨夜一辆汽车拉来了这些东西。
下午,姑娘给他带来许多大小纸盒。朝克巴特尔看到盒子上有汉字,有些还有外国文字,所有纸盒上都有蜜蜂的图案,便晓得,这是送来了蜂产品。南方养蜂人每年光顾这里。他们从大老远雇车过来,搭起帐篷,几个月风餐露宿,到秋天再返回。操着一口叽里呱啦南方话,养蜂人风餐露宿的生活看上去让人感到怜悯,可他们依然精神抖擞,信心百倍。朝克巴特尔想,比起我们,他们有无穷的能耐和智慧,肯定能赚到大钱。又想到,我们却没有能耐和智力,所以受邻村人的欺辱,如果碰上他们,会把邻村的那些像烧火棍似的家伙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再把东西出售给他们。
养蜂女谈笑些许后说:“晚上到我那儿吃饭吧!”这句话总算让朝克巴特尔听懂了。
“不,我在家里……”朝克巴特尔犹豫不决。
“一人吃饭多寂寞呀?两人在一起谈笑风生地吃呗。”
“那就……”
残阳如血,将近落下时,朝克巴特尔跟养蜂女来到她的帐篷。小帐篷里面非常干净,床单和枕巾好像刚刚洗过,弥漫着女人用过的味道。养蜂女拿出折叠的铁玩意儿,操弄几下,那玩意儿变成桌子一样的东西。她再从一个箱子里取出牛眼大的几个盘子,将还不够塞牙缝的各种菜肴往盘子里放,又拿出一瓶葡萄酒。锅里还煮着挂面。
姑娘啁啾一番,举起杯子时,朝克巴特尔大致听懂她说的是:“为蒙古族青年的美好。”而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姑娘不时哈哈大笑,拍着朝克巴特尔的肩膀,还打开录像机,播放外国电影,其间与朝克巴特尔频频碰杯。‘
朝克巴特尔觉得,彼女来这片谷地有如干旱的天空中升起雨云,抑或萨日朗花在野地草丛中独自盛开。别小看彼女待在小帐篷里,里面可是飘散着女人的香味,开动小发电机观看着外国录像,一天换几次大都市姑娘们才穿的衣服,出落大方。他整天见到蜂箱那边的几个灌木丛上姑娘晾晒着色彩斑斓的衣服。姑娘天天来朝克巴特尔家里,每天都邀请朝克巴特尔到她那里去看录像。
朝克巴特尔也爱看录像。录像中的那泛着银白色浪花的大海,海里游泳后躺在沙滩上休息的男女,绿萍中蜿蜒的公路,公路上疾驰的小汽车……多么美的地方,多么有福气的人们啊!想到这里,朝克巴特尔感到自己的生活让人厌倦。
一天,朝克巴特尔去井边打水,碰见萨仁其木格给羊饮水,才想起七八天没见萨仁其木格,便说:“真是个好天啊。”说完就笑。
萨仁其木格没说话。
朝克巴特尔便知道萨仁其木格在生气,急忙说道:“这几天我感冒得……”他扯了弥天大谎。
萨仁其木格嘀咕着:“也许吧……”又用幽怨的目光瞄他一遍,扔下水桶,赶着羊走远。
朝克巴特尔打水回来,养蜂女匆忙赶来说:“哥啊,这里有用卡取钱的地方吗?”
朝克巴特尔虽然知道有那种用来存钱的卡,但自己却没有那种东西,所以发怔说道:“旗里或许有。”
“哎呀,那怎么办呢?”姑娘快要哭了。
“怎么了?”
“听说我妈妈生病了,我要给她汇款……”
朝克巴特尔一听,就急了。从这到旗里有两百里,看这姑娘的样子到旗里汇完款时她妈也许已经病死,谁知道用卡汇款的地方在旗里呢?
于是,他问道:“三千元够吗?”
“先给三千,够了。”
朝克巴特尔走进里屋,从毡子底下拿出三千元钱,交给姑娘,对她说:“你如果原路返回,会见到公路,在那搭上过往的车,走一个来小时就到苏木。在苏木汇款吧!”姑娘的眼睛噙着泪水,流露出一丝感恩之情,甚至是惊喜的神情。
姑娘说:“哥呀,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给你写借款收据吧。”
朝克巴特尔豪迈地说:“嗨,真麻烦。我们彼此间借东西时从不写那玩意儿。”
“要不……我把存款卡抵押给你。”
“别麻烦了,还不快去汇款?”
姑娘的眼睛更加湿润了,说:“我如今明白了什么是蒙古族青年,什么是蒙古故乡。”她在朝克巴特尔脸上亲一口就离去了。
朝克巴特尔自打出生以来,还没有被人如此夸奖,还没有体恤和帮助比自己还处于弱势的人。因此,他觉得,在此瞬间自己已经变成另一个人。还觉得,我帮扶弱势者,看到她感激涕零,如此看来我还是个有能耐的男人啊!
姑娘去苏木汇款,直到傍晚还不见回来。朝克巴特尔有些担心,给她打电话。莫日根特古斯上次来时,给他留下一部旧手机,如今派上用场。姑娘却说:“天色已晚,我住苏木旅馆,明天再回。”她的这番话让朝克巴特尔得以安心。那夜,朝克巴特尔梦到姑娘,梦见姑娘在返回的路上迷路,迷惘地游走。还梦见姑娘要回到家乡,汽车上装着那些蜂箱。梦境里汽车声久久轰鸣,渐渐远去。
翌日,他醒来等姑娘,等到中午还不见回来。他想,是否她一回来就睡在帐篷里,就去那里一看,眼前的一切几乎让他不敢相信,让他发蒙。姑娘的蜂箱和帐篷好像被风刮走一般不见踪影。他走过去看到汽车轮子新扎过的痕迹。于是,他知晓昨夜听到的汽车声原来并非梦境而是真有其事。
他虽想到事情不妙,但又想那姑娘或许有什么急事,夜里搬走,几天后可能会回来,抚慰着自己。过几天后,他想姑娘已不再回来,便给莫日根特古斯打手机。
莫日根特古斯听完,叫苦连天地说:“你被骗了。就当做把三千块钱扔给狗了。”
“如果打听,也许能找到……”
“你知道那姑娘的姓名和籍贯吗?”
“她说她叫小王。籍贯是江苏呀还是江西,反正带着一个江字。”
“那就把那姑娘连同三千块钱一并忘掉吧。”
“那……只能如此了。兄弟,千万别对他人说这事,人家会笑话。”
“不说,你放心。”
朝克巴特尔好几天都感到寂寥。一想起那姑娘曾泪眼汪汪地说:“我如今明白什么是蒙古族青年,什么是蒙古故乡。”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你是看透了像我这样的蒙古人,才如此欺骗我呀。”站在门口望去,萨仁其木格的家就在南面,离这里很近。于是,他想到十来天没见萨仁其木格,她还生我的气吗?等他坐下来思索时见萨仁其木格朝自己走来。
朝克巴特尔有些慌张,不过他没有对不起萨仁其木格。
萨仁其木格来到他面前,若无其事地一笑,说道:“我想麻烦你一次。”
朝克巴特尔兴高采烈地说:“没关系,为什么这样客气。”
“我的羊圈破了。”
朝克巴特尔晓得,萨仁其木格是让他修羊圈为由,与他重归于好。萨仁其木格一路与他欢声笑语,但只字未提养蜂女。朝克巴特尔到她家修羊圈,萨仁其木格忙着做饭。
四
到了秋天,朝克巴特尔看见萨仁其木格屋外隔三差五出现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主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家伙,在萨仁其木格家进进出出。有时骑着摩托走了,过两天又回来。朝克巴特尔不明白那家伙是从哪里来的。萨仁其木格仍在自己的家外忙碌着,但他发现萨仁其木格有时候穿着红衣服,有时穿着蓝衣服,就想起萨仁其木格以前没有那种衣服,可能是那家伙从什么地方的地摊上买来的廉价衣服,还哄骗萨仁其木格说,价格不菲。
一天,萨仁其木格来到朝克巴特尔家,对他说:“晚上去我家吃饭吧。”
朝克巴特尔想,亏你还偶尔想起我这个大活人,怨声说道:
“我没空。”
萨仁其木格扑哧一笑,说:“姐姐我独自生活,还真难啊。现在等到有人光顾我家了。实不相瞒,我想能凑合就凑合吧。所以,来请你过去。一来,帮我看看他的为人,二来,你们两个大男人在一起乐呵一番也方便,姐求你了。”说完,她眼睛里噙满哀求和请求宽恕的泪水。
朝克巴特尔也被感动了,说:“好的,我去。”他想,我能为这可怜的妇人帮上多大忙呢?再说,她的儿子才比我小七岁。
晚上,朝克巴特尔来到萨仁其木格家,虽对那个骑摩托的家伙表现得彬彬有礼,但还是觉得那家伙怎么看都惹人烦。
那家伙是四十来岁的高瘦黑脸汉,一见到朝克巴特尔就摆着长者的谱,冷冷地跟他打招呼,又嘱咐萨仁其木格说:“倒茶。”
朝克巴特尔尽力稳住自己,露出一丝礼貌的微笑,坐在炕沿。萨仁其木格生怕他们俩尴尬,赶紧端肉斟酒。
“请你们喝酒。”萨仁其木格劝几下酒后,给自己也斟了一杯说:“咱们喝三杯。”
那家伙装出一脸正经,说道:“还整两盘菜吧。你一个妇道人家喝酒干嘛!”朝克巴特尔咬着牙忍耐着,强作欢颜。萨仁其木格依照那家伙的话赶紧放下杯子,开始做菜。
“来,喝吧,但年轻人可不能嗜酒。”那家伙说。
朝克巴特尔说:“哥,你也喝……我给您敬三杯酒。”又继续说:“我当弟弟的先喝三杯。”
如此,开喝起来,不一会儿,朝克巴特尔醉了。
“哥骑的摩托真漂亮。”说话间,朝克巴特尔的眼睛在凶凶发光。
只听那家伙“啊,嗷”地答应着。
“可是摩托已经过时了,人们都买汽车跑呢。看来你似乎没那能耐。”
“啊,嗷……”
“摩托可厉害呀!一不小心它就驮着你飞下悬崖。断胳膊断腿是起码的事,虽然受重伤瘫痪,还能保住一条命,但说来那比死还难看。若重重一撞,还可能立马死去……”
那家伙还在:“啊,嗷。”
“你是老家伙。如果想娶老婆,从故乡娶个老太婆,哄自己开心就行。为何跑到这里来?”
朝克巴特尔仿佛听见那家伙的喊叫,脸色显得格外狰狞。
“你怎么变成三角脸了?变成五角、十角也是个破流浪汉。”
接着,听到嗵瞠作响声,朝克巴特尔顿觉,好像和他打起架来了。可不知道谁揍谁。他喊道:“我宰了你这个坏家伙!”
忽然一觉,整个世界变得非常寂静。仔细一听,还不算寂静,有人在嚎哭。屋里漆黑一片。
“那个流浪狗在哪儿?”朝克巴特尔喊道。
“已经走了。”萨仁其木格还在抽泣。
“什……么?”
“是你把人打跑了!”
朝克巴特尔的头脑一清醒,觉得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他喊道:“我……我不是人……”他虽想起身,却挣扎几下,又瘫软倒下。
萨仁其木格趴在他胸膛上哭了许久才说:“可怜的你啊,你有那种想法为何不早对我说呀?”她猛然亲吻朝克巴特尔一番。
五
从那夜晚后,朝克巴特尔再也离不开萨仁其木格家。朝克巴特尔觉得,萨仁其木格的那两间土屋让他感到难以言喻的温馨,自己以前独守空房的生活不是人过的。萨仁其木格也有了依靠,心情也似乎平静许多,她虽整天操劳,却很少生气,干活时哼着小曲,还不时化妆打扮起来。她十分注重让朝克巴特尔吃好喝好,让他像样地穿着。若给朝克巴特尔做上一顿好饭,买上一件新衣服,她比朝克巴特尔还欣喜不已。在此期间,萨仁其木格也变得比以前年轻漂亮,不由让朝克巴特尔感到好奇。
眼看着到了秋天。那些日子里,朝克巴特尔仿佛忘却疲倦,干起活来不知停顿。一个月光遍地的夜晚,朝克巴特尔忙碌着堆起白天割的草,萨仁其木格站在他旁边说着:“你这是堆起草山!”便哈哈大笑。她拿出手巾,为朝克巴特尔擦拭着汗水说:“现在到半夜了,休息吧,明天做也赶趟。”
“我想不停歇地干下去。你先去睡觉。我把这些草全堆起来再睡。”
“那我也不睡觉,待在你旁边吧。”
从夏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冬天,他们俩如此陶醉在幸福之中。到了冬天,朝克巴特尔要给萨仁其木格买一部手机。萨仁其木格犹豫着说:“你不是有手机吗?两人中间有一部不就行了?”朝克巴特尔倔强地说:“每人有一部更方便。你儿子也可能来电话。”他到苏木邮政所给萨仁其木格买了新手机。
萨仁其木格有新手机,高兴得不时给儿子打电话。她儿子几年前中学毕业,在盟里打工。他两年前回到家住两天就走了,再也没回来。朝克巴特尔知道,那儿子看不起生母。
朝克巴特尔放羊回来,只见萨仁其木格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萨仁其木格叹口气,说一声:“唉,我这坏小子……”又说:“既然咱俩要一起过,无论如何要给儿子说一声。可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什么都没说吗?”
“我对他说,你也年年不来,我独自在这里受累。我儿子却说,你想找汉子吧,你已经老了,那样丢人现眼,干吗?但怎么说,现在的牧场、畜群、房屋都有我一份。看来他的性格比以前坏了许多。照他那性格,如果跟别人吵架打斗,出了事,咋办呢?”
朝克巴特尔不知说什么好,踌躇一阵后说:“这也不能怪你儿子,儿子是父母遗产的主人啊。”又说:“你把所有财产留给儿子,去我那儿过吧。”
“可我不愿离开儿子,怎么说那是我儿子,还是独子。”萨仁其木格哭了。
“别太伤心,苦难这东西,一咬牙就过去了。”
“但愿今年过年儿子能来。真想和他开怀畅谈。”
“就给他打电话说,必须回来。”
春节渐渐临近。一天,萨仁其木格笑容满面地说:“给吉日嘎拉图打电话了。他说,有空就来家过年。”
于是,萨仁其木格和朝克巴特尔开始忙活起来。朝克巴特尔清理垃圾,还弄来白灰,将屋里的墙壁粉刷得白白亮亮。萨仁其木格专门去苏木,买来床单等用品,为儿子将里屋收拾得清清爽爽,还准备了很多儿子喜欢吃的食品。
除夕之日,下午冷风吹起,尘土飘卷。朝克巴特尔打扫屋子,在门上贴好对联,不时探望着萨仁其木格家。他想,若吉日嘎拉图来了,就能瞅见。萨仁其木格家看起来,格外寂静。因前几天已进行彻底打扫,她家附近干净许多。萨仁其木格不时走出家,望望公路。如此,等到暮色低垂。
朝克巴特尔走进羊圈,给羊搁草后进屋想煮饺子,却又犯懒。他看起电视,坐了许久,才想营造年味而在锅里烧水,拿出酒小酌。此时,萨仁其木格进来了。
朝克巴特尔就知道吉日嘎拉图没有回来,却不知如何说起,只道:“来了,那么……”
“你没有煮除夕的饺子吗?”萨仁其木格说完,立即行动,从柜里找出能吃的东西,摆在桌上,煮起饺子。朝克巴特尔觉得,萨仁其木格一来,几分钟之内,屋里显得温暖、充满生活气息。他觉得,盼了许久的儿子没来,萨仁其木格可能在焦急,于是偷偷一察看,萨仁其木格丝毫没有焦急的神态,而摆出一副无论如何还得照样过年的样子,显得利落大方。
“劳累一整年啦,无论如何,欢欢喜喜地过好年。”萨仁其木格斟上酒。
从外面呼啸的风声中,他们听到远处的爆竹声。那是邻村的人们在过年。
萨仁其木格说:“咱俩也轰轰烈烈地放放爆竹。”
于是,俩人到外边放炮。用香烟点燃爆竹引线时,引线沙沙作响着燃起来,紧随其后的轰隆声震耳欲聋,不久升上高处的爆竹在狂沙席卷的夜空上红光闪闪地炸开,然后听见“嗵!”的一响。
“说是,爆竹声剧烈,来年运气旺盛。来年你会过得好。”萨仁其木格鼓掌欢笑。
那夜,他们俩都没入睡。不久,萨仁其木格喝醉,唱起《半圆的月亮》。
半圆的月亮
幽幽悬挂在苍穹……
夜深了,风暴愈演愈烈。
九
除夕,吉日嘎拉图没来,大年初一也没来,初二下午竟然回来了。还是醉醺醺地回来。
那夜,朝克巴特尔很晚才睡,所以睡得鼾声大作。忽然被重重的推门声惊醒,一开灯,只见一位陌生青年站在面前。朝克巴特尔揉揉眼睛,凝望一阵,才认出是吉日嘎拉图,问候一声:“什么时候来的?”又道一声:“过年好?”他闻到扑鼻的白酒味,便知晓他喝醉。
朝克巴特尔赶紧起来生火煮茶,还说:“我本想你除夕来。”
“路上碰见几个朋友,一起喝酒。”吉日嘎拉图口吃地说。继续说:“我一,回来就想给你拜年,夜里赶过来。”
朝克巴特尔给他倒奶茶,摆上糕点,斟了酒。
吉臼嘎拉图将酒洋洋洒洒地全干后说:“喳,我叫你啥呢?叫哥?还是叫爸?”他的眼睛在恶毒地盯着。
朝克巴特尔被这话给愣住,但他又认为这番话早晚都得和他说,今天亮开讲了也好,对将来也方便。于是犹豫一阵后吞吞吐吐地说:“啊……这事……”
“你没看我家穷吗?家里的东西对一个妈还不够,你还想分一杯羹,干什么?若有能耐就去分享别人的东西。欺负像我们这样的可怜人家……你还算是人吗?”
“不……不是那样的!”朝克巴特尔心急如焚地喊道。
“我们虽势单力薄,却还没丢掉脸面。可现在你侮辱我家的脸面。我们怎么说也是邻居呀?为什么欺辱我们家?”吉日嘎拉图异常疯狂地喊叫着。
朝克巴特尔更急了,说道:“你别哭……听我说……”
吉日嘎拉图嚎哭一阵后咬牙切齿地对他说:“像你这样龌龊的乡巴佬还要欺负我们!你老子我和市里的强盗都打得头破血流,杀你也是易如反掌。”
吉日嘎拉图突然抓起酒瓶砸向朝克巴特尔的头。朝克巴特尔未感觉到疼痛,却发觉热乎乎的东西顺着他的脸颊流。他丝毫未动,也没擦拭脸上的血。吉日嘎拉图跳起身,摁倒朝克巴特尔,骑在他身上,揍起来。已经二十五岁的朝克巴特尔可以轻松地拿下小他七岁的吉日嘎拉图,但他没那么做,而豁出身子,躺在那里,任由他打。不一会儿,他感到头晕目眩,神志迷茫。
清醒过来时,家里显得寂静,吉日嘎拉图走了。门开得敞亮,冷风吹进来。一想到吉日嘎拉图正醉着,恐怕倒在路上挨冻,朝克巴特尔跳起身,随手抓起手电,向外跑去。外面一片静谧,冷气袭人,仿佛要凝冻人的骨髓。朝克巴特尔一路喊着吉日嘎拉图的名字,来到萨仁其木格家,只见她独自哭泣。
“吉日嘎拉图没回来吗?”
“来后又走了。”
“这么冷的夜里走了吗?”
“他是坐朋友摩托来的。和他朋友一起走的。他发誓再也不回这个家……”萨仁其木格轻声细语地说完,望着朝克巴特尔问道:“打你了吗?”
“没事,没事的……”
七
从春节到清明,朝克巴特尔无数次地去找嘎查、苏木、旗里三个级别的领导,总算以二十年的期限承租到邻村的一片草场。那片草场里有一间被丢弃的房子,他跟房子主人说好,用十只羊来换房子,忙碌几天,才把房子收拾干净。
于是,他赶到萨仁其木格家,对她说:“你现在就搬到那里去。”
“我搬到那儿,你怎么办?”
“我随后到呗。”
萨仁其木格用疑虑的目光望着他。自从吉日嘎拉图来打朝克巴特尔走后,他们俩再也不谈论一起生活的话题。
“要抓紧了。”朝克巴特尔催促着说。
穷人搬家非常容易。朝克巴特尔借来嘎查书记那玛海的马车,一次就搬走萨仁其木格的所有东西,又拆掉她家的棚圈,搬运两天。最后,只剩下赶羊。走之前的晚上,朝克巴特尔在家炖肉,包饺子,与萨仁其木格美美地饱餐一顿。
“今晚咱俩醉个痛快。”朝克巴特尔豪爽地说。
“你怎么还草场二十年的租金?”萨仁其木格问道。
“我有办法,你别管。”朝克巴特尔说,“唱那首《半圆的月亮》吧。”
那天晚上,萨仁其木格唱得真好。歌声飘过在黑夜酣眠的乡野,响彻到很远很远。“从此,我走到哪里,都会怀揣着你半圆的月亮。”朝克巴特尔说完笑了。
翌日,朝克巴特尔帮萨仁其木格赶羊,把她送到新草场。
“你什么时候搬过来?要抓紧啊。”萨仁其木格说。
“不会太久……”
从此,朝克巴特尔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许久,萨仁其木格才知道,朝克巴特尔承租那片草场时,用自己的草场经营证做抵押,又把自己的房子和畜群都变卖成钱,还了草场三年的租金。萨仁其木格想到,他这样做是否为了和我一起生活,但又想事情好像并非如此。朝克巴特尔杳无音讯,过二十来天后,萨仁其木格去看以前居住的谷地。朝克巴特尔的房子被人拆走,只剩下几面墙壁。
他已经走了!萨仁其木格唉声叹气地往回走。走到谷地东边时已到夜里。那是个无月夜。月亮叫朝克巴特尔揣走了,不知他去了哪里?萨仁其木格边走边想……
(译自《花的原野》杂志2013年2期)
责任编辑 陈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