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城与女人
郭力根 何 静
作家的地域视野是受控于自己的精神类型和文化心理的。地域与文学的关系犹如土壤与植物、水域与鱼类、母亲与孩子。民间俗语有:女人是鱼,离开了水哪能活?由此看来,女作家与地域的关系或许更甚。又有人说:城市是女人创造的。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女人;有什么样的女人,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女作家笔下的女人往往更见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由是创造出形形色色的城市传奇。如萧红与她的“一幅多彩风土画”的《呼兰河传》,王安忆与她的“上海小姐”王琦瑶的《长恨歌》,池莉与她的武汉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胡辛从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发表并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至今笔耕已整整30年,回顾这30年的辛苦路,走千里行万里,还在江西的怀抱里。她的创作,无论是小说是传记还是影视创作,无论是散文是论文还是论著,皆与三座城市息息相关,郁孤台下的赣州、人杰地灵的南昌和享誉中外的瓷都景德镇,都使她拥有一个文化的制高点。
读胡辛的作品,往往有种恍惚,如同她自己在撰写传记时所提出的创作方法或曰原则:虚构在纪实中穿行或纪实在虚构中穿行。前者适合她的传记,后者适合她的小说。她说:如果说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那么传记文学经历岁月的流逝和淘洗,也应是蒸馏过的人生。她的创作,“可以说是一种怀旧,一种追忆逝水年华,一种人类对人无长久的无可奈何的哀悼!就像一张沉入岁月的河里的网,到得一定的时机,便迅猛地将它扯上岸,作一检点,作一总结”。
1
她出生在瑞金,但童年在赣州,解放初她随家人回到南昌。如果说童年记忆为她日后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心理积淀和文化资源的话,那么,我们从中篇小说《我的奶娘》《粘满红壤的脚印》《情到深处》和长篇小说《蔷薇雨》《聚沙》的或主干或枝干情节中的确寻到了她对赣南的红色回忆;而长篇传记小说《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则是对白色婚外恋情的回溯。从这种左右开弓或曰左右逢源的创作中,我们可以认同作家与童年的深刻又微妙的关系:童年构成了每个人最初的生活经历和环境遭遇,留下了短暂而又重要的情感记忆和心理积淀。作为一种心理效应存档在心里某个位置,影响乃至直接进入作家的文学创作中。但同时又不免疑虑: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能有多少真实的记忆和积淀呢?这种记忆在回忆中当有着多大成分的后天想象与充实呢?胡辛在散文《属于我的蔷薇》中曾披露心迹:“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位女性哺育着我,知识母亲的聪慧灵秀、雇农奶娘的坚韧善良,我都远远不及,我幸运的是,在我的血质中终究融会了这两位不同类型女性的精粹,当然也沉淀着我固有的种种劣质。”她出生40天时就由瑞金叶坪沙洲坝的雇农奶娘哺育,奶娘也曾几次回到自己的家,然而两岁女孩每当太阳下山时就坐在赣州小南门住房门槛上哭泣,她的母亲不得不托人捎信喊回奶娘,17年来奶娘一直跟随她家,只是每两三年回瑞金的家一趟。5岁那年,她家回南昌,人坐汽车,家具雇了帆船,由奶娘等押运,她也吵着坐了船。那顺赣江而下的船上的日日夜夜该留给了她多少记忆!开阔的风平浪静和险恶的惊涛骇浪,两岸风光的旖旎多姿与荒凉悲意,船家的质朴潇洒与贫困拮据,水上生活的浪漫与寂寞,都不是小小女孩能领悟和被感染的,但大脑如摄像机,悄然记录了一切。回到南昌,她的父亲曾在江西军区文工团工作,为创作大型合唱《江西是个好地方》,她父亲记录过奶娘唱的《送郎当红军》等红色歌谣,胡辛姐妹们是最早听到过原汁原味的原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的。而奶娘自身的传奇经历,也让小小年纪的她明白又糊涂所谓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我的奶娘》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原中央苏区一普通女性平凡又传奇的一生,“我”的奶娘是红军的妻子,当丈夫北上后,她种田砍柴,与孩子相依为命,当重伤的女红军牺牲后,为保护烈士后代石丹,她忍痛割舍了自己的孩子。为了生存,为了养育石丹,她离开了土地漂泊城镇,不得不多次改嫁,不得不做伪团长儿子的奶娘,在经历艰难坎坷终迎来解放,并与丈夫重逢时,但各自都有了家!她成了坏分子家属。然而她无怨无悔住回深山,并在非常岁月以博大的胸怀护卫着她奶大的孩子们。胡辛以女性视角作为一个切入点,以她特有的历史洞察力和穿透力,打破了“男性英雄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观,哺育不同出身的后代的故事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个人命运和人性光辉中的映照。

1999年三八妇女节前后,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邀请胡辛与主持人张越做作家访谈
这样的思考跨越世纪跨越千年,在24集电视连续剧和同名长篇小说《聚沙》中又得到张扬。《聚沙》是中国第一部由高校师生自编自导自演自拍摄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在对当代高校8个年轻人一年的研究生生活展现中,融入了江西特色的红色历史文化元素,红色经典电影《党的女儿》在剧中作为关键线索一再出现,剧中主人公秋月的养母殷山红是老区的乡村教师,殷山红的外婆正是《党的女儿》中玉梅女儿妞妞的原型之一。殷山红的血液里延续着《党的女儿》《我的奶娘》中的玉梅、奶娘等红土地女性淳朴、坚韧、无私之精神,并与人性魅力交相辉映,并不久远的历史与不乏浮躁的当今在碰撞中发人深省。
休说5岁的记忆不可靠,当一个女人走过岁月后的回眸,饱含着成熟女性的理性思考,虽并非完全的纪实,但人生况味的咂摸咀嚼,则是传奇外的心得。而且童年的记忆并非固定不变的,当在遗忘和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修改”、“筛选”乃至“更新”。“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太多有名无名的真实的女人男人,他们的真事比小说电影的故事更传奇更感人。”赣南地域文化作为红底色留存在胡辛作品里,一个个鲜活的普通生命跃然纸上。
长篇传记文学《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亦源于作家童年时听到的故事,赣南抗战时期蒋经国与南昌女子章亚若的一段恋情在她笔下演绎得柔肠寸断,催人泪下。这场婚外恋既轰轰烈烈又凄凄惨惨戚戚。女人在青春年华29岁即香销玉殒,留下一对非婚生孪生子。胡辛在此书的后记中明言:“作为一个女作家,尤其作为一个南昌籍的女作家,我以为怎么也应该为传奇且悲怆的南昌女子章亚若写下点文字。”《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是大陆第一部描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的长篇传记。真实是传记的生命,但史料对蒋章之谜的记载甚少,口述相传更是南辕北辙,这就造成了传记创作的难点。也正因如此,成为胡辛创作这篇传记的新起点,限制之中方见高手。童年经验的运用到创作中往往有偶然因素的触动,并有相关情感的铺垫。胡辛言:“1937年父、母两个家族皆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外婆家在南昌市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亲家帮佣,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动。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正是基于童年的积淀和兴趣,成年的理性思考和历史资料的运用,才理解和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短暂而又刻骨铭心的烽火情缘,尤其是章亚若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童年情感和虚构手法的大胆运用。该传记出版后在海峡两岸畅销多年,颇获好评。2011年秋,胡辛在台湾与蒋孝严先生见面,蒋孝严认为《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是最早的、第一部全面深刻写我母亲的书,我从头至尾从头至尾读了,很感动”。他特别喜欢胡辛笔下的他的外婆,他说,写得太好了,他外婆就是这样子的。
2
从小学到大学,胡辛整个学生时代都在南昌,大学毕业后她离开南昌在外地工作了13年,1981年回到南昌,《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正是她回昌后有感而发。不能不说四个女人都有生活的原型,因为她们确实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不能不说小说中的大街小巷就是南昌的实名实地,因为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弥漫于字里行间。小说叙事时空从1951年到1962年到1983年跨越了30余年,叙事主人公是古城小街小巷的平民小女。“小时候,她们四家分居在系马桩的两侧和桃花巷、松柏巷及干家巷。系马桩前无马系,桃花巷内没花香,松柏巷口不见松,只有干家巷内似乎还住着干氏大家族,但这些与她们有什么相干呢?”四个同龄女生“跑远点到抚州门外的绳金塔下仰脸看金光闪闪的塔顶,到孺子亭去捉迷藏,花五分钱坐渡船过抚河去三村看桃花,或进到佑民寺去看那又高又大的神秘的菩萨,就更有意思了!”这种“实名制”的地域空间,“描写准确的程度简直可以当作从未到过南昌的人的导游图”,怎能不牵动南昌读者的心怀?就在“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时刻,省妇女保健院的庭院里,阔别20年的四个平民女人鬼使神差地邂逅!欣喜之余,抚今追昔。其巧合情节以众多的真实的细节缀连,以对南昌的切切实实情感滋润,因而充满了质感的盈实丰饶和处世的艰辛坎坷。
中篇小说《街坊》实质上也是一部准自传体小说,作者亦融入自己童年生活的经验和情思,以女孩“我”的眼睛“我”的成长来看一曲世态变奏曲。描写朴实单纯又童趣横生,那些“史册永远抛弃的芸芸众生”在她的眼里却如此栩栩如生。老南昌老街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言行举止,善善恶恶的利害冲突,沉浮起伏的人物命运,在她的笔下铺陈得是那么淡定从容,使读者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街坊邻居,何处再觅屋前院中之聊斋呢?这又是一次精准的“实名制”描绘,如她自己所言:“在我,是刻意描绘这古城色彩风貌的,可以说,没有这城,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小说。”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南昌与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一样进入都市化、现代化高速发展期,这座古城日新月异得让人眩晕,很多古街古巷都不复存在,昔日城市文化符号,无论是自命清高清幽古朴的孺子巷,灌婴大将军曾洗过马的洗马池、系过马的系马桩,还是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与生活观念的六眼井、三眼井、大井头,这些不只是在小说里真实的生存空间,蕴含特定的地域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大众的集体记忆也在褪色,那么,见证时光的流逝与岁月的变迁的一种文化就此消失么?胡辛的南昌系列小说似在留住川流不息的时光,为这个城市留下永不磨灭的文化记忆。
长篇小说《蔷薇雨》则彰显出教授作家驾驭平民史诗式题材的气魄和智慧。在这部写足了女人的长篇小说中,高士徐孺子的后裔——水利总工程师徐士祯一家七个女儿在经济大潮中的迥然不同的命运,是徐家七姊妹人生悲喜剧的真实况景,从徐家书屋的家族变迁史折射出社会的嬗变。岁月悠悠沧海桑田,从灌婴筑城、陈蕃下徐孺之榻的典故,到后世所建孺子桥孺子亭徐家书屋,从读书徐家高攀官宦干家闺秀到干氏守寡与难产,从三眼井清洁堂小寡妇与挑水凌家的不知是“节烈”还是“殉情”之故事到当代凌家父子,从大井头染匠石家儿子抗日牺牲、钱嫂子母亲捆绑成亲时如炸弹般跳进大井头的亦悲亦喜之轶事到改革年代的厂长石平林与劳模钱光荣……转眼即到1990年代黑衣女子的重返徐家书屋,由此引出故事主干——古巷女子从春到冬一年四季情感纠葛的起起伏伏曲曲折折。虽是一现代故事,但小说中的人物却绝不是没有背景、没有记忆、没有来处也不知去处的飘忽者。一根看不见的线系着茫茫历史的那一端,使全书呈现出一种穿越历史的内审,弥漫着厚重的文化气息。《蔷薇雨》的创作实现了胡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像”的愿望。
徐家七姐妹、钱俏、姚鸿等现代女性虽思想观念、生活形态与旧式女人有所不同,但说到底,仍是“传统—现代连续体”式的女性形象,胡辛一次次做艰辛的突围,但又陷入了因全面转型所带来的一片惶惑的境地之中。面对老祖母家训老父亲的老观念,老三希玫认为徐家特殊的家训愚蠢荒唐可悲,七巧更是喊出:“不是家太肮脏,而是清白,清白得容忍不了一点污垢一点尘埃,这种清白便成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在我们本来就够弯的脊梁上又平添了重量。所以,我要离开这个家。”当七巧竟然选择白痴的姚宝宝,从而远飞美国,来求得一种逃离时,一个最有魅力最复杂最严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女人,你往何处去?从家里逃到城里,从中国古城逃到美国新城?或许这是一种历经历史沧桑的社会进步,因为即便传统伦理道德的守卫者——徐家老太也有这样的曾经:从她出嫁的花轿中扔出一束鲜艳欲滴的姊妹花的娇媚,甚至借接生婆之口说出的腹中胎的可疑来历。女人比男人更有飞翔欲。
胡辛在《蔷薇雨》中用语言给我们重新构筑起一个她所理解并认同的古城:古巷、民居、古桥、酒肆、茶铺、花生铺……地域开始被赋予一种崇高的象征地位,作品上升到精神层面,呈现为一个区域与个体生命的互为指涉的精神关系。我们看到的是活泼泼、热腾腾的古城人生景致,虽然间或有不那么明丽甚至是晦暗的时刻,但这就是生活,一寸寸都是活的生活。这里沸腾着浓酽的生活气息,满满的都是的人的生气。

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仪式,与胡辛(前排左一)一同获奖的有史铁生、张贤亮、陆文夫等
因了机缘,胡辛的《蔷薇雨》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看中,让她担任编剧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当65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杀青,开机在即时却又出现逆转,又经历花开花落七八个春秋,最后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与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热播大江南北,胡辛因此历经了从语言文字到声画图像的华丽转身,真正为古城南昌的老街巷和古城女子做了一次摄像留影。
如果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对南昌地域地志的描摹是一个全景的话,《街坊》《情到深处》就是中景,而《蔷薇雨》则更侧重于一个个特写,它放大了地域与个体、时代与个体、历史与个体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种种关系。“经过作家的审美选择和艺术裁决之后,那些被肯定的与被否定的文化价值以及尚待探索、追求的文化价值,都会形象生动地、饱含激情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在美感中感受、思考和向往。”作家借由这些物质存在穿越于历史与现实之中,奔忙于向后的寻根与向前的超越中。
3
景德镇就更不同了!胡辛22岁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景德镇教书,与这方水土有过8年的纠缠,因而也就有了一生的缅想。 如她自己所言:“一个女人,对失落了少女最初梦的一方水土,不会不长久地思恋。”
瓷都对胡辛而言,是座母性的城市。胡辛也一直把瓷都景德镇作为创作的母本。她拥有瓷都这一富有“母系社会遗址”意味的创作根据地,却呈现出另一种因灌注聪灵的女性气息而焕发出生命的激情。这不能不说是江西作家创作个性的成熟表现。陶瓷文化与女性的主体性交叉比较,胡辛在陶瓷的制作过程中发现了人类生命诞生的同构性。女性的变迁和女性的抗争都在火的炼狱中孕育、成长。于是那孕育生命的窑与门成了胡辛一个最富有激情的艺术顿悟。凭借这一顿悟,胡辛站在走向女性、走近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道口,窥见了女性那段辉煌。出土的母系社会陶器表明了远古先民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与图腾,窑与门的开启与功能,自然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的活化石, 胡辛创造了这一独特的审美意象,但并没有欢欣鼓舞,很快她就被一个残酷的现实困扰。昔日的图腾,沦落为今天的禁忌,窑门成了男人的圣地。广博、深厚的母性之门,拒绝了女性,也淹没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抗争是必然的,冲突也就此发生。胡辛的倔强和坚韧让她的笔尖划破了横在窑门上的封条。
不过,胡辛写景德镇的第一篇小说《昌江情》(《人民文学》1984年第5期)却仍是母性的颂歌。这又是一篇“实名制”。她以女性真实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景德镇的母亲河昌江东岸女性浣衣之壮观,这一近乎轰轰烈烈的浣衣图如今已彻底消逝,而胡辛为其留下了永恒的笔墨录像。景德镇的女人是勤劳的,每家每户的女性无论老少美丑,都有着洁癖似的爱洗洗刷刷,洗皮鞋且高高挂在竹杈上暴晒、连家中的门板都要扛到江边刷洗等细节让人忍俊不禁,但也折射出作者对女性生活的细腻观察。正是江畔一个守寡一辈子辛劳抚育儿子成才的洗衣老妇,对昌江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当儿子大学毕业并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后,给老母买了洗衣机,可母亲还是每天“下港”。起初儿子不理解老母,欲强行将母亲从江边找回时,却在落日的余晖中似得到了苍天的启悟,他理解了母亲,泪流满面,双手将瘦小的母亲抱起,并高高举起!虽是短篇,可字字珠玑,可当成平民史诗来读。
作为胡辛的母刊《百花洲》在景德镇地域小说的推出上,虽不是第一篇,但推出了系列,其中尤以中篇小说《瓷城一条街》和《地上有个黑太阳》为最佳。胡辛以清丽明快的色彩绘出《瓷城一条街》,又以浓墨重彩涂抹出《地上有个黑太阳》。这是两部风格迥然的小说,前者手法传统而且极富画面感,《禾草老倌》《河·江·海》等同此风格;而后者有着意识流般的时空交错,这与《“百极碎”启示录》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小说中的瓷都女性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个性却有着相同的共性,这可能也是胡辛有意为之的。她清楚她笔下的女性:目不识丁却胆敢闯窑最后征服把桩师傅的骚寡妇,身残志坚古色古香的彩绘女青青,活泼新鲜敢作敢当的现代派女大学生谷子,命运多舛却总也不向命运低头的老三届大学生景景,清澈似一泓水、热情如一捧火的纯情女中学生小弟……都烙刻着瓷都女性火的特征,而她们的结局多带悲剧色彩:骚寡妇因没名没分晚景终是凄凉,谷子因道德不容、景景因法律不容都只能独吞苦果,唯有小弟虽感受承受到生活中的忧和累却仍无忧无虑。胡辛了然:人的生命瓷的生命绝对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和缺憾,或太幼稚或太玄奥或太粗野或太精细或太浅显或太深邃,总之,难以完美。但只要有自己生命的独特个性,这就够了。有缺憾的百极碎是瓷中珍品。有缺憾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当然,胡辛笔下的男性,无论是《河·江·海》中的老画家教授、《瓷城一条街》中的龙隆隆,还是《地上有个黑太阳》中的火崽等等,都想从瓷中重现生命本真,从而敲破厚厚的文化外壳,归真返朴,让生命还原于没有外衣的生命,虽然有的功亏一篑有的成就一时。因而,胡辛的女性写作较其他女作家而言,较为沉稳,较为通达。她始终主张女性意识,首先应该是人的意识,女人的问题根本是人的问题。女性文学也是人学,它必须置于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把握、表达。这是胡辛创作的“圆心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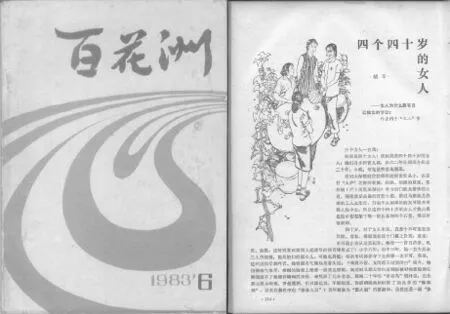
《百花洲》1983年第6期刊发胡辛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到长篇小说《陶瓷物语》所传达出来 的“越贴近泥土,怕越给人母性的思恋”的情愫就更见浓郁真挚了。胡辛言:“高岭土是白色的,拿一撮白色土放进玻璃水杯里,它会像白玫瑰一样一瓣一瓣开放,但是转瞬间就变成一摊白粉末了。这让我想起莎翁之句:女人像蔷薇,转眼就凋零。这些感触,我都放进了长篇小说《陶瓷物语》中。我去过高岭几次,高岭村窝在高岭里边,高岭因为堆积着历代高岭土的尾砂,扑入视野的是白色的荒原,就像默默奉献了一切的母亲的坦诚的胸怀。”《陶瓷物语》整个小说框架都以陶瓷为主体,其最高点就是对瓷的灵性感悟——石会崩,木会朽,人会亡,而瓷,即使粉身碎骨,千年万载后其质也不变。在梳理皇瓷镇整个陶瓷史的过程中,胡辛的女性意识又一次释放出来,只不过前期的那份激动逐渐被理性的审视 所替代。青龙缸与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的情史,永乐瓷与永乐帝和徐皇后的故事,高岭婆婆、孝女跳窑出祭红、青花仙女的传说,以及窑门的图腾都表明,胡辛是把陶瓷史和女性史融在一起来叙述的。瓷,的的确确是女性的,母性的。

1997年7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美国访问(后排左四)
时间是有重量的。胡辛在自己的精神之源留下“我们的历史”的努力和人生的感悟都给阅读者留下了诸多启示。破译瓷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记录了赣鄱大地的历史进程。合上书本,依稀可见胡辛沿着曲折的古河道,踩着古老的青石板,拾掇草蔓石缝间零星的文明碎片,一个声音亦从远方传来:当明灿灿的阳光流泻在一筐筐古瓷片上,仿佛连着悠悠岁月的另一端时,让我们回过头去思……
从历史到现状,从青花到颜色,从女人到男人,从老街到新城,从草根到学院派,从小说到散文,从影视到绘画陶艺……胡辛几乎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拥抱景德镇,而不仅仅是触摸。试问,如果不是对瓷都景德镇如此爱之深,憾之切,怎会在长达3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绵延不绝地对这方水土这方人如此充满了倾诉的欲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