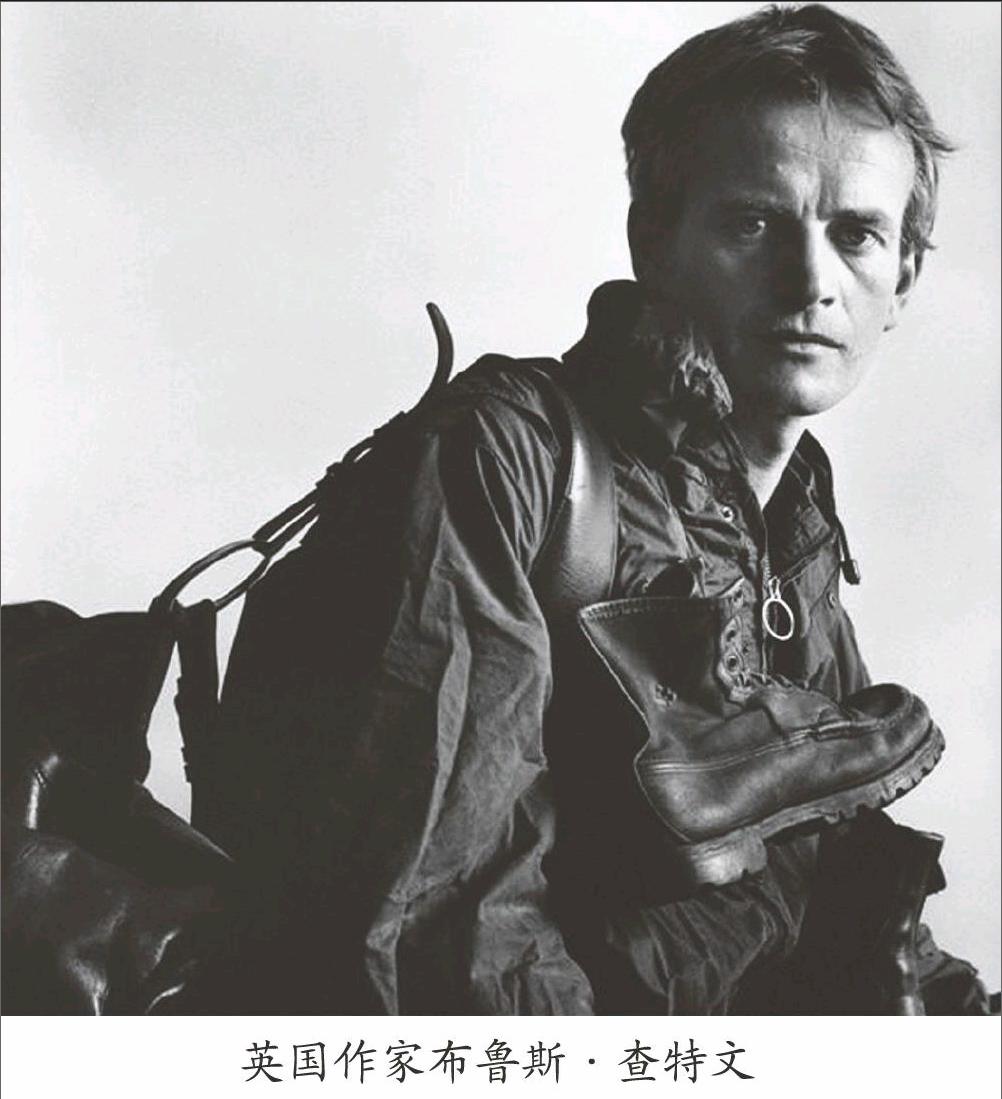


我们同这匆忙的世界一起,
万种灵魂消失于动摇与让步,
如苍凉的冬日里奔腾的流水,
明灭的星空一如泡沫,
仅存着孤独的面容。
——叶芝
[一]
《九十春秋》是本老书了,很多年前我曾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翻出来过,因为是常书鸿,便简单翻看了几页。那时的感觉:这就是一位老一辈艺术家的自传梳理,时间重点是在敦煌的五十年。仅此而已。如今再看,我却不知道该用什么的词藻、句式来做一个开场的修饰。或许不同的年龄、心境和环境下,对同一本书的感觉本就不同。三十岁的我和二十岁那年比起来,似乎更多一点地理解到了孤寂的敦煌之于常书鸿的意义吧。
1935年秋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边的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由伯希和編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里面有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他被深深地吸引了:“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对于这一次的偶尔发现,常书鸿在书中称之为“新奇的发现”。
对于常书鸿和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有抱负的时代青年来说,人生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仍有一种精神上的强烈吸引,让常书鸿在烽火年代几经转折前往敦煌,去感受千年文化的积淀。这一去就人生半百,一定不是为了“诗和远方”的简单文艺追求,常书鸿对敦煌的坚持,用冯骥才的描述,就是匪夷所思。这不仅是在于他放弃留学生可能享受的物质生活,来到这边远贫瘠的大西北,而且是在于敦煌带给他的无限的孤独。当年前有张大干,第一个来此编纂洞窟编号,后又董希文等学生跟随老师的脚步在此磨炼,但他们最终还是因为各种理由离开了,常书鸿留下来了。
这孤独在前期是先生描述的,在这个沙漠孤洲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的寂寞,职工竟会为等待亲友的书信,彻夜不眠;到后来,他的妻子头也不回地和手下私奔,他的学生和亲密战友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他倾注无数心血的敦煌研究所被撤除;再到后来,根据高尔泰先生的描写,他在文革之中被一手栽培的门生打的口角流血,他用那双画过金奖油画、修补临摹过敦煌壁画的手,撑跪在地上,从早到晚一端一爬,一端一爬给猪喂食,耳边是猪的吼叫和看管人的呦喝。然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当池田大作先生问起“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先生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二]
《师道——吴大羽的十封信》是吴大羽在20世纪40年代写给他的学生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等人的十封以谈论艺术和人生为主题的书信。这些书信在经过漫长的时间淹没后,除了有两封(其中一封是局部)曾被台北大未来画廊出版披露给世人外,其余均系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的序言是学生吴冠中在1996年元旦为纪念吴大羽去世八周年所撰写的《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而书名《师道》则是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那一代人对“师道”的感恩回报之情。
吴冠中开篇即言:性格决定命运。吴大羽的命运如何呢?吴大羽的生命遭际与他那一代人相比更加不幸。他的今日声名鹊起与好评如潮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有着非比寻常的中国现代美术创作与教育的才能与资格。我相信今日的社会对他的点赞大多都是真实的。尽管如此,这些与那个孤寂的艺术家又有何相干?从他的作品与文字以及相关文献中读到的大多是孤寂,然而这颗孤寂的心,是倔强而傲岸的就是了!他具有传统士夫文人的情怀避世昆明、香港、上海,甘淡如饴。
一如他在写给赵无极和谢景兰的信中所说:人生永像似一首没可命名的诗篇。每个名家(或伟人)都曾竭其精力,完成其所能,留痕于时代,戛然引去。在这一封信里透露出了他对时代的诸多无奈,但却也不以为然,因为他不屑于这些琐碎俗事的纷争,而只想竭尽所有精力,完成所能做到的。在书的最后,还收录了部分吴大羽的诗作。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吴大羽最早于1922年就开始写诗歌了,那时他还是一个19岁的少年,刚刚从名师张聿光处学成,在《申报》担任美术编辑。在这弱冠的年龄里写出的现代诗放在当时新诗中,水平都是不低的。有些像新月派的诗,但有自己的特点,跟整个所谓从现代到当代的诗坛流行的写法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他的诗夹杂着古汉语和汉代汉语,写新诗时用现代汉语比较多,他也写古诗,他的古诗字句严谨,对仗工整,行云流水。
[三]
《周思聪与友人书》又是另一种的人生记录。在中国的美术史上,成就突出的女艺术家寥若星辰。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耀眼的女性像流星一样不断划过以男性为主体的艺术天空。曾有人说,周思聪是自李清照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女艺术家。在美术圈外的人听来,这种评价也许过高,但周思聪的确是公认的杰出画家,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她有着超人的天赋和悟性,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画当之无愧的引领者。
在艺术明显表现出它的政治工具这一特征时,大多数艺术家无形之中接受了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歌颂党的丰功伟绩。没有人有条件并且敢于在这个时期去调查广大的农民、工人究竟喜欢什么,艺术家仅仅被告知艺术必须是健康的、歌颂的和具备符合党所要求的政治立场的。在党的文艺思想的不断宣传与教育下,人们似乎真的被培养出来一种新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意识,即崇尚“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和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场景。但周思聪说:“我不认为艺术一定离不开政治生活……但我也不认为只有与政治不沾边才是高尚的艺术。如果你画一棵小草,是有感情的,可以是高尚的艺术品;画政治性极强的,有感而发,当然也是高尚艺术。”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她的《人民与总理》中看出画家两种意识的混合:对总理的怀念与敬重,对百姓悲苦命运的同情与怜悯。这幅作品是艺术家自己的诚挚与悲恸在笔端闪烁,从感情内涵到形式技巧,足以呈现那一段历史的真实。
然而,事实上周思聪作为画家备受瞩目,但作为妻子、儿媳、朋友、女人的感情生活却不被重视,而实际上她日常生活中的困窘无一不在她的画作中体现,关注她作为人的情感,自然是理解她画作的通道。其中,卢沉作为丈夫对她的不冷不热、不理解,她作为儿媳备受刻薄的婆婆的脾气的压迫,都使她生活本身并不十分幸福。
勾勒她的一生,却是无比坚强的,不为权势低头,不为流行题材障目,从文革到商业化,都孤独坚忍站立。对过往时代的反思,让她对《河殇》《傅雷家书》《老舍回忆录》《干校六记》等文字抱有热情。此外,她不仅不让她囿于传统,反而对新思想和年轻力量保持兴趣和关注。作为艺术家和女人,她看《月亮与六个便士》以及《简·爱》吸取精神力量,感同身受。在《友人书》里,周思聪是儿媳、人妻、母亲,但也是一个阅读者和画家。
在她写的《自传》末尾,她说:“自传到此便传完了。人说没有坎坷经历的人,其作品便没有深度,看来此话正应验在我身上。画了30多年的画,始知自己天资平平。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顺其自然吧。我只愿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我。”周思聪的这些话,是她的肺腑之言,不是应酬的客套话。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画家。而作为观者的我们,往往为她艺术的天然本色所吸引,并深深感悟到其中蕴藏的非凡才华,不期然而然为之撼动心魄。周思聪具有打动中国文化人的人格魅力。她的沉默、干练、具有中年知识女性的美丽,宁静淡泊的品格,冰雪聪明的天资,继往开来的才智,以及她对静谧大自然和平凡人们的热爱,永远凝结在她的作品中,留驻在众多同行和无数观者的心灵深处,默默地焕发着永恒的光采。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