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纸张、迪多字体和悲伤
【美】乔舒亚·尤尼秋尔/著 徐 平/译
散文家和设计师之间常常并无交流。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散文家和造型艺术家,甚至那些与文字打交道的造型艺术家之间。在和语言打交道的人们之间缺乏沟通实在是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散文家和设计师,比方说,常常作为专门家而彼此分开,而不是进入对话。对我这么一个既写散文、又做设计、而且创作二者兼备的作品的人来说,这实在是种奇怪的静默。我知道这是历史的无形之手的影响:抄写员一般并不创造他们转抄在羊皮纸和彩绘抄本之上的内容,而越来越少的“平面设计师”会描写他们所设计的东西,尤其是在平面设计这一领域在包豪斯建筑学派晚期被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zlo Moholy-Nagy)正式建立之后。我也知道在三十至五十年代,大概正值平面设计初创的时期,在有关写作和艺术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讨论中发生了某种奇怪的事情。正如约翰娜·杜拉克(Johanna Drucker)在其《可视的文字》(The Visible Word)一书中所说的,“在对现代艺术实践的术语展开批判性的重新考察时,现代主义严肃而顽固地陷入对文学与视觉艺术实践的分别之中。” 她这里所指的就是文学那边的新批评派人物和艺术那边的形式主义者。她还说,“通过将它们本身所用媒介的特殊性作为这两个领域的本质的基础,视觉对象和文字必然以各种形式相互排斥,以确保其自身活动的纯粹的定义。” 这一点,杜拉克指出,尤其令人错愕,因为大多数现代主义者(在艺术史的意义上)并不认为在写作与视觉艺术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别(这多少是由于字体学当时是一个相当丰盛的新领域,以至于顽固地停留在写作与艺术之间)。因此,与其说我无法给“散文家”与“设计师”或者“艺术家”之间的缺乏沟通以历史的叙述,不如说我作为一个作者从未感到这一静默对我有什么帮助。通过对这一静默更深的思考,我发现在散文与艺术、字体学、图书装帧艺术、和其他视觉艺术形式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长期而且共时的对话,即文学和视觉艺术的混合实践,而这一实践既不是全新的,也远没有耗尽其潜能。

笛卡儿
这类作品的一个早期实例是斯特凡·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的1914年版《骰子一掷》(A Roll Of The Dice)。在《骰子一掷》中,我们看到散文写作可以存在于写作内容和其视觉表现即设计之间的交汇之中。这是马拉美就意象、语言、和作为艺术品的书籍的力量所做的一次复杂而朦胧的尝试或者试验、发现或者证明。写作与设计、字体学、书籍出版不再那么容易分开。就语义而言,此书在文学的意义上是纯粹的象征派作品,突出一系列具有松散联系的意象(海难、羽毛、深渊),而非任何叙述甚至叙述者。换言之,语言在此作为一扇“窗户”的能力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人们可以通过这扇“窗户”来看到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拉美要求这本书以迪多字体(Didot)印刷,因为该字体看起来纯然为机器所造,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因而具有透明感。通过迪多字体,读者在接触马拉美那一系列超验意象时不会受到任何阻碍。不过,除了棱角分明、轮廓清晰、和机器制造之外,迪多字体也具有高对比度的笔触、各种尺寸、斜体、和粗体,使这种字体引人注目、并具物质性。总体来说,《骰子一掷》本身也是如此。它可以按页、按对开两页、按字体尺寸、按粗体或斜体、或者按以上各方的任意组合来阅读。这种开放性的效果就是,《骰子一掷》具有一种曲折迂回的视觉逻辑,而这种逻辑更接近于读画、而不是读书的方式。然而《骰子一掷》的确是一本书,呈现于跨页的有限的可见度之中,既符合我们作为文学作品读者的期待,又对这一期待发起挑战。它的读者被要求同时阅读诗歌语言和设计语言,同时处理马拉美的抒情意象和视觉逻辑。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骰子一掷》并不是具象的、模仿的、甚或抒情的。马拉美并没有用迪多字体去具体地表现他的意象,就像福尔图纳托·德佩罗(Fortunato Depero)、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弗兰西斯科·坎吉乌罗(Francesco Cangiullo)、或者理查德·科斯特拉内茨(Richard Kostelanetz)在他们颇有价值的作品中可能会做的那样。像一个精明的设计师,马拉美也并没有试图模仿;他并没有用他的语言所拥有的那种驾轻就熟去选取字体、视觉层次、或者页面布置;虽然空白使页面显得很大,迪多字体却轮廓分明、具爆破性,而且视觉层次常常简明而突兀。最后,《骰子一掷》有抒情的朦胧性。就其庄重的语调、崇敬的意象、和错综复杂的悦耳之声而言,这部作品的语言是抒情的,然而此书的设计(在视觉的意义上)却非常明显地属于非抒情的;它毋宁是简明而线性的。在我看来,《骰子一掷》中语言和设计之间微妙的关系乃是它作为一篇散文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它不是模仿性的,也不是反模仿性的。它是朦胧的,因为它包含着多种效价或者轨迹、姿态、和情绪,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在语义上所说的和视觉上所示的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和企及。

乔治·贝克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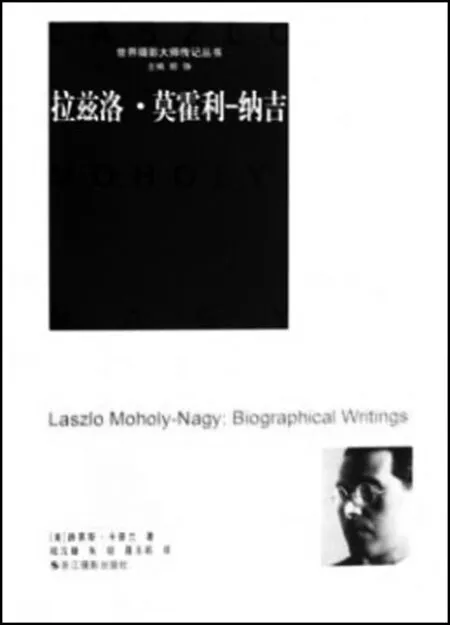
拉兹洛·莫霍利-纳吉
散文写作可以由作家和设计师合作进行。作家和书籍出版人或者视觉艺术家也是如此。在玛丽·汝弗尔(Mary Ruefle)最近出版的、由她写作由我设计的小书《落日之外》(Beyond Sunset)中,书的内容是一系列有关悲伤的错综复杂的表现的散文诗或者诗意散文。悲伤是按照颜色来表现的——红色的悲伤、绿色的悲伤、黑色的悲伤、蓝色的悲伤,等等。也许在设计上存在着悲伤,但更多的是不定、渴望、甚至冷漠。这本书印在5.5×7英寸大小的接近卡片厚度的奶油色纸上,每页只有一首玛丽的散文诗,在我的纯然抽象的现代派线条画之下。除了牛皮纸包封之外,这本书没有装订成册,只有在拿掉包封之后才能读到书页。而拿掉包封之后,书名、玛丽的姓名、我的姓名、和关于此书的简要信息不是被扔掉就是与书页分开。读者因此而失去了通常与书籍紧密相连的信息。书页没有装订,而且没有页码。拿掉包封,诗歌循环的构成便得以突出但却保持开放,就像一系列画作一般。这本书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好像它想要被装订起来(一本书),然而又不大能被确定为散页(作为画作)。所用的厚档案纸和它的尺寸(小于11×14英寸这一绘画的普通尺寸)更进一步增加了设计师的整体的不确定性和不知所措。同样,玛丽的诗歌与伴随着它们的线条画有一种不清楚的关系。这些线条画只是在色彩上与玛丽的每一首诗相对应。它们并不描绘她的任何一个文学意象,甚至并不完全与她的诗歌的情绪合拍。相反,它们阐明它们自身作为现代派的形式的增长,历经冷漠和脆弱,结构和瓦解。当然,在你读《落日之外》的时候,你读到所有这一切——玛丽的诗歌、线条画、空白、纸张、和包封——你同时读到所有这一切,或者把它们作为同一样东西的一个部分。每首诗的情绪和轨迹因此而成为复调音乐,而对我来说,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中,而不是在玛丽和我的作品本身之中,《落日之外》的写作才得以实现。

雷蒙·格诺
作为印刷媒体,散文很容易用来表达对物件和观念的思考。斯蒂夫·鲍登(Steve Bowden)和卡尔·哈斯(Carl Haas)的《大幅纸张》(Broadsheet)系列聚集了各艺术门类的作者来提供照片或板式、散文、或者与该期的题材有关的任何由作者选择的形式,而这题材总是一件日常的有型物件。有一期是关于纸杯的,有一期是关于水泥块的,有一期是关于软吸管的,还有未能完成的一期是关于锥形交通路标的。第二期是关于折叠椅的。它长长的纸张尺寸将注意力吸引到作为折叠物件的杂志或者书籍。它的内容包括各种形式,从个人散文到各种折叠在杂志中的加插,比如丝绢网加插,上面印有查尔斯·伊姆斯和蕾·伊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的图案,和激光切割的伊姆斯椅的组件,可供读者取出组装。总体来看,“折叠椅”这一期将读者引入显然有型的模组化思考,这一思考不但涉及折叠椅,而且涉及我们的身体与所造物件的关系,以及观念是如何变成所建之物的。“对我们来说,这是制作一个事物以迫使读者将其看作一个事物,” 鲍登解释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得到一个机会来重新思考我们平常不屑一顾的平凡事物。”

蒙田
像这样的散文也有能力运用语言的视觉性和物质性潜力。我2011年在《三季刊网络版》(TriQuarterly Online)发表了一篇散文,叫做《六幅套画一》(Hextych I),其语言的运作就部分地出自这种能力。这篇散文有六页,每一页有某种数位照片蒙太奇来融合文字和照片。参考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风格演练》(Exercises in Style),这篇散文的内容是按照六种障碍而重写的我在国外的平凡经历,这些障碍包括隐喻、逆行、和混排等等。照片是一系列的表面(涂鸦的墙壁、商店的橱窗、和人体的模型之类);它们与文本有关,但并不是文本的图示。在形式上,文字保持着相当常见的手稿格式。然而当它不得不与照片分享同一个视觉框架的时候,文字必须按照语义和视觉印象来读。取决于你的眼睛的聚焦之处,页面看起来像是一个个的句子,或者一组不明颜色背景之上的词语,或者一组模糊的深灰线条之上的照片。这是一种我从伊斯多·伊叟(Isidor Isou)的《自画像》(Self-Portrait)借来的视觉错觉,这部作品采用了类似的形式,但当然比我的作品更为老道。这种视觉效果、照片内容的表面的主题、和反复的形式主义的散文一起形成一种关于所有语言,甚至手稿的视觉性和物质性的表现。这一点也表现在页面的尺寸和纸张的形式。我为这篇散文设计的是8.5×11英寸,标准的文学(“文本”)尺寸,然而非常接近8×10英尺,标准的照片(“图像”)尺寸。这篇散文不是印在四十磅印刷用纸上的,我采用了经剪裁的光面档案照片用纸。这种纸型让页面被作为照片来读,但与此同时,纸张的尺寸又暗示着它们是页面。最终它们不得不被读作二者,说明文本和图像之间、写作和照片之间、或者写作和设计之间、或者写作和书籍出版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非常清楚,而且出类拔萃的散文可以出现于这二者的混杂、甚至融合之中。
这样的散文通常并不高调登场。它们“以身作则,”借用散文家兼诗人斯蒂夫·库斯司托(Steve Kuusisto)的说法。这是一种通过实行、通过演示而达到目的的努力。和卡茂·布拉斯维(Kamau Brathwaite)的《春奇镇摇摆》(Trench Town Rock)一起,马拉美的《骰子一掷》也收入了《散文探源》(The Lost Origins of The Essay)一书中。在“设计的散文(作为散文的设计)” [“The Designed Essay (Design As Essay)”]一文中,安德·蒙申(Ander Monson)强调了视觉效果、排版、和设计在散文写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蒙申的散文最初是以讲座的形式在2007年出现的;而达咖塔(D’Agata)的散文选集则于2009年问世。在2016年的今天,仍然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类相当复杂和棘手的散文依然是我们的起源的一部分,和我们的当代实践。以下仅仅是一个此类散文的不完整的书目:马拉美的《骰子一掷》和马塞尔·布达埃尔的《骰子一掷》;玛丽·汝弗尔的《小白影》和珍妮·霍尔泽的《尘埃画》;理查德·科斯特拉内茨的《自传》和弗兰西斯科·坎吉乌洛的《咖啡店协奏曲》;安德·蒙申的《致未来恋人的信》和苏珊·豪尔的《被绑架者》;埃尔·利西茨基和弗拉迪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和饶尔·豪斯曼的音素诗《kp’erioum》;F.T.马里内提的《晚上,...》和特奥·凡·杜斯伯格及科内利斯·凡·埃斯特伦的《反建筑》;奥尔夫冈·文嘉特的《NR 4》和约瑟夫·克苏斯的《艺术》;拉迪斯洛·斯特泽敏斯基及朱利安·普日博希的《自上》;卡茂·布拉斯维的《春奇镇摇摆》和马克·诺瓦克的《闭上关下》;林·黑吉莲的《我的一生》和阿梅利亚·博德的《瓦尔登旁注》;W.G.泽巴尔德的《奧斯特里茨》和梅尔·波何那的《误解》;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画诗》和马塞尔·杜尚的《绿盒子》;珍妮·宝莉的《身体》和简·白芬的《狄金森拼合系列》;格劳迪亚·冉金的《不要让我孤独》和拉拉·艾瑟迪的《聚合领域系列》;格兰·李贡的《隐形人(两个视角)》和哈娜·霍赫的《倩女》;约翰·伊顿及弗里德尔·迪克的《乌托邦:现实的文件》和布莱斯·桑德拉及桑尼娅·德劳内-特克的《西伯利亚纪行》;伊斯多·伊叟的《自画像》和本·凡·戴克的《解开我》;海伦·汝斌斯坦的《你是我妈?》和艾米莉·瑞尔斯的《斯克诶特》;翠西娅·翠丝、艾希莉·约翰·皮格福特等的《鬼魂》和玖安·林德的《阳光项目》;阿荣·弗林特·坚姆森的《薄板杂志》和汝迪·凡德兰及苏珊娜·里克的《逃亡者》;安妮·卡森、比安卡·斯东、及罗伯特·居里的《安提戈尼》和阿玛然·博苏克及布拉德·包斯的《书页与屏幕之间》。

斯特凡·马拉美
这样的散文提出了一系列特别的问题。其中突出的一个是发表的问题。在文学期刊和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散文困难重重,因为期刊和杂志的视觉和材质的选择常常是事前就确定了的:比如说页面的尺寸、字体的型式、纸张、及着色等等。但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愿意考虑并且发表这样的作品,如果有必要的话发表在互联网上。另外一个相关的是“氛围”(“aura”)的问题。像这样的散文往往都印成限印本,或者甚至作为唯一的版本而存在。这就意味着很难接触到这些作品,买起来很贵,在期刊和文选中重印又有些令人失望。换言之,这样的作品遇到的也就是绘画、雕塑、和装置艺术面临的难题。然而,通过一点努力,在特藏图书馆或者书籍艺术中心、美术馆或者博物馆还是经常能找到这样的散文的。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存在着有价值、价格合理、和接近原本的复制品的。要让这样的作品在学术对话中更为可行,写作演习室模式能够与美术工作室批评的模式融合起来。换句话说,这样的散文的氛围让事情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令人厌恶,然而并非完全不可能。值得指出的最后一个是技能的问题。像这样的散文需要文学和视觉艺术两方面的技艺,而这二者通常是两个不同的人才具有的。作家与设计师、出版家、或者装置艺术家合作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则是由散文家或者设计师/出版家/艺术家自己同时处理二者,这是一种愈益常见的交叉训练或者混合实践。在写作这一方面,设计有着空前多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有工具的话——我们的确有工具,不管是像Word这样低端、武断的文字处理软件还是像InDesign这样的多功能桌面出版应用程序 ——那为什么不用这些工具呢?” 安德·蒙申早在2007年就在其“设计的散文”一文中正确地指出过这一点。而我本人则在2010年以后提出,现在在印刷制作这一方面能够空前容易地采用凸版印刷、档案冲印或者数位、制作精美的书籍、超大幅纸张或者大幅面打印、三维印制雕塑或者散文家所能想象的任何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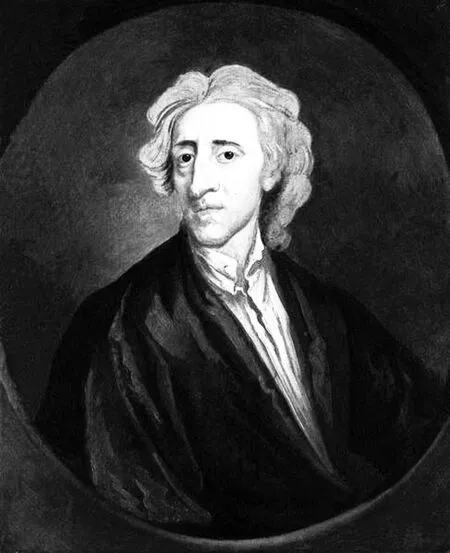
约翰·洛克
这其实是出人意料地传统的、甚至蒙田(Montaigne)式的情境。每每想到像这样的散文时,我都会想到蒙田,和他反反复复问的一个问题,“Que-sais je?” 这是蒙田的散文一再就其特定的题材问的一个问题(大拇指、食人者、怪物般的孩子),但他的散文也就散文本身问出了这同一个问题——“我知道什么?” 在蒙田那里,这也涉及文学与哲学作品之间的分野,和他的散文(essais)与笛卡儿(Descartes)、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这样的早期现代哲学家们的作品之间的分野。在思考像以上这样的散文时,我想到的正是蒙田探索散文写作的疆域的努力。蒙田的这个问题对我看待散文的态度和散文与设计之间、创造性写作与视觉艺术之间、以及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区别的方式有着教育的功用。在我理解散文的努力之中,我发现我自己并不想为它下一个定义,或者至少并不想为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为正是这个不确定性的边缘——它就是那个问题,“Que-sais je?”——才使得散文不致变得过于统一、类似、或者静止,以及使它对作为作者的我而言存在于散文的自然状态:一种努力和运动、探询和发现、试验和流动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