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沙漠》的叙事策略
李春光
荆门作家金成海的小说创作,大都是以“小江湖”这个地名为背景展开,故而他的中篇小说集干脆命名为《小江湖轶事》(2016年武汉崇文书局出版发行)。金成海以“精神还乡”为思想旨归,在“小江湖系列”故事中,探讨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农民遭遇的时代牵绊。而个中显者当属《叔叔的沙漠》一文,曾在《长江文艺》头条推出,被认为是作者“在精神还乡的道路上完成的飞跃”的标志。此文不狃于常规的乡土叙事,又不囿于赤裸的身体叙事,更不拘泥于俗套的传奇叙事,在借鉴先前的写作传统的基础之上独出机杼,可谓力透纸背。
乡土叙事
曾大兴先生认为,“乡愁”就是流动或迁徙在异地的人们,对于家乡的一种回忆式的情绪体验,包括对亲情、友谊、爱情的回忆,对家乡的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的回忆,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忆。正如金成海在是书“自序”中所说的那样,他痴迷于一个“此乡非彼乡”的虚构的文学地理空间——“小江湖”,由于时空的异质性,即“我的精神在四处游移”,导致了他的“精神还乡”,和他一起精神还乡的还有“我爷爷”、“我叔”以及“登九”等,他想通过他熟悉的“汉江沙滩”表现一种“原生态的东西”。而这种“原生态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隔帘花影般的“乡愁”,一种对故乡土地的隔空亲吻。有学者将乡土文学概括为三大品格,即“乡土病”、“农家苦”和“乡土趣”。而这其中,“农家苦”叙事策略的终极指向,是为了论证农民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虽偶有提及,但已去主流甚远。“乡土病”和“乡土趣”仍然是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聚焦的热点。《叔叔的沙漠》也不例外。
首说“乡土病”。这种乡土叙事,在开掘农业社会中农民精神层面的某些痼疾方面最是用力。男尊女卑的褫夺、家族宗法的威权、落伍时代的感伤等等,无不戳弄着作家充斥胸肋的乡愁。作家一方面在再现这些痼疾的症状与产生原因,另一方面也在搜求着疗救这种痼疾的良方。差不多每四年克死一个男人的“白虎星”白寡妇,在克死“我”本族叔辈、沔阳县的卖小鸡者、邻村的“半瞎子”以及她的小叔子之后,没人敢应她的“招”,最终成为绝佳的“临时苟合”的“草狗子”。族人们摆布着白寡妇的人生,“白虎克夫”的过时思维扼杀了她寻求真爱的权利。在听到“安徽省有人分田的消息”后,叔能够进入王家湾的那片河滩,便是族人们在宗法制的乡村中相互妥协的结果。叔与许书记在建养牛场上的分歧,正体现了小农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下的不合时宜与底气不足,而“汉江集团”的最终倒闭,与其说是经营不善,倒不如说是与时俱进的“误打误撞”与“铤而走险”的农民思维作乱的结果。
再说“乡土趣”。这种乡土叙事,最有乡土的模样。描绘如诗如画的故土风物,展现憨厚质朴的故土人情。依托田园牧歌式的恬淡书写,把作家淡淡的“乡愁”建构出了具体的轮廓,如此可感,又令人神往。“文学空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景观或场景,也不是见证时间在场的固化场所,而是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它的生成源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作家虚构出的王家湾,正是这种“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的最好注脚。王家湾的文学空间建构,颇有作家故乡的影子,流经村口的“襄河”以及上游的“丹江水库”,均为叔的沙漠提供了更好的凭依。进入沙漠之后,叔侄二人在草地上打滚、在瓜地里吃瓜、在襄河里游泳捕鱼、吃糍粑刁子鱼、喝汽酒,又是多少文人魂牵梦绕又难以折返的景象,正如“我”所说:“我羡慕他那田园式的生活”。总是喝得烂醉如泥却十分讨老婆欢心的“林不灭”,豪爽泼辣不拘小节的林芝,以及“背大时”却免除了乡亲们牛草钱的叔,借用镜子反光扰乱日军轰炸机的爷爷等等,均是“民风很淳朴的”的最好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最大的突破之处就在于,将“乡土病”的畸变与“乡土趣”的褪色淬炼在一起,而调和二者的佐料便是城乡二元结构冲击下的思维意识的渐变。“我”歆羡叔田园式的生活,可“我”更希望通过考大学来“走出这偏僻的乡村,吃商品粮”,过“星期天逛公园,看老虎狮子大象孔雀鹰子凤凰”的城里生活。陈春娘“臭骂”叔,“乡巴佬想啥美事?见过商品粮户口吗?”这些话让叔意识到,“原来这世上都是有等级的”。致使后来,叔把孩子全都转为“中价粮”,以提高孩子们的“社会地位”。“乡土病”畸变成了逃离故土、唾弃家乡的无力挣扎,与跻身“商品粮户口”的百般试炼,“乡土趣”则褪色成工业化时代下的不那么讲究“生态平衡”的开发,与世风日下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纠葛与情感羁绊。在时代的洪流中,叔的心就像他的沙漠中已经堰塞后的那汪死水,无甚可恋。
最终,叔叔的归宿,仍然是他的故土。每当叔叔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之时,他都会去沙漠边的襄河中游泳,这是一种逃避的表征,更是一种自由的解体。“返回自然出于人们逃避的需要,人们要逃避对不满社会的无能为力,逃避没有男人气概的矫揉造作。”其实,“自由”具有两种面相,“一方面,人摆脱外在权威,日益独立;另一方面,个人日益觉得孤独,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在襄河中,在沙漠里,这些渐远的乡土,起初是叔摆脱宗法权威、日益获取自由的“飞地”;后来成了叔大展拳脚、改天换地的“试验田”;最终成了叔逃避被时代碾压的落寞、舔舐千疮百孔的灵魂的“收容所”。
身体叙事
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对身体的格外重视已然成为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对身体的欣赏,尤其是对女体的欣赏,成了作家用身体言说故事的一种妙门。通俗者,容易把“身体”引入肉欲纵流的漩涡里而失之秽亵;高雅者,喜欢将“身体”并入色空观念的奥旨中而失于玄想。身体是叙事的媒介,并非叙事的归宿,文学作品中身体更是如此。“我们的活动总是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统一。虽然诸如吃、喝等行为通常仅仅被归结为身体性的,然而,它们却渗透着社会的、认知的和审美的意义。”这些文学性的身体,附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哲学思考与审美塑造,而对于秽亵与玄想之间的“过渡带”的把握,则取决于作家对身体意义的诠释与申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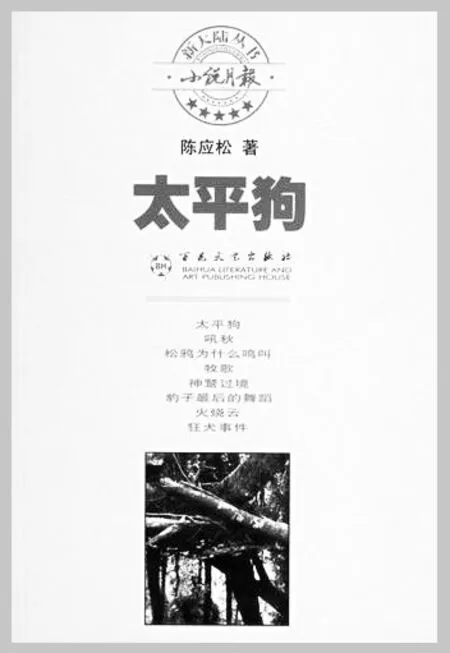
《太平狗》
与以往偏重于女体叙事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很多以男体叙事为构架的小说作品和文学形象,陈应松《太平狗》中的程大种,熊育群《无巢》中的郭运盼,鬼子《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无不袒露着男体叙事的觉醒与决心。《叔叔的沙漠》也是男体叙事中的一员,而金成海身体叙事的焦点则是叔的“体毛”。
叔的体毛,遗传了爷爷的优良基因:“爷爷从脸上的硬扎扎的连腮胡到胸口那吓煞巴人的胸毛,直窜到肚脐。”爷爷的体毛,成了“我”对雄壮男人的第一印象。白寡妇“油脂般洁白圆滑的身子趴在我爷爷那健壮的躯体上”时,最爱拨弄的就是爷爷的“胸毛”,而爷爷这条“青龙”没有被“白虎”克死,也从侧面十分滑稽地证明了爷爷生命力的旺盛。进而,这幅以身体(特别是胸毛)构成的春宫图,被迫地促成了爷爷与叔之间微妙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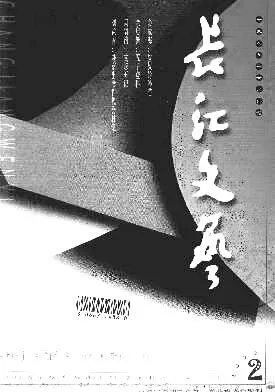
《叔叔的沙漠》原载《长江文艺》2002年第2期
叔想上河滩时,嘴巴上的绒毛是“渐黑渐粗”的。当叔上了河滩之时,“我”发现叔“从脐下往上直通胸膛已经有了淡稀的胸毛”(雪白的屁股,发育完全超过我的下体),这些都标志着叔已经成为一个“准男子汉”。而叔叉腰眺望远方的情景,和这青春萌动的身体一起构成了叔对美好将来的憧憬。这是一个发育良好的身体,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身体,是一个敢想敢错的身体。“身体并不满足于肉体所给予的空间体积范围,它通过想象、欲望、情感和意志,将自己延伸到物质性空间之外,试图占有一切象征性的空间。”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叔用他略显稚嫩的“准男子汉”的身躯,去构想、去设计、去搭建他的理想空间。
叔拥有了河滩的所有权后,他可以在他的河滩上大显身手。这时的叔,“胡子硬了长了,与鬓角连在一起”,还有“不算太浓的胸毛”,“腿上的汗毛密密的”(尖尖的喉结,硬硬的、有茧的、粗糙的手,满是抬头纹的额头,充满血丝的眼睛,赤裸的上身,硕大的男性器官),这是旺盛的生命在疯狂地生长,这是理想的版图在肆意地扩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叔用他男子汉的身躯,去刨取丰收的喜悦,去哀叹上苍的无常,去诅咒时代的吊诡。在曲折而螺旋上升的路轨上,叔的身躯除了流血、流汗,更多地是付出了朴素而又异于常人的智慧,而这聪慧的神经元就像叔身上愈发浓密的体毛一样,在翻滚的时代浪潮中,时而被风吹倒,匍匐于地;时而迎风微漾,高歌于空。
叔拥有了“江汉集团”之后,尤其是集团陷入经营窘境之后,叔“那淡淡的胸毛已变得浓密密的”,“可惜有些已白了”。这是一具看遍人世繁华、阅尽浮世沧桑的身躯,多少有了一些波澜不惊、宠辱偕忘的狡黠。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又似乎不在他的掌握之下。“江汉集团”“亏损二十多万”的现实,并没能扭转叔的旧式思维,反而变本加厉地将错就错。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当现代化的困境汩汩而来之时,除了放任自流,叔别无他法。当一个“土夫子”“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的梦想,居然是在误打误撞、铤而走险之中实现时,“我”才大梦方醒,叔“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啊”!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得左冲右撞的“小人物”。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潮汐中,这些小人物,在涨潮之时,解离故土,鱼跃成龙;在退潮之时,惜别城市,打回原形。而那苍白的不只是叔的胸毛,更多的则是无所适从的落寞与世道苍黄的无奈。
这渐变的体毛描绘了叔大半生的奋斗轨迹,它见证了叔身体的萌动、强壮与衰微。这个身体不仅为家族血脉而生,更多地则是为了发动时代的巨轮而生。“人们被其所处环境的不同要素吸引或排斥,这往往是一种颇具感官性和体认性的事情。但正是这些反应,而不仅仅是看似‘非具身性’的智识评估,为社会系统的维护、发展和转化提供了基本的动力。”正如叔为了保护每况愈下的S-2号肉鸭——致富鸭亦或是政绩鸭——而“用肩膀把即将倾斜的棚顶扛住”,身体也“一软躺在雨地里”,最终却赔了八百多块一样,无数个身体,无数个类似叔的身体,匍匐摔倒在历史的河岸边,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追赶时代的巨轮。少数人上了船,意气风发,从此一帆风顺;多数人则被甩回岸边,精神委顿,从此销声匿迹。
传奇叙事
乡土空间之中,总会有一些奇闻异事流淌到作家的血液中,而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尚“奇”的理念,先天就存在于作家的文学基因里。传奇叙事就在这样的循流中应运而生。金成海先生的传奇叙事,既有明清传奇小说的精神滋养,又有现当代创业史诗的珠玉盈泽。在传统的语境中生发人生如梦的亘古长叹,在现代的语境中揣度精神还乡的终极旨归。正如英国学者所言:“所有优秀的小说都必须带有传奇的一些特质。小说创造一个首尾连贯的幻影:它创造一个引人入胜的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详细的情节组成,以暗示理想的强烈程度为人们领悟;它靠作家的主观想象支撑。就最普遍和持久的层次而言,也许这样理解现实小说更为准确,它是传奇的变种而不是取代了传奇。”第一,叔的奋斗史。
叔的奋斗史,亦可称为“叔的传奇”。沈从文先生在《水云》一文中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传奇……再无什么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乐得失经验更加离奇动人。”此话用在叔身上再合适不过。70年代初,叔靠在河滩上打牛草卖给生产队而赚了300块钱;70年代后期,叔拥有河滩后,靠卖西瓜赚了600多块钱,而秋天的一场大水冲走了叔的所有收成;于是,叔开始贩牛,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成了县里最年轻的万元户,由于超生和坐吃山空,最终存款降至三位数;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始,叔经营起了“致富鸭”,由于摸不清市场经济规律,不但血本无归,还倒赔了800块钱;于是叔操起了自己的本行,以比市场价低15%的价格购进一批ST-1号肉牛,此时还是还不起欠乡农技站的30000块钱的S-2肉鸭饲料钱;后来,叔“以他的沙漠和现有的牛、资产占了60%的股份”成了“王家湾养殖总公司”的总经理,成了农民企业家和县人大代表;随着“组建企业的‘航空母舰’”的风行,“王家湾养殖总公司”更名为“汉江集团”,叔依旧是老总,是一手遮天、专权独断的老总,后来集团亏损20多万并最终倒闭,叔不但失去了全部财产,还倒贴了几万,最终只剩下100头牛陪着精神异常的叔,回到他梦想开始的地方。这是平凡人的创业传奇,更是当代农民的创业史诗。这个形象具有普适性,这个故事也有代表性。
第二,驼子点化叔。
驼子本身就是个传奇,他也曾经“受过高人指点,满腹牛经马道”。生平最重信义,为朋友的官司豪掷重金。他知道叔胸毛的走向,更知道叔前天夜里“跑过马”。“他能叫你一夜成名,也能叫你片刻功夫名声扫地”。这是传奇叙事的第一步,点化者颇有来历。
驼子和叔约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我讲的事儿要咽到肚子里,不许传给别人”。在驼子“倾尽了自己的平生所学之后”,他便在这个星球上消失了,“就像仙人一样只有其名没有其人”,只留下一个八角铜钱作为信物。叔也认为这个驼子“是上天在冥冥之中派来点化自己的”。而正是这驼子的点化,帮助了叔平安的度过了两次重要的人生转折。这是传奇叙事的第二步,被点化者不许泄露天机。
驼子还传授给叔“一个朴素的人生哲学道理”。他认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自己要做好人,其次要会认人,“知足就是个好人,不知足就是个小人”。他重义,信奉“钱是用的,水是流的”,切记一个贪字,“更不可坑蒙拐骗”,总之要知足常乐。这是传奇叙事的第三步,点化者给被点化者一些必要的启示,大多是业报轮回之苦、弃恶从善之念、贪恋知足之嗔以及修身养性之法等。
当叔历经半生缱绻最终跌入人生谷底之时,却在县城的街上遇见了一个卖老鼠药驼背老人,而这时的驼子已经不认得叔了。叔在被精神失常的驼子冷落之后,自己的精神也陷入了凌乱中,“时而狂笑,时而傻笑”。最终集团倒闭了,留给叔的只有一百头牛,叔又回到了沙漠,脖子上仍然挂着那个八角铜钱,“一切都恢复了原样”。这是传奇叙事的第四步,被点化者历经人间磨难,最终参透点化者当初的话语玄机,抒发人生如梦之慨叹。
这个故事刚好印证了那句“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古话。“似梦?似闹剧?反正一切都恢复了原样”,这是作者的叹息,与其说是在叹息叔叔的人乖命舛,倒不如说是在叹息生命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沧海一粟之感。这是人生的无常与历史的无常相互龃龉的产物,“无常感体现在面对历史的恢弘与循环,人们的渺小之感也应运而生”。叔叔从沙漠发家,并最终回到沙漠,这是一种循环,是一种天理人欲纠缠其中的循环。驼子的“天理”是知足常乐,叔叔的“人欲”是步步高升。当世间的一切早已如过眼烟云之时,谁还会记得自己当初那卑微的初心。为时已晚后,才发现那个被我们弃之如敝履的初心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但毕竟为时已晚。这正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刘小枫先生在《叙事与伦理》一文中认为,现代的叙事伦理可分为两种,即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
虽然叔这具“沉重的肉身”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出现在作品当中,但是这“具体的偶在个体”却承载了作家“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某些意图。文本中行文的暗线便是刻意模糊的历史叙事,正是作家的这种障眼法导致了“乡土叙事”与“身体叙事”的某些乖离。身体所追求的,乡土不能给予;乡土所承载的,身体偏要突破。当二者不能圆融之时,作家找到了破解此类迷关的屡试不爽的万能解药——传奇叙事,让人生如梦、万境归空的佛理道境出面调和,轮回与无常之感让文本的宿命论色彩渐次激升。而这种所谓的“宿命”,与其说是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最终告饶,倒不如说是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涟漪犹在。
作家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摄影师,他不能把有限的时空记忆转化成直观可感的观瞻之物。作家能做到的只能是在有限的文本空间内,去诉说自己的关切与耳语。我们从来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们总是一部分的诗人,我们的情感或许只能用逝去的诗歌来翻译。”而这“逝去的诗歌”便是作家在“精神还乡”的路上浅吟低唱的礼魂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