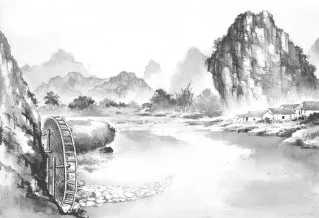
张衡,这位南阳籍的东汉名士,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并称『汉赋四大家』,他模拟班固《两都赋》而创作的《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是传世的辞赋名篇。但其实他真正广为时人所知的,还在于他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据《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出生于世家望族的他,从小通晓五经六艺,『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更为难得的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可以说,无论从天赋还是性情来说,他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读书搞研究的好苗子。他发明的候风地动仪,制作精巧,能够准确觉知地震发生的方位,验之如神,名震古今,这在小学课本上,已经作了十分生动的普及。因为在科学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被后世尊为『木圣』(即『科圣』),为『南阳五圣』之一。月球上有以他命名的环形山,太阳系还有以他命名的小行星,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人文情怀的理工男,或者说这样一位被科学事业耽误的文学家,真的是牛出了天际。不得不感慨,像他这样文理兼备而不偏废的人,历史上绝对是凤毛麟角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标格清奇、品学兼优、『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崔瑗语)的奇才,却很难在仕途上一逞其襟抱。他的一生,跨越了从章帝到顺帝等六任皇帝,从一开始的郎中、太史令,做到后来的侍中、河间相,乃至尚书,从官职上而言,不能说卑微,但是就抱负而论,也说不上得遇。主客观的因素都有,『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后汉书》),他淡泊名利,秉性忠正,不喜欢、不善于更不屑于去钻营,他在《应闲赋》中更是寄语明志道:『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这是他主观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东汉,几位皇帝多英年早逝,最短命的殇帝,去世时还不满周岁,加之宦官和外戚干政日益严重,章、和二帝之后,国力盛极而衰,朝政日益腐败,每况愈下,这是客观形势。张衡为侍中时,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宦官之做贼心虚和嚣张肆虐,可见一斑。张衡诡对,不敢犯怒明言,固然懂得明哲保身,但这皇帝也是,问这种敏感问题,为什么非得当着众人的面?不会私下召见么?也许有意为之,或者太傻太天真。在这种江河日下的环境里,能够独善其身,而不随波逐流,已经是相当难得了,想要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则近乎痴心妄想。更何况,张衡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尽了进谏警示劝勉的职分。而他在河间相的任上,面对『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的混乱局面,能够『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这说明他还是颇有执政能力和水平的,而非纯粹的书生意气。至于他内心的抑郁和真实想法,则更多只能在其《思玄赋》《骷髅赋》和《归田赋》等诸多文学作品中排遣宣泄出来。
《归田赋》是张衡写的一篇抒情小赋,从内容来看,当是其晚年之作,因仕途不如意,而欲归于田。张衡少无俗志,本就不恋权位,早在《应闲赋》中,就有句云:『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换言之,他认为自己的出仕,也无非是『朝隐』。他在《思玄赋》中有『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崟』之句,在《骷髅赋》中同样表达了其对世俗的厌倦,和对『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的向往,包括晚年的上书乞骸骨,他的超脱是深入骨髓贯穿一生的。他本身做的学问研究就是宏观领域的玄元之道,通于阴阳变化,视野开阔,格局高远,加之在经历了政治的残酷和仕途的险恶之后,早已经看透尘世的蝇营狗苟,连『朝隐』的必要也没有了,向往归田无非是求得一方清静而已。
赋文开篇写道:『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前两句既是能力的自谦,也是心迹的自陈。『俟河清乎未期』,说明作者对于世事已经感到绝望,与《思玄赋》系词中的『俟河之清只怀忧』同义,相互印证。『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作者借燕人蔡泽郁郁不得志之际请唐举相面的典故,寄托自己内心怀才不遇的感慨。一句『谅天道之微昧』,与其作《思玄赋》时,『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也是异时同慨。这些都正好可以含蓄地说明作者归田的原因。
在作者的向往中,理想田园生活的自然景观应该是这样的:『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这是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与惬意。当此之时,作者可以尽情享受高歌长啸和仰射俯钓的诸般乐趣,正所谓:『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和庙堂中处处掣肘如履薄冰的工作环境相比,田园是可以拥有自主权的生活场所,在这里,他可以享受身心的自由和解脱,『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
但作者并未因此而完全放任自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多年的人文修为,早已在他内心建立起一条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道法则。于是,『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老子的什么遗诫呢?大概是『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等逸豫亡身之类的警示。有鉴于此,作者在适度的游乐之后,回归到住所斋室,弹起五弦琴,深研古代典籍,练书法,搞创作,开始了诸般修身养性的室内活动。可以说,他的隐逸生活,是内外兼修,自然与人文并重的。
从张衡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来看,他受儒道文化影响颇深,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将儒、道、易三者贯通为一。他十分推崇扬雄的《太玄经》,曾经用心钻研过它,并对崔瑗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关于《太玄经》,略晚于扬雄的桓谭曾经评介道:『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玄经》三篇,以纪天地人之道,立三体有上中下,如《禹贡》之陈三品。』(《新论》)桓谭对扬雄也是激赏不已,他颇有远见,认为《太玄经》其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桓谭论《太玄》,已经点明其融贯儒、道、易三者的倾向,张衡宗《太玄》,无疑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学术主张。至于扬雄,能在生前身后有这两位知音,也算不枉此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