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是每个人必经的人生阶段,是由幼年到成年,由混沌到启蒙,由懵懂到文明的蜕变过程。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中这样定义成长小说:“时间进入人的内部,极大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含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经历一系列磨炼之后,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包含生理、心理、精神等多个层面的成长,也伴随个体融入社会,走向复杂的成人世界。
而苏童对少年成长的关注,解构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叙事,是典型的反成长。成长主体没有能够经历挫折和磨炼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个体和社会始终对立、疏离。主人公并没有按照成长小说一贯的模式,在成长过程中得到引导和教育,反而表现出孤独、迷茫、无助。他们甚至试图去对抗、反叛外部世界,但弱势个体的成长之路不断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和侵蚀。最终他们既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也无法保守自己的本真,无可避免地走向沉沦和堕落。
苏童的《舒家兄弟》书写了主人公舒农破碎的成长片段,是苏童反成长叙事的代表性作品。本文以《舒家兄弟》中的成长叙述为例,探究舒农成长悲剧的形成原因。除了《舒家兄弟》之外,反成长叙事在苏童的作品中高密度出现,具有普遍性和覆盖性,探微这些文本,背后是作者关于“文革”的独特回忆和反思,以及对成长问题的哲理性思考。然而,苏童的成长主体始终在成长的路上徘徊迷茫,并不是塞林格笔下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的成长写作仍有广阔的空间和前景,“成长”未完待续。
一、 《舒家兄弟》中成长悲剧的外因
《舒家兄弟》中的舒农是生活在香椿树街上的边缘人。家庭暴力、学校排斥、社会嫌弃,所有的人都孤立排斥他,挤压他的生存空间,他与周围异化的空间形成对抗和冲突,他曾试图反抗周遭的话语体系却遭遇失败,走向沉沦。最终他通过自我毁灭结束了成长之路。舒农成长悲剧的形成因素是复杂的,《舒家兄弟》中着重放大外部的社会群体、家庭父权和内部的主观欲望这三层内涵。从客观的外部环境来看,“文革”时代下香椿树街的沉沦社会,舒农作为本真的个体与他生存群体形成对立冲突,家庭中暴力罪恶的父亲压榨他的生存空间,传统文学中父亲的崇高形象被彻底摧毁。
苏童在《舒家兄弟》中多次暗示故事的时代背景,两次提及“这是一九七四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点出香椿树街沉沦世界的现实依托。“文革”的革命狂热造成了理智缺失,物质、精神的双重匮乏,个体已经消失,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整个社会群体都是沉沦、混沌的状态,恶劣的外部环境直接破坏了少年的成长。
《舒家兄弟》中的香椿树街就是“文革”时代的缩影,香椿树街竖立着三个大烟囱,嘈杂喧闹、拥挤脏乱,在《城北地带》中苏童借沈庭方之口点出了他眼中的香椿树街,“类似的邻里风波往往在不偏不倚的舆论裁决中结局,没有绝对的胜方和负方,公正之绳本身也是模糊和溃烂的,就像街上随意拉起的晾衣绳,或者就像工厂从香椿树街凌空高架的那根输油管道,人们每天从此经过却易于忽略它们的存在”。这样的生存环境混乱无序,邻里关系不和谐,人们冷漠自私、缺乏公正正义,在这条荒诞的街道上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丑恶的事,苏童写的这个南方生活群体充斥着人沸腾的欲望,人性扭曲而丑恶,而舒农是生活在这个混乱群体中的边缘人。
在小说中,除了舒家和林家之外,这群旁观者一直被称为“人们”“他们”。“人们”“他们”作为称谓有一种模糊不确定性,缺少个人的特征表现和真实感。文本中对旁观者这样的书写还有好几处,香椿树街群像总以“人们”为单位整体呈现,换言之,他们根本不存在个人的特征,他们已经是一个人性缺失的整体。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社会秩序混乱,家庭伦理坍塌,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现象。父亲老舒和邻居丘玉美每晚在楼顶偷情,舒工和涵丽还未成年就开始重复他们父母的偷情行为,香椿树中学的老师们普遍厌恶舒农,老师同学们都以看到舒农受罚为乐,酱油店的女人们整天传播谣言,糖果店的老史强奸了少女涵贞。香椿树街的游戏规则是一致的,他们人性丑恶,虚伪冷漠、沉迷欲望。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被掩盖的,就像一个个复制粘贴的人物。苏童自己也说,“香椿树街人对事物很敏感,但不善于采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这个生活群体普遍处于迷失的深渊中,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沉沦世界。
小说中苏童就暗示舒农和香椿树街群体的差异性,“你如果了解舒农你就知道这说法不正确。舒农不是傻孩子。你如果到过香椿树街,你会知道这是一个聪明孩子的故事”。苏童认为舒农是聪明的孩子,而在香椿树街的人看来舒农是傻子,这种差异源自舒农的本真天性,他尿床,亲近猫,好奇心强烈,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舒农都还处于儿童阶段。这也致使他做出本能、不可控的行为,但他周围的人们却无法理解,认为他是个怪物。舒农的本真天性与他生活群体的认知格格不入,他的个体生活与常人不同,违背了他所在群体的行为法则。这个沉沦群体在舒农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反面,因此无论是他的家庭和邻人都一致去驱赶这个异类。
舒农自始至终都羡慕猫的生活,小说一开始便提到舒农认为做猫比做人有意思。猫作为香椿树街无人管的动物,行为完全不受约束,“猫是能看见世界上所有事情的”,它可以走遍香椿树街的每一个角落。猫作为非人的存在,不需要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此猫象征的是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现实生活中舒农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在各种场合中都招致他人的反感与厌恶,所有的人都在一步步吞噬他,自由自在的猫是舒农的“精神乌托邦”,是舒农渴望达到的生存状态。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猫作为非人的存在,是“他者”,在香椿树街人们的眼中是被遗忘的存在。但在舒农的眼中,猫是高于人的,做人不如做猫,本真的猫高于沉沦中的人,这也是舒农对他周围群体的变相嘲讽。
猫、舒农、香椿树街的人们这三者,构建了一条生存状态的天平,猫和香椿树街的生存群体是两个对立面,舒农在绝对本真的猫和沉沦的群体间挣扎徘徊,处于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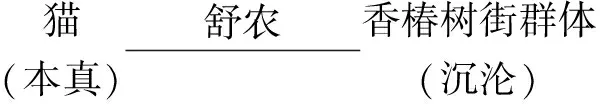
舒农生活的外部环境除了香椿树街这个社会,与他更密切相关的是他的家庭环境。对于成长中的少年来说,家庭的长辈是他们最重要的引导者。但在舒农的家庭中,母亲胆小怕事,毫无存在感可言。他整日生活在父亲老舒、哥哥舒工的暴力中。父亲老舒不顾伦理和邻居丘玉美偷情,淡漠亲情,违背伦理道德;暴力对待孩子,丧失父性。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父亲的神圣地位,《舒家兄弟》中父亲的形象具有颠覆性,父亲的野蛮、残忍被苏童渲染到极致,父亲被审视、打倒。传统的亲密伦理关系被打破和颠覆,父子关系疏离和冷漠,父亲的丑恶罪恶无形中影响了下一代,书写了一曲亲情的悲歌。
父子关系始终处于对立紧张状态。老舒和舒农除了血缘上的联系之外,甚至连陌生人都不如,父亲对儿子没有任何感情认同。父亲一步步挤压舒农的生存空间,最终父子走向分裂和对抗,传统意义上的父子关系被彻底瓦解。舒农生活在父亲的淫威下,一直试图反抗。舒农一次偶然看到了父亲老舒的偷情,老舒害怕舒农爆出自己的秘密,多次威胁要卡死舒农,威胁舒农时他的丑恶嘴脸暴露到了极致。舒农意识到他不再只是弱势地被父亲欺负,而是成为父亲幸福中的阴影。舒农试图进一步偷窥侵入父亲的生存空间。“他追踪了他们,因此一切都让他先看见了,有谁能躲过猫的眼睛?”舒农通过偷窥反抗对峙丑陋、强势的父亲,企图在“他者”的生存环境中获得话语权。然而面对父亲强大外力的压迫和蹂躏,作为弱势的个体终究无力抗衡,老舒对舒农生存空间的侵蚀在舒农自杀前达到极致。老舒漠视舒农的意愿,把他的眼睛蒙起来,耳朵塞住,自己和丘玉美就在旁边偷情,此时的舒农作为人最基本的生理感官权利被剥夺,他已经被看成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物”。最终舒农对父亲的反叛是以自己的毁灭为代价的,舒农又一次受到父亲的暴力对待,不让他吃饭,骂他小杂种,被摔出门外。舒农对父亲已经丝毫没有感情和依赖,对他而言,父亲已经变成令人憎恶的仇敌,他想要报复父亲,反抗父权。舒农在家里面浇了汽油,试图烧死父亲。至此,对于舒农来说父亲不再存在。
从另一个维度来看,父亲的丑恶罪孽在潜移默化中投射到少年身上。父亲老舒和哥哥舒工几乎是两个复制粘贴的人物,性格、行为都如出一辙,父亲的暴力和糜烂都被舒工全部接纳。“舒农已经习惯了舒工对他的拳打脚踢,他知道舒工有理由这么干。”舒工甚至对舒农说,“我不揍你让爸来揍你”,老舒和舒工已然成为同一个阵营的人。如果说舒工是老舒的完整复制版,舒农则是无可避免地也沾染了父亲的恶性。当父亲在舒农身旁偷情,是老舒主动把自己的罪恶暴露在舒农面前,父亲变成完全没有道德良知的存在,没有引导舒农成长,反而是诱惑他变恶。在纵火前,“舒农坐在门槛前,朝父亲看了几眼,他的手在地上划着字,有一个字是‘操’”。“操”这个词完全是父亲的行为和话语特征,弑父也是通过纵火这样的暴力行为来实现的,舒农最后的心理活动和报复行为本身,已经不再是那个本真舒农应该有的姿态,父亲的罪恶已经侵入他的生存状态中。
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的严父或慈父,《舒家兄弟》中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而审父和弑父也是苏童作品中一贯的母题。《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沉迷于金钱和情色的陈宝年对儿子狗崽不闻不问,孩子只是他纵乐后的意外产品。《桂花树之歌》中父亲为了利益逃离了“我”和整个家乡,父亲是不折不扣的背叛者。《刺青时代》中的王德基对好心给小拐喂奶的女人耍流氓,对天平整日拳打脚踢,完全是暴力的代言人。《河岸》中“我”对父亲库文轩的身份充满困惑和质疑,父亲的身份难以被认同。父亲对少年来说,本应是成长路上重要的引路人,苏童作品中的父亲却是缺失或负面的存在,变为少年成长道路上的障碍。从畏惧父权到反叛父权,少年乞求离开父亲,拥有自由的生存状态。本应作为启蒙者的父亲是畸形的存在,父亲被拉下神坛,权威地位被消解。
二、 《舒家兄弟》中成长悲剧的内因
从主体内部来看,舒农对情色的偷窥加速了欲望的膨胀、泛滥,本能的欲望扭曲畸形,成长必然走向幻灭的结局。少年本来就处于成长发育阶段,性幻想本来符合他们自然的天性,但他们的性成长却是不健全的。性欲想象错位、膨胀、泛滥,欲望本能缺乏个体理性的约束。舒农欲望的沦陷主要是通过偷窥来实现的,偷窥行为几乎伴随着舒农的成长,一开始舒农的欲望意识多出于本能的性幻想,通过一次次不恰当的偷窥,欲望从朦胧地觉醒到无限膨胀变形,最终在浑浊肮脏的欲海中沉沦。小说中舒农的最后一次偷窥,象征本真彻底消失,对性的本能意识失去了应有的纯洁。老舒和丘玉美原来的偷情基地被发现,他把舒农的眼睛蒙起来,耳朵塞住,他和丘玉美就在旁边偷情,“就这样舒农迎来了他少年时代最难忘的夜晚”:
有一种强烈的蓝光刺穿沉沉黑暗弥漫了舒农的眼睛,舒农无法入睡,也无法活动身子。他大口地吸进屋子里那股甜腥的气味,又大口地吐出去。他浑身燥热难耐,他想或许是那种暗蓝色光芒的缘故,它像火一样炙烤被缚的舒农,使他的灵魂像背负火焰的老鼠一样凄凉地叫着。
舒农这一次已经不再需要眼睛来偷窥,他在黑暗中用心也能感受到身边人的动静,真正摧毁舒农的是从第一次偷窥就出现的“蓝光”。第一次偷窥舒农只是觉得女性的身体是蓝色的,给他带来本能的感官满足和审美愉悦,他的这种感觉是人本能状态下心理代入式的移情。但随着一次次偷窥的深入,舒农对象征情色的“蓝”越来越迷恋,这一次他的感官已经完全被这种情色的诱惑覆盖。他甚至对这种蓝色的喜爱不再停留在感知层面,他感到浑身燥热,潜意识地表达出自己的性欲望,他想要获取那种蓝色的光,他想要落实到行动上,实际地像父亲和哥哥那样和女性水乳交融。
舒农的偷窥内容一直以男女的性爱为主,偷窥本质上对少年来说是一种模仿和学习,是构建认知的自我习得方式。通过多次对性爱不恰当的偷窥,舒农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父亲和哥哥行为的影响,量变的最后是质变,在最后一次偷窥中他已经陷入糜烂的性欲中难以自拔。在整个偷窥的心理活动中舒农再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只猫,舒农觉得自己的灵魂“像背负火焰的老鼠”。他一直认为香椿树街的人就是一群仓皇的老鼠,舒农眼中的老鼠等同于他周围的群体,这一次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老鼠,就是这个沉沦群体中的一员。舒农从猫到老鼠的转变,意味着他陷入真正的沉沦。他本质上已经和父亲、哥哥这样的人没有差异,他本真的精神世界完全崩塌,失去了个体性,沉入不可自拔的欲望泥淖。
苏童的作品中少年的性成长普遍扭曲,他们被本能欲望撩拨、驱使,性欲望肆无忌惮地畸形发展。《黄雀记》中保润躲在仙女的窗户下目不转睛地看仙女猩红色的脚指甲,内心愉悦而激动;《城北地带》中的红旗和《黄雀记》中的保润都因为本能冲动下的强奸,被送入监狱;《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狗崽整日在幽暗的阁楼中手淫,“他的脸终日肿胀溃烂着,在阁楼的幽暗里像一朵不安的红罂粟”。少年们生活在无性的年代,性教育匮乏,致使他们对性欲的想象更为强烈,但因为理性意识的缺失,他们却像郁达夫《沉沦》中的主人公一样,被本能欲望完全控制,在欲望中迷失自我。
三、 苏童反成长书写的独特观照
纵观苏童的少年写作,少年的成长普遍呈现片段式的成长悲剧,成长永远都是破碎幻灭的。正如前文提到,这群少年普遍生存在荒诞的社会群体中,家庭环境分崩离析,他们的性欲望扭曲、颓靡,他们成长的困境惊人地一致。不仅如此,最终少年的成长都走向共性的悲剧结局。《河岸》中库东亮最终被油坊镇的世界排除在外,变成失去存在意义的“空屁”。“即日起禁止向阳船队船民库东亮上岸活动!!!”《城北地带》中年幼的美琪因为被强奸选择跳河自杀,成为香椿树街上的幽魂,少女的生命戛然而止。小拐的结局是在黑暗中度过一生,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个精神扭曲者,“孬种小拐在阁楼和室内度过了他的另一半青春时光……孬种小拐羞于走到外面的香椿树街上去,渐渐地变成孤僻而古怪的幽居者”。这群少年或是成长之路被生生切断,走向宿命般的死亡;或是成为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香椿树街的世界中;或是精神已然扭曲、分裂,灵魂陷入永恒的黑暗中。显然,反成长叙事在苏童的作品中已经构成巨大的网络,成为苏童成长书写普遍的形态特征。弗洛伊德认为,某些被意识精心潜藏着的动机,最终会导致某种看似偶然的事故。苏童笔下这群少年共性的成长悲剧看似偶然,其实具有必然性,背后隐含的是作者苏童的话语言说,一方面他对“文革”时代中的少年成长提出质疑和反思,另一方面这也构成他对成长问题的哲理思辨。
苏童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的青少年阶段以“文革”为成长背景,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也构成他重要的文学内涵。《河岸》中慧仙扮演《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独立纵队》中男孩群体对小堂的批斗,《城北地带》中那群暴力的少年,“文革”的书写痕迹深深渗透在苏童的作品中。
苏童的童年深陷在“文革”的黑暗当中,“童年生活其实一直在我们身上延续甚至成长。一个人一生中要面临多少个黑夜,而孩子们眼睛里的黑暗是最浓重的,一个人一生中同样要迎来多少个太阳,而太阳对于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寓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童年是值得我们描绘的”。同时期出生的作家余华也曾回忆“文革”的荒诞,“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言语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文革”以极大的破坏力造成家庭、社会的全面崩塌,成人世界处于集体失语中,人性的缺失和沦丧已经变成社会常态。苏童目睹了“文革”时的狂乱与荒诞。“文革”构成了这群作家对世界的最初认识,“文革”灾难给苏童这一代的成长主体造成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
童年的“文革”阴影也成为苏童的文学资源,通过书写“文革”中的成长,作家重新认识了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相比较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把“文革”直接作为宏大主题,九十年代苏童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写作从这种宏大的话语场中退出,关注成长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关注的核心是成长中的少年个体。“文革”造就了这群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的少年,“文革”是他们成长的大背景,香椿树街的沉沦群体就是“文革”社会的缩影,他们是这个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他者”。在苏童的反成长叙事中,“文革”作为宏大叙事背景,直接阻碍了个体的成长,个人和时代始终对抗、疏离、冲突,“文革”历史语境下的少年个体无法找到话语的空间和存在的意义。
苏童谈到自己的成长创作,“共同的特点是以毁坏作结局,所有的小说都以毁坏收场,没有一个完美的阳光式结尾。所有的成长小说没有一个以完成成长而告终,成长总是未完待续的”。从这个意味上来说,这是苏童主观能动性的反成长,他认为成长本来就是宿命般的悖论。成长主体永远都是“在路上”的姿态,看不到出路,处于无助又彷徨的生存状态。成长之痛在他那里是观念性的存在,成长悲剧性的收场具有必然性和深层内涵。成长书写渗透着苏童哲学层面的思想内涵。
苏童自己曾经说,“潜藏在自己作品后面的,是一个身体不好,总在一条街区上游荡并东张西望的少年”,这个东张西望的少年就是苏童自己。在《舒家兄弟》中叙事者除了舒农之外,还有叙述者“我”,也就是隐含作者苏童。苏童不动声色地看待少年的成长,“那天傍晚我看见舒农在石灰场的乱石堆上晃来晃去”,“我看见舒农在初冬冷清的街道上游逛”。苏童的叙述冷静客观,几乎是零度叙述,他冷漠地看着香椿树街的少年在困境中徘徊,以淡然的眼光看待这群成长主体,这也构成他对待成长这一问题的态度和认知。少年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紧张疏离,个体试图抗争却最终失败沦落,成长宿命般的悲剧,这些在他看来本来就该如此,成长终究处于挣扎和迷茫之中,个体难以走出生存困境,最终陷入虚无。就像海德格尔认为,一旦此在作为常人,此在就涣散在常人中,掩盖了本真自己,封锁本己的精神世界。苏童的少年总是笼罩着生命永恒的荒凉和孤独,对存在价值和生存归属感的追问始终笼罩着主人公,这种生命的虚无感和孤独感挥之不去。在苏童看来,成长就应该是幻灭、破碎的片段,他没有试图去为这群少年寻找出路,成长本身就是荒谬的,令人失望的。

结语


注释:①M.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②《舒家兄弟》是苏童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最早刊登在《钟山》1989年第3期时名为“舒农或者南方生活”,收入文集后改为“舒家兄弟”。
③如小说中写“舒农觉得人群像仓皇的老鼠一样朝他家涌来一片嘈杂声”。苏童:《舒家兄弟》,《刺青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④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世界两侧》,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引文中省略号为本文笔者所加。
⑤苏童:《走向诺贝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⑥余华:《余华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⑦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
⑧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8~224页。
⑨苏童:《舒家兄弟》,《刺青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⑩如“看见舒农的身体像猫一样凌空跳起,掠过他的头顶”。苏童:《舒家兄弟》,《刺青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