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种“自主”:《红高粱家族》的本能个性主义
◆ 彭秀坤
莫言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肉体本能个性主义倾向的人物,像《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秋水》中的老三、《丰乳肥臀》中的司马库和《生死疲劳》中的蓝解放等,这些人物的个体经历、性格气质及生存背景有明显的差异,但他们听从肉身本能的个性自由精神是相通的。这些人物都带有一种来自个体肉身本能的个性“自主”精神。莫言小说中人物的个性“自主”,与现代意义上的个性自主并不相同。五四现代文学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个性主义其实是一种带有民主、平等思想的个体主义。而莫言小说中的个性主义主要是指人物顺从个体肉身本能,而不完全听从外来思想命令进行活动,其与五四文学中所讲的那种来自西方的民主、平等的个性自主的内涵是有差别的。因此,莫言小说的现代性已不同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而是一种既注重主体性的张扬,又重视人的灵性、本能或情感表现的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认为:“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与情感需求的强调,实际上,既是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包含着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乃至否定。”
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为莫言带来世界声誉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红高粱家族”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小说充分展现和探讨了肉身“自主”人物个性扩张的魅力。莫言对其小说中的肉身“自主”人物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对其敢于追求肉身本能“自主”的精神是肯定和赞赏的,但对“自主”中的唯我主义倾向又满怀忧虑。《红高粱家族》对人物肉身“自主”的探索最为全面和深入,也最能体现莫言小说的审美现代性诉求①。
一、 肉身“自主”扩张的特点
莫言在分析《红高粱》为何能引起这么大反响时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②。这种精神不但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民众的精神需求,而且那种来自身体本能的个性张扬精神给现实中久被压抑的人们以心理安慰和精神鼓舞,另外,这种“自主”人物的个性张扬精神也具有普世的价值,因而才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红高粱家族》发表后,评论界对其主题的评价形成了一些相反或相对的看法。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小说揭示了民族的生命意识,表现了作者所推崇和讴歌的“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③;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余占鳌的血性仅仅“是鲁迅所批判的土匪文化的主要内容”,“认同这血性的‘土匪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误解”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红高粱家族》的“‘匪气’象征生命活力、‘侠气’象征人格魅力、‘正气’象征民族意志”⑤。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那为何对同一部作品主题的理解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这主要是因对这种来自肉身本能的个性自由、个性张扬精神的不同看法所导致的。
莫言说,“《红高粱》歌颂了一种个性张扬的精神”⑤,但其在表现人物个性“自主”的张扬精神时也一直持矛盾而暧昧的态度,他把“高密东北乡”想象成最具个性“自主”精神之所在,但它也因此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⑦的地方。可见,在莫言的意识中,这种源自生存本能的个性张扬精神本身就具有矛盾性。小说既歌颂来自身体本能的个性张扬精神的原始生命强力,又对其利己负面效应持否定态度。
莫言小说中“自主”人物的个性扩张建立在人物身体本能的基础上。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想虽然主要源于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但五四时期许多思想家意识到,要想获得个性自由,必须反对奴化意识,寻求民族自然、原始生命野性的回归。鲁迅批判国民脸上只剩下了“驯顺”的“家畜性”,而“兽性”或“野性”⑧已消失了;陈独秀曾在1915年撰文主张把培养“兽性主义”作为教育之方针,他所说的“兽性”主要指“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⑨等思想。这一思想在五四文学中没能获得充分的表达,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有所体现。像沈从文的《龙朱》、《虎雏》、《月下小景》和艾芜的《山峡中》等作品,都张扬了一种原始生命的野性。与沈从文、艾芜等人的作品相似,莫言小说人物的个性张扬也是建立在个体生存本能的基础上,是一种“以自身为本位”的个性自由精神,洋溢着一种未经驯化的原始野性色彩。但与沈从文和艾芜等人的作品不同的是,莫言小说对这种建立在身体本能基础上的生命野性力量的探索更为深入、更为贴近人物的自然肉身。
小说为了探索“自主”人物个性张扬的可能,为人物个性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几乎无家庭压抑的特殊背景和超阶级的土匪身份,这与“五四”现代文学中的个性觉醒者大都有着封建大家庭的家庭背景和留学西方或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份完全不同。首先,作者将余占鳌放在一个缺乏父母关爱的家庭环境中。余占鳌从小无父,母亲在儿子杀死与之偷情的和尚后自杀了,因此,他其实长期生活在一种无父无母的环境中,这也说明了他受家庭的约束较少,自然个性较少受到家庭的压制。在莫言的心目中,家庭带给孩子的并不只是温馨和呵护,而更多的是对孩子个性的压抑。他认为,家庭对孩子来说绝对是一种痛苦,“极端的爱”里包含了“极端残酷的虐待”。戴凤莲的家庭关系,通过其父母为了得到一匹骡子就把她卖给了财主的儿子——麻风病人单扁郎为妻可见,其父爱母爱脆弱得如一张薄纸。正因余占鳌和戴凤莲成长在这种缺乏“正常”的父母关爱的家庭环境中,所以, 他们对一切有碍个性自由发展的势力都有着一种本能的抗争。其次,为了体现其个性自由精神,作者赋于这些“自主”人物以超阶级的独立的社会身份——土匪。莫言认为,“土匪是超阶级超社会超制度的一个产物”⑩。正因余占鳌具有超阶级的土匪身份,所以在抗战期间,他才完全体现出一种独立不羁的人格,他既不臣服于国民党的领导,也不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挥。在抗战来临时,出于生存本能,他自觉地联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共同作战,但在合作期间,他又始终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五四”现代文学中的个性觉醒者因大都有着封建大家庭的背景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份,其来自身体本能的个性意识大都受到严重的压制,他们也大都身陷苦闷与彷徨之中;而莫言小说中的“自主”人物有着宽松的家庭背景和超阶级的自由人身份,因而他们的来自身体本能的自然天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莫言小说“自主”人物的个性扩张是建立在身体本能的基础之上,这在其情爱叙事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许子东在论述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描写时认为,正常的性爱描写是创作者“企图在艺术中正视并讨论人的自然天性的一种尝试”。莫言小说创作中的情爱叙事往往也是探索人的自然天性的一种手段,这与现代文学的情爱叙事传统是一致的。在他的一些小说中,情爱往往是个性独立自由程度的象征,是建立在个体生理本能基础上的个性自由的表现。余占鳌之所以爱上了戴凤莲,有着潜意识的作用。小说写他因为握了“我奶奶”的脚而唤醒了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也彻底改变了二人的一生。欣赏小脚作为传统文化陋习之一,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曾彻底地鞭挞了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对小脚文化的认同,表面上似乎体现了创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欣赏,但其目的却是想通过爱欲的展示探索人物的个性“自主”问题。《红高粱家族》通过对余占鳌和戴凤莲的情爱叙事,展示了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爱欲本能,体现了对个性自由、个性张扬的探索。
如果把《红高粱》的情爱叙事与五四时期的情爱叙事予以对照,其所反映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差异是明显的。像冯沅君的小说《旅行》对一对未婚男女结伴旅行、夜宿旅馆的情爱叙事就颇具五四时代特色。《旅行》情爱叙事体现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局限,但确实反映出特定时代的文化特征。小说表现了理性约束下爱情的纯真,而这一切在《红高粱家族》中则完全沦为情爱的放任。二者一重精神之爱,一重肉身之惑,表现出鲜明的两极化倾向。
身体解放,特别是肉身解放,是“五四”现代文学未能完全实现的表达,也是新时期之前主流文学未能跨越的禁区。莫言在谈到“红色经典”作品时,认为当时许多小说描写的爱情,“革命的意义大于生理的意义”,《红高粱家族》中描写的情爱,基本还原到了个体的生理性身体的层面,也可以说,生理性身体本能基础上的爱欲追求是莫言小说情爱叙事的立足点。再如莫言的小说《爱情故事》中的爱情完全是来自身体本能的吸引与诱惑,这种情爱叙事具有超时代、超阶级、超政治的特征,但也有过于宣扬身体本能的倾向。
莫言小说中“自主”人物的个性扩张是建立在身体本能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个体生存本能基础上的,是一种强烈的个体生存观念的体现。为了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这些“自主”人物敢于同一切阻碍生命成长的势力作斗争,敢于为生命的自由发展牺牲一切,体现出一种原始本能的生命野性。在余占鳌等人物身上,确实体现出了一种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信念。“这样强烈的生存观念,是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热爱,也是中国人对于未来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表现。”余占鳌作为这类人物的代表,他嫉恶如仇、狂放不羁,作为土匪,他偷情野合、杀人越货,在生存本能下任意展示生命的强硬姿态。为了个人爱欲,他敢于反叛封建礼教,敢于杀死强娶戴凤莲的单家父子。但在抗日期间,他的这种高扬的生存意志又体现为鲜明的爱国精神。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也表达了对民间个体生存意志的赞扬。
不可否认的是,莫言小说表现的“自主”人物的个性张扬精神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个人主义特点,但正是这种非理性的身体本能为“自主”人物的个性张扬提供了动力源。许多人认为《红高粱》反映了对酒神精神的赞美。其实,凡是具有强烈的个性意识的作品,似乎都可以从酒神精神中找到理论支持,像屈原、竹林七贤、李白和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都有人从酒神精神的角度解读过。莫言在塑造这些“自主”人物时,都是基于本能层面的身体反抗意识,这与重视肉体的尼采超人哲学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尼采一生努力的目标是“回到本能”,他认为“理智是肉体创造的小理性,肉体和他的本能乃是大理性”,因此超人总是从本能里面找到真正的自我,“所谓的自我就是本能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回到身体的本能,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才能寻找到个性“自主”的动力。弗洛伊德把由“本我”需要而引起的紧张背后的力称为本能,他认为这是人的个性行为的真正的动力源泉,“本能意味着表现在精神生活上的身体的需要,它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因”。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所谓的个性张扬实质上就是“生的本能”的张扬,而“生的本能”就是一种爱的本能、自卫的本能,或者说自我保护的本能。
这种源自人物身体本能的“自主形象”扩张往往具有鲜明的抗争与反叛意识。莫言说:“我觉得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白昼宣淫’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报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一直是文学的主题,但五四文学中一直缺乏真正的“以自身为本位”的个性“自主”人物,鲁迅说要培养新一代“敢说,敢笑,敢怒,敢哭,敢怒,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一直呼唤超人的出现,“所谓‘新神思宗’意志解放的非理性个人主义,一直是鲁迅创作的原动力,也是他创作的目的”,但他的笔下却没有完整的“超人”,出现的大多是一些“狂人”或“疯子”。
莫言的小说写出了敢想敢做的精神,写出了来自于身体本能的个性“自主”的扩张者,但这样的人物都是生命本能的扩张者,凭借的都是人类生命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并不完全是现代文学所倡导的建设性的个性自由思想,有时还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除了余占鳌外,《秋水》中的为情私奔,去高密东北乡创造独立世界老三和二小姐,还有《天堂蒜薹之歌》的高马、《丰乳肥臀》的司马库等都是“自主形象”的代表,这样的人物最终都只能走向自我否定的悖谬性困境。
二、 肉身“自主”扩张的困境
莫言说:“我觉得鲁迅最缺少的是弘扬我们民族意识里面光明的一面。一味的解剖,一味的否定,社会是没有希望的。”这话虽不一定准确,但反映了莫言小说创作有着对五四文学传承与创新的意图。因鲁迅也曾致力于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像《非攻》中的墨子、《理水》中的大禹等都是其塑造的民族脊梁式的形象,可以说,“莫言和鲁迅都有很强烈的英雄‘情结’”。与莫言相比,鲁迅似乎对民间英雄人物缺乏深入探讨,但其代表作《阿Q正传》中的阿Q,作者其实是把其“作为‘吃人社会’的英雄人物”来塑造的,其“精神胜利法”也是作者“要使阿Q活下去的意志和作者的绝望——对黑暗社会的认识所展开的‘内在抗争’”的表现,而莫言小说中塑造的民间英雄形象,也是要“使人物活下去的意志”,也是基于个体的生存本能,在这一点上,二者又具有某种相似性。莫言小说塑造的所谓民间英雄形象在特定时期体现了民族的正义精神,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也有相反的一面,那就是这种基于身体本能的“自主”人物常陷入悖谬的困境,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在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基础上,莫言随后又创作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和《奇死》等作品,组成了“红高粱家族”系列,贯穿这一系列小说的统一主题就是对本能个性主义的探索及其发展困境问题的认识。如果说《红高粱》主要展示了来自身体本能的个性张扬精神,那么《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和《奇死》等则主要揭示了这种源自身体本能的个性张扬的悖论,表现了对“自主形象”扩张问题的深入思考。
首先,基于身体本能的“自主”人物,往往只强调个体生存的利益,而缺少对其他个体生命的尊重,这主要表现在余占鳌的杀人行为上。对于余占鳌的杀人行为一直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因为其生存在一个杀人的世界里,“是一个必须杀人否则就活不下去或活不痛快的世界”,认为其率性而行的怪异行为,与“日军蹂躏中华河山相比,书中人物的特立独行,严格讲,并无任何出轨之处”;有人认为“像余占鳌这样在张扬自我个性的同时,扼杀了其他人释放‘生命激情’的权利,这本身不仅只是余占鳌的霸权表征,也是叙事者的叙事霸权的表征,而且还是解读者的话语霸权的表征”。余占鳌的杀人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体现了一种生存的目的,如果不通过杀人个体就无法生存,这杀人的目的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这行为导致了对他人身体的戕害,那么这种个性张扬精神就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的悖谬困境。此后创作的《蛙》表现了对残害他人身体行为的忏悔,这是莫言思想的变化,也是对余占鳌杀人行为的否定。
其次,小说中男性“自主形象”的扩张有时缺乏对女性个体生命应有的尊重,也预示了这种基于身体本能的个性张扬必然会走向悖谬性困境。《红高粱家族》的情爱书写,是建立在传统男权文化的基础上的,这种传统思想缺乏对女性个体的尊重。余占鳌当年不顾一切地爱上戴凤莲,但最终却始乱终弃,与使女恋儿私奔,最后过上了一夫多妻的生活。另外,《四十一炮》的罗通、《丰乳肥臀》的司马库和《生死疲劳》的蓝解放等人物身上也体现了这一点,这都反映了男权文化无视女性个体尊严的现象。海外学者朱玲发现《红高粱家族》的戴凤莲和恋儿分别被塑造成了“天使”与“魔鬼”的两极代表,如果说戴凤莲是“魅力”的代表,那么恋儿就是“恶魔”的象征。小说写恋儿被黄鼬勾去了魂魄,陷入了“诱惑与死亡的泥潭”,并且最终体内的“恶魔”发作,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戴凤莲和恋儿两位女性形象似乎也象征了“自主”人物扩张的正负两面性:如果说戴凤莲象征了个性适度扩张的积极、正义的一面,那么恋儿则无疑象征了个性过度扩张的消极、邪恶的一面。恋儿的形象其实也可以看作余占鳌的个性扩张最终会走向悖谬的象征。
基于身体本能的个性扩张往往会产生正负两面性的结果,这也是人们对其褒贬不一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现象,有人早就指出:
重视人的本能无疑是对人自身的一种尊重,扼杀人的本能只能是对于人自身的一种无情摧残。人的本能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在人的创世纪、在非常艰难的生存条件下,人生存的本能往往会发出璀璨夺目的人性之光;当人的本能超出他的合理性,便成了丑陋不堪的“罪恶之花”。
对于余占鳌式的基于个体生存本能基础上的“自主形象”,有人称之为“强力型人物”或“强力型自然人”,认为“强力型人物的自我矛盾”,“强力型自然人无法确立超越精神”,这最终必然会导致“自我瓦解”。这些对小说中基于生理性本能基础上的“自主”人物的分析,确实指出了这些“自主形象”的矛盾性所在。《麻风女人的情人》的春山和《生死疲劳》的蓝解放等带有鲜明的本能个性主义特点的人物也都面临着个体生存的现实困境。由此可见,与“五四”现代文学基于“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不美善洁净”,应得到完全满足的个性解放的乐观想象不同,莫言小说创作对人物个性“自主”扩张的探索只能是一种审美现代性的想象。
三、 肉身“自主”扩张的文化渊源与时代意义
莫言前期小说创作中的“自主”人物形象,虽然与“五四”现代文学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因文化的时代差异“不只是时间性的,而是本质性的”。与五四文学的个性自由思想深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不同,莫言小说中“自主”人物的扩张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的庄子式随心所欲的个性自由思想和杨朱式的唯我主义特点。庄子强调个人不为外物所累,而要充分发挥个人的灵性,是一种审美的个性主义,但其给百姓所留下的,正是这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个人自由主义传统”,是“一种江湖侠客式的自由”。以余占鳌为代表的“自主”人物的无所规范、无拘无束的行为,确实具有一种传统的“江湖侠客式的自由”特点。另外,这种人物形象也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杨朱式的个人主义思想。杨朱提出“拔一毛利天下,亦不为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个人主义”。像余占鳌的抗战行为虽然反映了一种民族的抗争精神,但对他来说,其参与战争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个体生存,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是一种“为我”或“贵己”意识。这与现代个性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思想也有明显差异,“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是在法律之内以不损害别人自由为限度的自由”,因自由主义认为,“只有使每个人自由的程度未超出可以同其他一切人的同等自由和谐共存的范围,才能够使所有人都享有自由”,而《红高粱家族》表现的个性自由意识一切都是为了个体生存目的服务的,和现代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思想还是有明显差异。当然,小说中余占鳌的随意杀人与爱的始乱终弃等行为,与杨朱式“非损人”的个人利己主义思想也不完全相同,但其却有着我国传统个人自由思想的“唯我主义”特点。莫言小说中的“自主”人物形象大都具有明显的利己主义思想,这种个性精神的张扬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它既体现了民族文化光明的一面,也有极强的负面效应。与五四文学相比,莫言小说中这种“自主”人物的现实意义似乎非常有限,但其实不然。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张扬个性的个人主义思想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但“在中国当代个人主义之中,占主流的似乎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具有道德自主型的、权力和责任平衡的individualism,而是一种中国传统意义上杨朱式的唯我主义(Egoism),这种唯我式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以物欲为目标,放弃公共责任,是一种自利式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由此可见,《红高粱家族》个性张扬所展现的传统个人主义思想有着典型的时代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纷纷唱出“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时候,这正预示了传统唯我式的利己个人主义思想又一次在当代中国社会抬头了。当前社会存在的道德沦丧、欲望横流正是这种利己式的本能个性主义张扬所带来的恶果。莫言对此也非常困惑,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唯一健全的意识就是“农民意识”,如果不把“农民意识光明的一面弘扬起来”,社会是没有发展希望的,但“有时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发展下去,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去了。我目前是痛苦的,也是矛盾的”。这种痛苦和矛盾其实也是肉身“自主”人物在现实中面临的永恒的矛盾与困境。
1988创作的《人与兽》似乎可看作《红高粱家族》的续篇,是对余占鳌结局的续写,也是对这种“自主”人物归宿的思考。小说通过一个被抓去日本服役而独自逃到野外生活了11年的中国人,在即将对一个日本农妇实施侵害时,无意中发现其裤衩上的补丁而良心发现,并终止了自己的侵犯行为,这体现了“自主”人物尊重“他者”意识的觉醒,也是对《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式的“自主形象”的否定。
《红高粱家族》表现了莫言对男性形象个性张扬的探索达到了一个顶点,也意识到了“自主”人物扩张的悖谬性,意识到自由是有限制的,“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说:“人应该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的自由。”他认为,“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当莫言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思想已经与现代个性主义的自由思想实现了对接。
莫言小说人物的个性张扬是建立在身体本能基础上的,具有弗洛伊德的“生的本能”的影子,也有叔本华、尼采等非理性个人主义特点,但其表现的个性自由思想又具有明显的民族传统文化色彩,这体现了其对中西方文化思想结合点的探索,体现了其企图融会中西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努力。莫言曾说:“我个人理解,保持旧的文化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要借助这些传统,创造新的亚洲文化。”这应是莫言小说创作孜孜以求地探索传统文化中本能个性主义之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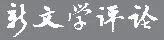
注释:
①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演讲》,选自《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③雷达:《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昆仑》1987年第1期。
④李宗刚:《民间视域下〈红高粱〉英雄叙事的再解读》,选自杨守森等:《莫言研究三十年》(下),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⑤宋剑华:《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论莫言〈红高粱家族〉故事叙事的文本意义》,《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⑥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⑦莫言:《红高粱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⑧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310页。
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随笔》,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⑩莫言:《在文学种种现象的背后——2002年12月与王尧长谈》,《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山东省临沂市临沂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